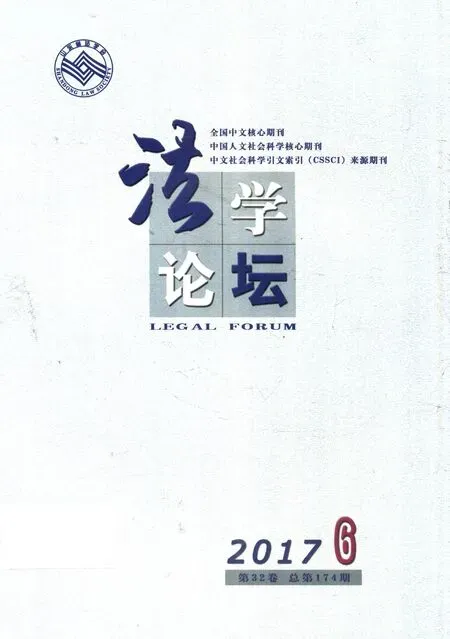論民法總則制定后環境權在民法典中的建構——從作為請求權的新型基礎權利出發
王 宏
(西南政法大學 經濟法學院,重慶 401120)
論民法總則制定后環境權在民法典中的建構——從作為請求權的新型基礎權利出發
王 宏
(西南政法大學 經濟法學院,重慶 401120)
傳統民法權利體系雖對環境權進行了部分吸納,但二者卻并不完全兼容,實質上更多地對環境權表現出排斥的情況,故將環境權在民法典中進行明確顯得尤為必要。正確厘清民法上環境權是解決環境權融入民法典的關鍵,鑒于請求權在民法權利體系中居于樞紐的地位,應緊密結合環境權中的私法要素,以環境權作為民法上請求權的基礎權利,對環境權請求權體系,即在民法典中明確環境權的內容、環境權作為基礎權利的請求權內容、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及恢復原狀、環境修復請求權等方面進行合理構建,力求讓環境權合乎邏輯、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民法典中。
民法典;民法權利;基礎權利;環境權;請求權
我國《民法總則》已于2017年3月15日表決通過,正式拉開了民法典編纂的大幕,邁出了民法典編纂實質性一步。①參見王利明:《民法總則體現了鮮明時代精神和特色》,載《光明日報》2017年3月23日。通覽《民法總則》全文,之前熱切呼吁的環境權并未在《民法總則》中進行規定,環境權在民法語境中仍停留在應有權利階段,其要上升到法定權利乃至實有權利階段仍舉步維艱。但值得慶幸的是,《民法總則》第3條、第9條、第110條第1款、第126條為環境權進入民法典提供了開放可能性,環境權在未來民法典編撰中仍有上升到法定權利之可能。雖然當前《民法總則》中并未對環境權進行明確規定,但在環境問題愈演愈烈的當下,民法典作為對私權進行全面保護之法律,將環境權的保護納入后續編撰的民法典分編的范疇,能夠更為圓滿而周妥地保障受害人的環境權益,環境權進入民法典是大勢所趨,極其必要,目前學界與實務界已對此進行了諸多的探討,應當給予其正面的回應。私法的工具將會適應環境保護的公共法律服務水平,②Mate Julesz, “The Individual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New Hungarian Civil Code”, The Open Law Journal, 2010, (3).私法權利亦有社會化之趨勢,徐國棟教授早在2003年就組織撰寫了《綠色民法典草案》,并呼吁要以主體、客體、方式三種路徑的綠色化為中心使民法典生態化。③參見徐國棟:《認真透析〈綠色民法典草案〉中的“綠”》,載《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當下亟需解決的現實問題是,環境權在《民法總則》并未對其規定的情況下應當如何融入到民法典之中?這同時也是民法典后續編撰過程中應當重點考量的問題。鑒于請求權在民法權利體系中居于樞紐的地位,其概括了幾乎全部民事權利及其保護方法,本文將緊密結合環境權中的私法要素,以環境權作為民法上請求權的基礎權利,對環境權的請求權體系進行合理構建,力求讓環境權合乎邏輯、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民法典中。
一、民法上環境權的厘清及其融入民法典仍具可能性
(一)民法上環境權的厘清
“環境權”一詞自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誕生以來,圍繞環境權的界定而展開的爭論至今仍不絕于耳。我國亦不例外,許多學者都對環境權進行過廣泛的探討,*蔡守秋教授將環境權分為狹義環境權與廣義環境權,廣義環境權泛指法律關系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國家)在其生存的自然環境方面所享有的權利及承擔的義務,較狹義環境權更為重要。參見蔡守秋:《環境權初探》,載《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汪勁教授持相類似的主張,其按照權利主體類型,將環境權劃分為公眾環境權、企業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權利、政府環境監管權。參見汪勁:《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0-72頁。呂忠梅教授認為環境權是一項基本人權,是指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壞的環境中生存及利用環境資源的權利,應由當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參見呂忠梅:《論公民環境權》,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6期;呂忠梅:《再論公民環境權》,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6期。黃錫生教授則將環境權剝離為環境行政權和公民環境權兩種,參見黃錫生、黃猛:《我國環境行政權與公民環境權的合理定位》,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5期。因各自秉持視角不同或對環境權的界定持不同主張,對環境權的界定至今尚未達成共識。上述爭論無疑使我國環境權理論得以長足之發展,但其后果同樣顯而易見,即造成環境權的內容顯得尤為龐雜,有學者將之形象地形容為“權利托拉斯”,*參見吳衛星:《環境權內容之辨析》,載《法學評論》2005年第2期。同時這也是環境權在我國仍停留在應有權利階段的主要因素。環境權是由公權與私權、程序權利與實體權利所構成的復合型權利體系,對其進行界定困難重重,然就其爭論的實質內容而言實際并無二致,可在尋求共識的前提下,將其界定為民事主體對環境資源所享有的法定權利。
以未來的發展趨勢來看,環境權應該獲得民法的保護。*參見王利明:《論法律體系形成后民法典的制定——獨墅湖畔人大法學論壇第四十九期》,載中國法學網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28933,于2016年8月2日訪問。環境權在我國能否順利地上升到法定權利乃至實有權利之階段,當下被提上日程的中國民法典的制定顯得尤為關鍵,不過這仍需建立在對民法上環境權進行明確厘清的基礎之上。誠如上述,環境權不應當走向“權利托拉斯”般的泛權利化趨勢,而應當回到法律的立法目的中尋求進路,民法上環境權的界定也應如此。民法之目的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環境權在民法語境下的表達也應遵循同樣之目的;另一層面,傳統民法所遵從的制度和原則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弱點,亟待在當下的社會變遷中及時跟進。*參見許明月:《公民環境權的民事法律保護》,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頁。基于對民法上環境權進行限縮以及對傳統民法予以適調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民法上環境權進行界定。
首先,民法典的私法屬性決定其不可能作出公法意義上的具體規定。*參見常紀文:《關于“民法典”如何規范動物和環境問題的探討——兼評我國三套“民法典”建議稿》,載《環境保護》2015年22期。環境權可分為公法上的環境權和私法上的環境權,因前者的主體之間并不對等,不符合民事立法之目的,應首先將該部分內容剝離出去。其中,國家/政府環境監管權屬行政權,企業環境容量利用權一般受政府管制,程序性環境權主要由法定程序來加以保障,均應歸入公法上環境權之范疇,不屬于民法上的環境權。準確界分以上二者,還可以實現環境權從以私法權利為重心轉向以私法和公法權利并重之目的;*參見徐以祥:《環境權利理論、環境義務理論及其融合》,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第二,自然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動物權利等已由傳統民事權利進行規范,雖然可將之納入環境權之范疇,但實無另起爐灶之必要,也應排除在民法上環境權范疇之外;第三,經以上層層排除之后,所剩下的權利便是剔除程序性權利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環境權,即公民享有在安全和舒適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換言之,環境權是公民或群體享有和支配良好環境的新型私權,包括清新空氣權、清潔水源權、清靜安寧權、安全無害權、良好生態權等內容,*參見劉牧晗、羅吉:《環境權益的民法表達——“環境權益與民法典的制定”學術研討會綜述》,載《人民法院報》2016年02月17日。這便屬于民法上環境權包括的范圍;第四,法人、其他組織等也可以享有美好環境的權利,但環境權是主觀感受型的權利,應具體到公民的層面而發揮作用,可融入到公民環境權的具體內容之中尋求救濟;第五,傳統物權法、人格權法能夠解決的部分仍然由傳統民法解決,環境權專門用來解決傳統民事權利所不能規范的環境權利。如民法典中關于動物的規定可歸入物權法中進行調整,不屬于本文討論之范疇。
(二)環境權融入我國民法典仍具可能性
基于對民法上環境權的厘清,可見環境權具備了私法要素的相應特征,這滿足了環境權融入民法典的基本條件。環境權在《民法總則》中并未上升為法定權利,與當下火熱的生態文明建設顯得格格不入,無疑是民法總則的一大缺陷,亟待更新立法之思維,力求在環境權的私法保護上取得進展。雖然如此,但可以看到,我國民法典的編撰采取的是漸進主義策略,制定《民法總則》只是民法典編撰的第一步,環境權仍有機會寫入后續編撰的民法典分編之中。《民法總則》為民法典的編撰奠定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民法典分編的立法目的、調整范圍、基本制度及基本框架。*參見謝瑋:《王軼:親歷民法典編纂》,載《中國經濟周刊》2017年第11期。但基于法解釋學的方法,《民法總則》的相關條款又為環境權融入民法典提供了較寬的開放空間。首先,《民法總則》第3條規定:“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民事主體除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外的“其他合法權益”包括知識產權、繼承權和社員權等綜合性權利,亦不能排除包括環境權在內的其他權益,該規定為環境權的私法保護留有充分的空間。第二,《民法總則》第9條規定了“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該條為民事主體設定了環境保護義務,根據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對等性是權利和義務關系一般相關性的表現,*參見王文東:《論權利和義務關系的對等性和非對等性》,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公民所享受的權利,是根據公民為社會所提供的條件確定的,該條規定從表面上看是為民事主體設定的環境保護義務,但實質上環境保護義務所對應的便是民事主體享受之環境權,能夠由此推導出民事主體享有與之相對應的環境權益,亦即環境權。第三,《民法總則》第110條第1款規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等權利。”該款規定是對自然人民事權利的不完全例舉,雖然其中并未對環境權進行明確,但民法上的環境權應當能夠包括在“等權利”之中,亦為環境權融入民法典留有相應的空間。第四,《民法總則》第126條規定了“民事主體享有法律規定的其他民事權利和利益”,基于該條規定,法律規定的其他民事權利和利益均可為民事主體所享有,該條中的“法律”可以是后續編撰的民法典各分編的規定,亦可是其他法律中規定的民事權利和利益,為環境權進入民法典提供了極大的開放可能性。
二、環境權建構之必要性:傳統民法權利體系對環境權的吸納與排斥
相較于傳統的民法權利體系而言,民法上環境權是一種新型權利,由于環境權的復雜性和廣泛性,使得傳統民法權利體系對環境私權表現出既吸納又排斥的現象。其對于環境權的吸納,主要表現在將環境權納入物權、人格權、侵權損害之中進行保護,然而上述劃分實質上已經對環境權進行了人為的割裂,且這種割裂的環境權又無法涵蓋民法上環境權的全部內容,對環境權造成了一定的排斥。由此可見,在民法典中對環境權進行明確規定是極其必要的,能夠改變環境權在當下傳統民法權利體系中的割裂狀態,進而納入民事主體享有的特定權利之中,能夠得到更為圓滿而周妥的保護,這同時也是呼吁將環境權納入民法典中進行保護的主要原因。
(一)傳統民法權利體系對環境權的吸納
傳統民法權利體系對于環境權的吸納,主要通過擴張傳統的人格權及財產權的范圍,同時再對侵權行為理論加以更新。將環境權與傳統權利適當協調以克服傳統法律之不足,并無必要另立模糊不定的環境權概念。*參見邱聰智:《公害法原理》,臺灣地區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9頁。傳統民法學者一般認為,雖然環境權的提出頗具建設性,但尚未為學者所普遍接受,理由是有破壞權利體系之虞,*參見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頁。這也體現在絕大多數國家目前的民事立法與司法實踐之中。傳統民法權利體系對環境權的吸納,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人格權對環境權的吸納。人格權包含了與人之人格相始終且不可與之分離的諸多權利,系由羅馬法中“人格人”概念的基礎上經歷現代民法拓展之后形成的概念。人格權發展至今,已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內容,但其與環境權發生直接關系者,當以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為主。*參見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頁。甚至有學者提出了環境人格權的理論,其強調私法中有關人格權的基本理論是環境人格權理論的直接來源。*參見付淑娥:《論環境人格權》,吉林大學2015年博士學位論文。日本法院往往依據人格權理論的相關法律來判決環境侵權案件,*如1970年大阪國際機場公害案、1980 年的伊達火力發電廠案均屬于此。參見杜鋼建:《日本的環境權理論和制度》,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6期;梅獻忠:《論民法典環境人格權的確立》,載《法制與經濟》2007年第2期。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8條第1項關于人格權請求權之規定,為司法實踐中涉及人格權內容的環境權之不作為請求權的行使提供了法律依據。我國有學者認為,環境權具有人格權的性質,適用人格權的保護方法對其進行保護,其從根本上講是人格權的一種類型,*參見楊立新:《制定民法典人格權法編需要解決的若干問題》,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亦有學者將環境權納入生命健康權之中。*參見徐國棟主編:《綠色民法典草案》,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頁。
第二,傳統物權對環境權的吸納。傳統物權中已經包含了自然資源所有權、自然資源使用權、地役權等許多涉及環境利益的部分。而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漁業權等準物權雖與環境相關,但其關聯不能與環境權的實質相吻合,亦應保留在物權法中予以保護。*參見侯懷霞:《私法上的環境權及其救濟問題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頁。物權對環境權的吸納,主要表現為物權上之除去妨害、保護占有之除去妨害請求權以及相鄰關系之運用。*參見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頁。傳統物權法并未將環境資源的生態價值和其他非經濟價值融入其概念以及制度之中,導致了環境問題的產生,*參見吳亞平:《論環境權是一種物權》,載《河北法學》2006年第6期。并從傳統物權法之基礎上引入生態價值理論以因應愈演愈烈的環境問題,由此形成基于物權之除去妨害不作為請求權。大陸法系國家大都引用損害賠償(侵權行為)或相鄰關系的法則來處理環境問題。*參見葉俊榮:《環境問題的制度因應:刑罰與其他因應措施的比較與選擇》,載《臺大法學論叢》第20卷第2期,第94-97頁。相鄰關系之運用,在物權對環境權的吸納中表現得更為重要。相鄰關系不宜再以狹隘之距離觀念為判斷標準,*同⑦。而應當以保護生存環境為出發點,在相鄰關系之上演繹抽象之環境權為人類之基本權利,以此作為環境權之依據。基于此,法國民法典中的近鄰妨害制度*參見王明遠:《環境侵權救濟法律制度》,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頁。、德國民法典中不可量物侵入的忍受義務規定*《德國民法典》第 906條規定了環境保護相鄰關系中不可量物侵入的權利人相關忍受義務,在忍受義務之內為不顯著之妨害,而超過忍受義務則構成侵權。參見《德國民法典》(第三版),陳衛佐譯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頁。、日本民法典中的“忍受限度”理論*環境糾紛之地域性、受損利益、土地利用先后、損害回避可能的因素來考慮環境保護的容忍限度,一旦超過了容忍限度則構成對相鄰權的侵害。參見湯大好:《相鄰不可量物侵害之受害人容忍義務比較法研究》,載《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成為了環境權私法保護之重要依據。
第三,債權法上的保護對環境權的吸納。債權法上的保護與人格權法、物權法上的保護相結合,構成了環境權在私法上的保護體系。債權法上的保護包括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和不當得利請求權,系傳統民法權利體系對環境權進行保護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因權利人受到侵害而享有的要求加害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權利,體現在環境權中大抵是對環境損害已經發生或已確定之事后補償制度。
(二)傳統民法權利體系對環境權的排斥:割裂的環境權
前述傳統民法權利體系對于環境權的吸納,實質上是將環境權人為地切割為物權、人格權、債權等權利,并適當拓展傳統民法話語體系來尋求依據。從整體上看,民法上的環境權與知識產權等權利一樣,其既非單純的財產權,亦非單純的人身權,而是具有雙重性質的權利,又可稱為綜合性的權利,其既具有財產權利的性質又具有人身權性質的權利。*參見劉凱湘:《民法總論》(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頁。若人為地將其進行切割,則無法涵蓋環境權的另一種權利內容,在形式和邏輯上極不周延。
具體而言,傳統民法權利體系對環境權的排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環境權與人格權存在差異。雖然對環境權造成損害最終可表現為對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等人格權上的侵害,但實質上,環境權是實現人格權的必要前提條件,其往往通過環境這一媒介對人格權造成侵害,而人格權保護系以對人格權的直接侵害為構成要件;*參見侯懷霞:《私法上的環境權及其救濟問題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頁。兩者在民法上保護之目的亦不相同,環境權以獲得良好、適宜、清潔的環境為目的,而人格權以保障民事主體的人格利益為目的;*參見李艷芳:《環境權若干問題探究》,載《法律科學》1994年第6期。此外,人格權一般僅涉及公民的個人利益,而環境權可能更多地涉及到“社會利益”,故而環境權與人格權不可相互替代。
第二,環境權在物權保護中的困境。一是在物權法定原則*所謂物權法定原則,又稱物權法定主義,是指物權只能依據法律設定,禁止當事人自由創設物權,也不得變更物權的種類、內容、效力和公示方法。參見王立明:《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頁。之下,物權只能依據法律設定,而環境權中的很多具有物權性質的內容卻并無法律規定,物權法定原則的局限極不利于對環境權的私法保護;二是傳統民法在物權法確立了所有權絕對的原則,而環境權所對應的日照、空氣、水等不能被人類所支配和控制,人們無法對之行使權力,也無法提出關于環境保護的請求;*參見許明月:《公民環境權的民事法律保護》,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頁。三是物權法層面的環境權重最為重要的是相鄰權,相鄰權是純私人性質的權利,其侵害之對象僅僅是特定的個人或某些人,其范圍一般僅限于以不動產的相鄰關系為前提的環境侵權行為,*參見許明月:《公民環境權的民事法律保護》,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頁。而環境權具有很大程度的公益性質,其侵害對象可以是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參見侯懷霞:《私法上的環境權及其救濟問題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頁。且環境侵權的范圍具有廣泛性,現代民法雖對相鄰權進行了一系列的拓展,但在對環境權保護時仍顯得力不從心。
第三,傳統侵權損害賠償對環境權的保護不足:一是與傳統侵權行為相比,環境權遭受侵害具有不平等性、不確定性、潛伏性、復雜性及廣泛性等特征,*參見曹明德:《環境侵權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4頁。其歸責原則、抗辯事由等均與傳統侵權行為有差異;二是環境權遭受損害后,其損害賠償的范圍包括了預防性損失、修復性損失、期間損失等,與傳統賠償的范圍不一致;三是如空氣、水體等環境權客體通常不具有傳統財產權意義上的要素,與傳統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不同,對其造成侵害并不一定會出現損害事實。*同②。
三、作為基礎權利的環境權:環境權請求權的提出
民法典中環境權的最新立法動向不容樂觀,這為環境權如何融入民法典提出了更多的思考。環境權體系極其復雜,其表達亦存在困境,這就需借助于在民法中處于樞紐地位的請求權的內容來行使,在環境權與請求權之間形成契合,環境權請求權的提出與展開,具有其獨特的特征,環境權可以不借助于物權、人格權等來間接發揮作用,而能使作為基礎權利的環境權更為直接地發揮其功能。
(一)請求權在民法中的樞紐地位
民法之權利屬于私權,即以社會生活之利益為內容者,按其作用可分為支配權、請求權、形成權及抗辯權。*參見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其中,請求權系德國法儒溫德塞由羅馬法上的Actio發展出來的概念,認為除訴權(公權)外,尚有實體法上的請求權(私權),即要求特定人為特定行為(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系由基礎權利而發生,為法學上之重大貢獻。*參見王澤鑒:《民法總則》(增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頁。溫德賽認為主觀權利就是客觀法所認可的意志力量,是法律秩序的產物,*參見辜明安:《物權請求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頁。并由此強調請求權是一切權利都具有的某種強制因素的實體權利。*參見金可可:《論溫德沙伊德的請求權概念》,載《比較法研究》2005年第3期。德國學者梅克爾亦認為權利之本質為法律上之力,即權利系由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兩個因素構成。*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頁。請求權是權利內化強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民事權利的本質是利益與法力的結合,則請求權的本質就是法律上之力,其與所謂的“基礎權利”并非一種單純的依附關系,而是一種共生且相互依存的包含關系。*參見楊立新:《請求權與民事裁判應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4頁。無論何種權利,為發揮其功能,或回復不受侵害的圓滿功能,均需藉助于請求權的行使。*參見王澤鑒:《民法總則》(增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頁。據此,請求權系基礎權利之有機構成,請求權在民事權利體系中居于樞紐的地位,其幾乎概括了全部民事權利及其保護方法。*參見楊立新:《請求權與民事裁判應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2頁。
(二)環境權與請求權的契合及環境權請求權提出的意義
如前述及,民法上的環境權與人格權、物權等傳統權利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故環境權不應完全建立在上述傳統權利的基礎上來行使請求權。如果硬要傳統的民事權利體系來完全適應環境保護的要求,則只能使這些理論失去其存在的基礎而變質變味,而且也難免存在掛一漏萬的風險,*參見呂忠梅:《環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114頁。客觀現實要求環境權應單獨作為民法語境下的基礎權利來對環境予以保護。*參見許明月:《公民環境權的民事法律保護》,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頁。環境權與物權、債權、身份權等傳統民事權利一樣,可以作為民法語境下的基礎權利,在此基礎上,環境權與請求權能夠實現契合,由此形成基于環境權之請求權,即環境權請求權,用以解決環境權私法保護的相關問題。盡管如此,環境權請求權在民法典中的體現,作為對傳統民事權利體系的革新,勢必會引來破壞傳統民事請求權體系之爭論,然而這種權利的實質內容無疑更為有效地保障了環境權,有勢在必行之趨勢。環境權中所包含的請求權,是公民的環境權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關部門請求保護的權利。*參見呂忠梅:《再論公民環境權》,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6期具體到民法領域中,環境權請求權系指環境糾紛的受害方有要求侵害方停止侵害、排除危險、賠償損失等權利。*參見汪勁、田秦:《綠色正義——環境的法律保護》,廣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頁。
環境權請求權在民法典中的提出具有極其積極的意義:一是實現環境權在私法語境下從割裂走向統一。環境權是兼具財產權與人身權雙重性質的綜合性權利,桎梏于傳統民事權利體系中的環境權實質上是一種割裂的環境權,不能兼顧環境權本身的財產權與人身權雙重屬性,而解決的有效路徑則是走向統一的環境權;二是能夠解決傳統民事權利體系所無法涵蓋的環境權內容。人格權、物權等傳統民事權利雖然可以經過生態化拓展來解決部分環境權的問題,然而作為傳統的民事權利,其本身就存在特定的適用范圍,將之進行無限擴大亦不能解決環境權私法保護某些方面的問題,而且會妨害傳統民事權利的既有體系,環境權請求權的提出則能有效地對此予以因應;三是環境權請求權的提出使環境權的私法保護更具直觀性。借助于其他傳統民事權利表現出來的環境權,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體現了環境權本身的內容,而系環境權在其他民事權利中所間接表達的內容,二者之間存在差異,若保持現有的救濟則無法體現環境權所直接表達的含義;四是環境權請求權能從實質上將環境權納入民法的保護范圍。使環境權在民法典中行之有效地進行融入。環境權作為基礎權利,其請求權之實現具有可能性,能夠使環境權在私法領域的保護更為全面、有效,進而從實質上將環境權納入民法的保護范圍。
(三)環境權請求權的具體特征
環境權請求權作為一種新型的權利,相較于物權請求權、人格權請求權、債權請求權來講,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環境權請求權基于環境權而生。其權利基礎應為民法典中關于環境權的規定,即享有在安全和舒適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二是權利主體為環境權人。企業環境權基本上可以通過財產權的相關規定或具體到公民環境權來實施救濟,國家環境權一般屬于公法調整之范疇,上述二者均無需作為民法語境下的環境權人。具有環境權請求權的權利主體是一般公民,屬于民法意義上的環境權人;三是權利客體特定。權利客體即為在安全和舒適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其權利的行使不能無限擴大,應承擔法律規定范圍內的一般忍受義務;四是與失效期間的適用關系。從本質上來講,環境權請求權系支配權請求權,不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和除斥期間的規定。但基于環境權而產生的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作為保障環境權的第二道屏障,應適用債權請求權的相關規定,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和除斥期間的規定;五是以回復環境權被侵害前的狀態為制度功能,且不以責任人有主觀過錯為構成要件。
四、從割裂走向統一:環境權在民法典中的合理建構
(一)環境權應在后續編撰的民法典分編中進行明確
在民法典中明晰民法上環境權的內容,是民法典生態化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雖然《民法總則》第3條、第110條第1款、第126條共同表明了民事權利客體范圍的開放性趨勢,但環境權作為民事權利客體只是一種可能性,需要其他法律對此進行明確規定后方能更好地行使權利。其第9條規定為民事主體設定了環境保護義務,實質上與之相對應的環境權呼之欲出,只是并未在其文本中明確規定而已,不過僅對民事主體設定環境保護義務仍顯不足,這不利于對具有復合性特征的環境權進行充分保護,加之民法所保護之環境權在除民法典分編外的其他法律中不一定能夠明晰其私權屬性,故而環境權還是應當寫入后續編撰的民法典分編之中,使其得到更為圓滿而周妥的保護,這對于環境權請求權的行使更為直觀、科學。民法總則規定民事活動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一般性規則,統領民法典各分編,包括合同編、物權編、侵權責任編、婚姻家庭編和繼承編等。*參見李建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的說明——2017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載《人民日報》2017年3月9日。綜合考慮未來民法典各分編的功能和作用,建議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增加“環境權”的內容,可具體表述為:“民事主體享有在安全和舒適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受法律保護。”楊立新教授認為,我國現行的《侵權責任法》第八章關于環境污染責任的規定條文較少、設計比較簡單,尤其缺少破壞生態損害責任的明確規定,應當在編撰民法典時予以補充,*參見楊立新:《民法分則侵權責任編修訂的主要問題及對策》,載《現代法學》2017年第1期。環境權正好可借此契機從應有權利真正上升為法定權利。退一步來講,即使環境權在未來的民法典分編中并未明確規定,亦可通過法解釋學的方法從《民法總則》的相關規定中推演而出,這并不影響環境權作為基礎權利的地位。
(二)環境權作為基礎權利的請求權之內容
大陸法系之民法以排除侵害與損害賠償為兩大支柱,其中侵害排除是權利救濟的第一道屏障,是比起損害賠償更為重要的救濟方式。環境權請求權的功能主要在于救濟,即對受到侵害的作為基礎權利的環境權進行救濟。邱聰智教授認為,公害侵害之救濟方法,包括不作為請求權之行使,重在排除目前已生之損害,并預防將來可能發生之損害,重在防范未然。*參見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頁。但僅包括不作為請求權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因為請求權不僅包括不作為請求權,同時還應當包括要求特定主體作為的請求權。在環境權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時,民事主體不僅享有停止侵害的不作為請求權,還包括了排除妨害請求權、消除危險的作為請求權,這同時也是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環境權請求權能夠解釋權利人之間在發生爭議之后到提起訴訟之前,權利人的權利狀況,為權利人在訴訟外獲得救濟提供理論基礎。《民法總則》第9條為民事主體設定了環境保護義務,從某種程度上講也能解釋為民事主體行使環境權請求權的依據。在環境權遭受侵害或僅僅具有侵害之虞的情況下,環境權主體就可以向相對人主張請求,一是行為人實施侵害他人環境權的行為正在進行或仍在繼續進行,受害人可行使停止侵害請求權;二是行為人實施妨礙他人正常行使其環境權的侵害行為,給受害人造成妨害或將要造成妨害的情況下,受害人可實施排除妨害請求權;三是行為人的環境侵權行為對他人的人身或財產安全造成威脅或存在造成損害的巨大可能時,潛在的受害人可行使消除危險請求權。*參見許明月:《公民環境權的民事法律保護》,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180頁。環境權請求權的行使能夠使環境最大限度地回復到不受侵害的圓滿功能,其行使相較借助于傳統民事權利派生出的請求權而言更為直觀、便捷,無疑更具優勢。
(三)環境權請求權之債權法保護: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環境侵害之救濟方法,又包括損害賠償之請求,重在補償已發生之損害,亦即救濟已然。*同③。當權利人的環境權遭受侵害以后,一般應首先考慮行使環境權請求權,之后再行使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可行以保障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參見PA Barresi:” The Right to an Ecologically Unimpaired Environment as a Strategy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Human Societies Worldwide”, Macquarie J.intl amp; Comp.envtl.l, 2009,( 6).當環境權請求權無法滿足環境權保護之需時,可以行使侵權法上的請求權,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屬于債權請求權的一種,系權利救濟的第二道屏障。我國《民法總則》第118條對債權請求權進行了明確規定,其第120條則專門針對侵權行為規定了侵權請求權的內容。此外,侵權制度要適應生態保護的要求,還需建立起將來性損害賠償制度和共同危險行為的侵權制度。
(四)恢復原狀請求權、環境修復請求權的證成
有學者從物權法的維度出發,認為物受毀損者,在被害人方面,只得請求金錢賠償,不得請求恢復原狀。*參見王伯琦:《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50頁。上述主張固然有一定道理,卻也有失偏頗,環境權的損害與傳統物權的損害不一樣,環境的生態功能承載了人類可持續發展之動力。要使受損的生態環境得以救濟,最終體現出來的實質上是讓損害者承擔民事上恢復原狀之責任,*參見徐以祥、王宏:《論生態修復性司法》,載《人民司法》2016年第13期。對受損的環境恢復原狀,并不是僅從外觀上進行恢復,而是以恢復至生態環境尚未受損時的生態基準,這種修復極其必要,故恢復原狀請求權在環境權的私法保護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應當作為請求權的內容。另外,環境遭受損害后不一定能夠完全恢復原狀,在這種情況下仍以恢復原狀來進行表述不太妥當,應著重于對受損環境進行最大限度的生態修復,以接近生態環境尚未受損時的生態基準,可謂之環境修復請求權。關于環境修復請求權,民法總則草案一審稿將“恢復原狀,修復生態環境”明確列為民事責任的主要方式之一,但二審稿、三審稿和出臺的《民法總則》卻將“修復生態環境”去掉,*楊立新教授認為,“修復生態環境”是針對生態和環境受到損害的救濟而增加的新的責任方式,如此規定雖然值得肯定,但較為突兀,贊同將其刪掉。參見楊立新:《民法總則規定民事責任的必要性及內容調整》,載《法學論壇》2017年第1期。最終在《民法總則》第179條第1款第(5)項規定了“恢復原狀”這一方式,基于這一立法背景,此處的“恢復原狀”應當進行擴大解釋更為妥當,其應當包含了環境修復請求權的全部內容。
結語
生態環境的公眾共用屬性會帶來“公地的悲劇”的發生,盡快將環境權納入法律保護之中顯得尤為重要。學界應當盡快對民法上的環境權的概念達成共識,以目前中國民法典分編的后續編撰為契機,盡快將當下仍停留在應有權利的環境權納入民法典中進行保護,并以環境權作為民法上請求權的基礎權利,對環境權請求權體系進行合理構建,力求讓環境權合乎邏輯、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民法典中,讓環境權盡快地上升為法定權利。
[責任編輯:魏治勛]
Subject: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 in Civil Cod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ly Fundmental Rights as Anspruchsgrundlage
Authoramp;unit:WANG Hong
(School of Economic Law,Southwest Politics and Law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120,China)
Environmental rights were partly adopted in the traditional civil right system. However, these two things cannot be compatible, actually in most cases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were intolerated, so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make environmental rights clear in the civil code.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civil right system, which is key to make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integrate into Civil Code. In view of that Anspruchsgrundlage is the maincenter in civil right system, private law elem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should be considered jointly in order that environmental rights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fundmental rights of civil right system and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Anspruchsgrundlage——the contents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the Civil Code, the contents of environmental Anspruchsgrundlage as the fundmental rights, the claim rights of the compensation because of infringement, repristination and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could be striven to fit the logic and integrate into Civil Code properly.
Civil Code; civil right; fundmental right; environmental right; anspruchsgrundlage
2017-06-22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國環保產業發展的制度困境與法律對策研究” (16BFX147)、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制度研究”(15JJD820007)、重慶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環境公眾監督權訴訟保障制度研究”(CYB16079)的階段性成果。
王宏(1984-),男,貴州仁懷人,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博士生,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法官,主要研究方向:環境法學。
D922.681
A
1009-8003(2017)06-01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