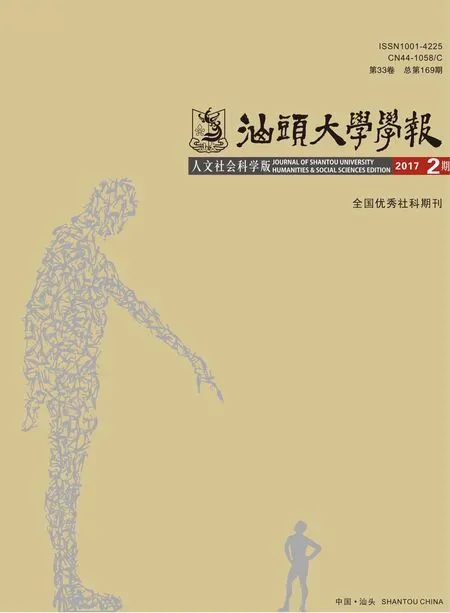立以骨骼·敷以筋絡·實以血肉
——劉俊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
李竹筠
(南京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
立以骨骼·敷以筋絡·實以血肉
——劉俊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
李竹筠
(南京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
劉俊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可分為三個部分:對世界華文文學體系的建構與闡發(fā),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條塊研究以及作家作品研究,分別從宏觀、中觀、微觀的研究視角“立以骨骼”“敷以筋絡”“實以血肉”,搭建了世界華文文學的意義世界。其著述表現出鮮明的風格化特征,即條分縷析、綿邈細密的邏輯推演功力與洞幽燭微、深情傾注的文本細讀精神。
劉俊;世界華文文學;立以骨骼;敷以筋絡;實以血肉
在一本專著后記中,劉俊教授記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流傳的一種說法:“一流人才研究古典文學,二流人才研究現代文學,三流人才研究當代文學,四流人才研究臺港文學”[1]。這一說法無疑體現了一段歷史時期,“世界華文文學”學科之位處“生物鏈”底端的邊緣、弱勢地位,以及這一處境內含的學科人才匱乏、學術資源貧瘠、學術生態(tài)惡劣之困局。反觀當下,“世界華文文學”儼然成為一門“顯學”[2]——其中暗含的“排座次”的本質主義傾向姑且存而不論——僅就其由“四流”而“顯學”的升沉而言,實勾勒與記錄了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發(fā)展軌跡,以及以既有成果倒逼學界對其進行重新認識和定位的能動意涵。學者的治學精神、堅守姿態(tài)以及不輟的著述是實現這一發(fā)展最重要的驅動力。劉俊教授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領域耕耘既久、用力甚勤、收獲亦夥,是這一學科發(fā)展成長進程的建設者和見證者,因此對其著述的考察不僅在于治學方法和治學經驗的總結,也適足為考察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取徑之一。
事實上,“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固然是劉氏的研究對象,作為一種視角和方法也是貫穿其著述的脈絡和理路。7本專著中①,除《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情與美:白先勇傳》以白先勇為研究對象之外,《復合互滲的世界華文文學》《越界與交融:跨區(qū)域跨文化的世界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整體觀》《跨界整合:世界華文文學綜論》4本徑以“世界華文文學”名之。《從臺港到海外:跨區(qū)域華文文學的多元審視》中的“跨區(qū)域華文文學”,則突出和標舉著“世界華文文學”的“跨”的性質。要之,劉氏的研究聚焦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體系,以其跨區(qū)域、跨文化特點所天然具備的比較視野出入于現當代文學、世界華文文學之間。具體說來,以對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內涵外延的構建、論證與“正名”作為研究的第一層框架;以基于縱向(歷史)、橫向(跨區(qū)域)、縱橫交叉的視角揭橥世界華文文學彼此聯(lián)系與影響的研究作為研究的第二方陣;第三個層面則為作家、作品的個案研判。若比之于一個實體建構的過程,三個層次的研究先是“立以骨骼”,次之“敷以筋絡”,繼之“實以血肉”,自宏觀、中觀、微觀的視角搭建了“世界華文文學”的論述體系。以下即從上述三端展開敘述,對劉氏著述作一整理、歸納、提要,以饗學人、以遺君子。
一、世界華文文學的“立以骨骼”
世界華文文學成為成說,多認為始自1993年第六屆“世界華文文學年會”的更名。此前第一、第二屆稱為“臺灣香港文學學術討論會”,第三屆稱為“全國臺港與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第四屆稱為“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第五屆稱為“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此可以見得其中清晰的流變過程,邊界不斷拓展,內涵亦隨之增廣。至1994年世界華文文學會籌委會成立,“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命名獲得了較大程度上的共識[3]。但“世界華文文學”的內涵、外延并非不證自明,這一概念不僅涉及地理意義上的不同國家和地區(qū),也在政治認同和文化歸屬的層面迭有疑議。即令上述問題可以略而不論的中國大陸,雖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已經逐步認識到‘新文學中心主義’‘精英(雅)文學中心主義’和‘大陸文學中心主義’的局限,開始有所糾偏”[4],但基于學科“正統(tǒng)”與歷史淵源的“傲慢與偏見”并未完全克服。既有的刻板印象乃至學科之間的隔膜也影響到認識的一統(tǒng)。以世界華文文學中的“世界”而論,中國自然包括在“世界”范疇之內,則中國現當代文學理應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個部分①世界華文文學通常約定俗成指涉華文文學中的現當代部分,蓋因中國(含臺港澳)以外的華文文學幾無古代文學,此處沿用習慣說法。,但事實上,“把大陸現當代文學也包含在‘世界華文文學’概念中的學者,雖然不乏其人,但始終未成主流”[5]1。高等院校的學科設置中,世界華文文學仍多襲用“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名稱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學科方向存在。換言之,世界華文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理應具有的包含和包含于的關系,卻在實質上以附屬和主體、支流和主流的反轉關系并存。臺港澳文學內涵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殆無疑義;但把海外華文文學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分支,在理論架構上不免捉襟見肘。
質諸大陸以外,臺灣大專院校或有以國文系、臺灣語文學系并置②如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文學院以二系并立。,儼然以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庭抗禮,其文學及研究場域的“去中國化”立場令人憂慮。史書美、王德威等人提出“華語語系文學”以對應/對抗大陸學界的“世界華文文學”的命名,而“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文學’希望通過學術建構來表達她的意識形態(tài)訴求,其分離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非常明顯”[6],“王德威對大陸學界文學‘國家主義’‘(大)中國中心’和‘四海歸心’‘萬流歸宗’的判斷,其實與事實并不相符”[6],這類認識或為有意的“誤讀”或為預設立場的“誤判”,同樣需要廓清迷霧、以正視聽。是以,劉氏以《“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fā)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為中心》系統(tǒng)追述二人的觀點、方法及所憑借的理論資源,援引學界從問題、理論、論述機制層面對其展開的批判,認為“華語語系”對“英語語系”“法語語系”的模仿與對后殖民理論的誤用及其對“華語語系文學”內涵的闡釋,暴揚了其“命名”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底色,揭橥“‘華語語系文學’實則是文學與意識形態(tài)交鋒的話語‘場’”[6]。知識生產與運作成為意識形態(tài)的“背書”,尤其是發(fā)端于學界一流學者的倡導之下,流弊所及不能不令人警醒。劉氏多次稱許王德威的“君子之風”[6],未必不是立身原則的“暗合”所引發(fā)的惺惺之感;而仍然訴諸“批判”——批判文章在其學術生涯中可為僅見——可謂“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破不立,劉氏對“世界華文文學”給出自己的定義:
以中文(華文)為書寫載體和創(chuàng)作媒介,在承認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源頭是來自中國文學,同時也充分尊重遍布在世界各地的中文(華文)文學各自在地特殊性的前提下,統(tǒng)合中國(含臺港澳地區(qū))之內和中國之外的所有用中文(華文)創(chuàng)作的文學,所形成的一種跨區(qū)域、跨文化的文學共同體。[5]5
上述立論貫通了“世界華文文學”中的“世界”邏輯(世界各地)、明辨了其“文學”家族(中國之內含臺港澳地區(qū)和中國之外),在尊重“海外華文”各自開枝散葉、靈根自植的訴求基礎上(尊重各自在地特殊性),亦回望了畢竟源流有自的來路(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源頭是來自中國文學)。追溯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源頭”之舉拆解了“華語語系文學”的“多中心”說,但這種源頭的追溯又異于現當代學者習焉不察的“中國中心”心態(tài),毋寧說是一種尊重歷史事實的、對文化源頭的瞻顧和梳理。強調“同源性”“共性”,也突出“特殊性”“異質性”,尊重各區(qū)域華文文學的主體性和平等地位——或有文學、文化“邦聯(lián)”的意味在內,體現出超越政治認同和意識形態(tài)紛爭、謀求文化認同與文化身份歸屬的開放、務實的姿態(tài)。這一定義在界定“世界華文文學”范疇、邊界的同時,識別出“世界華文文學”“跨區(qū)域”“跨文化”的基本特質:“既然跨區(qū)域和跨文化是世界華文文學基本形態(tài)和總體風貌的核心兩翼,那么因跨區(qū)域而導致的沖決文學區(qū)域邊界的越界,以及因跨文化而形成的各種不同文化之間的交融,就成為了世界華文文學這一文學共同體的核心樣態(tài)。”[5]11世界華文文學的“跨區(qū)域”“跨文化”的特點,表征著世界華文文學多樣、豐富、混雜、交融的整體風貌,亦展演了“跨區(qū)域”“跨文化”之“跨”的不同程度所帶來的區(qū)域文學之間的分野;“文化共同體”的共性與各自“特殊性”的個性又要求研究主體之間的平等、尊重、協(xié)商——這就不僅僅是在討論“世界華文文學”的內涵問題,而且已經觸及學科規(guī)范和研究方法的確立問題。
其實,早在劉氏首倡“跨區(qū)域華文文學”概念之時,就已經為“世界華文文學”的內涵作了增益與闡發(fā):亦即“‘跨區(qū)域’本來就是‘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方式”[1]85,“更能體現這一文學的整體感和內部不同區(qū)域文學之間的相似性”[1]25,“更能彰顯出這種文學的跨文化性質”[1]86,“更能顯示出這種文學相互‘重疊’(靜態(tài))和內部流動——旅行(動態(tài))的特質”[1]87,“可跳出特定地區(qū)(臺港)和地域(海外)名稱的專屬限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彈性”[1]88五個特質,對“世界華文文學”的“跨越”性質予以條分縷析的剖陳。只不過彼時劉氏的關注點主要在臺港海外華文文學部分,換言之即中國大陸文學以外的“世界華文文學”。嗣后逐漸把大陸文學整編入“世界華文文學”體系,進而以系統(tǒng)的“世界華文文學”論說取代了“跨區(qū)域華文文學”的概念,至前述引文則以更加開放、包容的話語完成了對“世界華文文學”的論證。劉氏重建“世界華文文學”之舉體現了與“華語語系文學”“臺灣中心論”的對話意識,以及在“文化中國”的共識基礎上為大陸學術界發(fā)聲的理論自覺。
二、世界華文文學的“敷以筋絡”
劉俊著述的另一特點,是研究中的比較意識和歷史意識。早年現當代文學的學術訓練及精通英文的雙語背景,為其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提供了天然的比較視野。具體到研究成果中,即對作家、作品作跨區(qū)域乃至跨時空的比較研究與影響研究,或對一個時期、地域的文學作追源溯流、爬梳剔抉的整體研究。這種通盤考量的研究方法避免了零星分散、互不相關、見樹不見林的弊端,且融會貫通、互相參證,形成綿邈細密、互相指涉的研究脈絡,一個歷史時期或一個地理場域的文學風貌、特征、流變、衍異于焉清晰浮露。
例如《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語言的衍變》[1]10《“家”的顛覆與重建——以“父子關系”為視角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變遷》[4]1《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上海書寫》[1]35主要著眼于歷時性的考察,在歷史的脈絡中厘析文學、語言、寫作主題不同的樣態(tài)呈現乃至變化流轉;《北美華文文學中的兩大作家群比較研究》[4]161《臺灣新文學誕生之初文學現代性的三種形態(tài)——以連橫、張我軍、賴和為中心》《“毀滅意識”和“自我表現”——對五四時期一種“自我表現”式態(tài)的考察》[1]59《“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尋——美國華文文學的一種解讀》[4]178《第一代美國華人文學的多重面向——以白先勇、聶華苓、嚴歌苓、哈金為例》更多是基于共時性的聚焦,研究一時一地文學的主題呈現、意義追尋、多元面向;而《“五四精神”/文學與臺灣現代主義文學》[5]3《臺灣文學的“輸入”與“輸出”》[5]53《二十世紀華文文學中的性別關系形態(tài)——以魯迅、張愛玲、白先勇和朱天文為論述中心》[5]99則打通時、空的邊界,在“世界華文文學”的宏闊視野中審視、研判具體而微的文學場域,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往往在相對“熟透”的研究領域里翻奇出新、別開生面。
在相對中觀的這一范疇,劉氏的研究體現了鮮明的風格化特征,即論述之細密、周延、密不透風、不厭其詳。以《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上海書寫》為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上海書寫的三個系列和傳統(tǒng)的形成過程,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三種不同類型(注重西化,注重左翼,注重形而上的終極)的知識分子從各自的立場和角度將自己對上海的發(fā)現、記憶、想像、感受和期盼通過文字化的方式予以凝定的過程。因此,這三個系列的形成和傳統(tǒng)的延續(xù),說到底其實是不同時代、不同類別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分野(對西化、左翼、日常性的不同側重)和對中國文學形態(tài)的審美追求(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心理分析-存在主義的各自注重)在上海書寫中的表現。”[5]55這一闡發(fā)重在從動態(tài)角度辨析三個上海書寫系列各自的承續(xù)以及彼此間的消長;對三個書寫系列的交錯、輪替及其所映現的時代風潮的發(fā)明,無疑有著文學史乃至文史互證的意義。結論有統(tǒng)(知識分子的上海書寫)有分(三個不同系列的上海書寫),描繪現象(不同類別的上海書寫)探尋淵源(不同知識分子認識的分野和審美的歧異),關注現實(當下的上海書寫)回溯歷史(20世紀的上海書寫),敘述線索縱橫交錯而脈絡分明,典型地印證著劉氏的論述風格。他說:
殖民地處境下的臺灣新文學,在其誕生之際以民族認同為核心的啟蒙思想,呈現出三種不同的現代性形態(tài),即以連橫為代表的以傳統(tǒng)中國(文學)的民族認同展開啟蒙(以反現代性面目出現的現代性)、以張我軍為代表的以現代中國(文學)的民族認同展開啟蒙(以趨現代性的面目出現的現代性)和以賴和為代表的以鄉(xiāng)土中國(文學)的民族認同展開啟蒙(以建現代性的面目出現的現代性)。這三者之間所體現出的文學現代性,不是縱向的線性進化關系,也即是說不是一個取代另一個的時間關系,而是橫向的并列呈現關系,也即是說同時并置的空間關系。它們各自代表了20世紀初中國臺灣的知識分子在傳遞啟蒙思想、表達民族意識、形成民族認同時的不同設計和努力方向。[7]138
這一論述同樣以一個結論統(tǒng)攝(20世紀初中國臺灣的知識分子在傳遞啟蒙思想、表達民族意識、形成民族認同時的不同設計和努力方向),其間明辨差異(三種不同的現代性)、追溯因由(不同的知識結構與價值認同),以對三個典型人物的萃取論證三類不同學養(yǎng)訓練和價值取向的知識分子之現代性探索;以一代百、舉重若輕,從研究視角、理論資源到推演過程絲絲入扣。不僅如此,這一發(fā)現/發(fā)明更為后學提供可持續(xù)的研判空間:如三類文學現代性的傳承譜系和歷史沿革、不同歷史時期彼此的盈虧消長及成因分析,乃至可以把三類文學現代性的呈現引進大陸文學場域或作兩岸之間的比較分析;凡此種種無不可為學科研究開拓新的增長點和視域。再如:
臺灣的海島性地理特征和自身歷史的復雜性,決定了臺灣文學具有一種開放性、中轉性和流動性,在它的發(fā)展歷程中,充滿著“輸入”和“輸出”的各種文學成分——這種一再的“輸入”和“輸出”,不但使臺灣文學自身內涵和發(fā)展充滿了復雜性,而且也因了它的存在而使世界華文文學變得不易概括和歸納,世界華文文學內部不同區(qū)域之間的文學因了臺灣文學的“輸出”和“輸入”而產生的各種交錯、流動、中轉和兼跨,導致了世界華文文學中的許多作家、作品的定性具有了揮之不去的多義性和不確定性。[5]70
限于篇幅無法體現其邏輯推演的過程,僅能尋摘其結論庶幾窺見一二。即以結論而言,上述論述指陳臺灣文學場域處于不斷變化、流動、增損的動態(tài)過程,考察臺灣文學對外部影響的吸收與拆解,以及臺灣文學之于外來影響的反作用力。研究由點到線、由線及面,基于“交錯、流動、中轉、兼跨”的動態(tài)流轉,把臺灣文學場域還原到三維“立體”乃至“力場”中進行多層次、多向度的考察。結論毋寧保持開放和發(fā)散(作家作品之“多義性和不確定性”),對祛除成見、定見之迷思,探索學科新邊界亦可謂思過半矣。
誠如夏濟安所言:“中國人的批評文章是寫給利根人讀的,一點即悟,毋庸辭費。西洋人的批評文章是寫給鈍根人讀的,所以一定要把道理說個明白。天下到底是鈍根人多……頂好還是把美丑好壞的道理說明白了。”[8]相較中國傳統(tǒng)詩學點到即止、印象式、感悟式的點評,借鑒乃至師法西方文學批評基礎上的現代文學批評更注重問題意識、邏輯推演、觀點論證;因此其科學性、嚴密性、系統(tǒng)性的優(yōu)長不僅在于觀點獨出,更在于文本肌理的豐滿與質感的細密;換言之,在于推演證成的過程和材料役使的功力。劉氏的著述即集中地體現了現代文學批評對推導論證的肌理呈現,著述之條分縷析、針腳綿密令鈍根人亦不能不憬然有悟。
三、世界華文文學的“實以血肉”
對世界華文文學的考察離不開作家作品研究,在劉氏著述中,作家作品研究幾乎占據其中半壁江山。舉凡北美華文作家如聶華苓、嚴歌苓、張翎、陶然、施雨、余曦、沙石等,臺港作家如賴和、呂赫若、紀弦、陳映真、朱天文、蘇偉貞、齊邦媛、董橋、柏楊、劉以鬯等,新馬作家如黎紫書、朵拉等,大陸作家如魯迅、郁達夫、施蟄存、張愛玲、畢飛宇等無不專文論述,往往獨出機杼,如“當他把自己置于這樣的譜系中——從30年代的‘現代派’發(fā)展到50年代的‘后期現代派’——時,紀弦其實是在‘橫的移植’來的新詩體系下,實行著‘縱的繼承’”[7]97,論者認為可被紀弦許為“知己”[9]。對呂赫若、施蟄存、歐陽子等的研究也每每“見微知著”、“不無學術創(chuàng)見”[10]。
當然,最為學界所知和樂道者還是其人對于白先勇的研究。在解讀白先勇的作品時,劉氏萃取“悲憫情懷”的關鍵詞,論者認為“對于‘悲憫’二字的理解已經成為研究白先勇其人其文的必不可少的基本立足點”[11]。僅以部分白先勇研究成果舉隅,便有學位論文《論白先勇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悲憫意識》[12]《論白先勇對中國傳統(tǒng)悲憫精神的傳承和發(fā)展》[13]《以悲憫情懷看待起伏人生——試論白先勇筆下“貴族的沒落”》[14]《邊緣孽子的救贖與悲憫》[15]等,單篇論文《悲憫的擺渡——散文的白先勇》[16]《悲憫情懷緣何處——論白先勇小說的佛教情結》[17]《回首看滄桑 落筆寫悲憫——臺灣作家白先勇訪談錄》[18]等。他如以“悲憫”為關目卻不見于題目者更不可計數。后之論者紛紛選取“悲憫”作為論述白先勇的基點,可見“悲憫”作為白氏作品核心特質之深入人心。
“在白先勇那里,‘悲憫’已不再只是一種看取的角度和立足的制高點——它已內化為一種精神品格和情懷氣質”[19]1,“白先勇在作品中表現了懷舊之情、追悼之情、寬容之情和堅執(zhí)之情——在某種意義上講,它們其實是悲憫之情的具體載體和呈現形態(tài)。”[20]以一個關鍵詞提綱挈領穿透文本,自“情感”“文化”“歷史—命運”“道德”和“政治”視角闡釋“悲憫”的“具體載體和呈現形態(tài)”,則“悲憫”既富儒家仁者愛人、民胞物與的“熱腸”,也具佛家慈航普度、悲憫眾生的“冷眼”,個中彰顯白先勇復雜的傳統(tǒng)文化的教化和精神氣質的養(yǎng)成。職是之故,悲憫不僅是一種“看取的角度”,更是內涵于文本的“文化集成”;傳統(tǒng)文化的不同基底在“悲憫”中不同的面向和呈現,使得文本的表意與解讀存在著交疊、復合、參差的多種可能——亦在在表露著作品的豐富、厚重、博贍。如此,文本賦予“悲憫”以獨具白先勇特色的含義,進而凝練、熔鑄成為研究白先勇的專屬“術語”。
為研究白先勇,劉氏熟讀許多周邊文本,包括白崇禧、李宗仁等周邊人物的傳記作品,更做了許多資料收集的田野調查工作,“單騎遠行,到愛荷華大學的教務及成績單位查考白氏在校所修課程……考掘出不少白先勇都記憶不清的在學生涯”[21]。“搜羅之勤,聞見之博”①轉引自陳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載陳援庵:《明季滇黔佛教考》,臺北:彌勒出版社,民72年(1983)版。,論者認為“當代學者中,劉俊無疑最了解白先勇”[21]。基于這樣的熟悉和了解,劉氏往往發(fā)前人未發(fā)之覆,如“在白先勇的命運觀中,其核心內涵主要由‘無常感’和‘孽’這兩個‘中國式’的概念組成”[19]25,斯論針對白先勇作品的精神內核而發(fā),挖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民間價值觀對白先勇的“映射”,并把其疊代入作品作為解讀的面向之一;“情感在白先勇的筆下經常與死亡聯(lián)系在一起,無論這種死亡是指向自身還是他人,死亡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寓示著‘情感’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劇性……他對‘情感’世界的基本感受帶有相當的否定性,也就是說,他一方面對人類追求‘情感’的行為有著充分的理解,但同時,他對人們能否實現‘情感’的溝通相當懷疑。”[19]44論及白先勇作品對情感追求“充分的理解”與“相當的否定性”,實則是關注其作品個人與命運之間的緊張、理想與現實內在的乖違——這種主題的復雜、曖昧適是成就一個偉大作家的質素。聯(lián)系到白先勇的童年經歷乃至與眾不同的取向,文本中情感體現的二重性更可作出弗洛伊德式的注解:“‘被人摒棄,為世所遺’的悲憤感的產生,在本質上其實是少年白先勇對自身與他人和世界關系的一種最初認定。”[19]11“這種對正常人世不適應的心理阻礙使他對這一世界總在心理上保持著一種距離和警覺。”[19]13對白先勇“個性”的挖掘本是劉氏用力最勤、成效最著之處;同時,作家與作品、文本內部與外部互相燭照、互相闡發(fā)的關系使得文本的意義網絡更形豐富。這種研究方法或許并不新鮮;但周邊工作的扎實與文本細讀的進入程度,分別了研究的層次;此即夏濟安所謂“同情的理解”,亦即唯有“對所評者同其情,以個人的生命去擁抱才可達其旨”[22]。
聯(lián)系白先勇的古典文學訓練解讀文本:“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它那回環(huán)往復,一‘唱’三嘆的強烈的節(jié)奏感,在不斷的意識回旋和愈演愈烈的節(jié)奏轟鳴中,人物內心的復雜意念和情感緒流得到了充分的展現,而這種‘節(jié)奏感’的具備,無疑地與中國傳統(tǒng)詩詞尤其是‘詞’對白先勇的熏陶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詞’對節(jié)奏感和音樂性的嚴格要求,培養(yǎng)出了白先勇對‘節(jié)奏’的敏感和自覺的追求,在引入意識流的手法時,他在對節(jié)奏的把握中開創(chuàng)了自己意識流表達的獨特方式”[19]85,以及注意到白先勇小說世界的“人物‘美’……音韻感受和文字視覺‘美’……‘色彩學’‘命名學’‘服飾學’‘飲食學’都深受《紅樓夢》的影響,帶有高度的美學自覺,極具美學意味”[20]253。前引文本揭橥了中國傳統(tǒng)文學、文化資源對白先勇的塑造以及在作品中的呈現——白先勇并非亦步亦趨于西方的寫作技巧,而是熔鑄中西、獨具特色——提示了白氏“現代主義作家”標簽之外的豐富面向,接駁了白先勇在文學史上的賡續(xù)、啟承關系,在古今、中西的參照系中界標定位,標示出白先勇個體的“絕對”價值和文學譜系中的“相對”位階。
《情與美——白先勇傳》與《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雖同為研究白先勇的專著,側重各有不同:前者重傳,后者重評;前者重人,后者重文。在更全面、系統(tǒng)梳理白先勇的人生經歷之后,結合作品對作家作出評價:“用一生鐘‘情’愛‘美’,致力于以‘美’傳‘情’、以‘情’顯‘美’。”[20]256認為“情”與“美”是白先勇畢生追求的一體兩面,亦是理解其人其文的重要關節(jié)。白先勇晚年致力于昆曲《牡丹亭》的整理、傳播,《牡丹亭》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是大眾熟知的;白先勇散文《樹猶如此》固然情深以往,其典故內含的“攀枝折條,泫然流淚”亦是真情流露。彌漫于著作中的“悲憫情懷”與上述情感枝葉交融,匯聚成白先勇生命中的“情”之一端。昆曲的繁復縟麗、目迷五色向來為人樂道,白先勇認為昆曲是“中國最精美、最雅致的傳統(tǒng)戲劇藝術”[23];讀過其散文的讀者也一定記得白氏繁花似錦、樹木蔥蘢的花園,與其作品中的“人物美”“音韻美”“視覺美”融合,亦匯聚成其生命中的“美”之一端。如此,對人和文的研究互相貫通,作品與作家互相闡釋、豐富,使其面目獨具、個性特出,研究成果也因此豁然貫通,經緯分明。
相較許多批評文章削足適履地應用西方理論,把文學作品變?yōu)槔碚摬傺莸目腕w乃至工具,劉氏著述從不為理論所役;理論僅為點染、發(fā)動批評的“觸緣”,整體上仍以文本細讀的新批評方法,承接中國傳統(tǒng)詩學洞幽燭微的精神,形成他的獨特詮釋方式。縱觀劉氏白先勇研究乃至《對“啟蒙者”的反思和除魅——魯迅傷逝新論》《執(zhí)著·比喻·尊嚴——論畢飛宇的〈推拿〉兼及〈青衣〉〈玉米〉等其他小說》《“單純/中國”與“豐富/美國”的融合——施雨詩歌、散文、小說綜論》等,皆主要以新批評方法出之。洞見學界追逐前沿理論、偏嗜“外部性”研究的人士或可覺出其中深意:回歸文本,以持之以恒的踐行糾偏補弊,把“方法論”堅守成為了“世界觀”。
縱觀劉俊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一方面,對海外“華語語系文學”等相關論說保持警覺和審慎,以“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整體推進傳達立場、發(fā)出聲音;另一方面,對世界華文文學的體系建構與散點透視相結合,在做點、面研究的時候胸中自有丘壑。此外,立足重要作家,深耕有年、探精抉微、自成一家,也使得劉氏的研究深具“密度”。君子治學,不惟授之以魚,也授之以漁。職是之故,對劉氏著述的盤點不僅特重其研究成果之精警,也意在提示其研究方法與治學精神的示范意義。
[1]劉俊.跨界整合——世界華文文學綜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2]陳遼.華文文學獨特風景線的呈現——評方忠《雅谷匯流》及其世界華文文學研究[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7).
[3]錢虹.從“臺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一個學科的形成及其命名[J].學術研究,2007(1).
[4]劉俊.世界華文文學整體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5]劉俊.越界與交融:跨區(qū)域跨文化的世界華文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6]劉俊.“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fā)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為中心[J].文藝研究,2015(1).
[7]劉俊.復合互滲的世界華文文學[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
[8]夏濟安.夏濟安選集[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9]古遠清.“我的聲音和我的存在”——讀劉俊《復合互滲的世界華文文學》[J].華文文學,2015(1).
[10]江春平.智心慧筆冷骨柔情——評劉俊《從臺港到海外——跨區(qū)域華文文學的多元審視[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S1).
[11]劉華.白先勇小說研究述評[J].文教資料,2011.
[12]趙蕊.論白先勇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悲憫意識[D].石家莊:河北大學,2008.
[13]顏吶.論白先勇對中國傳統(tǒng)悲憫精神的傳承和發(fā)展[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08.
[14]郭穎.以悲憫情懷看待起伏人生——試論白先勇筆下“貴族的沒落”[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09.
[15]丘薇.邊緣孽子的救贖與悲憫[D].廣州:暨南大學,2010.
[16]黃發(fā)有.悲憫的擺渡——散文的白先勇[J].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4(2).
[17]蘇楚然.悲憫情懷緣何處——論白先勇小說的佛教情結[J].安徽文學(下半月),2010(9).
[18]謝錦.回首看滄桑 落筆寫悲憫——臺灣作家白先勇訪談錄[J].小說界,2002(2).
[19]劉俊.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20]劉俊.情與美:白先勇傳[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
[21]李奭學.全方位的天才藝術家——評劉俊《情與美:白先勇傳》[J].文訊,2008(2).
[22]李奭學.批評即傳記——評隱地編《白先勇書話》[J].文訊,2008(10).
[23]白先勇.我的昆曲之旅[M]//樹猶如此.臺北:聯(lián)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65.
(責任編輯:李金龍)
I206.7
A
1001-4225(2017)02-0026-07
2016-04-08
李竹筠(1982-),女,河南夏邑人,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即正文征引的7本專著。此外尚有與人合著并作為第二作者的《精神分析學與文本解讀》一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