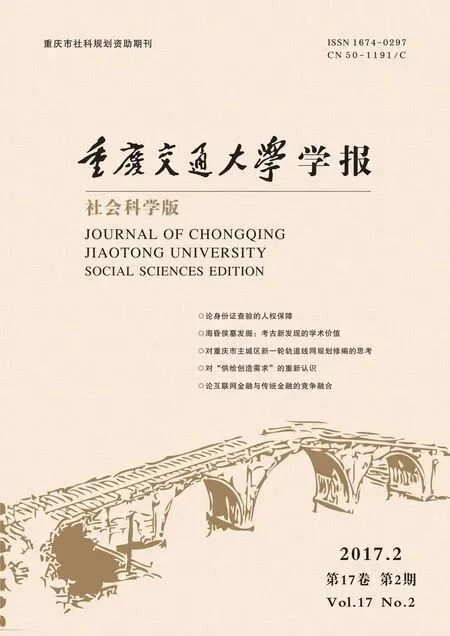另類的“文革”想象與敘述
——評王小妮《1966年》
徐 翔
(西安培華學院 人文學院,西安 710125)
另類的“文革”想象與敘述
——評王小妮《1966年》
徐 翔
(西安培華學院 人文學院,西安 710125)
“文革”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是難以回避的重大事件,親歷其中的人們對文革的記憶更多的是毀滅性的災難和難以言說的心靈痛楚。在文革后的很長時間內,出于傾訴內心痛楚和反思歷史的需要,文革被無數人不斷地言說。文革因此進入了文學視野,成為新時期文學一個獨特的文學標識,不同的作家都對那段歷史作出了不同的注解。王小妮的《1966年》別具一格,以舉重若輕的筆法描繪了那個特殊年代里的眾生百態,描繪了歷史大潮下小人物的生存體驗,展現了一種另類的“文革”想象和敘述。
王小妮; “文革”想象; 個人敘事; 浪漫詩意
“文革”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是難以回避的重大事件,親歷其中的人們對文革的記憶更多的是毀滅性的災難和難以言說的心靈痛楚。正因為如此,人們對那段歷史有著強烈的傾訴、宣泄、批判和反思的情感需要。作為影響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出于傾訴內心痛楚和反思歷史的需要,文革被無數人不斷地言說,因此就進入了文學視野,成為新時期文學一個獨特的文學標識。“如何回憶和敘述‘文革’的過程和細節,如何梳理和解釋‘文革’的來源和影響,這是一個中國大陸作家很少能夠忽視和回避的題目。”[1]面對這樣的題目,不同的作家對那段歷史作出了不同的注釋,加之文學本身具有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文革時代在不同作家的筆下呈現出了各自不同的特點。但無論以何種態度來書寫文革,作品中的歷史大多是作者親歷的,與自我的文革記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作為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作家,王小妮自然是文革的親歷者,但她并不像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對自己作為“親歷者”的那段歷史反復書寫。讀過《1966年》,會發現王小妮既沒有問責那段歷史,也沒有借那段歷史緬懷自己的青春歲月,相反,作者的態度是與文革拉開距離。“一個人離自己的家園越遠,越容易對其作出判斷,整個世界同樣如此,想要對世界獲得真正了解,從精神上對其加以疏遠以及加以寬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條件;同樣,一個人只有在疏遠與親近二者之間達到同樣的均衡時,才能對自己以及異質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斷。”[2]作者與自己所描寫的對象之間的距離,讓小說《1966年》發掘了歷史洪流遮蔽下的另一種真實。作者在小說序言里講到:“熱衷于大歷史的,始終還把它當做一個極特殊的年代,或褒或貶,我倒覺得它更像羅生門,未來會持續出現新的無限的講述空間。”[3]作為書寫對象的“文革”,在王小妮筆下因為視角的特別具有了另一種顏色,小說以舉重若輕的筆法描繪了那個特殊年代里的眾生百態,描繪了歷史大潮下小人物的生存體驗,發掘了文革敘事的新的講述空間,展現了一種另類的“文革”想象和敘述。
一、輕松的沉重
《1966年》這個書名會讓很多親歷者感到沉重、壯烈和悲傷,對經歷過文革歲月的人們來說,那是一段苦難歲月,是永遠不想回憶的夢魘,新時期之初的很多小說就描寫了十年文革給人們帶來的無盡的創傷,這樣的書寫方式是作家們在政治解壓后急于傾訴自己的痛苦和壓抑的情感所致。這些小說從不回避那個狂亂年代的社會景象:漫天的大字報、整日響徹耳邊的口號和革命語錄、如火如荼的武斗和大批判,以及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人倫悲劇。先鋒文學的文革書寫更是出現了令人發指的暴虐場景和猙獰人性,血腥和暴力、權力的爭奪與廝殺,讓人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的殘酷和暴虐。
《1966年》會讓人有一種陌生的感覺,讓人似乎感受不到那個年代的沉重。小說中沒有出現文革中慘烈的武裝斗爭、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也沒有出現傳統文革敘事作品中那些臉譜化的反面角色,甚至沒有出現文革時代的慣用詞匯“大字報”“紅衛兵”等,出現的只有“很多整張整張的大紙”、很多“戴紅箍”的人。小說寫到了游行、驚慌,但那只是作為背景影影綽綽的;寫到了死亡,但沒有描寫慘狀,也沒有家屬的嚎啕大哭,一切都平平淡淡,王小妮似乎在既定的寫作軌道上出了軌。小說筆法疏淡輕盈,敘述語言平淡,情節幾乎是寡淡的,我們無法通過作品感知作者對那段歷史的評價。不可否認,文革時代是荒誕并且沉重的,以往的小說在面對文革歷史時,或者將其當作一個政治寓言去解讀,或者著力去書寫敢于與荒誕時代對抗的“大寫的人”。《1966年》是獨特的,十一個片段式的簡單故事構成了那個時代的全部。
小說用簡筆畫式的手法勾勒了1966年幾個普通人的生活圖景以及他們的內心世界,小說中的人物皆不是個性鮮明的人,甚至面容也是模糊的,而且沒有名字,只以父親、母親、兒子、老太婆、水暖工、年輕人為代號。但仔細閱讀小說,會發現作品在很多細節、人物的心理行為刻畫和很多不經意的描寫中泄露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氣息——壓抑和恐懼。作品舉重若輕的描繪背后,確是一個個人、一個個家庭生命中無法承受之恐懼與傷痛。盡管沒有任何暴力的描寫,這些人卻被籠罩在一種山雨欲來的恐懼中,誰也不知道之前發生了什么,更無從預測下一分鐘的生活,即使沒有被劇烈的洪流裹挾,生命也變了色彩,變了溫度,變了聲音,充滿問號,這也許是人所經歷的最大恐懼。
《普希金在鍋爐里》是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故事。文革的到來讓平靜的家庭生活離一家人越來越遙遠。他們無法理解這個時代,也無法理解突如其來的另一種生活,如同小說里他們不理解為何住在日本人建的房子里是一種罪過。父母給四個孩子正兒八經開了會,告訴他們:“我們家才這么幾口人,讓一個工人階級來給我們干活是不對的,不應該,非常錯誤!”父母告訴孩子們以后得他們自己燒鍋爐,并給孩子們分了工,而且因為爸爸媽媽隨時可能“不在”,又告訴孩子們:“從今天往后,萬一家里大人不在,這個分工也不變。”小說中的父親每天都在等待即將到來的災難,“從1966年秋天開始,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陣山崩地裂的敲門,然后是一群人猛撲進來,喊他的名字,他的腿會立刻軟一下”,“這個提前等待著的預演,像一段折子戲,緊張而短促,從大楊樹開始滿街落黃葉到白霜下地,已經在父親的腦海里彩排了無數次”。主動來幫這家人燒鍋爐的年輕人也活在恐懼中,他的書包里裝著摘抄的普希金的詩集和蘇聯姑娘的照片,“那個書包給他帶來的危險比定時炸彈還大,比幾輩子的財主的變天帳還心驚膽戰”。為了安全銷毀這些,他主動來幫這戶人家燒鍋爐,卻讓這個家庭擔驚受怕,寧可受冷挨凍也要避開他。《新土豆進城了》講述一個小院里住了三戶人家,其中一戶是穿著埋汰的收廢品的老頭老太,在這一年收廢品的老頭好像感覺到了什么,他心顫了。有一天,老太太被人喊了20年前當妓女時候的名字,她慌了,知道大禍臨頭,轉身找老伴,卻發現相伴20年的人不見了,是多么深刻的恐懼讓這個男人斷絕了夫妻情分。
小說中的很多人都活在惶恐中,鍋爐工把他抄的普希金詩選和蘇聯姑娘的照片藏在床板底下,出租小人書的母親把小人書燒了,把滿洲時期的郵票藏在米袋子里,有過風月生涯的老太婆把一對金耳墜埋在刺玫底下,有軍功的醫生也因少年時曾讀過日本學校而惴惴不安。小說里文化大革命并未像一列橫沖直撞的列車闖入每個人的家門,把他們的生活硬生生地分成兩截,歷史的巨變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突兀,相反,那種變化是一點點浸入家常的日子里的。他們發現這個社會變了,原有的秩序被打亂,生活脫離了原有的軌道,變得不可理喻,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過去熟悉的世界漸漸崩塌,變得面目全非,只能被動或主動地陷入政治的狂熱之中。社會氛圍變得壓抑沉悶,每個人的命運都不再被自己掌握,明天變得不可捉摸。從城市到鄉間,從大人到孩童,每個人都壓力重重,惶惑不安,驚惶失措,甚至性格扭曲。王小妮用若即若離的筆觸,用平靜如水的語言,真實地記述了1966年無數人的噩夢,記錄了那個時代的壓抑、恐懼和瘋狂,給當下人提供了一種新的對歷史的感知方式,讓讀者在輕松中感受歷史的沉重。
二、從集體記憶到個人敘事
面對“歷史”是無數作家在寫作中都要面臨的命題,文學如何對“歷史”作出回應,是無數作家在面對文革記憶時都無法忽略的。新時期之初的“傷痕”“反思”文學關于文革的書寫被填充了過多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反思的內容,但無論是沉重的政治批判還是冷峻的文化反思,文革書寫都被納入了“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范圍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種話語霸權。作家們盡管是在寫個人的傷痛,但這些傷痛超越了個人,成為了整個國家和國人的傷痛。“在這里,個人的坎坷遭遇和國家民族的歷史災難已經被自然地連為一體,或者說,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歷史的曲折行程和未來發展。”[4]王小妮并不想以宏大視野去回顧那段歷史,小說中很難看到對文革史詩性、全景式的敘述,作者關注的并非歷史本身,而是“歷史中的個體”,是屬于他們的個人記憶。
從小說來看,歷史的巨變似乎并不是劇烈突兀的,反而不為大多數人所察覺,似在一瞬間就完成了新舊交替。盡管很多人面對變化惶惶如驚弓之鳥,但這些變化在更多人的眼中僅僅是新土豆進城了、天涼了、葉子黃了,昭示著老百姓生活中本應有的普通,日常市井中普通的人們在那特殊一年里依然重復著往日的生活。他們也許發現了街道沒有人打掃,街角的垃圾堆成了山,街上多了很多戴紅胳膊箍的人,但并未過多思考,他們都是活在當下的人,心里想的還是新土豆該怎么做,今年的菜窖要挖多深之類的瑣碎問題。這些小人物行進在歷史之中,卻又仿佛在歷史之外,時代的大浪潮在表層整合著他們的生活,但表層之下依然是個人的生活細流在涌動。“當歷史與個人相遇時,歷史的社會意義與價值被抽空,歷史萎縮為個人生存時間,甚至淡化為個人存在的氛圍。”[5]在那個特殊年代,宏大歷史往往憑借強大、不可抗拒的力量規范著市井民間的生活,但市井民間往往能突破宏大歷史的異己力量的約束。小說試圖去挖掘被宏大歷史遮蔽的民間生活和個人體驗。
《兩個姑娘進城看電影》中的主角是一對年輕鄉下女孩。一天早上,她們梳妝打扮換上最好的衣裳,騎上自行車去城里看電影,一路上憧憬著電影院的神奇。她們騎著自行車如馬飛奔地進入城市。她們發現城里變了,“紅磚墻上有粉筆寫的大字”,“沿著街的樓房從上到下都被大張紙糊滿”,但這并不影響她們看電影的好心情。兩個姑娘最后沒看成電影,電影院在開大會,她們美麗的辮子也被紅衛兵莫名其妙地鉸掉。事實上她們并沒有太苦惱辮子的問題,頭發終究會長起來,辮子還會再有,她們只是遺憾這次進城怎么就不給演電影了,她們并沒有感覺到這種變化背后的沉重。
小說里大部分故事平平淡淡,都是以普通人的視角來呈現那個狂亂的年代。小說呈現的是時代邊緣被人忽視的場景,本該是處在運動中心的那些激烈的紅衛兵運動、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殘忍的暴力場面在小說中反而缺席了。如果將書寫文革記憶的作家比作電影導演,王小妮的鏡頭偏離了時代的大軌道,卻瞄準了容易被人忽略的小軌道,記錄了一群遲鈍的人和他們對于這個敏感時代的遲鈍的感受,重繪了那個年代的另一種真實圖景,時代的苦難和創傷因為旁逸斜出的瑣碎生活畫面被淡化了。作為一個作家,在觸及歷史的時候應該先要找到一個支點,這個支點不必是龐大的,相反,一件小事、一個小人物就足夠,一個片段、一種情懷便觸及到了那段沉重歷史的內里。“普通人的感受,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輕視。任何真實確切的感受,永遠是純個人的,無可替代的和最珍貴的。”[3]小人物們對生活的感受和他們普通但恒常的生活方式化解了文革時代的意識形態話語,提供了另一種歷史的“真實”。所謂歷史,其實是由一個個小人物的生活構成的,他們的眉眼里藏著歷史的另一種質感。
《1966年》的個人敘事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主流意識形態邊緣的民間意識形態的體現,它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接近歷史真實的途徑。普通民眾的生活并沒有因為時代的巨變而出現大的變化,社會生活的多姿多彩也沒有被巨大的歷史激流蕩滌干凈,小說也因此跳脫了以往文革敘事慣常的寫作模式。王小妮用從容的文字、含蓄的方式,還原了那一年中北方小城的真實生活圖景,觸碰了歷史大潮中普通人的內心世界,故事簡單,但蘊含深遠的情感。
三、苦難中的詩意
王小妮是一個詩人,詩人的思維方式注定了她總是以詩意的筆法來記錄生活的點滴。在她的作品里,讀者會發現生活既平庸又浪漫,如同她小說里的那些故事,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背后隱藏著淡淡的詩意。《1966年》里的那些平淡故事在詩人筆下也就有了詩的特質,王小妮以細膩的筆法仔細編織著生活的每一個畫面,詩人特有的細膩筆觸緩緩展開了1966年大變局下的生活畫卷。小說盡管寫到了那個年代的沉重和壓抑,卻也輕輕撥開歷史沉重的一角,透入永恒與溫暖的光芒,讓人在沉重中也能看到人性的善和美,收獲些許希望和詩意。
《鉆出白菜窖的人》里,年輕的醫生因為上過日本學校,會說日本話整日惴惴不安,工作組上門調查他已經過世的老師是否是特務的時候,盡管自己已是岌岌可危,在百般逼問下他仍然要保護他的老師。《一個口信》中年輕的工人無意中聽到組織在調查同廠的一名女工,盡管他和這個女工三年間沒有說過話,但他決定要冒險給這個幾乎陌生的姑娘帶一個可能并無太多幫助的口信,因為他覺得“明是聽見,不能去遞個信兒,不能去說一聲,做人不能這么不仗義”。《火車頭》里有個“戴帽子”的人以組織的名義每月給無依無靠的小男孩送來五元錢,并告訴他要當一個好人,這個男人還叮囑自己的兒子,“你到某街某胡同某號去看看,有一個孩子,看他是不是還在家,暖氣熱不熱,有沒有吃的,要對那孩子好一點”。在1966年這個混亂的年代,很多人都會變,很多人的道德觀價值觀都被顛覆,但在小說里,讀者會看到人性所不曾泯滅的善良之光。在那個政治觀念裹挾一切的時代里,大部分人往往是以政治地位來判定個體的道德品質,但這些人有著他們的善惡是非觀念,有著異于主流意識形態的道德意識,這是開在苦難中的善之花。這些飽含著情誼的畫面盡管微不足道,只是歷史長河中不為人關注的一個點滴,卻為沉重的歷史注入了極具力量的永恒人性之美,讓苦難中多了一絲溫情和詩意。
小說中很多故事是以孩子的視角來寫的,這又讓小說呈現出了童真的色彩。1966年在成人和孩子心目中是完全不同的。對成人來說,這一年是殘酷的紅色風暴,讓他們無時不在恐慌和恐懼中;但對不諳世事的孩子們來說,這是一個狂歡的時代。政治運動的到來讓所有既定的秩序都被打破,這個時代的一切都處在一種無序的狀態下,卻為不少孩子帶來了歡愉的時光。孩子們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他們有無數的方法讓自己在物質供應短缺的時代里精神生活更加豐富。
《在煙囪上》是讓人讀起來感覺一絲開心的文章。小男孩被母親關在家里,但他有自己的樂趣,他用吃過冰棍剩下的小木棍搭房子和橋,然后拆掉基座上的一根,看整個建筑物一下子塌掉。他家是開小人書店的,為了避免迫害,小男孩的母親關閉了書店,并且把小人書都燒掉。小男孩偷偷藏起了小人書的封面,盡管被母親責罵,卻依然沒有說出它們的下落。后來小男孩不再是一個人了,五個小學生和他成了好朋友,最終小男孩說出了他的秘密,所有的小人書封面被他藏了起來,這個秘密成為了六個人的秘密。這是一種純粹的快樂,孩子們都是單純的,在那一瞬間,誰還記得外界是怎樣的環境,他們只記得那干凈的快樂。
事實上,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著自己的秘密花園,有著自己的夢幻空間,這內心的一角是靈魂深處最柔軟的所在,它不因外界的變化而改變,只忠于個人的心靈。在這個空間里,人們可以盡情地幻想,盡情在詩意中飛翔。《普希金在鍋爐里》寫到了一個小女孩的純情和夢幻的世界,小說盡管也寫到了壓抑和恐懼,但小女孩依然有著屬于少女的夢幻想象空間。這個十二歲的女孩喜歡看雪,她希望每天都能下雪,她喜歡一個白色的世界,“這是一個被白雪公主之類的童話蒙騙的孩子”,這樣的蒙騙又何嘗不是一種幸福?燒鍋爐的年輕人觸動了少女的心扉,“她的心里涌現出一種隨著雪片傾斜著飄舞的感覺”,“女孩覺得她并不在這個亂哄哄的世界上,她自己有另一個世界,暖和又有好看的顏色”。因為對年輕人好奇,女孩偷看了他的本子,普希金的一行行炙熱的情詩讓女孩子嚇壞了,這也導致了本子被扔到鍋爐里化為灰燼。年輕人不再出現,女孩感到一絲遺憾,女孩甚至想象“那些詩,也許就是他寫給她的”。一切好像童話一樣,仿佛是一個夢,小女孩在夢中成了公主,遇上了自己的白馬王子,盡管結局有點遺憾,但讓沉重的生活有了一絲亮色。
傳統關于文革的敘述大多是悲情的、控訴的、情緒化的,《1966年》則是舒緩的、綿密的,帶著淡淡的詩意,這詩意不是作家刻意營造的,而是來自于那個年代真實的生活,來自于人內心深處隱秘的一角。這是一首寫給普通人的詩,有人能在那個荒誕的年代中找到自己的童真樂園,有人能在人性泯滅的年代保存內心的善,有人會在那個蒼白的年代中保留對生活的夢幻想象。出于詩人的敏感,再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王小妮心里也能激起波瀾,小說中的詩意正是來自于一些不值一提的細枝末節。但正如她所說:“在平淡中,在看來最沒詩意里,看到‘詩意’,才有意思,才高妙。現在的世界太現實。人天生就應該有奇思怪想。”[6]王小妮用詩人般飄忽的筆來寫史,讓黑白的年代里多了一層彩色,讓苦難中多了些許詩意。
四、結語
小說《1966年》并不是要還原作為“集體記憶”的文革時代,而是提供了對文革時代的另一種敘述。作者對那個時代的描述滲透了自己對個體命運的思考,歷史中一個個鮮活的小人物是王小妮傾注了感情的寫作對象。作者在書寫文革時與歷史拉開了一段距離,但小說并沒有因為淡化的歷史情境而使寫作失去意義。王小妮的歷史講述是人的命運,是歷史時空里亙古不變的人性,是獨特的個體生存體驗,這在個體詩學意義上展現了個體在面對歷史時的選擇的自由。小說呈現了小人物在歷史大潮面前的真實反應,有怯弱和恐懼,有人性的善和美,有自己的詩意的空間。這些人面對歷史巨變的不同反應,讓小說具備了類似羅生門一般的多重空間,同時,這種多樣性的敘事改變了人們對文革歷史的單一刻板的記憶和認識,展示了一段另類的“文革”想象和敘述。
[1] 許子東.敘述文革[J].讀書,1999(9):12.
[2] 薩義德.東方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31-32.
[3] 王小妮.1966年[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4]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211.
[5] 周新民.生命意識的逃逸[J].小說評論,2004(2):34.
[6] 王小妮.半個我正在疼痛[M].北京:華藝出版社,2005:222-223.
(責任編輯:張 璠)
Alternative Imagination and Narration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 Review of WANG Xiaoni’s 1966
XU X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Peihua University, Xi’an 710125,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significant event happened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bringing people endless disasters and the trauma difficult to heal.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the need to pour out the pain and reflect the histor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always the speech topic of countless people.Ther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entered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has become a unique literary identity in the new period. Different writers have made different annotations of history. WANG Xiaoni’s 1966 is more unique. In order to ease the brushwork, the novel depicts the living beings in the special bigotry and the little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tide of history and experience, which shows an alternative imagination and narr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NG Xiaoni; imagin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sonal narrative; romantic and poetic
2016-08-23;
2016-09-06
徐翔(1981—),女,河南南陽人,西安培華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I207.42
A
1674-0297(2017)02-008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