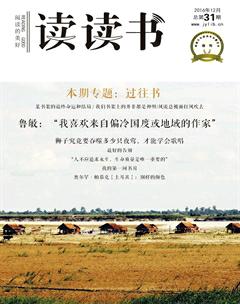面對暴力碾壓前的預備性訓練
殷羅畢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困擾和煩惱其實來自于一些平日里壓根不會發生的事件,或者只是端點上的事件——比如死亡、貧窮、破產或暴力。事實上,我們生命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處于平緩的日常狀況中。
但是恰恰由于對極少數的狀況我們沒有準備,缺乏把握和足夠的理解,所以我們大多數時間都處于不安之中。對于暴力的不安感,是我們當下最為突出的一種焦慮。
當我們談論暴力時,我們似乎在談論這人世間最堅硬最沒有討價還價的問題,因為圣人的轉過左臉都沒法解決甚至稍稍減緩一點這種沒有討價還價的特征。暴力,不跟你多啰嗦,它不說話。
暴力與死亡的區別,暴力內部的人間裂縫
似乎,死亡是暴力最后的現實。但是,當我們降到暴力死亡,這人世間巨型漏斗的最底部,似乎有一道奇異的裂縫出現。當我們不再是轉過臉去,而是徹底掉過身去,把自己的身體和性命掉落在地上,從死亡的那一端再看過來,來看看暴力,你會看到什么?
暴力的秘密在于,相比純粹的死亡,暴力依然充滿了人的氣息。它依然是一種人間的劇場。盡管死亡都直通虛無,但死有著各種死法。你走在大街上,被人排著隊驅趕,然后直接在街面上開槍射殺。或者,你走在大街上,直接被整棟樓倒下壓死,因為地震來了。
很顯然,在這些死中,我們也會選擇一二,而不是無論好死爛活都是一個樣。被地震震死,基本心滿意足,天災,純物理純概率的事件,就跟自己的出生一樣,純屬天道無常。因此,這樣的死與自己的生相齊平,有著最標準最客觀的零度面容,童叟無欺。但如果是人被人驅趕著,挾持著,最后殺戮著,這死就死得不標準不客觀不正當。因為,在這個死里面,有著過于強烈的人的氣息。人強加給人的死亡。而人是沒有資格來強加給人任何東西的,何況死亡。這樣的死亡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對人的羞辱和貶低。
至此為止,關于暴力的秘密,其實已經水落石出——即使它與死亡緊鄰為伍,但絕大多數的死亡都與暴力無關,它們都只是災難,是事故,是病變。所有這些客觀物理層面上的死亡,均帶有零度表情的特征。但是暴力卻充滿了人的表情,即使它可能對被殺害者毫無興趣,但是施暴者本身卻必須處于一種充滿情感情緒的場景和節奏之中。因為,暴力——以人殺人(或它的較低版本,以人毆打人),必然是一種對施暴者充滿了意義的事件。這過于濃郁的人的氣味,恰恰是暴力這塊巨型花崗巖內部深處的一道裂隙,我深潛到近乎無人的深處,所要找到的秘密就在于此。這裂隙看似只是針眼,但從中卻是豁然洞開了一個自由的宇宙。
在此,面對暴力的策略變得相當具體。面對暴力,即使它對你這個作為人的存在毫無興趣,只是像兒童撕碎一張紙一樣想把你撕碎,你也有機會加以反擊。那就是從自己的被害者情緒和處境中脫離出來,考慮和處理他的處境,從而把施暴者自嗨的所有環節和節奏破壞。這一反擊行動的意義不單在于可以盡可能減少暴力對你的傷害,更大的意義在于,即使暴力最終依然在物理上毀掉了你,那場毀滅也僅僅是物理上的,你會保有著盡可能不那么悲慘的人格與尊嚴,因為在面對暴力襲擊時你保持了與施暴者對等的人與人的地位。
施暴者的自嗨節奏需要受害者配合打拍子
小孩子撕碎紙張時,他并不在意紙張是怎樣想的(在訓誡和權力控制中,被害者怎么想卻是施暴者的目的和重點所在),但是他自嗨的整個過程需要有紙張被撕碎的嘩嘩聲助興。試想一場完全無聲的碎紙活動,該是一次多么無聊和無趣的過程,從狂歡變成了沉悶的勞作。純粹的施暴者的樂趣,也同樣需要受害者的種種聲響——哭泣、求饒、驚叫……
是的,通常情況下,受害者的種種反應,往往正是施暴者暴力節奏的節拍器,從情緒和動能上配合加速著施暴。因為,施暴者的心理動力一定程度也需要一種最基本的能量互動,他打出一拳,得到回應,然后就有了第二拳的更大動能。施暴者與受害者都會進入越來越投人的一場能量浸潤。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蘭德爾·柯林斯先生在他的《暴力:一種微觀社會學理論》一書中為我們提供了有說服力的典型案例,比如一位被搶劫的老太太向施暴者求饒后,她遭到了更猛烈的毆打,因為求饒就等于把自己的身體主權整個出讓給了對方。這使得施暴者越來越超出原先的暴力底線,做出他們自己之前或許都沒有設想的極端行為。這情景做一個不那么合適的類比,當一個男性與一個女性同處一室,如果女生把自己的衣服都脫除無遺,這時男生會覺得自己如果不做點什么似乎是不對的(請原諒我的直男癌邏輯),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情境動力問題。人的很多行為,往往是在情境暗示和推動下進行,暴力和屠殺也同樣如此。
而受害者在第一次打擊下做出的驚嚇反應求饒反應恰好是施暴者最理想的能量回饋。面對一個徹底放棄了自己的受害者,一個驚恐求乞的可憐蟲,這時候不多踹幾腳,豈不是天理不容?因為老天爺設置的時間空間——場景都讓你到了這一步。
所以,施暴者能否制造和控制住一個符合暴力自嗨的場景,是關鍵所在。街頭搶劫犯就往往會選擇讓受害者更無助的情境。“街頭搶劫主要發生在深夜10:00到凌晨5:00之間(Katz1988:170;Pratt 1980)。在這里,實用主義的考慮(目擊者較少)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搶劫者有一種在自己地盤上行動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是在屬于自己的“時間”里行動。搶劫者擁有這個深夜,而受害者則往往不太習慣在這個時間段外出活動。相反,大白天在熱鬧街頭出現的搶劫很少見,部分是因為氣氛完全不同;路人的心態更加放松,看起來不太像軟弱的受害者,而搶劫者的沖突性緊張/恐懼程度則更高,因為他們失去了自己的能量。”
這種無助情境的制造,除了時間空間之外,受害者本身的反應方式也是核心問題,因為受害者其實也是暴力能量互相浸潤中的一端。其中,哭泣是最符合暴力加速自己節奏的一種助燃劑。還是從加害者的視角來看,暴力過程是如何從一種試探性的侵犯變成徹底的霸凌的。
“我們的囚室里有四個人。其中一個見了訪客后,帶回來一些印度大麻。他分給了我們。我們開始打枕頭仗。他顯示出他是最弱的一個。我們三個開始集體攻擊他。我們開始揍他。一開始還像是開玩笑,后來就認起真來。我的朋友把他按在床上,我把枕頭壓在他臉上。他開始哭起來,我們則開始打他。我的朋友把掃帚捅進他的短褲里。如果他反抗了,一切就會在這里結束。如果他站出來維護自己,一切都會不同。但他卻只是一動不動地躺著,結果另一個男孩將掃帚捅進了他的肛門。我不知道我們為什么會這么做。在囚室里,我們常會覺得無聊,然后就會想辦法找樂子。不幸的是,我們往往是在弱者身上找樂子。(oDonnell and Edga r,1998a:271)”
對暴力的還擊——將施暴者拉到與自己一樣的通常狀態
而類似的情況,運用相反的策略,則有了完全不同的結局。一個被臨時監禁的男人,遇到向他敲詐勒索的囚犯,他明確表示自己什么都不會給對方。盡管打了一架,還打輸了,但他依然表示,不會給出任何東西。后來,也就沒什么后來。施暴者失去了暴力欺凌帶來的能量回饋,回到了通常的低亢奮狀態。因此,控制住暴力侵襲所帶來的震驚和反應空白狀態,控制住現場的節奏,是面對暴力時最好的對抗和自我保護。
不斷小規模地打斷對方的進程,又不完全激怒對方,從而讓對方在低烈度的暴力過程中完成他的任務和目標。這是一個面對暴力,進行相對完善防衛的案例。當然,誰也不能打包票說,你打斷對方的進程,同時又略略配合一下完成對方的目的,是最可靠的保證。在暴力的現場,沒有任何人可以預估和完全控制過程與結果,包括施暴者自己。
但是,淡定從容面對暴力,將施暴者拉到和自己一樣的通常狀態,或者說,避免讓自己瞬間懵逼、避免成為刀俎上的魚肉,至少在暴力的現場以某種有尊嚴的形式存在。這其中的微妙區別,會帶來內在心理上的力量感和自由感,暴力也就顯出它的情緒化面孔、它的人類氣息——內部充滿了沖動、恐懼和莫名不安定的因素。這些因素,恰恰是遭遇暴力侵襲時可以加以利用和還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