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符號VS審美資本主義
王杰++向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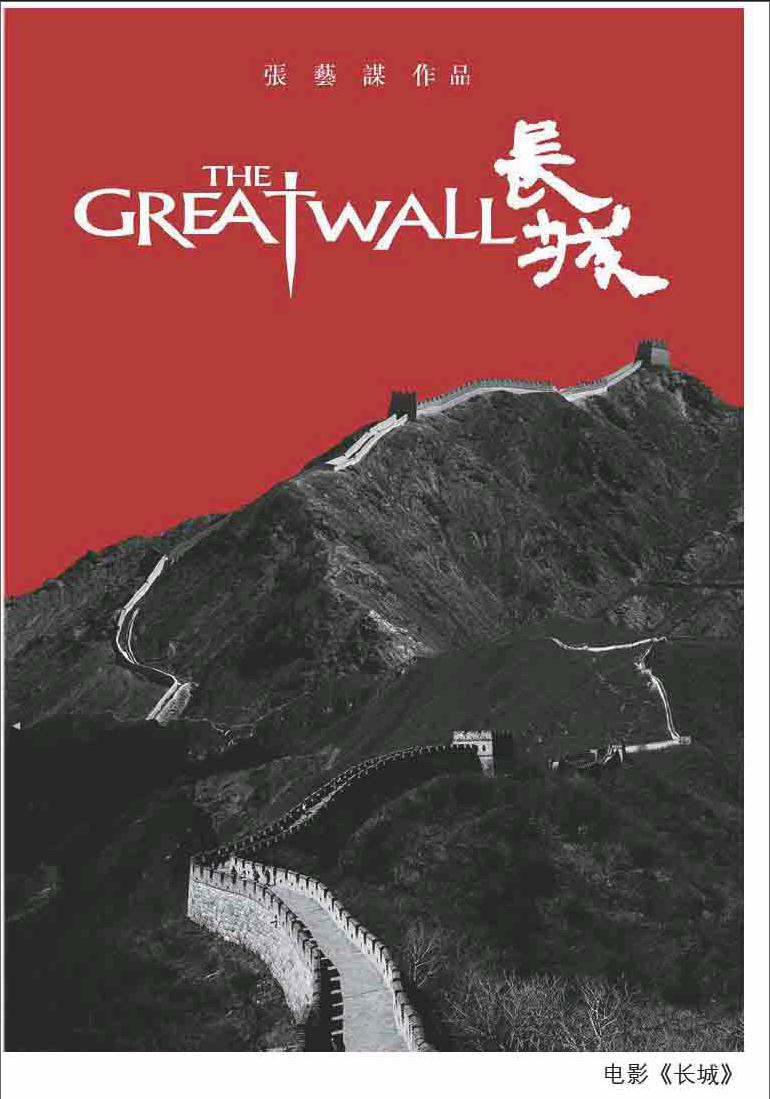

王杰(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近年來,我們對于當代中國電影進行了持續(xù)性的考察與討論,這主要源于我們共同的一個研究理念:在某種意義上,當代電影是理解與闡釋美學“當代性”的一個很好的文本。尤其是藉于當代電影觀察,通過對中國當代發(fā)生的審美文化現(xiàn)象進行分析,可以發(fā)掘和闡釋出中國經(jīng)驗的美學思想和批評形態(tài)。諸如近期上演的張藝謀導演的好萊塢版電影《長城》引起了眾多的討論,褒貶不一。盡管我們可以同意這并非一個好片子,但將其放置于審美資本主義的語境中進行解析,其多重文化疊合所折射出的鏡像及其幻象化,由此引發(fā)的諸多問題卻是值得我們深究的。
向麗(云南大學文學院教授)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中國當代文化呈現(xiàn)出一種雜糅著國家意識形態(tài)、消費主義邏輯以及多重文化資本、身份資本、審美資本等文化因素于一體的“反應”狀態(tài)。就今天討論的電影《長城》而言,我更愿意將其作為一個文化事件和美學事件來看待。正如張藝謀2002年執(zhí)導的電影《英雄》在某種意義上可謂關(guān)于“911事件”之后世界秩序的一種理解,比如殘劍所演繹的哲學就是以和平解構(gòu)暴力,那么,《長城》作為一種姿態(tài),它又將言說什么呢?
盡管張藝謀在今天所招致的批評多集中在他關(guān)于東方奇觀抑或東方情調(diào)的刻意營造,以迎合西方的某種想象和欲望。但無可否認的是,張藝謀在此種民俗政治的神話建構(gòu)中,攫取了時代的強勁資本,包括資金和文化的資本。面對《長城》在電影運作模式、敘事結(jié)構(gòu)、展演方式所出現(xiàn)的一些新特點,“審美資本主義”是一個重要的觀察切入口。
審美資本主義是一個綜合的且多維度的現(xiàn)象。審美資本是繼“經(jīng)濟資本”“文化資本”之后的一種重要的當代資本形態(tài),然而在國內(nèi)學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在我看來,審美資本主義至少具有如下三個特點:(1)恰如法國學者奧利維耶·阿蘇利所指出的,審美的動因成為當代經(jīng)濟增長的一個動力;(2)在馬克思關(guān)于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的空間隱喻中,審美資本主義使審美和藝術(shù)本身直接成為基礎(chǔ);(3)審美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生產(chǎn)力,不斷地創(chuàng)造新的消費制度,它不僅滿足一種已經(jīng)存在的消費需求,而且在不斷地生產(chǎn)與再生產(chǎn)出更為復雜的消費欲望,從而形構(gòu)出新的文化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和圖景。
就作為事件的《長城》而言,它首先具有一種戰(zhàn)略性的意義,是中國向外展演中國符號以及中國夢的一種儀式。電影力圖表達對于中國傳統(tǒng)與智慧的尊重,以及對于人類貪欲的救贖宏旨和與他者攜手合作的某種意愿。然而,正是在“資本在表達,而非藝術(shù)在表達”的格局中,中國敘事與他者想象之間的博弈引發(fā)了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在《長城》中,張藝謀化約式地提供著關(guān)于中國的想象,諸如其中拼湊的景觀世界、明星框架的空設,以及好萊塢審美品味的中國式嫁接等等,當審美自主性喪失后,災難也將發(fā)生。正如阿蘇利所指出的,審美資本主義的危機在于,“市場并非品位生產(chǎn)的地方,而是愉悅感的截獲,形式化和開發(fā)的地方。”當代中國電影觀眾的市場格局已然發(fā)生變化,集體的美學狂歡已讓位于觀眾的階層分化,我們需要傾聽多種聲音。今天我們圍繞審美資本主義探討中國當代電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彭斯羽(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審美成為經(jīng)濟增長的動因,抑或,審美和藝術(shù)成為一種新的資本,這的確是我們當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不僅如此,這種特殊資本的運作同時生產(chǎn)出復雜的消費欲望,尤其是生產(chǎn)出一種我想要去占有一個更美妙生活的欲望,所以資本主義正好抓住了這種欲望的深層動因,興起了關(guān)于藝術(shù)的蓬勃發(fā)展的巨大產(chǎn)業(yè)。就《長城》而言,它同樣是資本與藝術(shù)的攜手運作。在這種運作中,國人非常關(guān)注中國文化的輸出是否成功的問題。這是中國電影故事與好萊塢敘事模式的雜糅,因此其中所包蘊的討論空間非常之大。
蘇東曉(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副教授):《長城》號稱中美合資,按照好萊塢工業(yè)流水線制作與發(fā)行,瞄準中國與海外電影市場,野心勃勃渴望開創(chuàng)中國電影票房新紀元,同時希望充滿情懷,借好萊塢通往世界電影市場的大船,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等等。然而,電影在國內(nèi)上映不僅沒有獲得預料的超高票房,還被網(wǎng)絡影評一邊倒地差評,甚至引發(fā)資本、權(quán)力和自媒的一片混戰(zhàn)。我認為這是全球化的今天,由技術(shù)和經(jīng)濟的力量推動產(chǎn)生的混雜性進入文化領(lǐng)域的結(jié)果,是作為一種傳播實踐,激發(fā)和強化國內(nèi)的文化矛盾與文化沖突的一個典型事件。
從電影敘事層面上看,《長城》由好萊塢公司創(chuàng)作劇本,張藝謀導演,因此疊加了好萊塢經(jīng)典打怪獸電影的敘事結(jié)構(gòu)和東方影像,并且以共同對抗貪婪,以犧牲拯救蒼生及相互“信任”為立足點,尋求普適價值,試圖削弱中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對抗,消除西方觀眾的文化隔閡,并在一定程度上嘗試了中國集體主義美學與西方個人主義價值的對接。但《長城》比過往呈現(xiàn)出更為濃烈的東方對西方“東方主義”的反凝視性,但這種“反凝視”仍然是建構(gòu)在西方“東方主義”的框架之內(nèi)。在影片中,東方文明是以碎片與奇觀化的方式呈現(xiàn),東方價值觀深層次的內(nèi)涵是弱化和不清晰的,而且當東方面臨危機時,發(fā)揮關(guān)鍵作用的拯救力量仍然是西方主人公及其所攜之“物”。因此影片被認為仍然有強烈的“洗白”傾向,仍然是東西對抗中一種東方民族自我確證的審美幻象。總的來看,《長城》及其事件實際上是社會經(jīng)濟、文化領(lǐng)域中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與政治斗爭所形成的情感結(jié)構(gòu)在審美表達與評價中的呈現(xiàn),資本在中國市場強勢營銷的過程低估了中國社會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所賦予藝術(shù)的世俗意義與超驗意義。
王真(《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編輯部編輯):好萊塢的電影敘事模式在我所習得的電影品味中并不太入流,但我還是想做兩個方面的比較。一是我們可以比較一下近年幾部比較優(yōu)秀的口碑和票房都雙豐收的電影,從《瘋狂的石頭》到《泰冏》,到前年的《夏洛特煩惱》,在評論界都受到相當?shù)暮迷u,它們其實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以喜劇的形式對社會現(xiàn)實進行一定的批判。因此,電影是可以用一種普通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批判性的;另外,我還想談談李安電影敘事的復合性特征。李安是臺灣的電影導演,但是他在執(zhí)導的幾部影片中宣揚的卻是印度文化,比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從一個印度神話講起,表現(xiàn)了人的心靈成長的故事。再如《比利·林恩的中場戰(zhàn)事》也表現(xiàn)出了對印度教的某種皈依。我在看這些片子的時候多少會有些困惑,一個臺灣導演為何不借助我們中華文明,而是把印度教的隱喻放到電影當中進行表現(xiàn)?但細究起來,這實際上還潛藏著一種他者的心態(tài)。其實,最簡單卻常被人忽略的事實是,我們想進行文化輸出,我們首先要把自己池子里的水蓄足。當然,此種能力包括了審美資本與話語權(quán)的問題。就電影《長城》而言,我當時看到一些相關(guān)報道,說張藝謀實際上是被資本操縱,他并沒有獲得導演的自主權(quán)。當“資本在言說”起主導作用時,資本對藝術(shù)的“中傷”可想而知。
吳娛玉(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后):孤立地看《長城》或許并不一定明晰,我試圖將它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zhàn)事》對比。兩部影片都是華人導演,都是中美合作,都講述了英雄的故事,所以兩者極具可比性,而相較之下,兩者呈現(xiàn)出來的思想因子卻截然不同。(1)戰(zhàn)與反戰(zhàn):在《長城》中是人獸之戰(zhàn),因為是異類之戰(zhàn),所以當人殺死獸時絲毫沒有心理障礙,殺死多少都不足惜,這形成一個簡單的敵我二元對立的模式。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zhàn)事》的伊拉克戰(zhàn)場是人與人之戰(zhàn)。在殺戮的瞬間,人性的不忍、脆弱和無可奈何暴露無遺,殺戮和死亡帶給比利·林恩的心里創(chuàng)傷讓觀影者感受到了李安潛藏其中的反戰(zhàn)思想。(2)英雄的建構(gòu)與解構(gòu):《長城》是一個建構(gòu)英雄的過程,主人公威廉·加林最初是一個盜賊,隨著劇情的推進一步步成為拯救全人類的超級英雄,鹿晗扮演的角色是主人公的陪襯,他也是同樣從一個懦弱膽怯的小兵成為了勇敢無畏、視死如歸的英雄。這兩個角色是二而一的關(guān)系,仿佛讓我們看到了十七年“文革”文學中的英雄成長史,一個殘缺軟弱的個人在某種精神的引領(lǐng)下轉(zhuǎn)變?yōu)楦叽笕偷摹⑸嵘×x的英雄形象。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zhàn)事》卻是一個解構(gòu)英雄的過程,因為一個遺失的攝像機無意拍到了比利·林恩拯救班長的舉動,于是,他被美國媒體樹立為一個英雄典型,但是整個的影片實際是對英雄日常生活以及真實體驗的還原。主人公在戰(zhàn)爭中受到的創(chuàng)傷的內(nèi)心始終無法縫合,讓人們重新思考“英雄”和戰(zhàn)爭。
通過兩個影片的比較可以看出,同樣是大場面、大制作,但呈現(xiàn)出的思想因子卻不可同日而語,《長城》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敵我模式,是一個自我營造的人與非人的對立,與真實的現(xiàn)實相去甚遠,而李安試圖在事件的背后發(fā)掘人性的復雜和生活的真實。
張永芳(浙江警官職業(yè)學院副教授):盡管張藝謀的電影有其套路和重復性,但我認為《長城》還是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創(chuàng)新。首先,張藝謀的電影一直以來都能緊緊抓住現(xiàn)實,從《秋菊打官司》《英雄》再到《長城》等等,都是如此。《長城》在東方古典文化中植入好萊塢的商業(yè)模式和英雄主旋律,盡管弱化了甚至有人認為背離了中國的古典氣質(zhì),但全球化是人類不可抗拒的潮流和趨勢。藝術(shù)的內(nèi)容及形式,必然要跟上時代發(fā)展的趨勢,學習與借鑒人類文明的成果,有什么不好呢?同時,網(wǎng)絡游戲也已然是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成為現(xiàn)代人的生活方式,盡管這種生活方式有種種問題。因此,對網(wǎng)絡及游戲最為熟悉和鐘愛的年輕觀眾,更容易接受和喜愛《長城》,我們對《長城》的評價有好有差這一結(jié)果也就可以理解了。其次,從藝術(shù)與政治的關(guān)系來說,《長城》中怪獸最終被擊敗,是中西方合作的結(jié)果。饕餮作為人類自身巨大貪欲的隱喻,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災難,甚至是所有災難的主要根源,戰(zhàn)勝人類自身的貪欲,只有人類攜手合作。影片也正是著力渲染了東方集體主義精神與西方技術(shù)完美結(jié)合的價值取向,這也正是世界各國積極倡導的共識和努力的方向。
周曉燕(鹽城工學院教授):在我看來,張藝謀堅定地走著“生產(chǎn)專供出口的‘東方情調(diào)的藝術(shù)路線”是有其藝術(shù)價值的。從1987年《紅高粱》的民族風“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1991年《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西皮流水、《活著》中的皮影戲音樂、《我的父親母親》《一個也不能少》《英雄》《山楂樹之戀》中大鼓、小鑼和小提琴等古典、現(xiàn)代以及中西合璧的配樂,一直到《長城》,相比其視覺圖像語言、制作特效以及價值觀等,都超越了聲畫組合的傳統(tǒng)意義,實現(xiàn)了一種類似“聲象蒙太奇”的驚奇效果,極大提升了影片整體的表現(xiàn)力,展現(xiàn)出了不同凡響的美學價值。比如,《長城》影片開始景甜領(lǐng)銜的鶴軍出場又一次完美地展現(xiàn)了張藝謀式的集體主義美學觀——工整、穩(wěn)健、壯觀,你可以詬病這是團體操,但不能否定通過人群的秩序展現(xiàn)的美具有令人震撼的美學效果,讓人在瞬間體味到一種個體服從整體,個性融于共性的軍威和國威,萌發(fā)一種保家衛(wèi)國的豪情。
因此,盡管張藝謀這次“好萊塢爆米花”的嘗試被批判為“集體性掩蓋了人性”“擁戴極權(quán)”“價值觀平庸”“重復自我”等,但有一點毋庸置疑,《長城》的經(jīng)驗和努力,讓我們看到了國際合拍片的種種新的可能,這種可能的理論基礎(chǔ),我認為首先應該基于承認“審美資本主義”是一種事實,在西方社會如此,在中國社會也是;其次,我們與其一味批判出口“東方情調(diào)”是“當代意志的勝利”,或者一味地強調(diào)“品味”和“審美”與經(jīng)濟因素的對抗性關(guān)系,還不如認真分析“東方品味”與工業(yè)化進程、機械復制以及經(jīng)濟增長之間的張力。
尹慶紅(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很顯然,《長城》是按照好萊塢商業(yè)大片的模式來制作的。它具備商業(yè)大片的基本元素,并且都是吸引票房的重要砝碼。客觀地說,在大陸導演中,也只有張藝謀有這個能量把這些要素集合起來。正因如此,張藝謀有這么好的條件和優(yōu)勢,他應該創(chuàng)作出一部更高水平的作品來。然而,按照優(yōu)秀的好萊塢商業(yè)片的要求來看,《長城》也只能勉強算及格,遠談不上優(yōu)秀。好的電影一定是善于講故事的。但在《長城》中,我們發(fā)現(xiàn)張藝謀越來越不會講故事了,只注重場面的調(diào)度、色彩效果的渲染,將一個個絢麗的形象進行簡單的拼貼組合,看似熱鬧,卻沒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給人花里胡哨的感覺。作為反派的怪獸饕餮的形象也沒有什么獨特之處,僅僅只是在怪獸的頭上戴一個饕餮圖案,看起來就是一些頭頂饕餮圖案的恐龍。至于饕餮有什么獨特的造型,什么樣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性,有什么獨特的作惡手段等,電影都沒有體現(xiàn),饕餮只是一個象征貪欲的空洞的符號。至于如何貪,貪到什么程度,怎么個貪法,為什么貪等,導演都無心去思考和表達。
當然,這種簡單化的處理有其原因。影片故事的主要編創(chuàng)人員來自好萊塢,他們對饕餮神話和饕餮形象的了解有其倉促性和膚淺性。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輸出的主體應該是以“我”為主,“借船出海”只是手段和方式。但在資本裹挾和西方強勢文化面前,張藝謀的文化主體性是喪失的,表現(xiàn)出沒有文化自信。因此,從“借船出海”的文化輸出模式來看,《長城》是一次大膽的嘗試,值得肯定,但嘗試并不一定能夠成功。當然,從不斷的嘗試中總結(jié)經(jīng)驗、反思不足,繼續(xù)努力,可以做得越來越好。
王大橋(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長城》有著好萊塢大片一貫的風格,影像畫面炫麗華美,視聽效果不錯,即使故事的講述、情節(jié)的發(fā)展以及人物性格的扁平單一影響了影片的質(zhì)量,觀影感覺卻并非特別糟糕。不過這些都不是我要展開的內(nèi)容,就影片對中國文化元素的利用問題我談一點看法。饕餮是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中的怪獸,《山海經(jīng)》對其樣貌特征有所描述:羊身人面,眼在腋下,虎齒人手。饕餮紋的紋飾最早出現(xiàn)在玉器上,青銅器特別是鼎上更加常見。后世對饕餮紋飾有著各種各樣的識讀,張光直認為青銅上的饕餮等動物紋飾有溝通人神的神秘功能。影片要打的怪獸饕餮被表征為貪婪而瘋狂的影像符號,在“長城”“黑火藥”“孔明燈”“秦腔”“兵法”“葬禮”等中國文化符號所編織的影像敘事中,就連故事發(fā)生的時間“宋朝”也抽象化為一個模糊的時間概念。
圓通的中國文化因此被擠壓成扁平粗線條的狀態(tài),清洗掉特定文化的復雜內(nèi)涵,也許方便海外觀眾理解,但是因其高度簡化中國文化元素,張藝謀所期待的中國文化和價值觀輸出沒有辦法通過這樣的影片來完成。需要為張藝謀辯護的是,中西兩種文化相遇,跨語境的相互“文本化”難以避免,不過意識不到這一點,或者有意去強化“異文化想象中的中國”則另當別論,張藝謀早期曾因此受過指責。
肖瓊(云南財經(jīng)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張藝謀的《長城》意在借用好萊塢的模式,將中國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元素進行文化輸出。電影作為一種輸出方式確實是一種很好的媒介,但是怎樣輸出呢?為什么中國文化的輸出必須借助好萊塢模式?張藝謀能否熟練地講好這個好萊塢的故事?這些都是我在看這部電影時思考的一些問題。
其實,在文化全球化的語境中,中國電影不乏好的“講故事”的范例。比如鄭曉龍導演的《刮痧》,講述的就是一個非常溫情的中國故事:爺爺給孫子刮痧,西方人卻認為是虐待,在這種中西文化對立和沖突中,中國人身上所呈現(xiàn)出來的親情和溫暖、選擇和面對,最終讓西方人到中國探尋刮痧及中醫(yī)的治療魅力。《刮痧》同樣面對中國文化如何進行輸出的問題,但它講述的是中國式的情感故事,讓西方人明白中國的情感、中國的文化以及中國人處理事件的方式。
《長城》試圖以好萊塢的模式將中國電影進行消費性的包裝,完成將中國文化、中國審美和中國元素推向世界的宏大任務,終因敘事和內(nèi)容的貧乏招來眾多的吐槽。不過從悲劇的角度來說,也許是一種新的嘗試。馬克思說,任何新生事物在其出現(xiàn)時總是以悲劇性的形式推進。我非常同意向麗教授所說的,將《長城》作為一個事件。用巴迪歐的話來說,事件是 “正在生成并隨時變動的張力關(guān)系”。《長城》作為一個事件的出現(xiàn),含有對當下固有狀態(tài)的打破和變動,可以檢驗或者探測出中國當下的審美趣味取向和復雜的情感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而對《長城》的各種評說就說明了這一點。張藝謀的《長城》或許真的是在以吃螃蟹的勇氣開拓出以電影走向世界并進行中國文化輸出的第一步,但愿在不斷摸索的過程中能夠建構(gòu)起真正基于中國審美經(jīng)驗和敘事模式上的美學風格。
強東紅(咸陽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在當下社會,審美與資本主義的合謀已經(jīng)越來越成為一種常態(tài)了。根據(jù)布爾迪厄的觀點,資本主義與審美并不敵對,只有藝術(shù)越遵循美的規(guī)律,越顯得美,越顯得自然而然,藝術(shù)的內(nèi)容與形式越是完美統(tǒng)一,就越能吸引觀眾,也就越有市場,資本就越有利潤可賺。對于與資本運作密切相關(guān)的影視藝術(shù)來說,這一點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導演和編劇在美學和藝術(shù)方面應該懂行,從而在對人物的心理的細膩變化的把握、人性的復雜性的充分展示上,才會更為到位。我覺得韓片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比如《healer》和《洛城生死戀》等都體現(xiàn)出對世界經(jīng)典文藝作品的爛熟于心,并在鏡頭剪裁、情節(jié)設置和制作臺詞上,進行點鐵成金和脫胎換骨的再創(chuàng)造,并且在商業(yè)運作上大獲成功。反過來看《長城》,就覺得在文化上有所欠缺,如對饕餮形象的理解,就顯得非常無知。饕餮的文化意味,絕不是看上一千多張圖片就能領(lǐng)會的。我覺得中國的導演和編劇在文化知識和藝術(shù)修養(yǎng)上,還是有進一步充實和提高的空間。電影必須符合美學規(guī)律,展現(xiàn)出來豐富的思想意蘊和歷史意味,才可能讓觀眾喜歡,才會有更高的和穩(wěn)定的票房收入。只拍一次性消費的片子,在獲取資本利潤上所冒的風險可能會更大。
連晨煒(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電影公映后不久,面對評分網(wǎng)站上不斷走低的評分,《人民日報》公眾號發(fā)文批評豆瓣網(wǎng)友給《長城》的低分是對中國電影的傷害,然而到了晚上,在公眾的普遍質(zhì)疑下又發(fā)了另一篇推文說要有容得下一星的勇氣。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主流媒體的聲音是分裂的,政治介入藝術(shù)的邊界在哪里。另外,我還注意到今年電影票房的增長沒有達到年初預期,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即將迎來拐點。這也說明了今天的觀眾已經(jīng)越來越理性,單純依賴聲光效果和明星加盟的制作方式不一定就能夠獲得票房的成功,這反過來也會促使電影制作人思考如何實現(xiàn)藝術(shù)性和商業(yè)性的平衡。
王杰:《長城》這部電影已不僅僅囿于其藝術(shù)性的層面,而是審美資本主義時代中的一個文化事件。我注意到了主流媒體的直接介入,其實以前電影盡管也有評價方面的分歧,但官方不太直接介入。而對于《長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等多次發(fā)文,張揚其形塑的中國文化信心,展演出不同于民間的評價維度,在我看來并無必要,顯得沒有自信。
對于《長城》,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比如審美資本主義的背景、后殖民主義理論的角度以及神話學的角度。具體而言,包括饕餮在中國的民間文化里是怎樣的一個東西,都值得細究。饕餮這個東西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是神獸,雖然貪吃,但正是通過強大的吞吐能力,它具有將壞的事物轉(zhuǎn)化為好的事物的轉(zhuǎn)換機制。而張藝謀只是把饕餮作為一個怪獸和惡魔植入中華文化的框架中去,有將中國文化妖魔化之嫌。據(jù)說《長城》用的是中國的資本、美國的編劇,張藝謀的導演權(quán)被極大地削弱,所以有人戲說“張藝謀死了”,從美學的角度看的確如此。
在文化輸出問題上,“走出去”和“如何走”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文化事實。在《長城》的文化輸出中,我認為張藝謀缺乏知識分子的情懷和立場,被大寫的文化輸出和消費主義邏輯所役使。在審美資本主義或文化經(jīng)濟時代,中國其實擁有很好的“走出去”的機遇,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現(xiàn)在文化走出去方面,有點亂了方寸。激進的需要將真實的需要遮蔽了,這是一個需要多加思考的問題。
當然,主流媒體對影片的認可主要是因為電影表達了中國文化的某種價值觀,諸如為了國家犧牲個體的集體主義精神。但正如本雅明所討論過的一個很重要的美學現(xiàn)象,叫做政治的審美化,盡管這是一種事實,但仍然潛藏著某種危險性。美學在今天或者說在審美資本主義時代,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正價值。“美”在審美資本主義時代是一個多義的存在,在其具體的語境中,“美”的意義才有可能顯現(xiàn)出來。在此種意義上,張藝謀和李安對于中國文化符號的表現(xiàn)真的值得比較。李安反思美國當代的問題,批判性很強,而張藝謀恰恰是迎合現(xiàn)在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這包括迎合資本的需要。
在我看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在美學上。張藝謀其實心存幫助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好意愿,但他沒有好的idea,找不到中國文化有當代普世意義的idea,于是草率地借用好萊塢的idea就以為可以拍當代電影了。類似的事情時常發(fā)生。所以我覺得中國文化要走出去,現(xiàn)在最大的困境就在于,如何富于智慧地運用中國的美學,尤其是,我們?nèi)绾问怪袊糯軐W智慧與現(xiàn)代情境相結(jié)合,從而激活其強健的基因。做不到這一點,中國文化是很難在真正意義上“走出去”的。此外,電影作為一門表現(xiàn)性藝術(shù),必須充分考量它所表現(xiàn)文化的核心價值。比如,對于貪婪的恐懼,對于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的稱頌,在西方和在中國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深層內(nèi)涵和情感邏輯。因此,我們就要好好考慮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