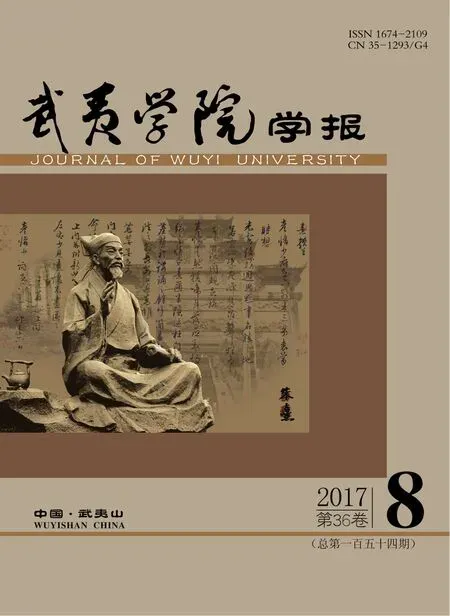民主轉型的新路徑:結構分析與戰略選擇的結合
郭良坦
(天津師范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天津 300387)
民主轉型的新路徑:結構分析與戰略選擇的結合
郭良坦
(天津師范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天津 300387)
民主轉型研究是比較政治學中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主要存在著兩種研究理論:結構分析理論和戰略選擇理論。前者運用結構——功能的分析范式,強調宏觀條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后者則強調政治精英的戰略選擇及其他微觀過程性因素對民主轉型的作用。這兩種理論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歷史時期對于解釋民主轉型各有特色和優勢,但二者無論在現實還是在理論上均存在一定的解釋困境。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而構筑結構——精英選擇的理論模式則非常必要,民主轉型正是結構條件下政治行為者戰略選擇的產物。
民主轉型;結構分析;戰略選擇;結構——精英選擇
民主化浪潮于20世紀初興起,不僅重塑了世界政治體系的格局,而且促進了學界對民主轉型理論的深入研究。新興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推行工業化戰略,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等結構性條件為民主政治的轉型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民主轉型研究的結構分析理論由此誕生。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興起后,后發國家的民主轉型研究則更多地關注精英之間的策略互動,形成了以微觀政治過程為研究重點的戰略選擇理論。然而在民主轉型的研究中,結構分析缺乏對行動者行為過程的研究,而戰略選擇分析又缺乏對結構約束功能的關注。因此,結構——精英選擇這種融合性的方法論就成為了更加適宜的研究視角。
一、民主轉型的內涵
民主轉型理論由羅斯托 (Dankwart A.Rustow)首創,他在1970年發表的一篇名為《民主的轉型:一個動態模型》的文章中建立了民主轉型的“動態模型”,用以敘述和解釋民主轉型的路線、過程及可能的結果[1],奠定了民主轉型的理論基礎。一般而言,現代政權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和民主(democracy)。三種政權之間的相互轉換就是政治轉型,而民主轉型就是其中的一種特殊方式。為了更好地理解民主轉型的內涵,有必要厘清政治轉型和民主轉型的區別。
政治轉型(political transition)就是從一種類型的政治體制向另一種類型的政治體制轉變。政治轉型通常有起點也有終點,如從極權主義轉變為威權主義或民主,從威權主義轉變為極權主義或民主,從民主轉變為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等,都可稱之為政治轉型。“若沒有政體性質的變化便稱不上政治轉型”[2],所以,按此邏輯演化,政治轉型必須是政權類型的轉變,而其他類型的轉變,如從邦聯制變成聯邦制、從一黨制變成多黨制和從總統制變成內閣制等都不是政治轉型。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就是由非民主的體制轉變為民主的體制,即特指以民主政體為目標的政治轉型,其外延比政治轉型少得多。[2]由此推之,從民主政權向其他類型的政權形式的轉變并不是民主轉型,那種向非民主政權的回溯被稱為民主崩潰(democratic breakdown),例如德國魏瑪政權的崩潰、智利20世紀60年代的軍事政變導致的民主政權的崩潰、西班牙佛朗哥政權之前的民主政權的崩潰等等。[3]此外,從民主政體轉變到“更民主”的政體也不是民主轉型。民主轉型不是“更民主”的意思,“更民主”是一種程度性概念,而非性質的轉變。因此要確定民主轉型的起點之前的政權是非民主的政體,才能夠符合民主轉型的內涵。所以,民主轉型是從非民主政體轉變成民主政體的過程,其內涵和外延的范圍都比政治轉型要小。
民主轉型的結果是民主政治,意味著憲政體制的建立,新的體制對公民社會與反對黨的容納,并舉行競爭性的以不確定性為特征的選舉。當政治行動者遵照一系列正義規則獲取政府職務和解決沖突,民主成為政治生活的常態特征,那么轉型就完成了。
二、民主轉型的理論范式
由于分類標準不同,現有的解釋民主轉型的動因被分為不同的維度,結構分析理論和戰略選擇理論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種研究范式。結構分析理論建立在“民主的實現需要一定的條件”的邏輯起點之上,側重考察宏觀歷史結構。而戰略選擇理論則重視政治過程的分析,側重考量微觀政治行動者的策略選擇。
(一)結構分析理論
結構分析理論主要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去分析民主轉型的先決條件和民主制度的發展過程,認為對政治轉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狀態、階級力量對比和外部環境等結構性因素。
由于受到現代化理論和行為主義的深遠影響,結構分析理論在具體論述民主轉型的相關問題時較多采用“結構——功能”的分析視角[4]。其邏輯起點是:民主政治的實現存在一定的結構性條件,不同的結構在推動社會整體進步的過程中發揮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結構性變量與民主轉型的關系也不同,因此,結構分析理論又衍生出了多種分析模式。首先,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分析模式。該模式將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民主轉型的決定性因素,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民主轉型越容易實現。李普賽特(Lipset)通過對50個國家的樣本分析發現:“一個國家越富裕,就越有可能實現民主”[5]。其基本的分析邏輯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帶動了財富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公眾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而影響了公眾的政治參與行為,也影響了社會穩定程度,導致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進而使民主轉型的產生與發展成為可能。第二,以社會文化為核心的分析模式。該模式認為成熟的公民文化是民主轉型的基礎。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和維巴(Sidney Verba)將英國、德國、意大利、美國和墨西哥等5個國家的普通民眾的政治態度進行比較,認為民主政治過程的穩定性及有效性依賴于一定的公民文化[6]。只有在社會培育出公民文化時,民眾的文化需求提高,威權政府通過經濟發展已經難以滿足民眾的文化訴求,才為民主轉型創造了直接動力。第三,以公民社會為核心的分析模式。這種分析模式源自于對民主發展過程中階級力量的重視,但現代的階級力量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式微,因此轉向對次階級的社會力量即公民社會的分析。以多元利益集團為內容的公民社會通過提高公民的政治技能和效能、提供限制國家權力的基礎、構筑新的表達和傳遞利益的渠道等方式,實現民主的穩步前進。第四,以外部環境為核心的分析模式。該模式認為大國干預和諸多國際組織、國際條約等外部環境促使許多國家按照憲政民主的標準活動,如國際人權組織、國際人權大會和 《國際人權宣言》、《世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等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客觀上推動、維護了許多國家的民主進程。
(二)戰略選擇理論
戰略選擇理論是精英理論的一種運用,側重于從微觀的角度考察精英的互動策略,認為民主轉型能否實現取決于精英作出何種戰略選擇。這一理論范式除去結構因素的影響,主要關注民主轉型過程本身,將民主轉型看作是相關政治精英集團基于自身利益而產生的相互沖突、相互協調和相互合作的產物[7]。
戰略選擇理論主要從兩個維度分析民主轉型:轉型的開端和轉型的模式。第一,民主轉型總是以精英間的分裂為開端的。在民主化進程中,由于對民主轉型有著不同的動機、理念和目標選擇,原本整合在一起的政治精英會步入不同的陣營和派別。在對精英分裂的研究中,奧唐奈(O'Donnell)和施密特(Schmitter)將精英分為統治精英和反對派精英兩大派別,統治精英又分為強硬派和改革派,反對派內部又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8]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沿用了奧唐奈和施密特的分類方法,但他細化了強硬派和改革派的分類,將官僚、警察和某些強硬的媒體人歸類于強硬派,構成統治集團內的壓制核心;將政權內的一些政治家和國家機關外的資產階級等群體歸類于改革派。[9]在統治精英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會激發社會各組織擺脫控制、傾向獨立的動力,社會精英就會在某些方面通過組織等方式提高統治精英的控制成本,以使原有的統治在統治者看來不再值得,從而謀求轉型。
第二,民主轉型的模式是不同精英之間博弈的結果。在民主轉型進程中,不同派別的政治精英根據各自不同的力量基礎、利益要求以及特定的政治情勢制定他們的政治戰略,而不同的轉型模式就是不同陣營的政治精英之間合縱連橫的結果。亨廷頓 (Huntington·Samuel·P)根據各派精英不同的博弈方式而提出了民主轉型的不同模式:居于統治地位的精英迫于反對派精英的壓力而進行自我變革式的轉型;反對派精英通過革命等劇烈手段取代執政精英的位置實施置換式轉型;反對派精英與執政精英進行談判合作而實施移轉式轉型。[10]卡爾(Carl)和施密特(Schmitter)根據精英與大眾之間不同的互動關系而提出了四種轉型模式:一是協定型,即統治集團內外的各派精英經過協商讓步而達成各派都能接受的多邊合作協定;二是強加型,即統治集團內部的精英運用強制力量單方面促成政權轉變;三是改革型,廣泛動員民眾,以非暴力的方式迫使統治精英與民眾達成妥協,對現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且仍保有當前統治精英的地位;四是革命型,大眾被武裝動員起來,推翻現有政權。[11]由此可見,精英之間不同的博弈方式會產生不同的轉型模式。
三、民主轉型范式的融合
結構分析理論和戰略選擇理論分析民主轉型的視角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很強的解釋力。但也都存在著一定的理論困境,難以全面地解釋和預測民主轉型的全過程。因此,在民主轉型的研究中,比較理想的狀態是將這兩種分析范式有機融合,構建出結構——精英選擇分析的新方法。
(一)結構分析理論的困境
結構分析理論一味強調經濟、文化、環境等結構性因素的決定作用,而忽略了社會政治發展中的復雜性、曲折性和偶然性,最后必然陷入決定論的泥潭。[12]結構分析理論以已經實現民主化的西方國家經驗為基礎,選擇性地作回顧性的解釋,預設了一旦民主的結構性條件全滿足,則民主轉型自然會實現。但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現實層面,結構分析都面臨著一系列的解釋困境。從理論層面來講,羅斯托(Dankwart A.Rustow)認為結構性因素是民主轉型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換言之,具備了一定的結構性條件并不必然產生民主轉型。[1]亨廷頓也認為經濟發展不一定帶來政治發展和民主,恰恰相反,經濟發展會導致更高的政治參與要求,而如果現有的制度難以容納這些要求,就會使現有的政治系統不穩定進而使得現有秩序瓦解。[13]從現實層面來講,那些向民主體制轉型的國家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文化迥然、社會環境各異,社會結構方面差異巨大,結構分析理論參照西方模式所設定的政治發展道路遇到了極大的挑戰。比如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等地區一些比較富裕、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較高的國家中,貧富差距嚴重,經濟發展帶來的參與增長反而引發了政治秩序的不穩定,街頭政治盛行,民主政體崩潰;而那些由于缺乏相應的社會結構條件被認為最不可能發生民主轉型的國家如布隆迪,卻出現了一定的民主。結構分析理論面臨的這些困境,極大地削弱了經濟發展等結構性因素對民主轉型的解釋力。
(二)戰略選擇理論的困境
戰略選擇理論過分強調了政治精英的戰略選擇的地位,與結構分析理論相比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戰略選擇理論也面臨著理論與現實的解釋困境。從理論上來講,戰略選擇理論是一種微觀研究,它超越了宏觀結構分析,容易走向意志決定論的誤區:政治精英可以完全脫離現實條件的制約而任意選擇民主轉型的模式[4]。實際上,人們的利益不是抽象存在的,而存在于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之中,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認識也要受到一系列社會、歷史和文化環境的制約。此外,悖論是戰略選擇理論表現出明確的精英主義取向,為了保證締結協議獲得執行而限制大眾參與,所以協議是通過不民主的方式在寡頭化權勢集團之間建立的制約機制。這些寡頭集團在缺乏競爭和民主監督的情況下制定了政策議程,扭曲了公民原則。[14]從現實上來講,戰略選擇理論對于東歐國家的民主轉型缺乏解釋力,在東歐民主轉型中,邏輯上的戰略選擇模式與事實相去甚遠,這些國家民主轉型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受蘇聯解體和西方國家對其強行注入 “民主”影響。總而言之,政治精英的策略選擇、行為方式和動員能力很大程度上會受到社會結構條件的限制,而戰略選擇理論恰恰忽略了這一現實情況。
(三)結構——精英選擇的分析路徑
鑒于結構分析理論和戰略選擇理論固有的理論困境,在民主轉型的研究中,比較理想的狀態是將這兩種分析范式有機融合,構建出結構——精英選擇的新方法。該方法一方面認可結構分析理論所主張的結構性因素對政治精英獨立活動空間的限制,另一方面承認戰略選擇理論所主張的政治精英即時性和意向性的行為獨立于社會結構的特性。認為經濟發展、公民文化和社會環境等各種結構性因素通過影響政治精英的力量對比和行為選擇,從而影響民主轉型的發生與發展。
結構——精英選擇的分析路徑是對經濟發展水平、公民文化、國家制度與精英選擇的綜合考察。亨廷頓就傾向于對民主轉型的動因進行綜合性的解釋,他認為民主轉型的動因在不同地區的不同歷史時期差異巨大,不存在普世而又可以解釋所有民主轉型的自變量。所以,他對近代以來的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動因做了不同的區分:20世紀前20年開始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主要在于不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老牌帝國的解體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等結構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其動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結構性因素,即二戰的戰勝國與先發民主國家在全球開展的民主化運動;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其動因綜合性較強,包括合法性、經濟發展、示范效應、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的行動以及宗教變革等等。[10]亨廷頓在對現代民主轉型綜合性動因的分析中,尤其強調經濟發展與精英選擇的重要性,認為二者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相輔相成,“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現實”[13]。在他看來,結構性因素為民主轉型提供了可能性,而要想真正實現民主體制還必須依賴于政治精英的現實選擇。
海哥德 (Stephan Haggard)和考夫曼 (Robert R.Kaufman)認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為統治精英提供績效合法性,能夠強化其統治,而突然性的經濟危機則會沉重打擊居于統治地位的精英,甚至會促使其政權瓦解從而產生政治轉型的可能。[15]在他們看來,影響民主轉型的因素主要是環境條件和政治選擇,環境條件即為結構性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整合程度、政權危機等,政治選擇就是領導者根據不同的環境變化與互動博弈而進行的制度設計。任何國家的民主轉型都是由各種因素進行不同程度組合的結果,每一種因素會影響政治體系的不同結構部分,任何單一的結構性因素或意志因素都不足以推動民主的整體發展。同時,政治精英對民主轉型路徑的選擇并非是無限可能的,而是基于一定的結構性因素的組合為其政治選擇創造的特定的條件。
民主轉型是在社會結構和精英選擇的雙重作用下發生的。客觀的結構性條件的出現并不代表民主制度一定會出現,但為民主轉型提供了可能性,限定了政治精英戰略選擇的范圍。社會結構的不斷變化創造了可供政治行動者選擇的政治機會,從而為民主轉型提供了必要的動力與契機。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一些南歐國家的民主化運動就是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基于有利的社會結構條件而領導的結果。其發生邏輯是:經濟的發展導致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社會結構不斷變化,進而出現不同階級或利益集團力量的此消彼長,為爭奪有限的資源,不同階級和利益集團之間不斷進行斗爭。一方面,為了適應不同的斗爭形式,統治精英會根據不同的社會條件在自己可控的范圍內調整統治規則和形式,使得民主轉型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利益團體之間的斗爭培養了體制外反對精英的成長,并且使得統治集團的社會控制成本增加,出于一種理性的選擇,統治精英會選擇不同的統治策略,或改革、或協商、或武力鎮壓。換言之,社會結構對民主轉型的影響是通過精英人物的行為選擇來實現的,而政治精英的戰略選擇對民主轉型的路徑和結果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因此,結構——精英選擇的分析路徑更加符合現代民主轉型的真實模式。
四、結語
民主轉型是一個國家從非民主體制轉化為民主體制的過程,是民主化的重要組成結構。每一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轉型國家往往經歷著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發展結果。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民主轉型的發生與發展過程無疑受到社會結構和政治精英的雙重影響,是政治精英在對社會結構形勢作出判斷后而進行博弈和戰略選擇的結果。社會結構的變化為民主轉型提供了動力和契機,但民主轉型的具體進程則無疑要更多地受制于政治精英的理性選擇。此處所講的理性選擇從統治精英的角度來講是指對統治成本大小的考量,對體制外反對派精英來講則是對反抗成本的衡量。當然,民主轉型的具體過程并非單一的線性的變化模式,其邏輯起點可能是經濟發展促進精英力量的變化,也可能是精英實力的變化促進經濟發展,或者在經濟、精英等變化的過程中,社會文化不斷在其中發酵,與各種不同的結構性因素發生化學反應,進而共同推動民主轉型得以實現。總之,在對現代民主轉型模式的分析中,結構分析理論和戰略選擇理論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單純的從結構性因素或戰略選擇角度出發去分析民主轉型都是不充分的,必須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唯有如此,民主轉型才有可能得到更充分、更合理的解釋。
[1]RUSTOW D A.Transformation to Democracy:a dynamic model[J].Comparative Politics,1970(2):337-363.
[2]吳文程.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45,46.
[3]包剛升.民主崩潰的政治學:選民分裂、政治制度與民主崩潰[J].公共行政評論,2013(5):169-177.
[4]高春芽.社會結構與政治行動者之間的張力:方法論視野中的民主轉型研究[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2):115-124.
[5]西蒙·馬丁·李普賽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M].張紹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7.
[6]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438-460.
[7]陳堯.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民主轉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6.
[8]吉列爾莫·奧唐奈,菲利普·施密特.威權統治的轉型:關于不確定民主的試探性結論[M].景威,柴紹錦,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5-17.
[9]亞當·普沃斯基.民主與市場:東歐由于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改革[M].包雅鈞,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47.
[10]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M].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153,46-54.
[11]CARL T L,PHILIPPE C S.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1(2):269-284.
[12]郭定平.論當代政治轉型理論的背景與邏輯[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7(3):56-65.
[13]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23,380.
[14]GRAEME G.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Elites,Civil Society and the Transition Process[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53.
[15]斯迪芬·海哥德,羅伯特·R考夫曼.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M].張大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45-75.
Searching for a New Path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the Combination of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Strategic Choice
GUO Liangt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
Stud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 a unique research fiel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There are mainly two kinds of research theories:Paradigm Based on Structure Analysis and Paradigm Based on Strategic Choice.The former is used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aradigm,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The latter emphasizes the initiative of the political elit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trategic choice and other micro process factors on the role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These two theories have different advantages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but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both reality and theory.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bine these two paradigm and constitute a new model that consisted of elite selection and structure,and regar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 as the product of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political actor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tructure.
democratic transition;paradigm based on structural analysis;paradigm based on strategic choice;paradigm based on struc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
D082
A
1674-2109(2017)08-0009-06
2017-03-07
郭良坦(1991-),男,漢族,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外政治制度研究。
(責任編輯:陳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