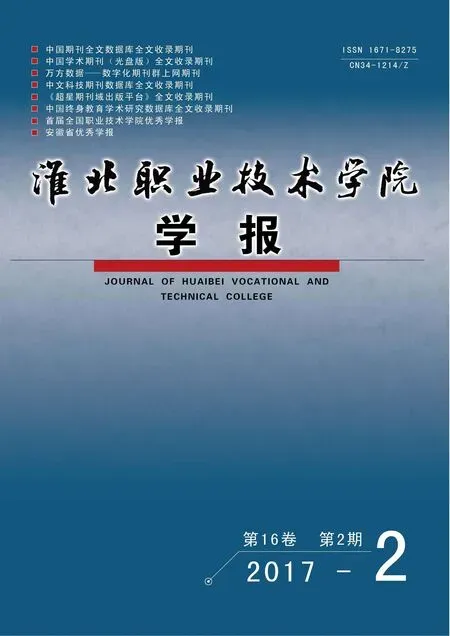淺析《林海雪原》對革命的合法性論證
黃夢蕓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淺析《林海雪原》對革命的合法性論證
黃夢蕓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革命通俗小說”《林海雪原》作為“十七年文學”的一部經典作品,雖在政治上沒有進入主流,但卻擁有廣大的讀者,是一部不容忽視的佳作。小說給革命戰爭賦予了浪漫色調,并通過“階級”這一想象共同體、革命本體化邏輯和狂歡化敘事這三方面得以完美呈現。
《林海雪原》;想象共同體;本體化;狂歡化
基于文學創作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契合,作品需鮮明反映時代精神面貌這一觀念,通常我們會把“三紅一創”,即《紅巖》《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認為是“十七年文學”中成就最高的作品,然而,一些“革命通俗小說”在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迎合與傳播上也占具了不容忽視的地位。其中,曲波創作的《林海雪原》最具代表性,這部小說的創作源于作者的親身經歷。小說中關于革命的敘述處處彰顯著浪漫性因子,將革命浪漫化自然是為了沖淡我們民族對于革命的“黑暗記憶”,同時,也是對革命所做作的合法性論證。
一、“階級”這一“想象的共同體”之于革命
美國學者安德生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體:民主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對“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概念作了闡釋:“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接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1]。基于這樣的共同的想象,通過如此想象的思維和方式,我們可以對不同的共同體進行區分,同時可以更好地加深不同共同體內部的團結。由這種想象方式的相關話語構型所建立起來的民族,雖然在內部會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但通過想象所建立起來的這種民族友愛關系總會“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愿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象——去屠殺或從容赴死”[2]。“民族被想象成為一個共同體,即使在民族內部存在著一些不公平與剝削現象,平等的同志還依然被認為是民族內部的主旋律。”[3]將“民族”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置換到“階級”的想象中也是如此,“階級”這一“想象的共同體”對于革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林海雪原》中革命者對黨和人民群眾衷心耿耿,為革命事業不惜犧牲寶貴生命,其堅定意志充分建立在對共產黨這一“階級”的想象的話語構型之上。作為“階級”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的成員,他們在思想上達成高度共識,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與此同時,對立的階級——敵人也必然形成。這樣一來,在明確了目標和對手后,對于革命的進程勢必起到推動作用。在小說中,楊子榮將黨與敵人鮮明對立起來,“這仇人的概念,在楊子榮的腦子里,已經不是一個楊大頭,而是所有壓迫、剝削窮苦人的人。他們是舊社會制造窮困苦難的罪魁禍首,這些孽種要在我們手里,革命戰士手里,把他們斬盡滅絕”[4]183。在這里,仇人的概念由楊大頭這個個體的概念上升到一個群體的概念,“他們”“我們”明顯呈現出“二元對立”。楊子榮對于“階級”的區分有清晰的界定,作為敵人這一共同想象體對立團體——黨組織下的一員,楊子榮表示:“要把階級剝削的根子挖盡,讓它永不發芽;要把階級壓迫的種子滅絕,叫它斷子絕孫”[4]183-184,這樣的“想象方式”始終支撐著楊子榮將“剿匪”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想象的共同體”內部成員對于自己的信仰是矢志不渝的,工作隊同志們在面臨匪首侯殿坤、馬希山的殺害時,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信仰,“他們高呼共產黨萬歲!人民解放軍萬歲!向同志們宣傳,不要受騙,不要害怕,要打倒反動的革命黨匪徒”[4]382。由此可見,“階級”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的建立對于革命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二、革命浪漫性想象下的“本體化”邏輯
革命歷史小說能將革命的浪漫性想象充分地展現出來,具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功能,“本體化”就是對革命的合法性進行有力論證的重要體現。“文學的敘事是用話語虛構社會生活事件的過程,敘事的內容是社會生活事件,即人的社會行為及其結果,其價值就在于顯示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過程和意義。”[5]153革命勝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并且永無止盡,局部的勝利不過是斗爭的開始,緊接著還會有更大規模的戰斗,而革命取得大規模勝利之后,還需時時保持高度的警惕,為即將打響的革命隨時做好準備。因此,革命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充分體現出“本體化”這一在今天看似荒謬的邏輯。
在《林海雪原》的創作中,遍布了這種革命“本體化”的圖景。從整個故事情節來看,革命斗爭這一線索貫穿始終,且絲毫沒有表明革命會有終結的時候。由團參謀長少劍波、偵察英雄楊子榮、戰斗英雄劉勛蒼、攀登能手欒超家等組成的小分隊自成立那天起,就肩負著“剿匪”的重任。第一站是乳頭山,消滅了勢力強大的許大馬棒。可是這并沒有意味著革命的勝利,而只是革命的開始,戰士們時刻都得做好戰斗的準備,隨時待命。在少劍波的策劃和指揮下,革命戰士依次消滅了座山雕、九彪和馬希山三股國民黨殘余勢力。盡管如此,也只能說明由少劍波帶領的小分隊本次革命任務了完成,并不意味著革命已畫上了句號。小說的結尾處:“新的斗爭開始了!……”這是革命的“本體化”邏輯: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永遠革命的文學版的再現。
三、“狂歡化”敘事對于革命話語的建構
“狂歡化”是巴赫金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意思是對刻板的、等級化的日常生活秩序的顛覆,其特征是一種全民化的縱情表演。“狂歡化”的理念對于革命話語的構建提供了依據和模本,伴隨著革命而來的是戰爭,而戰爭就必然意味著流血犧牲,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在“狂歡化”之上的關于革命的浪漫性想象對消解革命暴力、血腥的一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狂歡文化本身具有全民參與性、自由平等性、顛覆性和再生性,是一種與理想,與生活相平行,不交融的游戲式的生活理念。在革命歷史小說中,當革命被賦予了浪漫色彩,具有了神圣化、樂觀化、理想化時,通過浪漫性想象建構起來的革命話語能夠使人們產生高昂的戰斗熱情,全身心進行革命斗爭,懷著對革命美好的愿望,將內心深處積蓄已久的狂熱和狂情充分地展現出來。
“狂歡化”敘事對于革命話語的建構體現在情節的敘述上。《林海雪原》故事情節曲折離奇,富有傳奇色彩,描繪了一幅第二世界和第二生活的圖景。小說的開篇,我們看到的村莊是一片令人膽寒的“觸目驚心的慘狀”:“村中央許家店門前廣場上,擺著一口鮮血染紅的大鍘刀,血塊凝結在刀床上,幾個人的尸體一段段亂雜雜的垛在鍘刀旁,有的是腿,有的是腰,有的是胸部,而每個尸體卻都沒有了頭。……狼藉地倒著二十多具被害者的遺體,有老頭,有小孩……”[6]5-6。群眾被殘忍殺害的慘狀是作者從敘事層面上使這群匪徒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的有力論證。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每一次剿匪行動都是一次偉大的狂歡活動,敵我雙方的暴力拼搏彰顯出我軍英雄人物的大無畏精神。
此外,關于巴赫金對于狂歡節的描述:“狂歡文化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慶典文化,是一種非常強的生命力。狂歡節是一種全民參與的活動,沒有邊界,無論高低貴賤都可以自由地參與其中”[7],這一分析也完全適用于革命戰爭的敘事,激烈的戰爭場面最能表現出這種狂歡的意味和效果。在革命小分隊與匪徒九彪的交鋒中,敵我雙方進入對峙的局面,我軍前方指揮員和小分隊、民兵陣容、醫療兵等形成壯闊的狂歡廣場:“劉勛蒼小隊負責在山神廟前布火、擺雷”“孫達得、馬保軍負責四挺機槍的安排”“李勇奇的民兵,主要負責外圍捕捉”,戰斗在我方謹慎而又輕快的節奏中以勝利告終,軍民進入了一場狂歡:“每人舉一塊燃燒正旺的大松明子,照得滿屯通紅,扭著,唱著,廣場上又燒起歡樂的篝火。直達通宵。”
《林海雪原》通過“階段”這一“想象的共同體”、革命的“本體化”邏輯、“狂歡化”敘事建立起來的關于革命的合理化論證,給革命蒙上了一層神圣的外紗,從而消解了革命在現實世界中殘酷性的一面,使每個個體所遭遇的流血、死亡等殘酷事件被給予了合法性的解釋。這樣一來,革命成為人人心向往之的事,革命戰爭的痛苦情然隱退,彰顯出一種革命的快感。
[1] 武永東.蘇格蘭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15.
[2] 王宗禮.論多族群背景下的國家建構[D].蘭州:蘭州大學,2005.
[3] 陳思.比較史學視野下《想象的共同體》[J].青年文學家,2016(9).
[4] 曲波.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5] 姜輝.紅色經典的模式化敘事研究·革命想象與敘事傳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王作東.曲波在齊齊哈爾創作《林海雪原》的前前后后[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015(6).
[7] 吳雯.“2008奧運”中國人的狂歡節:以巴赫金狂歡理論為視角[J].新聞世界,2008(11).
責任編輯:之 者
2017-01-03
黃夢蕓(1993—),女,貴州安順人,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
I247.4
A
1671-8275(2017)02-00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