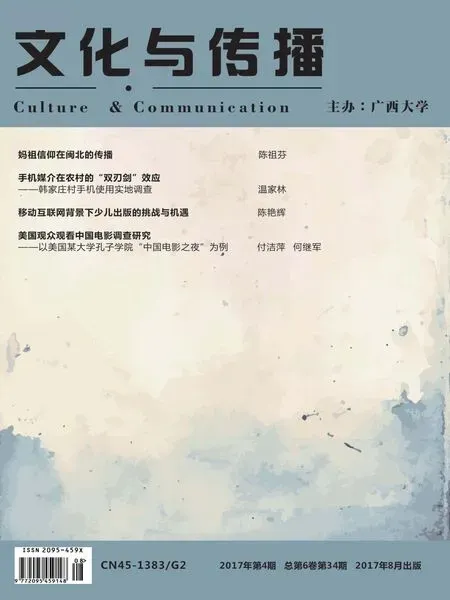孔孟荀“罵詈”的原因探析
姚海濤
引言
西哲海德格爾有一個關于存在與語言關系的著名論斷:“存在在思想中達乎語言,語言是存在之家。”[1]368人作為一種存在,注定只能通過語言這一特定方式來完成對世界的感知、參與。這也是人“宿命”式的存在方式。這一論斷代表了西方哲學思潮的語言轉向,后成為哲學視域中的一個重要命題。維特根斯坦也曾說過:“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2]15他將語言方式定義為生活方式。語言在人的表達、溝通、接受、反饋等方面的不可或缺性構成了人在世的方式。
在中國先秦時代的經典文本中也有關于語言的修飾、說出時機、言與默的關系等多方面的思想內容。如言與默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言說”方式。《詩經?小雅?賓之初筵》中就有:“匪言勿言,匪由勿語。”[3]245《周易?系辭下》中也有“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4]258語。《論語?為政》中孔子說過“慎言其余”[5]59“予欲無言”[5]168等。《孔子家語?觀周》中的金人背后有銘文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6]128《道德經》有“大音希聲”[7]228“不言之教”[7]237“知者不言,言者不知。”[7]280《莊子》中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8]320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具有往不可返、覆水難收的特點。無論是西方哲學還是先秦儒家、道家,其對待語言的思想傳統具有某種意義的一致性。重言、慎言、不發傷人之言成為中西方哲學一個根深蒂固、源遠流長的傳統。罵詈可歸為語言的一種,但它是語言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也是一種極端表現形式。如果將罵詈與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視界聯系起來,無疑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人人都有罵人的經驗也有被罵的經歷。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語言現象,罵詈有著與人類語言同樣久遠的歷史。人類歷史上的“首罵”源于何時又出自何人之口早已不可考。《詩經》中已有大量罵天、罵人等詩句表達。《說文解字》中這樣解釋罵:“詈也。從網,馬聲。莫駕切。”[9]155《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中“罵”有如下兩個意思:“一是用粗野或惡意的話侮辱人;一是斥責。”[10]865一般情況下,我們將惡語加于人視為“罵”,而詈則是罵的書面語。如果將罵詈行為視為濫施淫威和無道德修養的失和、失態,將那些罵詈用語視為語言禁忌,那么罵詈行為就沒有任何正面意義與價值。但我們更應該看到罵詈與卑鄙、骯臟、齷齪語完全不同。
罵詈是“不言”之“言”。罵詈是跳脫出正常溝通交流軌道的一種獨特的言論與思想表達。罵詈是不言之“默”,是在根本問題上的“默示”。它建立在對話雙方正常溝通被打破的特殊情況下,無進一步交流之必要與可能基礎之上。甚至罵詈者之間由于思想差異巨大,也不處于同一“時空”維度,是無法溝通之后的“默”。甚至連罵詈的目的也是“默”。罵詈有使對方噤聲,達到“默”的狀態,以防止邪說異端污染、誤導甚至蠱惑大眾,有利于屏蔽有害信息的傳播,造成隔離、隔絕的默的狀態。但不可否認的是,罵詈本身還是體現出了思想專制與語言暴力的傾向。罵詈是“不辯”之“辯”。罵詈之于辯論這種思想碰撞形式,更像是無理之“鬧”,已經不是語言的辯論,更像是一場以言語為利器的野蠻廝殺。當然,罵人也可以不僅僅是個體的情緒化表達,而且還可能出于某種理論上的考量,甚至有深刻的內在理路依據。也即罵詈可能有其正面意義與價值。
在先秦儒家的思想視域中,嘻笑怒罵皆成文章。罵詈有理、有故、有據、有意義,甚至構成了罵詈的思想視界。在這里,罵詈無關個人品行,甚至也無損個體大雅,反而可以體現個性特點、個人氣象。如果將先秦儒家的罵詈行為作為一種普通語言現象與其學派特性、語言風格、心理機制、道德觀念等實現視界融合,打破整體性與系統性的入思向度,重新對先秦儒家文本進行觀照,就能尋繹出罵詈的邏輯基點,從而窺見其文化鏡像及成因,開掘出先秦儒家罵人的背后玄機及被遮蔽的理論意義。甚至透過他們的罵詈論域,還能體味到其社交技巧、語言藝術、思想語境等多方面豐富的意涵。
一、孔子之“和藹”罵詈:吹面不寒楊柳風
儒家向來以強調個人道德修養著稱,但先秦儒家卻將罵詈視為一種言而當、默而當、罵而當的正常語言現象。翻檢先秦典籍,我們發現儒家代表人物均有罵詈行為。儒家之罵基本是非罵不可,不罵不足以辨曲直,不罵不足以別是非,不罵不足以清門戶。孔孟荀“罵詈”風格各不相同,其異如面,其反映的思想視界也略有差異。
先從孔子談起。孔子雖說過“一朝之忿,忘其身,非惑與?”[5]131的話,強調“訥于言而敏于行”[5]73但是他也說過“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5]69。所以孔子罵詈也就毫不奇怪了。孔子罵詈指向對象非常廣泛,可以說無人不可罵,大致可分為政治人物、孔門弟子、朋友等。《論語》《孔子家語》等相關典籍中的孔子是一個和藹而明快、溫潤而含蓄的學者形象。宋代儒者將其評價為“無跡”,是“元氣”,是“明快人”,是“無所不包”之天地。所以孔子之罵詈亦當如是觀。觀其罵詈,語氣“和藹”,罵詈方式、路數因人而異。可曰無罵不精當,無罵不精彩。
孔子罵詈有其深刻的春秋末年之時代背景因素與儒家根本思想作支撐。孔子對其是否罵詈是由儒家根本價值觀念“仁禮合一、仁為禮本”來衡定,具有深刻的倫理判斷于其中,而非純任個人私心。孔子平時根本無暇對任何人進行評論,有“夫我則不暇”[5]147“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5]155的說辭。凡是孔子所評價過的歷史人物“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5]155孔子之評論,或詆毀或贊美,必須是經過夏、商、周三代嚴苛的“直道而行”道德標準考驗衡量之后而做出,決非隨意隨性而為。
1.罵詈管仲:倫理判斷與歷史評價的合一
孔子對政治人物的罵詈主要涉及到管仲、季氏二人。孔子對管仲既有罵詈之譏,也有“如其仁”的高度評價——“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如其仁!”[5]144“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5]144這里涉及到對歷史人物的理性評價問題。孔子在進退兩難的評價中包含了倫理判斷與歷史判斷的合一,社會公德評價與個人私德評價的合一,仁與禮的合一,德與才的合一等諸多復雜的理論標準。
孔子在評價管仲時有“器小”[5]66“不儉”[5]66“不知禮”[5]67之譏。從這些評價用語基本可以認定評價中含有罵詈語,當屬罵詈范疇。儒家向來重視私德與公德的統一。從倫理判斷角度觀之,管仲在私德方面確有所欠虧。“器小”朱熹解釋說“言其不知圣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5]66管仲有“三歸”,一人兼數事,極其奢侈。再者在公德方面,管仲與邦君一樣“樹塞門”“有反坫”有僭越禮儀之嫌,正所謂“不知禮”。無論是公德還是私德方面都落人話柄。
孔子向來提倡王道而非霸道。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齊國春秋第一霸主地位。但在孔子看來,管仲政治統治上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聯系到《荀子·仲尼》中的“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11]54就不難理解儒家自孔子到荀子都對此事耿耿于懷了。因為管仲政治上“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11]55,他沒有把政治教化當作立國之本,沒有達到崇高的禮義政治境界,施政也沒有讓民眾心悅誠服,只是在策略、方法上取得偶然的、暫時的成功,而非政治大本上的成功。這些均可與《孔子家語·致思》中子路問孔子“管仲之為人何如”[6]83一事相印證,也可能為同一事的不同記錄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對管仲的“如其仁”“仁也”的稱贊之語讓人有些措手不及。從工具理性的視角來看,管仲確實是一代名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所以必須給予歷史地位的確認評價。畢竟“管仲才度義”,其才智勝過了道德,建立了不世之功勛。所以孔子對管仲既有罵詈,又有稱贊也在情理之中。類似矛盾的心態其實反映的是孔子對人全面、廣闊而辯證的評價標準。既有價值理性又有工具理性的考量,既關注政治人物的個人私德更注重其社會公德、歷史貢獻,將評價置諸宏大的歷史場域之中,又安放于當時歷史時空背景之下。在具體評價中也是以其仁禮合一、德才合一之視域與立場,既以外在之禮來衡定,又涉及內心之仁的考量,實現了倫理判斷與歷史評價的合一。
孔子評價季氏八佾舞于庭之時,說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5]61的經典罵詈語。季氏以大夫身份而僭用天子之樂,這是嚴重違反禮樂之事。孔子“深疾之”[5]61。在這里,孔子罵詈的標準在于個體行為是否合于周禮。孔子有納仁入禮、仁為禮本的思想,所以有“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5]62之言。禮與樂是第二層次的外在標準,而最根本的第一層次的標準則是“仁”這一內在尺度。“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5]61也成為后世罵詈文化中的經典語句。孔子對當時政治生態有過罵詈式評價。如當被問到“今之從政者何如?”[5]138時,孔子的鄙薄與不屑躍然紙上,“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5]138意思是說,咳,這班器識狹小的人算得什么?聯系到對管仲這個政治人物的全面評價,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對當時從政者的極度失望之情。與當時的從政者比較,歷史上的管仲足以稱得上是“如其仁”了。至少在孔子一系列評價標準中還是具備衡定資格,而當時器識狹小者卻根本無足道也。
2.罵詈學生:學而不厭與時常砥礪的合一
孔子作為一個教育家,素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育態度。當然,他對學生的罵詈也自然不可免,但大都充滿一團和氣,釋放十足善意。罵詈主要出于砥礪學生勤奮學習之意。在此,孔子主要是將學而不厭與時常砥礪合一,不斷催發學生積極上進、有所作為。針對學生的罵詈主要集中在宰予、仲由、樊須、冉有這四位弟子身上。如宰予(字子我)晝寢。孔子發現后,生氣地責備道,“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5]76“晝寢”在當時可能是懶惰不上進之人所為,而非君子所為,故有此深責之詞。并且他氣憤地說出了“于予與何誅”[5]76,對其失望至極,并得出了“聽其言,觀其行”評價人物的經典標準。宰予位列孔門四科之賢者,是孔門高足。可見嚴師出高徒,此言不虛。對于另一位高足弟子仲由(字子路),孔子曾以“野哉由也!”[5]134“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等評價,都是深刻地指出了子路性格中的弱點,可見孔子知弟子之深。孔子教育弟子要做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所以有了“小人哉,樊須也!”[5]134之罵詈。主要因樊須(字子遲)志向淺陋,不解孔門培養弟子重心不在稼穡,而在為政,而以“小人”評價點示、警醒他。對于冉有(字子有)這位高材生,因其在季氏那里從政,使季氏富于周公,但其心術不正而不知反求諸身,只知一味迎合季氏貪欲,不斷為其聚斂民財。所以孔子很生氣地宣稱與其斷絕師徒關系——“非吾徒也。”[5]120還與其他學生講“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5]12孔子經典罵詈還有記錄于《孟子》中的“始作俑者,其無后乎!”[5]191孔子對始作俑者尚且深惡痛絕,對于“民饑而死”的情況必定更加憤怒。在此罵詈語中,孔子將罵詈與家庭、血統相聯系,能起到震撼心靈的效果,也有醍醐灌頂之功用!
3.罵詈朋友:以禮為根據
原壤是“孔子之舊”,也就是孔子的同齡人兼朋友。朱熹認為原壤“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于禮法之外者。”[5]150在《孔子家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曾為原壤的母親主持過喪禮。子路曾以孔子說過的“無友不如己者”一語規勸孔子與其絕交。但孔子認為即使將原壤視為一個普通老百姓也應該去幫助他完成喪葬母親之事,何況是老朋友呢!對這位老友,孔子終生不棄。孔子為了盡力幫助原壤提高對禮的認識,提升自身素質,在“原壤夷俟”違禮之時,孔子教育他說“幼而不孫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5]150在這里,“夷俟”是蹲踞之意。他在等待孔子到來之時,竟然采用了蹲踞這種極不合當時禮法的方式,足以敗常亂俗,所以孔子非常不悅。孔子在這里用了“死”“賊”這樣的罵詈禁忌語來提醒這位故人,可見用心之重、用情之深。并且孔子還“以杖叩其脛”,罵詈這種動口行為有進一步升級為擊打行為的趨勢。孔子之罵詈均以時機化、境遇化的當場呈現方式展開,凸顯正常語言無法抵達之妙用。
二、孟子之雄辯式罵詈:風刀霜劍嚴相逼
與孔子和藹式罵詈不同,孟子的罵詈行為與語言風格打上了個人氣象的烙印。宋代儒者對孟子的評價是“有英氣”“有圭角”“秋殺盡見”“其跡著”,有“泰山巖巖之氣象”。所以孟子之罵詈亦當如是觀。如果說孔子的罵詈是“和藹”的,孟子就是秋殺式罵詈、雄辯式罵詈、高屋建瓴式罵詈。讀《論語》如沐春風,孔子亦然;讀《孟子》如聞戰鼓,孟子亦然。孟子為什么要罵詈?孔子所處的時代學派之間的對立、沖突還不甚明顯。及至孟子,情況急轉直下,仁義之道不彰,各種荒謬的學說、殘暴的行為屢見不鮮。這使得極具儒門擔當感,有“舍我其誰”大氣魄的孟子,舉起儒家仁義思想的大旗,鳴起罵詈的戰鼓,以語言為干戚,砍向那些異端學者與門派。用孟子自己的話說就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5]254孟子不是為了辯論而辯論,不是為了罵詈而罵詈,而主要是為了端正人心,破除邪說,抵制偏頗的行為,批駁錯誤夸張的言論,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遺志。但孟子的罵詈語言總是那么銳氣逼人,罵詈場景總是那么劍拔弩張。
孟子罵詈對象包括是兩類,一是無道國君,一是儒家之外的楊、墨學派學者。孟子對國君的罵詈仿佛刻意為之,極具批判色彩與力度。難怪一些封建帝王如朱元璋之流就很不喜歡孟老夫子。難怪近人覺得孟子身上透露出現代知識分子才具有的批判精神氣質。可以說孟子罵詈最多、最狠者當屬無道國君這一群體。他甚至說出了“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5]271這樣極具沖擊力與殺傷力的大逆不道之言。歷數那些被孟子“教訓”過的國君,古代有夏桀、商紂,當世則有梁惠王、滕文公、齊宣王等。如在與梁惠王初見之時,就出于“先攻其邪心”[11]304的需要,與其有了“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5]187的爭論。之后又有“賢者何樂”的辯論。在辯論中,孟子又祭出了《湯誓》中的革命誓言“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進而引出了孟子“與民偕樂”的政治主張。更有“不仁哉,梁惠王也!”[5]341這樣赤裸裸的罵詈。
對楊、墨學派的罵詈集中體現于“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5]253“禽獸”之罵詈可能會將孟老夫子的高大形象毀于一旦,因其有運用語言暴力之嫌。一方面說明孟子是真性情之儒者,其并不想偽裝成一個高大全的形象以示后人;另一方面,罵詈其實在罵詈之外。罵詈之言背后有理據,正所謂“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5]254人禽之辨是孟子理論的重要組成。“禽獸”一詞也在《孟子》中大量出現。雖然人與禽獸的差別就在于“幾希”。“禽獸”之罵能體現出人與動物強烈的對比感及由此衍生的狠毒的歧視與強烈的蔑視。孟子遮撥楊、墨的儒家立場豈能以近乎粗暴的語言表達以置自身于無理之境地?所以禽獸之罵背后定有深意。
與“禽獸”之罵相類似的還有“非人”“無恥”語。表面看去,這也是粗野的罵詈。“非人”“無恥”一詞直譯出來就是“不是人”“不知羞恥”之意,是極具殺傷力的罵詈語。如果基于孟子思想,對其進行學理向度的闡釋與解讀,“禽獸”也好,“非人”“無恥”也罷,決不僅僅是語言暴力這么簡單。孟子有“四心”“四端”“四體”之說。“四心”是人之所以為人之依據。如果不具備這“四心”,當然也就“非人”了。如果不是人,雖然表面上像個人的樣子,但內在與人無所同,那就混同于“非人”“禽獸”了。所以孟老夫子的“禽獸”罵詈,甚至可以不將其看作是罵,是基于人性善得出的一個小推論。“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5]221不是人,當然就是“禽獸”了。孟子還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5]328“恥之于人大矣”[5]329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不知羞恥的那種羞恥,真是不知羞恥至極。羞恥之于人關系重大,其出于“四心”之“羞惡之心”。圣賢能存此四心而不失之,而常人有可能因為環境熏染或個人修養不夠而失之。無此心則入于禽獸之列,人當深以為恥。
孟子之罵詈立意高遠、意蘊深厚、言辭犀利,洋溢著泰山巖巖的雄辯氣與寒意襲人的秋殺氣。這既與戰國血腥與暴戾之時代背景有關,也與孟子個人氣質、思想相呼應。孟子之雄辯式罵詈可以說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反饋、碰撞、融合于其價值理性之中的必然呈現。
三、荀子統類視域之罵詈:不信東風喚不回
與孟子雄辯式罵詈不同,荀子的罵詈行為、語言風格與其理性主義若合符節。荀子是先秦思想的總結者,奏出了理性時代最強音。歷來對荀子的評價中有“尊孔氏而黜異端”“通達而不迂”之語,所以荀子之罵詈亦當如是觀。如果說孟子的罵詈是感性雄辯式的迸發,那么荀子就是統類視域下,合理性、合邏輯的罵詈。荀子罵詈的對象主要集中于儒家學派內部的一些“敗類”。從荀子“與人善言,暖于布帛;傷人以言,深于矛戟”[11]25之語,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非常重視語言恰當性的儒者。如其雄健深厚文風所顯示的那樣,荀子并沒有孔子春風和煦式的罵詈,也沒有孟子疾風暴雨式的罵詈,有的只是理性的學派之爭所逼迫出來的“罵詈”。孔子歿后,儒分為八。儒家在經歷學派分裂之后的整合變得必要且迫切。荀子明確認識到儒家有在百家爭鳴中話語權、影響力越來越小的巨大危險性。如何讓眾多的儒家門徒掙脫出來,形成合力以重振儒學,也就成為荀子批判與清理之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荀子的罵詈完全出于學派內部清理、解構、重構的實際需要,出于批駁儒門內部異說、邪說、妄行的需要。其罵詈主要集中體現在《非十二子》一文,也散見于其他篇章。且其罵詈也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層面情感發泄,始終沒有偏離理性探討的論域。
基于性惡論的基本預設,荀子將不能化性起偽者視為必罵之列。荀子罵詈的主要對象是儒門敗類。他以邏輯分析方法將儒進行了明確的統類劃分與分類,比如具有不同特點與位階的陋儒、散儒、腐儒、溝瞀儒、俗儒、雅儒、大儒等。荀子罵詈“俗儒”——“逢衣淺帶,解果其冠……其衣冠行偽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11]72俗儒穿著寬大衣服墨而不自知,言稱先王以獲取衣食之用,一幅得意洋洋小人得志之嘴臉。對于子張氏之賤儒,荀子罵詈道,“弟陀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11]53子張氏之賤儒歪帶帽子,說著平淡無味的語言,故作禹舜的步伐。正所謂窺豹一斑,從其形式化的固執來看,子張氏一派儒者當是孔門中的形式復古派。荀子罵詈子夏氏之“賤儒”——“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11]53衣冠雖整齊但面色嚴肅,故作深沉之狀。更有子游氏之賤儒——“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11]53,偷懶怕事、毫無廉恥之心,熱衷于口腹之欲。
荀子統類視域合邏輯之罵詈主要體現于對罵詈對象從不輕易下結論,而是先具體描摹其行為外在表現,再對其行為指向的思想進行歸類整理,再下確當結論。這樣就保證罵詈符合邏輯分析而不是任意無謂的語言攻擊。荀子罵詈也絕非如郭沫若所說,“荀子罵人每每不揭出別人的宗旨,而只是在枝節上作人身攻擊”[12]125。荀子罵詈或說批判的目的是“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11]47。在其對儒的罵詈式論述剖析中,可以體會到這是對當時社會大劇變、大動蕩、大撕裂 問題開出的極具針對性的藥方。這是荀子統類視域中對儒進行解構與重構的理論成果,也成為荀子批判式融合與創造性重鑄儒思想理論的組成部分。
結語
綜上,孔子、孟子、荀子罵詈各有其個性特點與學派共性。孔子之罵為和藹之罵詈,可謂催人上進之罵詈。在罵詈手法的選擇上,孔子是見事而為,絕無空頭指點,運用如朽木、糞墻等類比、比喻手法,有“吹面不寒楊柳風”的溫潤和煦之感;孟子之罵為雄辯式罵詈,可謂防人下滑之罵詈。在罵詈手法的選擇上,孟子是論辯式的,是高屋建瓴、莫之能御以提振儒家為己任的,有“風刀霜劍嚴相逼”之感;荀子之罵為統類視域下,
合理性、合邏輯之罵詈,是條分縷析、罵之成理、罵之有故的,主要出于清理門戶、齊言行、壹統類的目的,有“不信東風喚不回”之雄渾自信之感。值得提醒的是,罵詈的文化生態在今天仍然存在,所以罵詈現象決不會自行消失。更應該看到當今社會戾氣太重,往往一言不合,即刻升級為罵詈,甚至升格為網絡群體罵戰、群毆。只能通過適當的社會治理來疏導社會戾氣,盡量減少罵詈產生的社會根源,同時也應當提高個人修養,慎用罵詈語,還社會一片潔凈的道德天空。
[1]海德格爾.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A].路標[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2]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1995.
[3]程俊英.詩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魏]王弼撰.樓宇烈校釋.周易注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2.
[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6]楊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語通解[M].濟南:齊魯書社,2013.
[7]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8]曹礎基.莊子淺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0.
[9]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11]章詩同.荀子簡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2]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