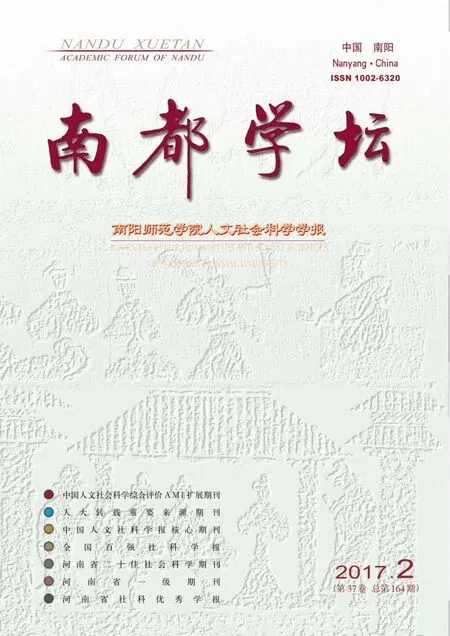漢武帝“巡邊至朔方”與直道交通
王 子 今
(中國人民大學 國學院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北京 100872)
漢武帝“巡邊至朔方”與直道交通
王 子 今
(中國人民大學 國學院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北京 100872)
《史記》《漢書》記載漢武帝經營朔方,又有“獵新秦中”“北至朔方”“并北邊以歸”“巡邊至朔方”事跡。這些事跡均表明,無論是朔方軍事防務的加強,軍運的充實,還是民戶的大規模遷入,都是因交通運輸效率的保障才能得以實現,秦始皇直道的交通條件,很可能在當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司馬遷自己在敘說蒙恬悲劇時也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司馬遷行歷秦直道,應當是隨行漢武帝出巡。漢武帝往返北邊,很可能經過秦直道部分路段。對于這一交通史跡的相關考察可以推進交通史、軍事史、邊疆史與民族史的研究。
秦始皇;直道;交通;漢武帝;司馬遷
《史記》《漢書》記載漢武帝為抗擊匈奴,經營朔方,又有“獵新秦中”“北至朔方”“并北邊以歸”“巡邊至朔方”等行跡。漢武帝北邊之行很可能經行秦直道部分路段。進行這一交通史跡的考察,有益于深化西漢邊疆史、民族史、軍事史的認識,對于秦始皇直道的歷史作用,也可以有新的理解。
一、“筑衛朔方,轉漕甚遼遠”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記述了漢武帝時代解決邊疆問題的多方面努力。因文景之治多年積累形成的經濟優勢,使得漢武帝堅定了有所進取的信心:“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1]1420于是,多方向的邊疆開發成為當時漢王朝的基本政務,相關措施不同程度地導致了國家財政的危機與社會負擔的加重:
自是之后,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財賂衰秏而不贍。[1]1421
東南、西南、東北方向的進取致使局部區域面臨經濟困難,或產生社會問題,即所謂“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巴蜀之民罷焉”“燕齊之間靡然發動”。而由于匈奴軍事壓迫之沉重所導致的北邊形勢的嚴峻,使得這一方向的軍事動作牽動全局,影響整個社會,即所謂“天下苦其勞”。
《平準書》記載,漢武帝組織了積極的軍事進攻。“其后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又興十萬余人筑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其后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余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余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余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秏,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設置“武功爵”的建議,引錄了漢武帝“北邊未安,朕甚悼之”的感嘆。由于“北邊”未能形成壓倒性的軍事強勢,漢武帝不能心安。隨后又有遠征匈奴的勝利:“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余巨萬。”[1]1424
據《漢書》卷六《武帝紀》,元朔二年(前127年)即開始經營朔方:“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余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數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2]170。隨后,直接或間接經由朔方出擊匈奴的戰役有如下記錄: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余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3]171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余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余級。還,休士馬于定襄、云中、雁門。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3]172
元朔六年(前123年)六月詔曰:“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其議為令。”于是,“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2]173。所謂“巡朔方,征匈奴”,體現“朔方”在征伐匈奴戰略中地位之重要。元狩三年(前120年)秋,曾經宣布“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2]177。這一跡象,似可理解為這一方向匈奴軍事壓力的減輕。正如王先謙《漢書補注》所說:“因三郡益少胡寇,故減其半,以寬天下之徭。”[3]90所謂“益少胡寇”,是有漢代文獻依據的。如《漢書》卷一一〇《匈奴列傳》:“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1]2909
朔方軍事防務的加強,與布防嚴密,即所謂“筑朔方”“興十萬余人筑衛朔方”有關;也與軍運充實,即所謂“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有關;也與民戶的大規模移入,即所謂“募民徙朔方十萬口”有關。這些條件,都因交通運輸效率的保障方能得以實現。
秦始皇直道的交通條件,很可能當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一交通史現象,也可以通過漢武帝巡行北邊的實踐得以認識。
二、天子“獵新秦中”
司馬遷在《史記》卷三〇《平準書》中還記述,“天子為伐胡,盛養馬”,又“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
規模空前的北邊移民,安置地點在所謂的“新秦中”。關于“新秦中”,裴骃《集解》引用了幾家注說:
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
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
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1]1425
《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2]1162可能是相對應的記載*而從移民數量看,《漢書》卷六《武帝紀》的如下記載值得注意:“(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初算緡錢。”第178頁。。有人以為有“新秦中郡”設置[4]。其說無據。
“新秦中”是秦直道經過的地方,也是秦直道聯系的區域。漢武帝此次移民計劃的設定,應有利用秦直道交通條件的考慮。“七十余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有賴于借助秦直道實現人口的移動和物資的運輸。“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也直接體現出秦直道交通的效率。
《平準書》記載漢武帝又一與“新秦中”相關的政治表現,涉及其“巡”“行”實踐: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逾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裴骃《集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于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第1438頁。今按:“新秦中”地方被看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裴骃《集解》:“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于民也。’”第1438頁。今按:“新秦中”馬政的發展,是與漢武帝實地考察密切相關的。馬政,是軍事交通的重要條件。
《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行西逾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2]1172《西漢會要》卷一八《禮十三·田獵》與卷六六《方域三·亭障》均說事在“元鼎中”[5]。呂祖謙《大事記》卷一二以為事在“元鼎五年”[6]。而所據《漢書》卷六《武帝紀》的記載只是:“(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2]185此“行西逾隴”“北出蕭關”“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的交通行為,不排除局部行踐秦直道路段的可能。所謂“行往卒”,裴骃《集解》引《漢書音義》:“卒,倉卒也。”[1]1438與“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情形近似。之所以出行“倉卒”,應與行程設計者對行經道路的通行條件有所了解甚至相當熟悉相關。
漢武帝經歷“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之先北上后南歸的行程,實地考察了“新秦中”的交通狀況。“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交通建設不完備狀況的發現,正是由于此次對基層的考察。“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的特殊政策的設定,也基于“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的交通體驗。
漢武帝“獵新秦中”事跡,也是直道史研究者應當注意的。
三、“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漢武帝時代另一次大規模充實北邊的軍事行政舉措,也是和馬政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平準書》記載:
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1]1439
所謂“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的決策導致空前規模的軍屯。“卒六十萬人”的兵員運動,本身就是牽動諸多軍備條件的交通事件。其中前往“上郡、朔方、西河”的“屯田”“塞卒”,有可能經秦直道北上。而直接支持“上郡、朔方、西河”“戍田”的運輸行為,“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應當會利用秦直道交通條件。
其實“河西”“戍田”的啟動,也需要“中國”遠程運輸支援。這一方向的轉輸,經由秦直道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至于“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的情形,使我們聯想到此前有所討論的上郡武庫設置與秦直道的關系[7]。
四、“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關于前引《平準書》“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的史事,還有更具體的記述。
司馬遷在《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中記載了漢與匈奴戰爭史中一則重要的史事:
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漢。何徒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于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于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1]2912
時在元封元年(前110年)。所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漢武帝北上的道路,極大可能經行秦直道。
關于漢武帝“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向匈奴炫耀武力事,《漢書》卷六《武帝紀》及卷九四上《匈奴傳上》都有記載。《武帝紀》寫道:
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云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詟焉。還,祠黃帝于橋山,乃歸甘泉。[2]189
“冬十月”宣布“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應當很快啟程。這是不尋常的軍事表現,違反漢王朝出軍北上往往在春夏之季的季節性規律[8]。所謂“行自云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者,說明自“云陽”出發,經歷上郡、西河、五原,行至“朔方”“北河”,大致經直道北上。而“還,祠黃帝于橋山,乃歸甘泉”,也應當經過秦直道路段。“遣使者告單于”的“使者”,就是郭吉。《匈奴傳上》:
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于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2]3772
《武帝紀》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余里”,《漢紀》作“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十余里”[9],《資治通鑒》取用《漢書》說,作“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余里”[10]卷二〇“漢武帝元封元年”。
漢武帝“北至朔方”的路線,很可能與蒙恬主持修筑的秦直道重合。然而史念海說:“這次北巡,是由云陽啟程,后來回到甘泉。甘泉就在云陽,也是直道南端的起點。北巡途中經過五原。五原就是秦時的九原,乃是直道北端的終點。因而這次北巡所行經的道路,可能使人聯想到直道。其實并非如此。”史念海判斷,“武帝北巡得由直道南端起點甘泉發軔,而轉到其東的另一條道路,至于上郡”。他還指出:“武帝此次北巡所經的諸郡中有西河郡。西河郡為漢時所置的新郡,西河郡治平定縣,在今陜西神木縣東北和內蒙古準格爾旗之間。遠離由上郡至九原郡的道路。”[11]然而“北歷上郡、西河”,未必一定經過上郡郡治和西河郡治,行歷此兩郡轄境,也可以說“北歷上郡、西河”。即使確實經過上郡郡治和西河郡治,則此次北巡“由云陽啟程,后來回到甘泉”,“途中經過五原”,如果完全避開直道線路,不經過直道部分路段,幾乎是不可能的。
五、“天子北至朔方”“并北邊以歸”
《平準書》記載漢武帝此次出巡,言“北至朔方”,隨后東行“海上”,又“并北邊以歸”:
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并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1]1441
《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
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2]1236
《漢書》卷六《武帝紀》也寫道:“(元封元年夏四月)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2]192漢武帝“并北邊以歸”,“至九原”再南行“至甘泉”的路線,很可能與秦直道主要路段重合。
史念海明確指出,漢武帝“走過蒙恬所筑的直道”,即依據《郊祀志》和《武帝紀》有關此次出巡的記載[11]。
漢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與夏四月至五月兩次北邊之行,中隔“東到太山,巡海上”,后者“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是一次全面的“北邊”國防線視察,自然與對匈奴的軍事政策設計有關。林幹《匈奴歷史年表》“公元前一一〇年,漢武帝元封元年,匈奴烏維單于五年”條只錄“冬十月,武帝巡邊,北登單于臺(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西),至朔方,臨北河(今內蒙古河套的烏加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經千余里,威震匈奴”事,不言“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事[12],不免千慮一失。
六、司馬遷“適北邊,自直道歸”
關于秦始皇直道工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卷一五《六國年表》、卷八八《蒙恬列傳》、卷一一〇《匈奴列傳》都有記述。正是司馬遷的記載,保留了關于這一偉大工程的真切的歷史記錄。《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寫道: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1]2570
司馬遷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明確告知《史記》的讀者,他曾經親自行歷秦始皇直道。
這是第一位曾經行走在秦始皇直道上的歷史學者,也是第一位留下自己行經秦始皇直道親身感受的歷史學者。這是第一位記錄秦始皇直道工程的歷史學者,也是第一位就秦始皇直道發表自己對這一交通建設之評價的歷史學者。
司馬遷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適北邊,自直道歸”的呢?清人繆筌孫曾經考察“太史公”歷史考察行旅路線:“太史公南游蹤跡,《河渠書》贊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屈原傳》贊云:‘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即南游九疑,浮沅、湘時事。《樊酈絳灌傳》贊云:‘吾適豐沛,問其遺老。’即‘過梁、楚以歸’時事。《河渠書》贊又云:‘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其為郎中使巴蜀時事。歸途或至隴右,故登崆峒與?惟北游未知何時。《五帝本紀》贊:‘予嘗北過涿鹿。’《蒙恬傳》贊云:‘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自有北游龍門、朔方之實跡。”[13]他認為,“太史公南游蹤跡”或可指稱某時事,然而“惟北游未知何時”。如“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者,雖“自有北游……朔方之實繼”,但是不能明確當時具體情景。
史念海在討論漢武帝元封元年巡行北邊的路徑時,曾確定“武帝此次出巡,司馬遷實在從行之列”,“司馬遷說,他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這就足以證明他是隨從武帝東巡歸來的”[11]。“此次巡幸,司馬遷曾經隨行,故而對直道的起訖地點能夠明確記錄下來。”*有學者也認為,司馬遷隨同漢武帝元封元年巡行,曾經行歷直道。“(漢武帝)沿海北上到了碣石(今河北昌黎縣),經過遼西(今遼寧義縣)、北部邊郡,到達九原(今內蒙包頭市西),五月間,回到甘泉。武帝這一次巡行,路程約一萬八千里,沿途勞民傷財,揮霍無度。司馬遷隨同漢武帝巡行,對我國北方有更一步的了解。他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直道’即自五原至甘泉的直通大道。”參見許凌云:《司馬遷評傳——史家絕唱,無韻離騷》,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35頁。[14]這樣的意見,是正確的。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王先謙,撰.漢書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影印版(據清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1983.
[4]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182-185.
[5]徐天麟.西漢會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92,776.
[6]呂祖謙.大事記[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王子今.西漢上郡武庫與秦始皇直道交通[G]//秦漢研究:第10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6.
[8]王子今.西漢時期匈奴南下的季節性進退[G]//秦漢史論叢:第10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9.
[9]荀悅,著.漢紀[M].張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235.
[10]司馬光,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676.
[11]史念海.與友人論古橋門與秦直道書[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4).
[12]林幹,編.匈奴歷史年表[M].北京:中華書局,1984:31.
[13]繆筌孫.云自在龕隨筆 卷二:論史[M].稿本.
[14]史念海.略論秦直道[G]//秦文化論叢:第5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
[責任編輯:劉太祥]
Emperor Wudi of Han “Imperial Visit to Shuofang” and Zhidao Traffic
WANG Zi-jin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InShijiandHanshu,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Shuofang, such as Emperor Wudi of Han managing Shuofang, “hunting in Xinqinzhong”, “visit north to Shuofang”, and patrol-supervision to Shuofang”. All of the stories show that the traffic condition of Zhidao built by First Emperor of Qin is likely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uofang. Emperor Wudi of Han possibly passes part of Zhidao to the north back and forth. So, the study of the traffic history at that time can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traffic history, military history, frontier history and history of nationality.
First Emperor of Qin; Zhidao; traffic; Emperor Wudi of Han; Si Maqian
2016-12-20
王子今(1950— ),男,河北省武安縣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
K234
A
1002-6320(2017)02-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