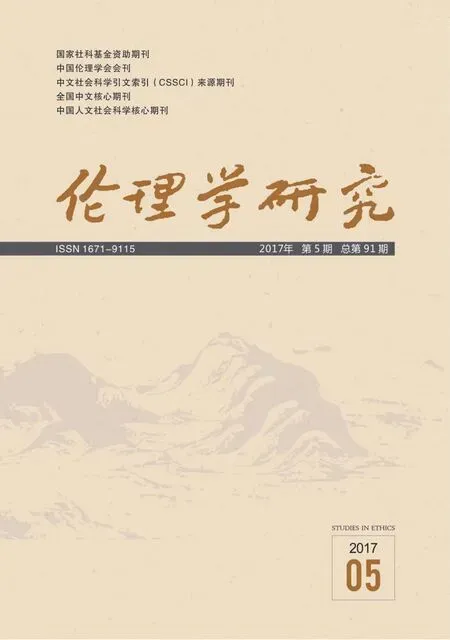《易傳》道德哲學新探
李佩樺,徐孫銘
《易傳》道德哲學新探
李佩樺,徐孫銘
《易傳》通常被認為是釋《易》之作,其中包含了豐富的道德哲學思想,但目前的中國倫理思想史教科書多不見對《易傳》倫理道德思想的闡述,這與《周易》“群經之首”的地位是不相稱的。有鑒于此,本文從三個層面上對《易傳》的道德哲學思想進行了新的系統的闡釋:一、依據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維架構,闡述《易傳》陰陽相反相成而為“易”(即“變”)、“生生之謂易”的生命本體論,人道本于天道,故人要成就自己,就必須“繼善成性”,人之所以能夠“繼善成性”的依據是“天地設位,圣人成能”;二、“繼善成性”的具體實現路徑是“修業進德”即內修其身與開物成務,其原則是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具體方法是“擬之而后言,議之而后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三、“修業進德”的境界是“圣人氣象”即“與天地合其道,與日月同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同其吉兇”的圣人境界。
《易傳》;道德哲學;《周易》
《易傳》作為《周易》中相對經(卦辭和爻辭)而言的部分,通常被認作是后人對經文的解釋和對《易》的思想進行闡發之作。“作為《易經》的八卦,本是用于占卜的概括性的符號,其中包含有遠古先民對自然現象和歷史經歷的經驗描述和理解。”[1](P126)如果說,在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經驗解釋中包含著某種樸素的哲學思維的話,《易傳》則是對作卦占卜以定吉兇這樣一個整體事件所進行的清醒的哲學理性的反思與提升。換言之,《易傳》雖出于解釋卜筮之事,并于其中描述歷史經驗,但其思維和理論高度卻又超出于此,融合宇宙萬物的演化與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于一體,成就了一套高度哲學化的形上宇宙論和人生觀。《易傳》的宇宙秩序在其后被董仲舒等漢儒承繼,建構出更為緊密復雜的宇宙生成圖式;其中所包含的豐富的道德哲學思想,則被宋明儒者不斷發揚光大。然而,目前的中國倫理思想史教科書多不見對《易傳》倫理道德思想的闡述,這與《周易》“群經之首”的地位明顯是不相稱的。本文正是基于此一缺憾,通過對《易傳》道德哲學的重新梳理,揭示其所蘊含的生命本體——工夫——境界的邏輯三部曲,以求明得荀子所言“善為《易》者不占”的緣由,彰顯出《易傳》之所以影響深遠且應當被加以正視的道德哲學根基。
一、本體:基于生命憂患意識的挖掘與建構
《易傳》的核心,也是其最為引人入勝的內容,是對以下兩個問題的回答:一是圣人為什么要作卦?二是圣人是怎樣作卦的?至于對具體卦、爻辭的解釋說明,都是為了印證對上述問題的思考所得出的結論。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回答,正是《易傳》本體論進路的展現。
從《易傳》看,圣人之所以作《易經》,乃是源于一種對個體、對整個人類整體生命存在的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其實是人類整體對個體生存有限性的思考。具體來說,生命之憂患意識的根源又可從三個維度來展開:其一,個體生命之渺小與短暫。相較宇宙之浩瀚無垠、悠久綿長,個體一生是極其有限的,如何在險惡且變化的自然環境中保存下來,并盡可能實現自我生命在價值上擴大和延長,成為生命體必須面對的困境。對于前者,我們開創出了以農業為核心的生存模式,對于后者則出現了《禮記·夭壽》所載“死而不朽”的生命實現路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其二,社會關系的內在張力。個體生命必然在地球上存活,地球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極其有限的,個體之間以何種原則共處,又以何種原則來分配資源?①這不僅涉及到社會的構成、群體的結構,也必然會引發個體之間的緊張。因為,無論人與人之間如何結成社會、安排秩序,都無法跨越個體獨立和資源有限的屏障,以致導致彼此之間在一定程度上的爭奪關系。這種爭奪一旦擴大,則最終致使整個社會的失序與重構。為此,如何盡可能結成穩定的社會,推進個體間的和諧成為了政治哲學亙古不變的中心議題。其三,特殊的生存背景。個體降生之家庭、時代環境,無論是富貴還是貧賤,是治世還是亂世,其實都免不了面對前述的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困局。
《易經》所主的卜筮行為,作為趨避吉兇、趨利避害的神秘性術數活動,其根源即在于個體本身即是一種力求否定生命的無常、無意義而把捉生命之安寧與穩定、尋求生命之真實感的活動,這正是一種生命之憂患。《系辭下》載:“《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2](P84)孔穎達注:“此之所論謂《周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者,若無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故知有憂患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后,以防憂患之事,故系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兇也。”[3](P89)這說明,《易經》正是因作者身處憂患,又或有感于前世和周遭他人之苦難而作,以期為后世立下避禍的方法。“西伯拘而演《周易》”的說法則進一步從史實中印證《周易》的憂患背景和意識:“《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4](P85)《易經》所包含的憂患意識不僅是從物事的興衰轉化中間接呈現,也在多處行文中直接可見①。
總覽《易經》之說,雖然開啟了對生命憂患的自覺,并在描述上未免過于艱澀和零星,且用途也重在占卜,并未就此作系統的整理和哲理性的升華。《易傳》作為對經的詮釋和擴充,成書于戰國中后期②,相較于《易經》所作、所演之時,人類整體文明對人的價值、人與自然關系,以及社會秩序建構等也有了更為豐富的實踐、更清晰的認知。同時,也經歷了人類社會的大動蕩時期,個體的旦夕禍福、國家的興亡更替,無不警世并激化著世人的憂患意識。借助文明累積與時代變革的大背景,《易傳》的創作者從《易經》本有憂患意識出發,不僅使之上升為一種系統的、哲理性說明,而且將之鮮明地凸顯出來。
《易傳》以生命憂患為要旨的致思路徑,內在地決定了它的出發點和歸宿必然是對真實的生命存在的追尋。圣人觀象作卦,是因為“象”之中隱含著生命存在之法則與真理。卦,不過是以符號化的形式把它展示出來,以給人的生命活動提供依據,從而在保存自身肉體的基礎上,成就自己的真實存在。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5](P87)又: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5](P87)。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及“順性命之理”,正是以古典語言表達出來的一個人類永恒的話題:探究真實的生命存在。那么,這個出于人的生命憂患意識,牽涉天地運轉法則的發問,其結果是什么?或者說,生命的本體是什么?《易傳》給出的答案就是“易”或者說是“道”③。
“易”作“變易”解,本是造成生命憂患,即個體生命生滅、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社會秩序治亂的緣由。但《易傳》恰恰借此來建構生命的真實存在,將其原本的否定意涵巧妙地轉化為肯定意義,即要找到生命變化之所以然,對之作形上的詮釋,并要形下的變動者順從之。這種反證邏輯,無疑是《易傳》對于儒家思想,乃至整個中國哲學體系的重要貢獻,也是中國哲學之所以區別于國外哲學的重要支點④。
《易傳》借助“易”的“生化”特性,把整個宇宙存在的一切,包括自然、社會、文化,都看作是一個動態的、自然的生成過程,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展開過程:
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6](P92)。
這樣一種天道與人道、人生與世界的生化過程作統一性解釋的范式,即“生生”之“易”。“易”在此不只是單純的變化之義,而是被賦予了一種偉大的德性——“天地之大德曰生”[4](P81)。正是此般將天人相合,將自然與歷史相統一的“生生之德”,才成就了“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7](P76):宇宙萬物的氣象萬千、蓬蓬勃勃和日新月異,人類生命的不斷演化與成長。
既然“易”是自然和人事之所以生成,且必須始終奉行的大道。那么如何把捉這種變幻和生成的規律,即這種“生生之德”是如何運作的,其動力機制為何?《易傳》認為,“易”乃是根源于生命內部兩種既相反又相成的“力”——陰與陽,陰陽相摩相蕩而成萬物。陽是天、是日、是乾,陰是地、是月、是坤,陽主健和動,陰主順與靜,健順相得,動靜相宜,遂成整個宇宙的生生不已。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8](P1)。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9](P4)。
陰與陽相反相成,相得益彰,既是“生生之易”的源泉,也是“易”中之“不易”的常道,若是明得其中道理,則能“簡易”地洞悉萬物之理。借助陰陽相合的動力機制,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之間實現了溝通,變化原理與包含這一原理的具體生命存在之間內在地統一起來,不相隔絕。
概而言之,從《易傳》出發,生命的真實存在即在于“變”,在于自身的“生”,離開了“生”則生命即不成其為生命了。這個“生”既有消極的“生存”之意,更有積極的“創生”之義。對于人而言,其全部的意義和價值,就在于繼此“生”道,成此“生”性,從而實現為“生”德:“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7](P76)
二、工夫:基于“成己成物”的進德與修業
生命的本體既然在于陰陽相摩相蕩所引發“易”和“生”,那人如何才能“繼”、“成”此道?對此一問題的解答,正是對《易傳》所內含的工夫論的梳理。“繼善成性”工夫的總綱在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因為,生命的真理是“生生不已”,正是乾或陽作為主導,通過健動以“資始”,坤或陰作為基礎,憑借順勢以“資生”,二者的合力構成了生命之源的自然流行。將此乾坤的特性具體落實到人的生命之上,則要求生命進程中不斷地“修業進德”。
在《易傳》中,君子所修之“業”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將之歸納起來,則大致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觀象設卦”,“以類萬物之情”,這實際上是通過“觀”的方式來體察、把握生命之本體,也即把握宇宙萬物的生成和運作法則,明得其中吉兇、利害,及相互間的轉化機制;一是以此對生命之真實存在的把握為依據,去實現這真實的生命,即將其所“觀”、所察,推及到人類社會的生產與生活中去,構建整體的秩序、安頓個體的身心。“觀”與“行”作為“修業進德”的一體兩面,是不可分割的。唯有依靠真切之“觀”,即對生命本真的自覺,才能最終在實踐層面實現治平與安頓;只有通過生命實踐,“觀”才得以落實,不致成為虛妄清談。
“觀”是整體之“觀”,是“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7](P76),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4](P81),是“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7](P77),是“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7](P77),故是綜合的、統貫的、有機的,而非分析的、單一的、機械的。通過此“觀”,就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4](P81),能“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7](P76),即把握到生命的真理,人據此而行,就可以趨吉避兇,補過無悔,成就自我之生命。“成性存存,道義之門”[7](P77),此之謂也。
從另一方面說,通過“觀”得到的是觀念或理論,此觀念或理論還必須落實到具體實踐中去,才能將此真實的生命開顯出來。這種落實在《易傳》中又體現在兩個維度:一是君子要內修其身,做到“慎言行”,一是君子要人文化成,實現“開物成務”。此二者的統一即構成內外合一的生命之存在和生長過程。關于前者,孔子曾在《論語》中作過大量的闡發,不僅主張要通過“聽其言而觀其行”來審定為人,直接指出“巧言令色,鮮矣仁”[10](P50),“剛毅木訥,近仁”[11](P139),更是直接將言行與君子的求學之道、為政之方等相聯: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12](P54)。
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13](P59)。
《易傳》亦引孔子之言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7](P77)言行作為人格的直接外顯,其適宜與否,不僅直接關系自身生命的榮辱,甚至也影響“天地之道”的正常運作軌跡,不可以不慎。唯有謹言慎行,才能讓自身盡力避開羞辱與懊悔。這一要求,其實也正是生命憂患意識的直接表現,是力求實現“無咎”的重要路徑。
關于后者,《易傳》認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7](P77)“易”之“生生”大道,是萬物之所成,并各安其位,各盡其職的根源。“易”在天,是其自然、自發的結果,在人,則雖有其內在的深刻根源,但人們所實現的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形成的“象”——一種生命的理念。所以,此“變”在人間的真正實現就不是一個純粹自然的過程,而必然需要貫注人的主體性因素,即“易”之道對人而言,在原則上當順從和效法,在條件和結果上則需積極創造,以求安頓自身和百姓之位,使得上下有序,社會和諧。所以,《易傳》云:“擬之而后言,議之而后動,擬議以成其變化。”[7](P77)又稱:“天地設位,圣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4](P85)可見,“開物成務”是一種飽含著深層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使命感的文化創造活動。從《易傳》看,每一卦象都代表著一種生命的理念,此生命理念的現實化就是文化,是歷史,是價值。在這樣的解釋框架下,結繩為網、耜耒之作、賈市之設,都是道之流行,是生命的自我實現,是“生生之德”的具體表現。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7](P81)
三、境界:基于“天人合一”的追求與實現
若是生命體能全然依照上述“修業進德”的兩個方面來要求和展現自身,便是在人生和社會的層面順從并推進了“生生”之道,實現了“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本真路徑。如此,個體便成為“大人”,從而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14](P4)換言之,若是能讓自我德性的內修與社會實踐的外化都“順性命之理”,便不僅把捉到形上層面“一陰一陽之謂道”的生化原理,而且在形下層面實現了與天地萬物共處的“游刃有余”。如此,人道與天地之道合一,自然能讓一己之生命無往而不利,成就富有之大業、日新而又和諧之世界,而這也就實現了自己真實的生命存在了。
《易傳》所述的“圣人氣象”,其關鍵表征就在于天地萬物在“位”上的“當”與“正”。《易經》中頻繁出現的“位不當”,大多即是言明對應卦象之兇陷。反之,若被解為“位正中”,又或“位正當”、“正位”,則表明對應卦象之吉利。《易傳》承接此一邏輯,將尊卑、高低等“位”的安頓與否,視作是天地萬物是否順承應然之“變易”法則的標識。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7](P75),所表達的便是天地皆有其秩序,若能依循此一秩序展開世界,使得萬物各得其位,各盡其能,自然便成就大道,即完成“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7](P75)的完滿。反之,若是不能使萬物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則自然引發危機:“危者,安其位者也。”[4](P85)將此一定“位”的思想貫徹到人類社會,則要求君子、圣人做到前文所述的“修業進德”,通過“天地設位,圣人成能”[4](P85),以安自身,平天下,使君臣有義、長幼有序、男女有別。
《易傳》的這種境界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中庸》所載的“贊天地之化育”或“與天地參”,以及“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4](P38)的天地之大的論調。但,二者又在進路和格局上有所差異。《中庸》雖同樣有形上世界的建構,基礎卻在于心性之“至誠”,格局主要局限于人倫的范圍。《易傳》則是依托于宇宙生成圖式而發,包納人與天地、歷史與自然等各個層面,不僅蘊含了道德理性,而且充滿著知識理性的要素,這也就使其在實踐上具備了更高的可行與普及價值。與之相仿,荀子也表達過“參天地”的境界論: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16](P163)
荀子所說的“天地”,主要是指外在自然,是需要人類去利用甚至征服的對象。荀子所期盼的“參天地”則主要表現為對人力的高度推崇和張揚,他根據“天人相分”的邏輯,主張在此基礎上通過“君子”對禮、義的制定來對社會生命進行必要的群、分,最終實現社會關系的和諧、社會秩序的安定。相較之下,《易傳》之“天”則是雙面的:既是外在于人,且要人對之加以順從的陰陽之道,也是內在于人,被賦予了人的精神的德性生命(即生生之德)。這樣的天地大道,一方面,蘊含著“天人相分”的特質,而要君子、“大人”發揮自身主體能動性,以實現萬物和百姓的各安其位;另一方面,更指向著“天人合一”的目標,即人道與天道是一致不二的,都是一陰一陽的相反相成,這不禁為人化育天地、平治天下提供了內在的便利和無盡的信心。
借由以上三者對“圣人境界”陳述的異同比較可知,《易傳》之說在致思進路上更具客觀性,在格局營造上更為宏大,在內容上也更為廣闊。這不僅預示著《易傳》在此一層面建構中的兼容并包,更代表著其承前啟后的學術地位和價值。
當然,“圣人境界”畢竟只有少數人方才有機會達到。若境界只此一層,則無疑與一陰一陽之道的無所不包、無處不在的屬性不相比配。為此,就應當還有一“小人”境界,即對于那些無勢無位、無甚才學的普通人而言的“生生之道”。這些人并非被排除于“一陰一陽之謂道”之外,只是因條件所限,以致“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換言之,“百姓”也同樣被統攝在“生生”之“易”當中,但其自覺之程度、實現之范圍都有所限度,他(她)不能如“大人”那般主動地化成天下,只能夠在自身內部的小環境中安頓自身,被動成為“圣人氣象”得以實現的構成部分。
四、結 語
《易傳》以“生生”為生命之本體的思想,明顯不同于孟子和《中庸》的本體觀。在孟子和《中庸》,道的具體表述雖然不同,但其心性論的論證進路,以及限于人倫之道的論證范圍,是相同的。這決定了此二者的生命理想也同樣局限于人倫方面,著重于個體的道德修養,因而在規模上顯得相對狹小和局促。相比之下,在《易傳》的“生生”之道中,則包含著一切有利于生命成長的內容,從天道到人道,從自然到歷史,從世界到人倫,可謂無所不包。而且,它們在“生生”的理念中都可以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共同構成蔚為大觀的生命之流,這樣的格局與氣勢無疑更為宏大。
更為重要的是,“生生”本身是一個自強不息的奮進過程,因而,人不應該滿足于既定條件,而要使自己的生活世界展示出它的日新月異的本性,通過“開物成務”創造更為絢爛的文化世界、更為和諧的社會秩序。《易傳》開出的道德哲學的工夫論中,既有道德理性的執著——君子謹言慎行;也有知識理性的探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觀象設卦”;還有實踐理性的指引——借助“觀象作卦”的結果來指導生命的展開和社會的組織。
總括而言,“易”之道廣大悉備,“易”之德生生不已,這樣的道德與今天所謂道德,在范圍上要廣得多,它在“生生”的前提下,擴大了道德理性的范圍,使人的存在納入了無比豐富的內容。
[注 釋]
①如乾卦九三爻辭的“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頁 1);坤卦初六爻辭的“履霜,堅冰至”(頁 5);否卦九五爻辭的“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頁17);困卦上六爻辭的“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頁 55)……
②目前學界對《易傳》的成書時間、作者及其所屬學派并未形成公論:(1)司馬遷、班固等漢儒堅持《易傳》為孔子所作,屬于儒家經典,此一觀點不僅在歷史上影響深遠、廣受認同,在當代也大有追隨者,如金景芳、呂紹剛。(2)宋儒歐陽修作《易童子問》,認為《文言》、《說卦》而下,皆非孔子所作,而眾人所述,眾說混雜而成。此一論調,開啟了宋以下學者的新視角,宋代的趙汝楳、清代的崔述,以至于近代的馮友蘭、顧頡剛、錢穆等都認為《易傳》諸文并非出自孔子。(3)在《易傳》成書、作者等打破一統之論后,近現代學者眾說紛紜。就成書時代上,影響重大的主要有兩類:A高亨、朱伯崑等認為成于戰國時代;B李鏡池、黃慶萱等則主張成于秦漢之間,甚至于西漢初期。就歸屬學派論,主要論點有:A郭沫若持《易傳》出于荀子門徒一說,并被李澤厚所承接和發揚,將其與《荀子》、《老子》并列起來闡釋;B張岱年認為《易傳》是顏氏之儒的遺著,只不過以孔子名義來擴大影響;C劉大鈞則以為《彖》《象》與《系辭》的寫成與思孟學派密切相關;D陳鼓應等則指出《系辭》中蘊含的豐富道家思維與邏輯,認為顯著受到老子學說的影響。
縱觀上述種種論調,無論是出自孔子,歸于儒家;出自孔子門徒,歸于儒家;還是將之與儒家“門外之徒”荀子相關聯;又或將之與道家并列而視,其實都逃不脫春秋戰國的大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在戰國末期以及秦漢之際,人們對未來格局之預判和期待上有了更多的積極性態度。結合《易傳》中賦予“天”的積極樂觀意志(即“天行健”),無疑應是發生在這一亂世行將結束之時(即戰國末期,甚至秦漢交替之際),才更具合理性。
此外,就《易傳》中所蘊含的儒道互補且陳述成熟的取向,也表明它首先是在百家爭鳴之際發生的,唯有如此學說之間的溝通才能頻繁,依此,孔子之時所作便不可能,在秦代高壓統治之際,武帝“獨尊儒術”之后也不現實。其次,它還應該在爭鳴的成熟而非發端期所作,唯有如此學說之間的融合才能真正嫻熟。
有鑒于上述觀點,本文主張《易傳》成書于戰國末期,是以儒家(在此主要指荀、孟兩派的思想)邏輯為核心,融合道家思想而成。
③一般認為,“道”即指變化所遵循的法則,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實際上,《易傳》中,“道”與“易”是同等意義的范疇,易有“變易”、“不易”、“易簡”三義,這三義都與“道”相關。在《易傳》中,變易本身即是萬物和人之生成和生活“道”,所謂“為道屢遷”、“唯變所適”正是這個意思。后兩義則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聯。“不易”指的是各種卦象所反映出的宇宙自然和人類歷史的客觀規律,此一規律正是“一陰一陽”相反相成的“常道”。“易簡”則是對把握此一規律或規律之要領而言的,其實,天道和人道、自然和歷史不過都是陰陽(剛柔)相摩相蕩的結果,此外再無特殊、新奇之處;又,“天之道”的核心表征是“健”,即以陽為主導,催動萬物生成之始,“地之道”的主要表征在“順”,即以柔性來展現承載萬物的厚德。
④西哲中出于個體生命渺小和短暫的憂患,其給出的出路大致可分為三:(1)尋求一個外在的、永恒的存在,如柏拉圖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2)確立個體或人類自身的絕對性,以抗衡外在的壓力,尼采的超人、文藝復興的張揚人欲即是;(3)放棄對一切穩定的追求,主張相對主義,以致陷入虛無主義,如古希臘智者學派。《易傳》尋求穩定的形上建構則異于此三者,它將“變易”本身作為形上的依據,將自然和人類生命視作一種過程,是不斷展開的,無固定形態的。此一思想與孔子所言的“君子不器”、“無可無不可”,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1]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2]吳樹平 等,點校.十三經(點校本)·周易[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3]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
[4]吳樹平 等,點校.十三經(點校本)·周易·系辭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85.
[5]吳樹平 等,點校.十三經(點校本)·周易·說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87.
[6]吳樹平 等,點校.十三經(點校本)·周易·序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92.
[7]吳樹平 等,點校.十三經(點校本)·周易·系辭上[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76.
[8]吳樹平 等,點校.十三經(點校本)·周易·乾·彖[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9]吳樹平 等,點校.十三經(點校本)·周易·坤·彖[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1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子路[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學而[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政[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4]吳樹平 等,點校.十三經(點校本)·周易·乾[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1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6]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0.
李佩樺,湖南科技學院講師;徐孫銘,湖南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兼職教授。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傳統孝道養老倫理及其現代啟示研究”(14Bzx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