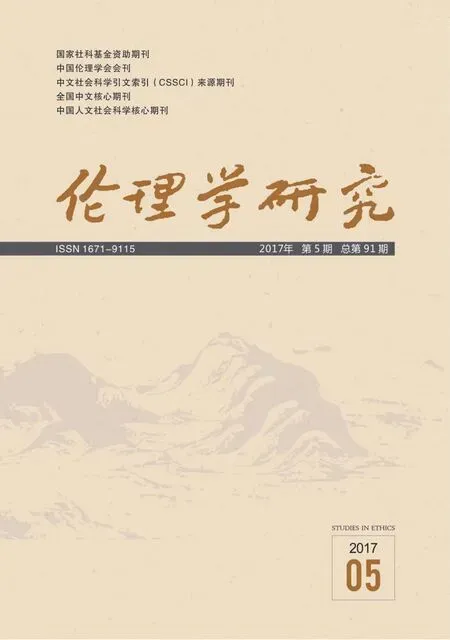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呂本修
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呂本修
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范疇,是傳統道德的基本規范,也是中國人的精神標識。先秦儒家孝德思想是中國孝文化的源頭,它發端于夏商,萌芽于西周而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內容豐富,養親、敬親、諫親、安親與喪祭等內容自成系統。這一思想系統在傳統社會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必須站在正確的立場上運用科學的方法對其當代價值作出科學分析。
先秦;儒家;孝德
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范疇,是傳統道德的基本規范,它深深地侵染著中國人的心靈,培育著中國人的德性,成為中華民族精神重要的內在基因,甚至成為中國人的精神標識。因此,從源頭上探索其形成及演變、內容及特點,從現實角度評價其意義及價值,對于我們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重要意義。
一
孝德思想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但是具體形成于何時,學術界則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通常認為,西周時期,孝德思想已經非常明確,甚至孝的行為在社會中也已經非常普遍。
孝德思想的形成有其社會歷史條件,遠古時代的原始禁忌與崇拜成為孝德思想形成的重要淵源。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這一原理告訴我們,“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P591)。在遠古時代,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極低,遠古祖先生存與生活能力也很低,在與自然界的抗爭過程中,人類力量弱小,完全受制于外部自然的力量,自然界像是人類的異己力量,不僅制約著部落及氏族的生存與生活,而且更加控制著個體的生存與生活。在這種社會狀態下,“人的感情、思想、活動,并不是從他自身出發的,而是被一種外在的力量印在他身上的。部落的每一個成員對部落習慣法的無意識服從,很長時間來被看成是構成研究原始秩序人們遵守法則之基礎的基本公理”[2]章(P138)。這里的“部落習慣法”其實就是遠古人類由于對于外部力量的恐懼而形成的各種各樣的禁忌。如果說原始禁忌源自對于外部世界的“畏”,而崇拜則是來源于遠古人類的“敬”。遠古人類通過占卜、祭祀等活動向崇拜對象表達友好,甚至以近乎諂媚或祈求的態度來討好崇拜對象,從而換取自身需要或利益的滿足。原始崇拜的對象主要由三類:第一類是天神、上帝;第二類是日月星辰、山川林澤等自然物;第三類是先王、祖先。相應地,原始崇拜根據崇拜對象的不同可以分為天帝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三種崇拜中,祖先崇拜成為遠古人類崇拜的核心。在遠古人類看來,自己的祖先去世以后就會升天并且成為天帝的工臣,陪伴于天帝左右,可以與天帝溝通交流;同時,遠古祖先人類,自己的祖先會福佑自己的后代,會像母親愛護孩子一樣保護自己的后人。這樣,人類的愿望與需要,通過祖先的轉達,呈現于天帝,天帝降福于民于世,從而實現原始人類的愿望。這一過程中,祖先無疑是關鍵的角色,他們是達于天帝的關鍵甚至是唯一中介環節。因此,西周以前的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對祖先的祭祀與頌揚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遠古人類表達的對于祖先的深厚情感,以及對于祖先的真摯的誠敬之心,這種原始祖先崇拜中蘊涵的真摯情感、誠敬之心以及彰顯出的原始質樸的品格雖然不是后世意義上的孝觀念,但毫無疑問,這是孝觀念形成的重要淵源所在。
西周時期,隨著宗族與個體家庭的發展以及人類德性的自覺,孝觀念得以真正凸顯。夏人尊命,商人事鬼,甚至到了每日必卜、每日必祭的迷戀癡狂的程度。在他們看來,神靈的存在是社會生活的根本保證,是宗族和家庭在內的一切社會關系和諧協調的基礎,人的一切包括人的地位、作用、等級、權力等等都需要從神靈那里得到解釋與說明。因此,夏商時期,神權社會是其典型特征,人與神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的主要表達方式,正是由于這種社會倫理關系的不成熟以及人類德性不自覺狀態,決定了孝觀念不可能真正確立起來。而這些在西周時期慢慢發生了諸多變化,甚至是根本性變化。就祭祀而言,一方面,西周時期的祭祀體系,不論是祭祀的對象、祭祀的程序、祭祀的儀式等等都比夏商時期更加系統,更加完善;另一方面,神靈的權威在不斷下降,它們不再是西周時期社會生活的核心與主宰,人的存在更多地從神性回歸于人性,人的生活也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理性化的、人性化的社會生活。其一,西周時期,天帝與祖先被賦予了具有倫理意義的道德品格,周人開始試圖用一種新的途徑取得帝神與祖先對自己的眷顧。在周人看來,神靈不再是不可知的、變幻莫測的恐懼的崇拜對象,人類完全可以感知天帝以及祖先的意圖,在這種神意的指引下最大程度地完善并保持神靈賦予的道德品格,繼而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對神意的影響。在人與神的關系中,神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其核心與主宰地位漸漸地被世俗社會的人類本身所取代;社會關系也不再以人與神的關系來呈現,而是直接地呈現為家族、家庭為主的社會關系;道德要求也不再通過神靈來表現,而是成為人類現實的社會需要。其二,西周時期,對于天帝與祖先的崇拜心理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夏商時期,原始崇拜的心理機制主要是敬畏,功能機制主要是祈福。而周人對于天帝心理上不再畏懼,對于祖先也不再是僅僅為了自身的福祉與利益,而是在內心深處存在著一種對于天帝與祖先的深厚情感,甚至深知他們的偉大,在一種感恩的心態下頌揚他們的豐功偉績以及對于子孫后代的無私奉獻。孝德思想也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社會需要以及這種德性觀念的基礎上才真正形成。“孝”體現著人的原始質樸的道德情感以及由此情感而生發的道德自覺,是德性觀念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體現。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當時歷史社會的變化,孝德思想也不斷成熟并且日益完善。首先,從孝的對象來看,在世父母成為孝的最重要的對象。西周時期,從孝這個字的用法上來說,使用最廣泛的有兩種用法:一是“享孝”,二是“追孝”。享字的本義,即是祭獻、上供。《說文》釋義:享,獻也。其義也是指用祭品獻于鬼神使其享用。可見,享的對象是鬼神,前文已述,鬼神主要有三種,其中主要的是上帝以及人類的祖先。這也是西周時期祭祀的主要對象。這里我們可以推知,享孝的對象肯定不是在世的父母,而應當是已逝的先祖。追孝的使用通常有兩種涵義。其一,把“孝”在一般意義上理解為“美德”,把“追孝”理解為追繼祖先的美德,頌揚祖先的功德與恩德。其二,把“追孝”理解為后人以祭祀的形式繼續對先祖行孝行。這是西周時期金文中主要的用法,它與“享孝”之意相通,也體現著祭祀是西周時期體現孝的最主要的途徑。可見,追孝的對象也不是在世的父母,也是已逝的先祖。所以說,西周時期,孝的對象主要是先祖,還不是在世的父母。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平民階層的獨立與分化,孝敬在世父母的觀念逐漸從貴族向平民滲透,并最終成為社會共同認可的重要道德規范。
其次,孝德思想的內容已經相當豐富且比較完善。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孝觀念從上層社會向民間社會的滲透與傳播,孝觀念的內容也不斷豐富。孔子對孝提出了許多要求,比如“養”、“敬”、“隱”、“諫”、“色難”等等。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孝的思想,并從性善論的角度揭示了孝的本體論基礎。荀子作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從性惡論角度論述了人性與孝、仁義與孝的關系,對于孔孟孝觀念做了有益補充。《孝經》作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對孝從地位、方式、層次、功能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論述,是先秦儒家孝德思想的集中表達。
二
先秦儒家繼承了歷史上“追孝”與“養孝”的思想,同時又創新性地賦予了諸多新的內容,使孝德思想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調節父子關系的思想系統。
《說文解字》釋孝曰:“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3](P398)《爾雅·釋訓》曰:“善父母為孝。”[4](P106)《唐律疏議》卷一:“善事父母曰孝。”[5](P12)可見,善事父母,是孝的最基本的含義。
第一,養親。《孝經·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6]百姓要善于利用天時地利的變化來獲取資源,行為舉止,小心謹慎,用度花費,節約儉省,以此用以供養自己的父母。孔子弟子子游向他問孝時,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7](P78)曾子亦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8](P1225)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7](P5151)在先秦儒家看來,養親是孝的最低層次的要求,甚至在孔孟看來,養親連孝也算不上,因為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德性。孝子要盡可能滿足父母在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使他們居有其所、腹有所食、體有所衣、疾有所治。
第二,敬親。物質上贍養只是孝的最基本要求。先秦儒家倡導精神上的贍養,心理上的敬。孔子不單倡導在物質生活上養親,更加倡導在精神生活上敬親。他認為“孝”要盡心侍奉,說話謙遜,行為恭敬,發自內心的和顏悅色。敬親體現著子女對父母的深厚的情感,這種情感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它會推動著子女踐行孝道。《禮記·祭儀》認為“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這里是從孝子的角度來說的,孝子之所以能夠有“和氣”、“愉色”與“婉容”,那是因為內心里充滿著對父母的愛,否則,孝子面對父母就不會有和顏悅色。從父母的角度來說,物質上生活好一些,這不但不是父母的全部需要,而且不是父母的最主要的需要,它只是父母生活的最基本的需要,精神愉悅才是父母生活中的重要精神需要,同時這也是對孝子的基本的要求。因此,“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7](P79)還不是真正的孝,真正的孝是“色難”,意即和顏悅色,一方面是孝子基于對父母的愛敬而面對父母能夠真正的和顏悅色;另一方面是父母基于對子女孝行的真正滿足而呈現出來的和顏悅色。
第三,諫親。孝德思想的形成與演變深受宗族制度與宗法制度的影響,父子關系在先秦時期不是平等的,但是有一定的對等性,意即父子雙方都是道德權利與義務的承擔者,對子來說要“孝”,對父來說要“慈”。可見,先秦儒家講孝并不要求子女對父母的絕對的順從。孔子雖然認為子女應該忘記父母的過錯,要敬重他們的優點,但是孔子提倡的敬,不是對父母無原則的敬,孔子反對愚孝,提倡諫親。《韓詩外傳》第八卷記載:
曾子有過,曾晰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為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菙則待苔,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9](P352)
這一故事說明,孔子并不認為曾子的作法是真正的孝。曾子之所以不躲避父親的懲罰,甚至蘇醒后還鼓瑟以悅父心,就在于他認為孝就是要順從父親的意愿,不僅曾子認為他的做法是對的,而且當時“魯人賢曾子”,都認為曾子的做法值得稱頌。孔子則用舜的故事教育曾子,父母的責備打罵確實有時因情緒或緣由,子女應當承受,但是如果父母的責備打罵太過激烈,使父母背上不義的罪名,則不能一味地順從,而應該適當地規勸甚至逃跑。否則,如果自己被父親打死,不但不能給父母盡孝,而且會使父母更加悲傷,同時還要擔當殺人的罪名,這才是真正的不孝。
順從與諫爭,是孝的一體兩面,兩者都是出于對父母的愛敬,順從是常態,諫爭是補充。諫爭的前提是父母有過,“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6](P32);諫爭的方式是含蓄地勸諫。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字不匱’。”[8](P1287)不能因為父母有過,而對父母橫眉冷對,惡語相加,而應當是細心、耐心加小心地“微諫”;諫爭的結果是敬而不違。“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7](P103)父母悔過且改,皆大歡喜;如果對父母多次諫爭,仍沒有效果,父母不為所動,仍然故我,孔子認為這個時候子女仍然要從內心里愛敬父母,既要努力尊重父母的意愿,更要以禮而行,努力做事而毫無怨言。
第四,安親。《呂氏春秋·孝行覽》中說:“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10](P381)可見,安親算是孝德思想中比較高的要求,也是很難做得到的事情。孝作為調節父子關系的道德規范,主要強調的是子女對父母的義務。安親,看似簡單,實則非常困難。它比“色難”、“無違”的要求高得多。父母安排的事情,子女都能做好;父母沒有安排的事情,只要子女能想到的,也都為父母做好;甚至父母對這些都很高興,很滿意。這樣算是安親了嗎?其實也未必。父母因為子女孝行生活幸福,這是安心的前提,或者說這是父母安心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可憐天下父母心,父母不但希望自己生活幸福,而且更加希望子女德業雙馨、生活幸福,這也是安親的重要內容。因此,安親不僅需要處理好與父母相關的事情,使父母生活幸福,而且需要處理好自己的事情,使父母心安。只要父母在世,子女凡事都要小心謹慎,力求合乎中庸之道。《大戴禮記·曾子本孝》中記述了諸多孝子的行為:“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痹亦弗憑;不茍笑,不茍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險涂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11](P82-83)。曾子為什么強調孝子要注意上述諸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敢忘其親”,不敢使“父母憂”也。心中裝著父母,把孝敬父母當作子女的第一等事,就會心存敬畏甚至是恐懼,怕因為自己不當或不義之舉而使父母不安心。
第五,喪祭。祭祀是先秦儒家孝德思想的重要源頭,先秦時期,儒家孝德思想繼承了祭祀傳統,但是極大地降低了祭祀祖先的重要性,祭祀的重要對象由先祖轉變為喪祭逝去的父母,從而對于逝去父母的喪祭成為孝的重要內容。“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者,生于喪祭之無禮也。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12](P342)。《論語·為政》中孔子亦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兩處資料都是孔子從禮的角度談孝,意即強調孝要合乎禮。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孔子本人是非常重視喪祭之事,父母在世,事親為重;父母仙逝后,與事親同等重要的事情就是喪祭之事;喪祭可以使我們思慕父母之情,讓我們在感情上感覺到父母猶在,這樣我們就可以仍然像以前一樣贍養父母,祭祀本身就是生前盡孝的延續;同時,喪祭可以使人近仁、能仁,進而能孝。反之亦然,如果不能很好地喪祭父母,則不能近仁,那就不能成為孝子。
先秦儒家不僅重視喪祭的重要性,而且對喪祭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其一,三年之喪。孔子認為“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三年之喪,實際上是二十五個月,服喪期間,孝子單獨居住在服舍(服喪的房間)內,不能參加政治、文化和娛樂活動。其二,嚴肅且節儉。在先秦時期,喪祭之事是頭等大事,關于哭喪、裝斂、出殯等都有規矩,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孔子在祭祀的時候也很講究:祭祀前為了要潔凈自己,必須進行沐浴;在沐浴之后,不能夠衣著綢緞,而必須穿著“明衣”;同時改變平時的飲食,不飲酒、不茹葷;居住也一定搬移地方,不和妻妾同房。孔子雖然重視喪祭之事,但是在他看來,喪祭不必追求物質上的奢華,而應當量力而行。因此,他認為“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余也。”[8](P202)其三,哀敬為本。“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7](P275)當父母逝去時,雖然喪葬要依禮而行,但更重要的是子女的哀思之情。如果沒有這種哀痛,外在的禮儀沒有任何價值;反之,如果有了這種內在的哀痛之情,即便有損于外在禮儀也是可以理解的。《孝經·喪親章》說:“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6](P38)當我們祭祀祖先的時候也要表里如一,內心地充滿對于先祖的恭敬之情,就好像真切地感覺到祖先、天神真在那里一樣。可見,哀敬是孔子喪祭觀中重要的情感標準,這種真切的哀思之情實質就是對父母以及祖先誠摯的敬,是生人對先人養育恩德的思念緬懷。
三
孝是先秦儒家文化系統中的一個重要要素,甚至可以說是核心要素。正如《孝經》開篇所講,“夫孝,德之本也”,它是“至德要道”,可“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6](P1)。可見,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在我國社會歷史的政治經濟發展及文化傳承過程中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代中國,“傳統文化熱”、“國學熱”方興未艾,《孝經》《弟子規》倍受追捧,全國各地“孝德”工程、“當代孝子評選”等等社會實踐活動不斷展開并推向深入,那么,對于傳統孝德思想,我們究竟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不論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態度,首先要解決兩個基本的問題,一是正確的立場問題;二是科學的方法問題。其一,正確的立場。立場不同,態度不同。對于先秦儒家孝德思想來看,如果站在傳統文化的立場上而無視社會發展,就一定會有相對保守的態度;反之,如果站在社會主義文化的立場上而無視傳統,也一定會有相對激進的態度。因此,正確的立場是科學態度的前提。對待先秦儒家孝德思想的正確立場是人民的立場、社會進步的立場。也就是說只要有利于人民利益及福祉的增加、有利于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我們就以積極、肯定的態度對待它;反之,如果不利于人民利益與福祉的增加、不利于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我們就以消極、否定的態度對待它。其二,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就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就是全面地、辯證地、歷史地看問題的方法。比如全面辯證的方法要求我們既要看到先秦儒家孝德思想的精華,也要看到其糟粕;歷史的方法要求我們既要看到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它在當代社會進程中的作用。總之,正確立場與科學方法是我們評價先秦儒家孝德思想的前提。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省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談時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習總書記提出的“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鑒別對待”、“揚棄繼承”是我們對待歷史文化尤其是傳統道德規范的基本原則,自然也是我們對待先秦儒家孝德思想的基本原則。
首先,根據“鑒別對待”的原則,要區分先秦儒家孝德思想中的精華與糟粕。《現代漢語詞典》對糟粕的釋義是:“酒糟、豆渣之類的東西,比喻粗劣而沒有價值的東西。”[13](P1427)糟、粕,兩字都是形聲字,從米,意味著與造酒有關,兩字的本義都是酒滓的意思。因此,《現代漢語詞典》釋義為“酒糟、豆渣之類的東西”,“沒有價值的東西”是其引申意。“糟粕”,此處我們是在其引申義上使用。先秦儒家孝德思想中的“糟粕”并非本身就是粗劣而無用,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化,原本有意義有價值的思想不適應當代社會的需要而“變成”了“糟粕”。也就是說,精華與糟粕之區分,本身就體現著社會的現代變化與現實要求,體現著當代價值觀的視野。先秦儒家孝德思想由于是應當時社會之需而形成的,不可避免地會有諸多范疇、論斷與思想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與當代社會的需要,從而成為糟粕。如“三年之喪”、“父母在不遠游”、“無違”、“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父子互隱”、“不登高,不履危”、“不茍笑,不茍訾”等等,諸多的論斷、觀念思想及要求,從當代社會看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此就成為應當予以拋棄的糟粕。
其次,根據“推陳出新”的原則,對先秦儒家孝德思想中的有益部分及其精華進行改造發展。關于孝德思想的地位,先秦儒家認為是“德之本”,是“至德要道”。孝是先秦儒家的重要范疇,甚至是核心范疇之一。但是孝德思想無論如何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文化或是社會主義道德的核心內容,因此,我們必須在重視先秦儒家孝德思想的前提下對其地位進行改造創新,讓孝這一概念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機構成要素,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系統的內在要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其作用。關于孝德思想的內容,比如上文所闡述的“養親、敬親、諫親、安親、喪祭”等內容,諸多是有益的甚至可稱為精華。孝德中的養敬順安等內容,在當代中國社會仍然有重要價值,以至于我們今天仍然流行講“孝敬”、“孝順”等詞匯,今天講的“孝敬”“孝順”與先秦儒家孝德的敬與順有聯系也有區別,是對先秦儒家孝德中的敬順思想的繼承與創新,這意味著即便是先秦儒家孝德中的有益部分甚至精華部分,我們有時候也難以照搬照抄照講,必須是根據現實生活的實際情況與具體需要來賦予其時代的新內容從而對其改造創新。比如先秦儒家孝德中的順親這一范疇,它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順親的背景是宗族與宗法制度下不平等的父子關系;其二,順親與諫親構成對立統一的一對范疇,其中順親是常態,諫親是非常態(父母行不義時),順親比諫親的要求具有更多剛性;其三,順親在父子關系上具有單向性、非對等性。這些特點在今天我們倡導的“孝順”規范中都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孝順所指陳的對象不僅僅是對父母,而且包括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有親戚關系的長輩;由于現代家庭關系的平等性,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父母與子女交流比較充分,父母更多地對子女成長提出指導性建議,“順”并不是這一時期父對子的剛性要求;孝順更多地體現在子女成年后對父母的感恩與回報。
最后,根據“揚棄繼承”、“古為今用”的原則,充分發揮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我們雖然不可能回到倡導“孝治天下”的時代,但是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對于當代社會建設無疑具有現實意義。比如個體德性的重塑。德性衰微具有世界性,近代以來,隨著理性與技術的崛起,德性不斷失落,越來越不被人們所重視。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隨著商品、貨幣地位的不斷上升,德性的地位不斷下降,直到被人們忽略甚至遺忘。我們不再像先秦儒家那樣把德性的重塑希望寄托于先天的人性基礎上,我們更多地強調教育與實踐,教育與實踐的場域與主體固然很多,無論如何,家庭與父母對子女德性的培養與鍛煉是個體德性成長與完善的最重要的基礎。而在家庭教育中,孝德教育是一個最佳的途徑。父母對子女的愛是把雙刃劍,過分地溺愛不僅傷了孩子,而且最終也會傷到自己。我們不僅要讓子女感受到父母的愛,感覺到家庭的溫馨,而且也要及早對子女進行孝德教育與實踐,讓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但可以鍛煉孩子的獨立意識,而且有利于孩子德性成長。孩子在不斷地被給予中體驗到的是被愛,助長的是自我中心意識;只有在給予中才能真正地體會到愛,才能真正體現自我價值。所以,孩子只有在回報中才能懂得感恩,只有在分享中才能懂得尊重,只有在困難中才能懂得勇敢,只有在做事中才能學會責任與擔當。總之,我們可以通過孝德教育與實踐把德性的種子早早地植入孩子內心深處,讓它伴隨著子女的成長不斷地成熟完善。成年人也普遍存在德性缺失現象,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可以使我們成年人反省自身,重返初心,省察克己,重塑德性。當然,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對于家庭和睦、社會和諧都有積極的價值,對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必將發揮其積極作用。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卡西爾.人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3]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葉青,注.爾雅[M].大連:大連出版社,1998.
[5]長孫無忌 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
[6]胡平生.孝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6.
[7]朱熹.四書集注[M].長沙:岳麓書社,1988.
[8]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9]賴炎元,注譯.韓詩外傳今注今譯[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10]張雙棣 等,譯注.呂氏春秋譯注[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1]錢世明.說忠孝[M].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
[12]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M].濟南:齊魯書社,2013.
[13]現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呂本修,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校刊部副教授,山東省倫理學與精神文明建設研究基地學術骨干。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理論創新工程項目“習近平道德建設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