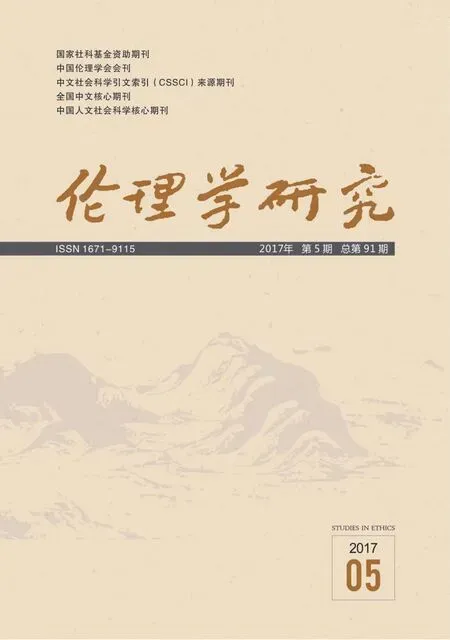論政治社會的共享目的
——以羅爾斯為視角
余 露
論政治社會的共享目的
——以羅爾斯為視角
余 露
羅爾斯一方面恪守自由主義的中立原則,另一方面又拒斥霍布斯式的“私人社會”,認為良序社會的正義原則及相應的制度是一種內在善,是公民應為之奮斗的共享的終極目的,兩者形成了緊張關系。為了解釋其張力,羅爾斯援引奧克肖特關于事業聯合體和公民聯合體的區分指出,有著共享目的的政治社會不同于嚴格意義上的共同體,而只是實踐聯合體(公民聯合體),它相容于中立原則。但事實上,對于羅爾斯而言,中立原則和共享目的的和解依賴于更深層次的共享——對自由及其相關價值的共享。正是奠基于這兩個層次的共享目的,政治認同得以確立,“穩定性論證”才得以完成。
政治社會實踐聯合體政治正義共享目的政治認同
大多自由主義者都提倡特定類型的國家中立(state neutrality)①。這一原則強調“公共的政策、制度等應該平等地包容所有值得的善觀念”[1](P126),它并不要求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現實影響是中立的,而是認為國家/政治社會在對待不同的善觀念時要恪守中立的立場,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作為自由主義陣營的巨擘,羅爾斯典范地詮釋了中立原則,并試圖借此探討理性多元社會的長治久安之道。然而,羅爾斯又旗幟鮮明地指出,良序政治社會建立而踐行正義的制度是一種偉大的內在善,是公民所應共享的終極目的。因此,對羅爾斯而言,如何理解價值中立與共享目的之間的關系便成為重要的問題。而且,這還引出了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自由主義的中立原則限度何在?共享目的在政治社會中有何作用?
本文將從羅爾斯出發,通過對相關文本的分析來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探討,找尋答案。首先,文章將在第一部分通過概述羅爾斯的“穩定性論證”來呈現他對中立原則的持續追求,進而指出羅爾斯并未因此落入“私人社會”的窠臼,他認為政治社會的公民持有某種具有內在善的共享目的。然而,第二部分將指出,由于共享目的對于內在善的強調,它的確與中立原則構成了緊張關系。于是,理解政治社會的善與中立原則之間的張力,將是第二部分的主要工作。在第三部分,我們通過進一步剖析發現,中立原則與共享目的的和解倚賴于公民共享的自由價值,政治社會實際上在兩個層次上擁有共享目的。最后,本文將嘗試性地探究共享目的與政治認同的關系,以彰顯共享目的在政治社會中的作用。
一、政治社會的善
“歷史地看,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共同主題是,國家決不能偏袒任何完備性學說及其相關的善觀念。”[2](P202)羅爾斯自覺地秉承自由主義的這一原則,努力地確保政治自由主義在目的上的中立性:基本制度的設計并不旨在鼓勵特定的完備性學說。正是這一追求,促使羅爾斯將對正義的“穩定性證明”從“一致性論證”調整為“重疊共識論證”。
在《正義論》中,羅爾斯為穩定性提供的證明被稱為“一致性論證”。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道德心理學角度描繪良序社會的成員如何經由權威道德、社團道德和原則道德獲得正義感;第二階段關注正義感與善觀念怎樣共同發揮作用、維護正義結構。第二階段最基本、最核心的論證是由康德式的解釋給出的,它將一種特殊的人性和道德能力指派給人們——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并認為實現這一人性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將正義感(按照正義原則行事的欲望)作為調節性的欲望。換言之,選擇正義原則并按其行動,是內含于人性的要求。羅爾斯試圖借助這一論證表明,人們在原初狀態下選擇的兩個正義原則具有穩定性:即當無知之幕揭開,人們進入到由正義原則支配的政治社會中,他們會形成正義感并依據正義原則行動,當正義原則與他們的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也會自覺地讓利益受正義原則的規導。作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人們會遵循正義原則,而正義原則“規定了在不同的宗教和道德信仰之間以及它們所屬的不同文化形態之間進行調解的協議”[3](P173)。
然而,一致性論證并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各宗教、哲學和道德學說及所屬文化形態間的差異,因為康德式的論證將一種特殊的道德人格賦予人們,這種道德人格確保人們“接受相同的正義觀,并似乎還接受相同的完備性學說,那個正義觀正是此學說的一部分,以及是從此學說中推導出來的”[4](P554)。在這里,“正當原則的證成……是奠基于某種特定的人性觀,這種人性觀界定了什么是人最重要的‘好’,并促使人有最高序的欲望去實踐人的本性”。這種對人的詮釋是完備性的,“它界定人的本質,限定人理解自我的方式,規定人的根本利益,以及人如何看待自身與他人的倫理關系”[5](P201-202)。但是,民主社會的公民不可能就完備性的人性學說達成一致的看法。羅爾斯自己就曾設想例外情形:“假定即使在一個良序社會中也有這樣一些人,對他們來說肯定其正義感不是一種善。假定由于他們的目標和需要以及他們本性的特有性質,對善的弱描述不能成為他們保持這種調節性情操的充分理由。”[3](P455)也就是說,在羅爾斯看來,雖然道德人格確保了正義感具有壓倒性的動機地位,但仍有一些人不依正義原則行事。我們當然可以繼續援引道德人格的普遍性來指責這些人不合乎理性,進而將他們排除在社會合作系統的考量之外,但這難免武斷。“或許羅爾斯認為,‘康德式的解釋’只在那些相信它的人身上才是動機性的力量。”[6](P887)那如何應對這些反對者呢?巴里指出羅爾斯只有兩條路:走向重疊共識論證;退回霍布斯,援用懲罰手段強迫反對者遵從正義原則。羅爾斯并不否認懲罰性手段的作用,但“穩定性問題并不是讓那些反對某一觀念的人來分享該觀念的問題,或者說,如有必要的話,通過有效制裁讓他們遵循該觀念來行動的問題”[4](P553)。更為嚴重的是,它違背了中立原則的要求,并沒有公平正義地處理不同宗教和道德學說之間的沖突。于是,羅爾斯走向了“重疊共識論證”。
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試圖利用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交迭共識)來為正義原則的穩定性作論證。這一論證指出,民主社會的公民能就政治的正義觀念經由臨時協定、憲法共識形成重疊共識,并以此調節因所持有的多元化完備性學說而導致的在政治領域的矛盾。更進一步,由于政治價值的重要性無與倫比,它們又兼容于公民的完備性學說,所以它們具有壓倒其他一切價值的優先性。隨著政治合作因重疊共識不斷取得成功,政治正義觀念的穩定性便得到了保證。
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清晰地看到,因為康德式的解釋“沒有考慮多元論的境況”而不具現實性,羅爾斯放棄“一致性論證”,走向了“重疊共識論證”。這背后的動力正是對中立性的追求。羅爾斯竭力避免將穩定性論證建基于某一獨特的善觀念(如康德式的人性),而試圖中立地、無偏倚地對待所有完備性的道德學說、哲學學說和宗教學說。
這似乎讓羅爾斯陷入了霍布斯式的“私人社會”:個人和小型共同體都有自己的目的,政治制度安排僅僅被視作達致特殊目的的手段,“正如每個人在沿著公路旅行時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地”[3](P412)。但在羅爾斯看來,并非如此。他指出,秩序良好的政治社會有被其公民共享的目的,即由正義觀念(原則)所規制的基本政治制度,這一制度并不僅僅因為實現了人們的利益、滿足了人們的需要而善,它本身就是善的,它的成功實施是所有社會成員共享的最終目的。古德曼(Gutmann)在評論桑德爾對羅爾斯的批評時曾說:“如果我們假定,按照定義,我們的認同由善構成,那么我們就必須將正義感看作認同(不可分割)的部分。我承諾將他人視作平等的人并因此尊重他們的宗教自由,恰如我作為猶太人并因此與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慶祝逾越節一樣,都是我的認同的基本部分。”[7](P311,note14)羅爾斯極其贊許古德曼的看法,認為他的說法“肯定是正確的”,“互相以正義對待這種終極目的是公民身份的組成部分”[8](P240頁腳注)。
羅爾斯的這一基本立場貫穿了其思想始終,并沒有隨著穩定性論證的改變而發生變化。在《正義論》中,羅爾斯指出,“人們事實上分享著最終目的,他們把他們共同的制度和活動看作自身就是善的”[3](P413)。作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物,遵循正義制度、將正義感置于動機系統的頂層是實現人性的必要條件,因而,人們會認可正義制度、正義觀念并意愿按其行事。這樣,我們進入到一種“人類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成員們從彼此的由自由的制度激發的美德和個性中得到享受,同時,他們承認每一個人的善是人類完整活動的一個因素,這種活動的整個系統是大家都贊成的并且給每個人都帶來快樂”[3](P414)。在其本科論文《簡論罪與信的涵義》中,青年羅爾斯指出,人格只有在因信而結合的宗教共同體中得以體現。這里,我們似乎發現了類似的斷言,“一個良序社會的成員們有共同合作以便以正義原則允許的方式實現他自己的和他人的本性這一共同目標,……正是通過維護這些公共的安排,人才能最好地表現他們的本性,才能獲得對每個人可能的最廣泛的調節性美德”[3](P417-418)。
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依舊認為,良序社會中的公民擁有著共同的終極目的:“他們……認肯相同的政治正義觀念。這意味著他們共享一個非常基本的政治目的,而這一政治目的具有高度的優先性:即支持正義制度的目的及因此而相互承認對方之正義的目的,更不必說許多也必定為他們所共享并通過其政治安排來實現的其他目的。此外,政治的正義目的也許是公民相互間最基本的目的,他們通過這些最基本的目的來表現他們構想成為的那種個人。”[2](P214-215)只是,羅爾斯不再談及人性,更不強調共同體是實現人性的必要條件,而是認為,無論公民自身持有怎樣的完備性學說,他們都會就“憲法根本”(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和基本的正義問題②達成重疊共識,而這一共識的核心是政治正義觀念。受正義觀念規定的憲法根本就構成了公民共享的根本目的,這樣的政治社會便是公平正義的良序社會。這一社會在兩個方面是善的。在個體的意義上,它對于個人而言是善的。一是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深刻地體會到實踐兩種道德能力是善的;二是因為,“該社會確保他們享有正義的善和相互尊重與自尊的社會基礎”。在社會的意義上,共享的目的需要許多人的合作方可達到,“建立并長期成功地運行理性而正義的……民主制度……乃是一種偉大的社會善,值得我們尊重”[2](P216)。
二、共享目的的中立性
在一定的意義上,共享目的發生了與穩定性論證的轉向相應的變化,它不再訴諸于以康德式的人性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但是,它的內涵卻始終如一、前后一致:首先,良序社會應該建立并踐行理性而正義的民主制度,這是公民應該為之奮斗的終極目的;其次,這一目的并不僅僅在工具性的意義上為善——有助于個體過上好的生活,它更是一種內在善,正義相待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善;再次,這一目的具有壓倒性的優先地位。
羅爾斯這一立場讓人心生疑問:它在什么意義上是中立的呢?德沃金曾如此談論中立性:“政治決定必須盡可能地獨立于任何關于好生活或賦予生活以價值的特殊觀念。”[9](P191)如果對政府一般結構和政治運行進行規定的根本原則必須體現某種內在善,公民必須在應然的意義上共享著某種終極目的,這樣的政治社會到底與有著完善主義傾向的、嚴格的政治共同體又有何區別呢?
羅爾斯指出,良序的民主社會顯然不同于共同體,共同體是依靠完備性學說統一起來的、特殊類型的聯合體(association);而政治社會卻有著與聯合體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民主社會是“完全而封閉的社會系統”——“在它自足且給予人類生活的所有主要目的以合適地位這一意義上,它是完全的。……它……又是封閉性的,……人們只能由生而入其中,因死而出其外”[2](P42)。這一特征被后來的學者深為詬病,“現實中如過江之鯽的移民浪潮足以證明,即使是在憲政民主國家中,‘社會成員資格’也并不都是先行給定的,而是有相當部分由主體自愿選擇的”[10](P165)。但周濂后續的討論實際上提供了理解羅爾斯的進路:羅爾斯所強調的是“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以法律地位’來界定的公民身份”[10](P170-171)。而且,羅爾斯并非在實然的意義上言及公民在現實政治社會中獲得公民身份,而只是在應然的意義上指出良序社會的成員應被視為“平等而自由的公民”——“這些正義原則必須在市民社會的背景制度中給予基本自由和機會以優先性,它們使我們能夠首先成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并根據這種身份將我們的角色理解為個人”[2](P42)。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社會的完全性得以理解:只要兼容于政治的正義觀念,公民由其完備性學說所界定的各式各樣的特殊的終極目的就具有平等的地位,受正義觀念規制的憲法為公民形成、修改、追求其特殊善觀念提供了足夠的背景支持。
其次,良序的民主社會“沒有任何……在完備性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目的和目標”,它只有“憲法意義上的特殊社會目的,在憲法前言中所陳述的那些目的……必須歸于一種政治的正義觀念及其公共理性的名目之下”[2](P41-43)。
在討論完兩者的區別之后,羅爾斯增加了這樣一個腳注:“本節對社會與聯合體所作的區分,在很多方面類似于邁克·奧克肖特……對實踐聯合體與目的性聯合體所作的區分。”[2](P43頁腳注)
在《論人的行為》一書中,邁克·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區分了兩種模式的聯合體:事業聯合體(enterprise association)和公民聯合體(civil association)。事業聯合體是人們在追求“某些共同的目的、某些共同獲得的實質性事態或某些持續地被滿足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關系。在其中,踐行者(agent)是由于共同地追求某些想象的或渴望的共同滿足而關聯起來的,他們將需求之滿足作為共同目的加以承認,也通過自己的選擇來擺脫這種關系。奧克肖特進一步指出,只要事業聯合體的目的不是轉瞬即逝或者被確信會被形式化所損害,那聯合體中的踐行者就會承認某些規則或類規則的安排具有權威性。但這些規則并不能確認更不用說定義一個聯合體,它們與聯合體的目的相關聯,是實現聯合體目的的手段。公民聯合體則不同,它是踐行者因實踐(practice)相互關聯而形成的,在這種關系中,人們共同地認可某些慎思(如用法或規則)并在自主選擇的行為中明智地遵守這些慎思。公民聯合體有兩個重要特征:首先,它是一種形式的而非實質的關系,人們是因使用共同的“語言”或同樣的表達而非因擁有同樣的信念、目的或利益而形成的聯合體;其次,它是一種平等的關系,這并非因為所有使用者都有著同等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都關心相同的技能并被指定具有相同的地位[11](P112-122)。
特里·納丁(Terry Nardin)指出,羅爾斯所描述的政治社會并非如其所言是“公民聯合體”(“實踐聯合體”),而恰恰相反,他筆下的政治社會是“事業聯合體”(“目的聯合體”),因為“國家似乎就是個體聯合起來追求共享目標的聯合體——這個聯合體的規則僅僅是那種追求的手段,它們只有在服務于個體利益的意義上才對聯合體具有約束力。羅爾斯不僅將制度也將社會本身理解為個體間的‘社會合作圖式’,規則只有在個體從參與社會合作中獲得‘公平份額’的意義上才具有權威性”[12](P263)。
羅爾斯回應道,納丁抓錯了重點。關鍵點不在于政治社會是一種合作圖式,而在于合作的方式及其取得的成就:良序的民主社會里,“人們是作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來進行合作的,他們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在理想的情形下)是一種具有正義背景制度的公正的基本機構,這些背景制度是實現正義原則并給公民提供著滿足他們作為公民之需求的全能目的性手段的背景制度。他們的合作是確保他們相互間的政治正義。而在聯合體中,人們是作為聯合體的成員來進行合作的,他們所要實現的正是驅使他們加入該聯合體的動機,而這一點又會隨著他們從一個聯合體到另一個聯合體而發生改變。作為公民,他們合作實現的是他們共同分享的正義目的;而作為一聯合體的成員,他們合作實現的目的卻分屬于他們各自持有的不同的完備性善觀念”[2](P43頁腳注)。結合之前的討論,我們很容易理解羅爾斯的回應,羅爾斯從未將良序社會僅僅看作達致個體善觀念的工具,而是認為其本身就是一種內在善,這種內在善并不因個體所持有的特殊善觀念而有所差異或發生改變。
羅爾斯認為,他所提倡的政治社會只能是公民聯合體或者實踐聯合體。這樣的政治社會具有兩個典型的特征:一方面,公民有各自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的完備性善觀念,他們僅僅就“憲法根本”所依據的政治正義原則形成一致的意見,這也是政治社會所共享的目的;另一方面,人們在這一聯合體中被平等地對待,社會的基本制度給予了每個個體公平的基本善,以確保他們兩種最高階的利益,并在此基礎上追求、實現自己特殊的善觀念。
也就是說,在羅爾斯看來,即便政治社會將正義原則視為共享的終極目的,但這一目的并不偏袒或鼓勵任一特定的完備性學說,它賦予了一切合乎理性的善觀念以平等的地位,因而它仍是價值中立的。如第一部分所說,這種中立性的訴求促成了羅爾斯從前期到后期的轉變。在《羅爾斯后期正義理論研究》一書中,楊曉暢指出,羅爾斯的正義觀念前后期之間有四個重要的變化:性質從奠基于康德式道德主體觀念之上的完備性學說轉變為獨立于諸完備性學說的政治正義觀念;建構方式從道德建構主義轉變為政治建構主義;外延從“作為公平的正義”之兩個原則擴展為“自由主義的正義觀念家族”;作用則在保留規范引導社會基本結構的基礎上增加了為公共證成奠基的功用[13](P143)。其中,最核心的變化當屬性質的轉變——從倫理正義走向政治正義。“在《正義論》中,羅爾斯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為現代民主社會提供一種普遍合理的社會公正倫理學基礎支持,其理論核心是建立一套既能確保個人自由又能維護社會公平秩序的‘公平正義’原則。……‘公平正義’本身……既是其社會正義倫理的理念基始,又成為羅爾斯心中建構現代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念基礎。”[14](P623-624)也就是說,《正義論》時期,正義原則不僅規范著制度,還帶著濃郁的價值屬性。到《政治自由主義》,羅爾斯明確地宣稱,他要“尋求一種政治的正義觀念”,這一正義觀念有三個特征:首先,它適用于現代立憲民主制度結構;其次,它獨立于一切完備性學說;再次,它的內容是借助隱含在民主社會公共政治文化中的重疊共識理念得到表達的[2](P11-14)。羅爾斯一再強調,政治正義適應的政治領域是個獨立的領域,它無需以任何完備性學說為前提,而它與完備性學說之間的關系則留待每個公民自己解決。似乎,羅爾斯后期所推崇的正義觀念已盡可能地抹去了價值性。換而言之,作為共享目的的正義原則與中立價值達成了完全的和解。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三、共享目的與政治認同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先引入科特·拜爾(Kurt Baier)的一對重要概念。在《正義與政治哲學之目的》一文中,拜爾區分了“正義概念的觀念”(a conception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和“正義的觀念(或原則或標準)”(a conception or principle or criterion of justice)。“正義概念的觀念”指對“在一個語言共同體中擁有正義概念意指什么”的看法,正義概念(the concept of justice)是一個規范的道德觀念,它將正義和非正義行為區分開來。在拜爾看來,安克魯-撒克遜語言共同體有單一且內在一致的正義概念,但哲學家就這一概念有不同的看法即不同的觀念。“正義的觀念”是羅爾斯的術語,它是關于“如何才能滿足正義之道德要求”的看法。在此基礎上,拜爾指出,“我們已經就正義的觀念存在共識,雖然我們也許還沒意識到這一點,因為我們還沒認識到這是關于我們正義概念的正確觀念。”這一共識就是公平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equitability),這一原則只包括程序性的政治憲法原則,“我們已有的憲法共識似乎足以支持穩定的社會統一”[15]。
借助拜爾的區分和評述,我們可以推測,羅爾斯的重疊共識所彰顯的“價值中立”是有限度的:“價值中立”只是針對諸多“正義概念的觀念”的中立,其背后有著更為底層的、共享的“正義概念”。這一推測可以得到兩方面證據的支持。第一,羅爾斯一再強調重疊共識要從隱含于公共政治文化中的根本性直覺出發,而且,在重疊共識的形成過程中,羅爾斯納入了很多實質性的自由主義價值取向,比如賦予了公民以平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甚至將這些價值訴求視作討論的起點。第二,羅爾斯對多元性的考慮也是有所限制的:并非所有的善觀念都可以被納入到政治考量中去,只有那些合乎理性的善觀念才被允許。正如墨菲(Mouffe)所指出的,羅爾斯對合乎理性的學說和不合乎理性的學說間的區分,實際上是“在接受自由主義原則和反對這些原則的學說間劃了條界限”,有些完備性學說之所以被視作不合乎理性的,只是因為它們“會在公共領域危及自由主義原則的支配地位”[16](P4)。實際上,羅爾斯自己曾清晰地表明過這一立場。在《重疊共識理念》一文中,他說,政治正義觀念可能不止一個,但“適合立憲政體的任何可行的政治正義觀念,事實上必須是自由主義的”[4](P482-483)。羅爾斯的理論針對的是特定類型的憲政民主國家,這類國家是“自由主義化”的國家,自由及其相關價值作為底層的價值已深深植根在公共的政治文化當中,被人們所共享。正如周保松所言,在“自由主義化”的民主社會,其中的多元宗教學說、道德學說都已“將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內化成信仰的一部分。這些理念包括道德平等、個人自主、基本權利和寬容等。經過這樣的轉化,他們不再覺得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是不得已的政治和道德妥協,而視之為現代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5](P248)。
論述至此,我們發現了羅爾斯思想中兩個層次的“共享目的”:一個層次是“顯性的”,即持有多元的完備性學說的公民以政治的正義觀念及相應的政治制度、活動為共享目的;另一層次是“隱性的”,即民主憲政國家或良序的政治社會里,公民共享著自由主義的價值——自由及其他相關價值。在隱性的自由主義的價值基礎之上,顯性的共享目的確實可以與中立原則相容,因為它并不偏袒也不給任何特殊的完備性學說以優先性。完備性的學說只要接受自由主義原則,就可以在政治領域中獲得平等的考量。與之相應,中立性是一個“范圍概念”(range concept),在羅爾斯那里,中立性的范圍“通過只納入普遍原則所允許的生活方式而排除另一些生活方式來彰顯”[17](P502)。
正是借助這兩個層次的共享目的,羅爾斯完成了穩定性論證,也達致了公民對于良序社會的政治認同。穩定性論證是依靠重疊共識論證完成的。而人們之所以能就正義原則及其制度形成重疊共識,是因為他們共享著自由及相關價值,相互以正義相待是“自由主義化”的內在要求。建立在自由主義政治觀點基礎之上的穩定性,“它的目標是希望取得合理且理性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的接受,并因此訴諸于他們的自由公共理性”[4](P552)。而這正是契約論者處理政治認同問題的進路。“Rawls理論關注的不是認同問題,然而它的若干重要概念——如‘交疊共識’……卻是自由主義者談論國家認同不可或缺的工具。”[18](P114)
一般而言,政治認同即個體對政治組織的認可、歸屬和效忠③,它表現在個體對政治組織的根本原則的接受并自覺地依其來規范自己的政治行為。契約論者在應然的意義上追問政治認同何以達成,即政治組織滿足何種條件才會被其治下的成員所認可和接受。這并非“實際的被接受”,而是一種“合理的可接受性”[10](P150)。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對于穩定性的探討實際上就是在處理政治認同問題。一致性論證和重疊共識論證表明,“有理由期望全體公民都能夠贊成的方式”,便是憲法根本和基本正義問題符合正義原則的要求。對《正義論》時期的羅爾斯而言,作為權力的行使主體,國家唯有憑借正義原則方可得到其成員的認可。更準確地說,只有當國家的立憲、立法以及實操都符合正義原則時,國家才可能獲取其治下人們的認同,因為這是與人性相契合的。到《政治自由主義》,羅爾斯否認了一致性論證,但其核心立場卻未發生變化。“作為公平的正義”觀念的政治價值仍被視作為一系列基本問題——憲法根本和基本正義問題提供了理想的答案,也就是說,當國家的憲法根本——“具體規定政府一般結構和政治過程之根本;具體規定公民的平等之基本權利和自由”——符合“作為公平的正義”時,國家就會得到公民的認肯,因為公民能就政治正義原則形成重疊共識并接受其調節。
在羅爾斯的文本中,正義的穩定性與政治認同是緊密關聯的。共享著自由價值的公民們對民主憲政國家達致政治認同是借助穩定性論證呈現的。而一旦政治認同達成,正義的穩定性也得以確保。“‘政治認同’就是指一個人對這些政治價值的接受與肯定。如果一個社會中絕大部分成員愿意實踐上述民主社會的政治德性,以之作為彼此解決社會爭議的憑借,則政治共同體就獲得公民們的認可,也獲得了穩定。”[18](P116)
如果本文的討論是可接受的,那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中立性”是一個“范圍概念”,自由主義的國家中立原則有一定的適用范圍,只有“值得的善觀念”才會被平等地對待,“值得”最外圍的邊界是由其共享的自由主義的價值所框定的,其內部范圍又因自由主義者各自倚重的價值而有所差異;二是,政治社會必定會有共享目的,顯性的制度共識(或原則共識)和隱性的價值共識,缺一不可,這是公民對政治社會達致政治認同的基礎。
[注 釋]
①Peter Balint區分了三種形式的中立,即證成中立、意圖/目的中立和結果中立(neutrality of justification,intent and outcome),參見 Peter Balint,“IdentityClaims:WhyLiberalNeutralityisthe Solution,Not the Problem”,Political Studies,2015,Vol.63,pp.495-509。本文因關涉羅爾斯,故只討論前兩者,而不考慮現實影響和結果。實際上,羅爾斯在拉莫爾(Larmore)啟發下也做過類似區分:程序中立(procedural neutrality)、目的中立(neutrality of aim)和效果/影響中立(neutrality of affect or influence)。參見羅爾斯:《羅爾斯論文集》,第517-520頁。
②在羅爾斯看來,憲法根本和基本正義問題包括兩類:(1)對政府一般結構和政治運行過程進行規定的根本原則;(2)公民平等的基本權利。詳細討論參見《政治自由主義》第六講第五節“憲法根本的理念”。
③政治認同依據認同對象可區分為國家認同、政黨認同等不同類型。但因本文的話題僅僅關涉羅爾斯,其文本聚焦于政治社會;而且,現代政治中,國家是政治的主要活動場域、也被公認為是一定疆域內使用強制性權力最合適甚至唯一合適的組織,所以,本文將“政治認同”簡單地等同于“國家認同”。本文不使用“國家認同”一詞,是因為“國家”一詞意義含糊,易引起爭論。
[1]FrankLovettandGregoryWhitfield.Republicanism,Perfectionism and Neutrali t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ume 24,Number 1,2016,pp.120-134.
[2]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M].萬俊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3]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4]羅爾斯.羅爾斯論文全集[M].陳肖生,等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3.
[5]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增訂本)[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6]Brian Barry.JohnRawlsandthe Search for Stability[J].Ethics,Vol.105,No.4(Jul.,1995).
[7]Amy Gutmann. Communitarian Critics of Liberalism[J].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14,No.3,1985.
[8]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M].姚大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9]Ronald Dworkin.Liberalism[J].in A Matter of Principl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0]周濂.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11]Michael Oakeshott.On Human Conduc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2]Terry Nardin.Law,Morality and the Relations of States,Princeton[M].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13]楊曉暢.羅爾斯后期正義理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4]萬俊人.現代政治自由主義的建構[M].政治自由主義(附錄).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15]Kurt Baier.Justice and the Ai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J].Ethics,Vol.99,No.4,1989.
[16]Chantal Mouffe.The Limits of John Rawls'Pluralism[J].Theoria: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Vol.56,No.118,2009.
[17]Peter Balint.Identity Claims:Why LiberalNeutrality is theSolution,Not the Problem[J].Political Studies,2015,Vol.63.
[18]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M].臺北:楊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余 露,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講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協同創新中心、湖南師范大學共享思想研究中心成員。
湖南省教育廳優秀青年項目“政治認同視域下的愛國美德研究”(17B177);湖南師范大學共享思想研究中心項目“政治社會的共享目的”(17GX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