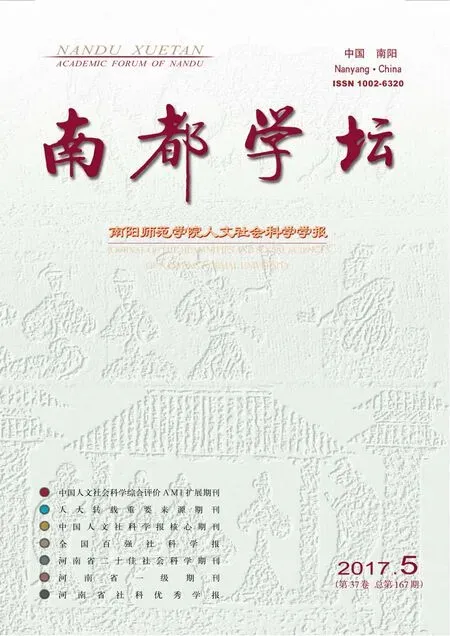上封事制度與漢代政治的關系
徐 福 舉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
上封事制度與漢代政治的關系
徐 福 舉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
封事是源于漢代的一種密封奏章,上封事制度的產生與漢代中期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尚書機構的發展是上封事制度產生的客觀原因,而漢宣帝與霍氏家族的權力斗爭又是上封事制度產生的具體因素。上封事制度對漢代政治的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彈劾權貴、對皇帝進行諫議、舉薦人才三個方面。漢代封事易漏泄,保密性不強,責任多在于皇帝,因而上封事者多遭受政治報復,上封事制度有其制度上的缺陷。
上封事;密奏;漢宣帝與霍氏;漢代政治
上封事制度源于漢代,其時文獻多見“上封事”或“奏封事”之詞。《漢官儀》曰:“密奏以皂囊封之,不使人知,故曰封事。”[1]這里的“封事”,意指臣下上奏給皇帝的秘密奏章。作為密奏,封事與漢代政治具有密切的關系。上封事制度的產生,與霍光死后漢宣帝和霍氏家族的政治斗爭密切相關,是宣帝與霍氏家族政治斗爭的產物。對于漢代上封事制度的基本狀況,已經有不少文章論述過①廖伯源《漢“封事”雜考》,初刊于中國上古秦漢學會編印《中國上古秦漢學會通訊》創刊號,收入氏著《秦漢史論叢》,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95-204頁;王劍《漢代上封事考論》,載《學習與探索》,2005年第6期,第201-205頁;袁禮華《試析漢代的上封事制》,載《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第127-131頁;王慶云、趙麗《漢代封事的內容及其運作》,載《唐都學刊》,2011年第4期,第25-29頁;趙麗《漢代封事的產生及意義》,載《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第5期,第21-24頁;代洪寶、康麗瀅《試論漢代上封事制度》,載《平頂山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第65-68頁。。但是上封事制度與漢代政治的密切關系并沒有深入的討論,本文擬對此一問題作進一步的考察。
一、西漢中期的政治狀況與上封事制度的產生
(一)尚書機構的發展是上封事制度產生的客觀原因
秦及漢初,尚書為少府屬官,是皇帝身邊的任事小臣,因其在殿中主管收發文書并保管圖籍,故稱尚書。卜憲群認為,約在武帝后期時,尚書已“處于轉呈章奏的核心地位”[2]274。此后尚書機構獲得了更大的發展,這種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體現是“副封”制度的產生。“副封”就是臣民在給皇帝上奏時,奏疏要提供正副兩本,領尚書事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3]3135。關于副封制度的形成時間,祝總斌認為:“估計大權獨攬的武帝之時不可能也不允許出現,而只有形成于霍光輔政之時,最合乎情理。而這正是領尚書事權力擴大的標志之一。”[4]副封制度的產生有其合理性,因為隨著尚書機構所要處理的政務越來越多,一些無價值的奏章確實沒有上奏給皇帝的必要。但是另一方面,副封制度對于霍光以領尚書事的身份控制朝政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在霍光死后,宣帝即聽從魏相的建議,“去副封以防壅蔽”[3]3135。
關于“去副封”是存在歧義的,宣帝并非真的廢除了副封制度。《漢書·霍光傳》載霍光死后,霍山領尚書事,諸儒生多上書揭發霍氏,“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3]2954,可知副封仍然存在,霍山仍然具有開發副封以及處理奏疏的權力,所以副封制度并沒有被廢除。實際上“去副封”與設立上封事制度實為同一事。首先,魏相奏去副封,與宣帝設立上封事制度,在時間上相近;其次,在目的上,兩者皆為“防壅蔽”“知下情”;最后,《霍光傳》載霍山利用副封制度隔斷儒生們的上書以后,“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3]2954,可知上封事是對付副封制度的一個策略,這可以作為一條旁證。這一觀點廖伯源先生已經進行過討論[5]196-197,可以參看。
副封制度的產生,凸顯了尚書機構的重大發展,而封事的特征恰恰是無副封,這顯示了上封事制度與尚書機構的密切關系。設立上封事制度,目的是對尚書機構權力進行制約。可以說,尚書機構在西漢中期的重大發展,正是上封事制度得以產生的客觀原因。趙麗認為自武帝以來“加強中央集權、強化君主專制的歷史趨勢是封事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6]。這樣的解釋未免太過于寬泛,沒有針對性,很多制度的發展似乎都可以用之來解釋,并且上封事制度與加強中央集權也無明顯的關系。結合封事“無副封”“不關尚書”的特點,將其產生的根本原因系之于西漢中期尚書機構的發展更為合理。
(二)宣帝和霍氏家族的權力斗爭是上封事制度產生的重要因素
一個制度的產生,常常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上封事制度的產生也是這樣。尚書機構的發展,是上封事制度產生的客觀原因。霍光死后,漢宣帝與霍氏家族的權力斗爭則是上封事制度產生的具體歷史因素。
《漢書·宣帝紀》載地節二年五月,“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乃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3]247,表明上封事制度的官方設立時間為宣帝地節二年五月,霍光死后,宣帝親政之初。設立上封事制度的建議源于魏相,正是他建議宣帝“去副封以防壅蔽”,才促成了上封事制度的產生。魏相曾被霍光下獄,與霍氏嫌隙頗深,王鳴盛說:“魏相為河南太守,為霍光所惡,下之廷尉,獄久系始赦,后為御史大夫,遂奏霍氏專權,舉發其弒許后,事雖未免報復私仇,然其言則未可以挾私訾之。”[7]王氏所說魏相報仇霍氏的兩件事,都與上封事制度有關。霍光死后,魏相通過平恩侯許廣漢上封事,認為霍氏貴盛,“宜有以損奪其權”[3]3135。舉發弒許后事,雖然不是魏相舉奏,但是魏相奏去副封,建議宣帝設立上封事制度,此后吏民奏封事不關尚書,是以弒許后事始得上聞,則將之系于魏相頭上,也有一定的道理。
地節二年三月霍光去世,五月宣帝設立上封事制度,在這兩個月之間,宣帝與霍氏家族進行了初步的權力爭奪,并且成功占據到了優勢。《漢書·張安世傳》載:“大將軍光薨后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余年……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上亦欲用之……后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3]2648而《百官表》載:“地節三年四月戊申,車騎將軍光祿勛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3]803-804在時間上與霍光“薨后數月”并不相符。《資治通鑒》則將此事系于地節二年夏四月戊申,司馬光《通鑒考異》曰:
《百官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大司馬當在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8]
經過司馬光的考證分析,“地節二年”的說法顯然更具合理性。另外,如若將此事與當時的政治環境聯系起來,《通鑒》的觀點也更有說服力。霍光之死,引起了朝廷政治勢力的新變化,即“霍氏黨徒控制朝野的局面由三股政治勢力所代替。一為霍氏勢力,主要勢力為霍氏及霍氏諸婿。二為反霍勢力,主要以魏相、趙廣漢、蕭望之及外戚許氏為代表。三為舊大臣,即霍光死后而不愿依附于霍氏者,主要有張安世、杜延年、丙吉等人”[9]。在這種情況下,為人“謹慎周密”[3]2649,資格最老,又與宣帝和霍氏皆有關系的張安世代替霍光任大司馬,是各方都能接受的選擇。《魏相傳》載霍光死后,宣帝“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3]3134。這是雙方的妥協,張安世并沒有任大將軍,而是被任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霍氏家族方面霍禹為右將軍,霍山領尚書事,這樣就達到了一種均衡。故張安世為大司馬當在地節二年夏四月戊申,魏相上封事當更在此數日之前。此時尚未設立上封事制度,魏相也沒有被宣帝任為給事中,所以這件封事很可能是通過許廣漢等宣帝親信傳達的,畢竟魏相曾經“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3]3134,而“史文有‘封事’之詞,蓋用日后之名稱”[5]196。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上封事制度設立之前,魏相已通過上封事的方式,參與了霍光死后的政治斗爭,成功地使張安世擔任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削弱了霍氏家族的勢力。在這之后,針對霍山領尚書事這一狀況,宣帝采納魏相“去副封”的建議,正式設立上封事制度,即《宣帝紀》所說“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之所指。所以,上封事制度是宣帝除去霍氏家族勢力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當時政治博弈態勢下的產物。
(三)上封事制度在宣帝鏟除霍氏家族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上封事制度產生于漢宣帝與霍氏家族的權力斗爭,產生后也確實在宣帝清除霍氏家族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霍光傳》載:“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于是霍氏甚惡之。”[3]2951由此“甚惡之”,可知霍氏對于上封事制度的憎恨與懼怕,證明上封事制度對于打擊霍氏勢力確實起到重要作用。這種作用是隨著上封事制度的逐漸普及而不斷加強的,《霍光傳》載:“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后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3]2954由原來的正常上奏被屏蔽,到后來吏民盡奏封事,表明上封事制度逐漸為人所熟悉及使用,這可看作是上封事制度的普及化。隨著吏民上書盡奏封事,霍氏家族再也不能屏蔽信息的上達,危機感逐漸加深,最終走向了造反而被族誅的結局。
二、上封事制度與漢代政治
霍氏家族覆滅以后,上封事制度并沒有隨之被廢除。作為一種密奏形式,上封事制度“有利于增加皇帝之消息來源,有利于皇帝對形勢之控制,加強皇帝之統治力量,故封事出現以后,即成制度,在兩漢行之不斷”[5]200。上封事制度在漢代政治中發揮的作用,可以歸納為三點:第一,上封事彈劾外戚及宦官等權貴;第二,針對皇帝的行為提出建議;第三,舉薦人才。
(一)上封事彈劾權貴
由于封事具有“不關尚書”的特點,所以不必經過領尚書事者的審查,可以直接到達皇帝手中,這對于那些通過尚書來控制朝政的權臣是一個制約。西漢宣帝以后,東漢章帝以后,均出現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政的局面。漢代朝臣為抵制外戚與宦官的專權,進行了大量的斗爭,這其中總能看到上封事制度的身影。
弘恭、石顯自宣帝時開始干預政事,此后歷元帝世,干政近二十年。宣帝時,蓋寬饒上封事批評宣帝信任中書宦官,宣帝“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二千石”[3]3247,將蓋寬饒下獄,終致蓋寬饒自剄于北闕之下,“眾莫不憐之”[3]3248。元帝時,針對中書令石顯專權,“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于公車,咸抵罪,髡為城旦”[3]3727。成帝時帝舅王鳳權勢更勝石顯,京兆尹王章借日蝕之機奏封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結果是王章“為鳳所陷,罪至大逆”[3]3238,死于獄中。東漢和帝時,外戚竇氏專權,尚書何敞上封事彈劾,結果為竇憲外放為濟南太傅,司徒袁安也曾上封事反對過竇憲。和帝掌權后,欲清除竇氏勢力,司徒丁鴻趁機上封事彈劾大將軍竇憲,“書奏十余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于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10]1267。《后漢書·謝弼傳》載靈帝時謝弼上封事諫去左右宦官,結果“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10]1860。宋登“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10]2557。在以上事例中,朝臣都是通過上封事來舉報外戚、宦官,這足以證明上封事制度在彈劾權貴方面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大部分上封事彈劾權貴的事例并沒有被文獻記載下來,《蔡邕傳》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兇獲吉。”[10]2001-2002說明有大量的官員曾經上封事“改政”“除兇”,抨擊干權亂政的外戚及宦官。
(二)上封事對皇帝提出勸諫
上封事制度在設立之初的意圖,是方便宣帝了解下情,防止霍氏家族憑借領尚書事的便利屏蔽信息。但是因為封事是一種上行文書,并且保密性比正常章奏更好,正常情況下其中內容只有上封事者和皇帝知道,所以很多時候官僚會選擇以上封事的方式給皇帝進諫。另外,東漢時皇帝也經常因災異詔令群臣上封事直言其過,所以上封事就成了官員向皇帝進行勸諫的一個重要方式。
通過上封事對皇帝提出勸諫,大致有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對皇帝的不當德行提出批評,其二是針對具體行政措施向皇帝提出改進意見。前面提到,蓋寬饒上封事要宣帝罷退中書宦官,結果是宣帝“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盡管很多官員求情,蓋寬饒還是被下獄,可知蓋寬饒上封事是要對漢宣帝直接提出批評和勸諫。哀帝寵幸董賢,假托傅太后遺詔給董賢加封,結果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3]3498,對哀帝寵幸董賢的行為提出批評。因為讖緯的流行,東漢皇帝更是常在發生災異時詔令群臣上封事,直言不諱。如建武六年秋九月發生日食,光武帝下詔曰:“吾德薄不明……百僚并上封事,無有隱諱。”[10]50其后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沖帝、桓帝、靈帝、獻帝皆有此類詔令,其意皆在于認為天降災異,罪在天子一人,故要求臣下針對皇帝的失德之處予以直接的批評,以使天子改過遷善。所以與西漢相比,東漢時臣僚更多借助災異發生之機上封事,并且在內容上也有更多對于皇帝的指責。不管是否借助于災異上封事,通過上封事對皇帝進行勸諫,都是上封事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
另外針對一些具體的行政措施進行諫議,也是上封事制度發揮政治作用的一個方面。元帝時發生水災和地震,元帝下詔求問得失,翼奉上封事,認為是后族勢力過盛,后宮才人過制所致,隨后上疏提出迭毀宗廟以及限制建造宮室等建議。陳湯上封事請求營造初陵,認為“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余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強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3]3024,遷徙關東豪強,以強干弱枝,加強中央的控制力。《后漢書·郭躬傳》載:“章和元年,赦天下系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10]1544-1545由此彌補了章帝赦囚政策的不足。在這些事例中,官員通過上封事提出具體行政諫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政策。
(三)上封事舉薦人才
上封事制度對漢代政治產生影響的另一重要方面,在于官員經常通過上封事推薦某些重要官職人選。霍光死后,魏相就奏封事推薦張安世擔任大將軍,對霍氏勢力產生了重要的鉗制作用。元帝時,“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平陵朱云,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3]2912-1913。成帝時,“有司奏(馮)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3]3303,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為馮野王申辯,認為馮野王才德兼備,后成帝拜馮野王為瑯琊太守。其后京兆尹王章借日蝕上封事,“諫野王代(王)鳳”[3]3303。哀帝時,王嘉奏封事推薦前廷尉梁相等“明習治獄”[3]3499。光武帝時,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推薦伏湛曰:“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尤宜近侍,納言左右。”[10]896成帝無子,諫大夫毋將隆甚至奏封事諫議征定陶王為太子,也就是之后的哀帝。征藩王為太子的事只是特例,但是上封事推薦大將軍、御史大夫及尚書等重要官職的人選,確實是上封事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原因應該是,這些重要官職牽涉各方權益,故需要保守機密。
三、上封事的保密性原則與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
封事的保密性,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一是制度上的保密性,二是實際效果上的保密性。有學者認為,“漢代群臣上封事有嚴格的保密要求,須謹慎周密地防范一切有可能的泄密”[11],這一點從制度上講沒有問題,封事無副封、不關尚書、皂囊封裝以及親自手書等的規定,使得封事的保密性高于一般的奏書。但在現實中這些制度性的規定并未被很好地遵守,如王章奏封事彈劾王鳳時,其妻曾進行勸阻,可知封事內容為其妻所知。那些上封事謹密之人,如張純“時上封事,輒削去草”[12],楊賜“謹自手書密上”[10]1778,陳群“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13],史書對于他們“謹密”的贊許,或許恰恰表明,在現實中多數官員奏封事不夠“謹密”。所以在制度性的保密措施中,手書以及對家人保密等要求,難以得到貫徹,只有無副封、不關尚書、皂囊封裝三個方面是得以真正實行的。
從實際情形看,官員上封事多有因失密遭受政治報復者。王劍認為,封事“從封章的書寫到最后呈達御前,存在著諸多保密不善的問題”[14]。但是從實際情況看,封事內容的漏泄,往往卻并未發生在傳遞過程中,而最主要在上奏給皇帝之后,發生于皇帝身邊。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近侍制度導致信息容易漏泄,二是皇帝不注意對封事進行保密。王章奏封事勸成帝以馮野王替代王鳳時,成帝多次召見他,并且“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但是“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3]4021-4022。蔡邕上封事直言“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愿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奸仇”[10]1999-2000,結果“章奏,帝覽而嘆息,因起更衣,曹節于后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10]2000。這兩個事例說明漢代近侍制度,很容易導致侍中、中常侍等近侍人員獲知封事內容,即便皇帝做了保密措施也難以防范。另一方面,皇帝自身維護封事保密性的意識也不強。蔡邕在封事內容泄露以后,對靈帝抱怨說:“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兇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10]2001-2002再結合前文中,大量官員因為上封事而遭受報復的事例,可知皇帝不僅沒有為上封事者很好地掩蔽,在他們受到政治報復時也很少能給予保護。封事所言,多涉一時政治機密,所批評對象多為權臣貴戚,而宮省之內保密性又如此之低,上封事者普遍遭受政治報復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四、余論
通過上面詳細考察,可見上封事制度與漢代政治的密切關系。漢代上封事制度也跟漢代的災異觀密切相關,受經學的影響很大,這一點學界已有不少探討。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說明的是,上封事制度產生于漢代,也與漢代崇尚“諷諫“的觀念有關。《白虎通·諫諍》篇曰:
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窺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不顯諫。”[15]
古人諫議的方式有五種,這其中漢人最推崇的是諷諫,因為這是最聰明的諫議方式,它保護了納諫者的自尊,所以最容易被接受。對君主的其他諫議方式,實際上是彰顯了君主的過失,對于君主的權威是一種損害。“諫而不露”“為人臣,不顯諫”,給我們提示了這種諫議觀與封事之間的內在關聯。哀帝時,師丹使屬吏書寫封事,造成了信息漏泄,“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3]3506-3507在這件事中,上封事與“忠臣不顯諫”直接對應,凸顯了諷諫的觀念對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的重要影響。諷諫觀念與上封事制度的關系,是有關上封事制度很重要的一個問題,行文有限,在此不再詳述。(注:本文得到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劉敏教授、閻愛民教授、黨超老師的審閱和批改,特此致謝。)
[1]應劭.漢官儀:卷下[M]//孫星衍.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190.
[2]卜憲群.秦漢官僚制度[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89.
[5]廖伯源.秦漢史論叢:增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8.
[6]趙麗.漢代封事的產生及意義[J].南都學壇,2011(9):21-24.
[7]王鳴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83.
[8]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805.
[9]張小鋒.西漢中后期政局演變探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91-92.
[10]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11]袁禮華.試析漢代上封事制[J].江西社會科學,2009(10):65-68.
[12]劉珍,著.東觀漢記校注[M].吳樹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147.
[13]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4:638.
[14]王劍.漢代上封事考論[J].學習與探索,2005(6):201-205.
[15]班固,著.白虎通疏證[M].陳立,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235.
[責任編輯:劉太祥]
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ystemofSubmittingFengshiandthePoliticsofHanDynasty
XU Fu-ju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Fengshi is a kind of sealed written report to the emperor since Han Dynasty. The appearance of the system of submitting Fengshi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ministry is the objectiv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ystem of submitting Fengshi. And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Han Xuandi and Huo family is the specific factor of the creation of the system of submitting Fengshi.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system of submitting Fengshi on the politics of Han Dynasty embodies the three aspects of impeaching bigwigs, giving advice to the emperor and recommending talents. The emperor is mostly to blame for the information leakage of Fengshi. As a result, the submitters always suffered from political revenge. Obviously, there were institutional flaws in the system of submitting Fengshi.
submitting Fengshi; sealed written report; Han Xuandi and Huoes; the politics of Han Dynasty
2017-05-12
徐福舉(1991— ),男,山東省荷澤市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秦漢史。
K234
:A
:1002-6320(2017)05-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