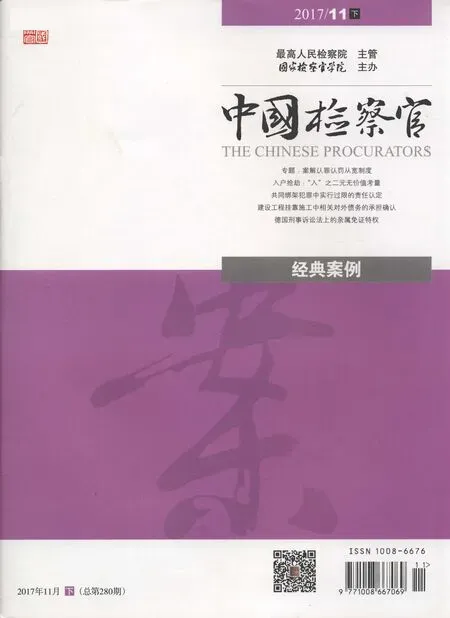共同綁架犯罪中實行過限的責任認定
文◎葉迪南
共同綁架犯罪中實行過限的責任認定
文◎葉迪南*
一、基本案情
2017年2月16日,楊某、趙某、陳某至A市預謀綁架楊某曾經工作公司的董事長毛某索要錢財,后三人準備車輛、手銬、手機等作案工具,并跟蹤毛某至其所在小區,并選擇一樓房作為關押被害人的地點。期間,陳某以其母親生病為由告訴楊某、趙某不再參與犯罪。2017年2月27日晚上,楊某、趙某至毛某所在小區地下車庫欲實施綁架,但因毛某未出現而未著手實施犯罪。次日晚上,楊某、趙某又至上述地下車庫伺機綁架。當晚9時許,馮某駕駛奔馳車進入地下車庫,楊某、趙某用折疊刀、手銬、膠帶等工具控制住馮某,后駕車至事先踩點的樓房關押、看管。3月1日上午,趙某電話聯系馮某父親索要贖金50萬元。
二、分歧意見
本案中,針對陳某是構成綁架罪(預備),還是綁架罪(既遂),抑或是二罪并罰產生了諸多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索財型綁架犯罪行為人的故意相對概括,且綁架毛某的預備行為對綁架馮某的實行行為有促進作用,應整體評價為一個犯罪,故陳某構成綁架罪既遂。
第二種意見認為,一個犯罪只存在一個犯罪形態,本案中既有綁架毛某的犯罪預備,也有綁架馮某的犯罪既遂,因而是兩個犯罪,但楊、趙二人綁架馮某的犯罪行為未超過陳某的共犯故意,故陳某構成綁架罪預備和綁架罪既遂,同種數罪并罰。
第三種意見認為,索財型綁架犯罪是嚴重侵犯人身權利的犯罪,因人身權益具有專屬性,故楊、趙二人行為對象轉換后綁架馮某的行為宜認定為另起犯意,該行為已超過陳某的犯罪故意,是實行過限,陳某僅成立綁架罪(預備)。
三、評析意見
我們同意第三種意見。
(一)從罪數判斷是否為實行過限
本案首要考慮的問題是,從犯罪構成來看,作為實行犯的楊某、趙某的行為是構成綁架罪一罪還是綁架罪二罪。如果實行犯構成綁架罪一罪,作為幫助犯的陳某當然構成綁架罪(既遂)。但是,如果實行犯構成綁架罪(預備)和綁架罪(既遂)二罪,則需進一步考察楊、趙二人綁架馮某的行為是否超過陳某的共犯故意。本案中,雖同時存在預備行為和實行行為,但該兩個行為并非基于同一犯罪故意,也并非同處于一個犯罪,因而不能認定楊、趙二人僅構成綁架罪一罪。
首先,同一故意犯罪中不可能同時存在犯罪預備和犯罪既遂。犯罪的特殊形態,以行為符合構成要件為前提。如果同一故意犯罪中存在犯罪預備和犯罪既遂,就會產生一個犯罪符合兩個犯罪構成的邏輯矛盾。而且,犯罪的特殊形態是終局性的停止,即該犯罪行為由于某種原因不可能繼續向前發展。所以,如果在綁架行為持續階段出現犯罪預備形態,表明該綁架行為已經終止,不可能再繼續發展為犯罪既遂的形態。如果行為人繼續實施其他綁架犯罪,則是第一個犯罪終了后實施的第二個犯罪,而非同一犯罪中不同階段的預備行為和實行行為。
其次,人身權益具有專屬性,行為對象轉換導致法益主體變化的是另起犯意。傳統理論認為,綁架罪的法益包括他人的人身自由權、健康、生命權以及公私財產所有權。[1]不過該觀點過于抽象,也不能體現刑法各章對不同法益保護的邏輯關系。《刑法》第239條將綁架罪規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中,故該條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保護人身權利,其次才是財產權益。當然,也有觀點認為,綁架罪的法益僅僅是人身權益,即被綁架人在本來的生活狀態下的行動自由以及身體安全。[2]筆者認為,無論是否將財產權益納入綁架罪的法益范疇,都不影響人身權益作為綁架罪首要保護法益的地位。同時,考慮到人身權益具有專屬性的特征,除刑法理論規定的行為對象轉換后仍按一罪處理的情形外(對象錯誤和打擊錯誤),同一犯罪中不能發生行為對象轉換,否則,就會因人身權益專屬性的變化導致具體構成要件要素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具體的犯罪構成要件。
最后,數個綁架犯罪實行同種數罪并罰更具有合理性。刑法理論通說認為,同種數罪原則上不并罰。不過,該觀點未能將司法實踐中可能存在的罪刑失衡現象作進一步思考。例如,多次輕傷不同的人,無疑多次符合故意傷害(輕傷)罪的構成要件。按照通說不應并罰的觀點,無論輕傷多少人,都只能以故意傷害(輕傷)罪一罪定罪處罰,最重判處3年有期徒刑。顯然,該處罰結果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所以,有觀點認為,除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法定刑升格條件包含多次犯罪時,以及將數額(數量)較大作為犯罪起點,并針對數額(數量)巨大、特別巨大的情形規定了加重法定刑等情形時不應當并罰外,同種數罪原則上應當并罰。[3]因此,對于生命、健康、自由等個人專屬法益,無論一次針對多人,還是多次針對一人或多人,只要不能評價為加重情節而做到罪刑相適應,根據規范行為論,都可能根據人數作為同種數罪進行并罰,以有效保護法益和實現罪刑相適應。[4]
本案中,作為實行犯的楊某、趙某的行為構成綁架罪二罪無疑,陳某也顯然不構成綁架罪(既遂)一罪,但其是構成綁架罪(預備)一罪,還是綁架罪(預備)和綁架罪(既遂)二罪,即作為幫助犯的陳某是否需承擔楊、趙二人臨時起意綁架馮某的刑事責任,還需進一步考量楊、趙二人的行為有無超過陳某的共犯故意。
(二)從共犯故意內容判斷是否為實行過限
共犯故意是判斷實行過限的核心內容。一般而言,只要行為人的行為沒有超過共謀內容的范圍,則無論其行為手段、犯罪情節如何變化,均是在一定限度內的量變,并不能引起質變。但是,如果行為人的行為超過共謀內容的范圍,故意地實施了另外一種犯罪或者故意實施性質、手段、對象等與共謀內容不同的犯罪,則其行為已經發生質變,是實行過限。
那么,司法實踐中如何判斷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是否超過共謀內容的范圍?筆者認為,應當確立兩個不同的判斷標準,即宏觀上考察行為有無超過共同犯罪的故意,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在共同故意的范圍內,則是共同犯罪行為;反之,則是過限行為。例如,張三教唆李四綁架甲,而李四卻臨時起意綁架了乙,從宏觀上看,李四綁架乙的行為已超過張三的故意范圍。不過,該判斷標準過于抽象,難以滿足司法實踐中對個案的判斷需求。因此,仍需從微觀上對犯罪構成要件進行判斷,即在同一犯罪構成要件內,主觀故意的認識內容是否與具體的客觀構成要素相一致。如果一致,則成立共同犯罪,反之,則是實行過限。
犯罪構成要件既有抽象性,又有具體性。就某種行為是否成立某種犯罪而言,應考察行為人實施的具體行為經過抽象后是否與該種犯罪的構成要件相吻合,此時主要考察構成要件的抽象性。但就某種犯罪是否與行為人共同謀議的犯罪相吻合而言,則應考察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在具體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上是否與共同謀議的故意內容一致,此時主要考察構成要件的具體性。[5]比如,甲教唆乙毆打丙,乙毆打丙后,發現現場還有仇人丁,乙又臨時起意毆打了丁。乙毆打丁的行為雖然與共同謀議的行為在構成要件上完全吻合,但顯然不屬于共同犯罪行為,而是實行過限。因此,不能機械地以符合同一犯罪構成要件直接否定實行過限,還需進一步考量具體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因為該要素均是獨立的、個體的,不能相互替代。
就本案而言,陳某與楊、趙二人預謀綁架毛某,并準備犯罪工具、制造犯罪條件,但陳某中途借故退出犯罪。數日后,楊、趙二人在預備綁架毛某過程中,由于毛某未出現,又臨時起意綁架了馮某。從宏觀上來看,陳某與楊、趙二人共謀綁架的是毛某,而非馮某,楊、趙二人綁架馮某的行為已超過陳某的犯罪故意。從微觀上來看,作為具體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不能超過陳某與楊、趙二人共謀的故意范圍,而本案作為具體構成要件要素的行為對象已經由毛某變更為馮某。陳某與楊、趙二人約定的行為事實與楊、趙二人實際實施的事實發生實質性改變,即便楊、趙二人實施的綁架行為與陳某共謀的綁架行為在構成要件上具有抽象的相符性,但由于具體構成要件要素已發生變更,且考慮到人身專屬法益主體不具有替代性,故楊、趙二人綁架馮某的行為超過了陳某共謀的故意。
當然,并非超過共謀故意即可直接認定楊、趙二人實行過限,還需進一步考察陳某對楊、趙二人臨時變更綁架對象是否具有預見可能性。如果具有預見可能性,則成立共同犯罪,反之,則是行為過限。
(三)從預見可能性判斷是否為實行過限
預見可能性是指共犯對直接實行犯的行為以及該行為在客觀上、法律上通常可能的結果能夠預見,即該結果的出現在情理之中,其他同案犯應當預見,如果放任犯罪結果發生,其主觀上就是間接故意。[6]預見的內容,應是對行為性質、對象和結果能夠認識,并不要求對實施該行為的手段等具體細節能夠預見。不可否認,綁架過程中存在實行犯隨意變更綁架對象的情形,但該情形并不具有普遍性。
從刑法條文來看,普遍、慣常發生的行為或結果才能被納入法律法規。如多次盜竊是構成犯罪的情節,多次搶劫是法定刑加重情節。之所以將“多次盜竊、多次搶劫”納入刑法規范,主要是因為在侵犯財產權益的犯罪中,行為人連續實施犯罪或轉換行為對象的情形較為普遍,行為對象的轉換也往往具有可替代性。因此,在侵犯財產權益的犯罪中,行為人應當對實行犯可能臨時轉換行為對象具有一定的預見性。如果行為人未消除先前行為對實行犯的積極影響,仍需承擔實行犯臨時起意實施犯罪的刑事責任。然而,刑法并未將多次綁架作為法定刑加重情節進行規范,說明該行為在社會生活中不常見,不具有普遍性,沒有必要將其納入刑法進行規制。
在司法實踐中,多次綁架或綁架多人的案件也少有發生。綁架犯罪是嚴重侵犯人身權益的犯罪,處罰嚴厲至極,多數行為人在實施綁架犯罪前均有嚴密計劃,尤其是綁架對象的選擇,直接決定行為人能否實現最終的犯罪目的。所以,綁架過程中行為人不會輕易轉換行為對象。在綁架犯罪行為對象的轉換不具有普遍性的情況下,不能苛責行為人對綁架實行犯臨時轉換行為對象具有預見可能性。
當然,也存在例外情形,不能以沒有預見可能性的一般情形推定行為人臨時起意行為均為實行過限。對此,還需參考行為人的事后態度,即如果事后其明確表示反對新的實行行為,如拒絕分得該實行行為取得的贓款贓物等,應認定其對該實行行為不認可,成立實行過限無疑。反之,如果行為人事后對新的實行行為表示認可、贊賞,抑或接受分贓,則可以推定其具有預見可能性,不成立實行過限。
本案中,陳某實施的綁架預備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對楊、趙二人綁架馮某的行為確實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否因此就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呢?筆者認為,陳某不需要為楊、趙二人綁架馮某的行為負責。陳某等人預備綁架毛某和楊、趙二人綁架馮某是兩個犯罪,陳某無法預見楊、趙二人會利用其預備階段準備的工具綁架馮某,其預備行為的責任范疇不能涵蓋有效防止所有犯罪結果發生。在陳某不具有預見楊、趙二人綁架馮某可能性的情況下,其沒有阻止楊、趙二人綁架馮某的義務,因而不能認定其具有放任馮某被楊、趙二人綁架這一犯罪結果發生的間接故意。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由于陳某缺乏主觀故意,楊、趙二人的犯罪行為已超過陳某共犯故意的范疇,所以,無論楊、趙二人在綁架馮某時是否利用了陳某預備階段的幫助,陳某都不應該對楊、趙二人的過限行為負責。
注釋:
[1]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469頁。
[2]張明楷:《刑法學》(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第886頁。
[3]同[2],第 536 頁。
[4]參見陳洪兵:《涉及個人專屬法益犯罪的數罪并罰問題》,載《人民法院報》2012年1月18日。
[5]參見葉良芳:《實行過限之構成及其判斷標準》,載《法律科學》2008年第1期。
[6]參見張榆:《共同故意傷害中實行過限的甄別——浙江高院裁定祝光銀等故意傷害案》,載《人民法院報》2015年5月18日。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檢察院[31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