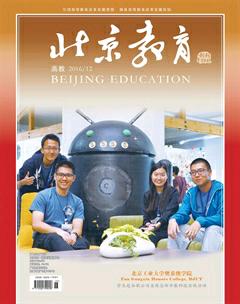學生權利的崛起與大學權力格局的變革
摘 要:民權運動所引發的大學民主化浪潮有力地促進了學生權利的保障,但也引起著名學者布魯姆對大學違背其傳統使命、走向膚淺的憂思。布魯姆的批評揭示出大學內部權利格局的變化本質上必然是權力格局的變化,學生權利與學術權力之間存在張力。這種變化是工業化和社會分工高度發達的經濟社會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并不必然引起思想道統的淪喪。大學應當回歸其作為教師、學生、國家和社會的共同事業,真正承認學生的主體地位。
關鍵詞:大學民主化;學生權利;高等教育;學術權力
當今世界對學生權利的強有力保障,與風起云涌的20世紀60年代密切相關。由美國民權運動、歐洲左翼思潮等引起的反抗潮流,使學生的權利保障急劇強化。在這股熱潮中,美國著名學者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可謂一個異類。他對過分膨脹的學生權利進行了鞭辟入里的抨擊。這種言論富有代表性,也和國內的某些較為“保守”的高等教育觀念頗有些共通之處。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建立學生權利保障的理論基礎,不能離開對類似布魯姆式立場的反思與回應,更不能脫離這些思考所指向的本質問題。
學生權利的崛起
在20世紀60年代,學生權利隨著民權運動的風潮和歐美高等教育的改革迅速崛起。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衰微、正當程序在學業處分中的運用、平權運動與“反向歧視”在高等教育中的興起、信托理論等幾種新型“學生—學校”法律關系模式的出現等,均始于20世紀60至70年代。總體上說,隨著特別權力關系理論與大學特權觀念等進路的衰微,學生在高等教育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得到日益強調,以教育權為中心、以權利保護為基本視角的權利保護進路,在高等教育領域里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潮流。這一潮流的基本觀念構成包括:一是將受教育、也包括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視為一種權利乃至是基本權利;[1,2,3]二是這種權利的保障以自主選擇權和平等保障為兩個最主要的核心原則;三是高校學生的權利除了受教育權和一般權利保護外,尚獲得一些特殊的權利保護,如(公正)對待權(the right of treatment);四是學生的權利義務關系被置于學生權利/個人權利與教育權力,尤其是紀律(discipline)權力之間的結構中理解。[4,5]這一潮流將高校學生權利義務從理論上抽象為這樣一種基本結構:高校學生的權利義務主要由一般公民享有的權利義務、受教育權以及有限的紀律限制三大部分組成,而紀律限制又很大程度上相伴于受教育權。因此,實際上相當于在一般權利義務上嵌入了一個教育領域特殊權利義務的構成,從而呈現出一種復合卻非簡單疊加的權利義務結構。這種權利結構只是政治事物在法理層面上的體現,其背后是學生乃至整個由青年和少數族裔混合的社會力量的崛起。
在歷史上,強有力的學生權利并非新鮮事物,在中世紀早期的學生型大學中,我們能看見比當今社會也許更為強大的學生權利:學生們能夠享有自由旅行、定居、自主選擇多元化的救濟途徑,也受到全面的人身保護。[6]但是,學生型大學在14世紀初隨著一次騷亂而走向凋亡。在它的歷史存續期間,它包含的理想與當代學生權利高漲所蘊含的精神幾乎截然不同。在以博洛尼亞大學為代表的學生型大學中,所謂的“學生”,實際上是自發的求學者,用《居住法令》(Authentica Habita)的語言來說,他們甚至就是“學者”(scolaribus),其教師則為“教授”(professoribus)。在此,學生的權利并非相對于學校和教師,而是相對于大學以外的宗教和世俗權力;而學生本身是作為學者而被尊崇和加以特殊保護的。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學生權利的保障則更多地起源于現代民主權利本身的高漲,本質上是自民權運動以降的一次政治力量的重新配置。對此,我們在布魯姆的論述中可以瞥見更多的內容。
布魯姆的批評
布魯姆直截了當地指出:“對我們的大學今天在發生些什么事,最顯見、最綜合也最真實的解釋是,對民主制的某種激進的平等主義獲得了對自由的大學最后的殘余物的勝利。”[7]395-396此種“自由的大學”就是布魯姆所理解的“曾經的”大學:“它企圖建立一個反思和教育的中心,這個中心獨立于政制及其原則的普遍影響,不受無論是粗糙的形式還是精致的形式的公共意見的主導,而是致力于不帶偏見地探求重要的、廣泛的真理。它曾要成為公民社會中的獨立之島,一個至高無上的文字共和國。”[7]395而在當代的大學中,這個獨立之島不復存在,當 “黑人學生扛著槍并挾持著數以千計的白人學生的支持,堅持教員們要放棄大學的評判制度……教員們竟屈從了”之時,布魯姆認為,在這些事情的背后,“首要的一點是學生權力的出現,這至少意味著大學極端的民主化。”[7]397在這種背景下,大學還面臨內外夾擊,逐漸地趨于政治化,“政治人士常常在談大學,談它們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大學……失去了對其命運的控制。”[7]396獲得了更多權利(以及權力)的學生在學習目標、課程設計、參與校內事務等一系列方面享有了高度的自主權,“由學生構成的民主統治體就像所有的統治體一樣,確立了政策,政策進而成為它的利益所在。”[7]398隨之而來的是畢業標準的降低乃至放棄,必修課與傳統的主修科目受到削弱,而教授的思想需要適應學生們的“市場需求”,“學生有權判斷一個教授或他的教學的價值,這就是把大學變成了市場,在這里—賣者得取悅買者的市場,其價值的標準是被需求所決定的。”[7]400-402
在布魯姆看來,除了社會的背景外,大學自身的性質變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學轉變為“巨型大學”,日益成為專業化、技術化的教育場所,而各個系科很少相干,已經無法提供一種整全的知識,更加無力教導目的與善惡。在高等教育權力結構遠未發生革命性變遷的中國,這幅圖景對于部分人似乎顯得激動人心。因為教導善惡、提供目的、“建立從人的完美角度提供的標準”[7]400-401等隱含著一種讓人不安的權威,可以作為某種為所欲為的權力的面具。布魯姆對古典大學的印象也似乎過于理想化,以至于將其假定為一個探求真理的孤島,而似乎沒有看見自隆卡利亞大會(Diet of Roncaglia)[8]以來大學就一直依附外力而難求清靜的處境。馬西利烏斯和奧卡姆的威廉被迫出逃、伽俐略的受審、巴黎大學委派與抵制校長的斗爭[9]等,都折射出大學維持其真理孤島之理想的不易。但是,在市場力量及專業化教育全面介入以前,大學仍然具有那種由有關目的之知識帶來的崇高地位。而現在,“我們對曾經作為大學中心事業的東西已甚少記憶”。[7]407在布魯姆的心中,學生權利的高漲實質上是權力格局的變化,而這背后是大學—尤其是其中的人文教授—基于使人走向完美、走向更高標準的知識及引導能力而擁有的權威的根本削弱。在此種局面下,青年很難通過他們自身成就出類拔萃的心靈,而只剩下一種空洞的自由和使人趨向于平庸的民主。“所有的榮譽都給了一個大聲嚷嚷的抗議者群體,這些人所有的是輕松易得的、嘩眾取寵的意識形態,以此作為思想的替代品。……他們在既無經驗又乏知識的情況下能判斷什么呢?……他們的開放變成了空疏,變成了無法培育任何根深的植物的土壤。”[7]404-405自然,學生們的思想深度和厚度無法和布魯姆這樣繼承了某種歷史悠久的知識傳統的教授相比,但在其中關鍵的是某種被稱之為“教誨”的關于人本身的知識,進而是有關人之目的及其自身達致完美的知識,正是這種知識的權威急劇消退,留下了一個純粹由權利、權力、利益和博弈組成的結構—而這個結構本質上和大學相去甚遠。
對布魯姆批評的反思:如何定位大學及其學生?
如果對布魯姆所代表的學術傳統缺乏一定的了解,布魯姆的論述或會令人訝異。現代的權利理論和自由主義觀念極端排斥那種古典傳統,較之自由城邦對蘇格拉底的反感并無二致。在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中,青年本屬無辜,學生作為一種弱者,其權利應當毫無疑問受到更充分的保護,免受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濫用之侵害。在此,筆者無意去評判布魯姆式立場的得失,只是他的若干洞見依然對我們探討學生權利保障問題是有益的。
第一,布魯姆的論述中可以瞥見的前提是:權利格局的變化,本質上首先必然是權力格局的變化。沒有強有力的大學民主化的浪潮作支點,學生權利不可能獲得有力的伸張。在法學及政治學的語言織體中,基于“支配”及“權勢”(potestas和potentia)發展出來的“權力”概念是一種相對較新的觀念形態,[10]它相對于基于“法”和“支配”(ius及potestas)發展出來的現代“權利”概念[11]而言更為現實及直接:它不僅表明什么屬于誰、符合正義及法理,更表明誰能夠合法地采取何種影響他人的行動,以及此種影響力的外部結構。大學治理結構的根本變遷是強化師生權利保障的保證,而不是相反。從歷史上看,權利的蛋糕背后是權力的蛋糕,而權力的語言本身是改頭換面的權利的語言。我們必須重視學生權利保障背后的制度動力,而不是簡單地認為只是設幾個多元化救濟機構或改進某種救濟渠道就足以提供堅實的保障了。在這個意義上,惟有將學生權利(乃至我國的教師權利)的保障與整個大學治理變革的語境結合起來,才有實質性的意義。
第二,布魯姆揭示了學生權利與我們今天籠統稱之為“學術權力”的東西之間的張力。在當今世界,還有誰,或者何種道統能夠斷然宣稱自己是關于人之完美或善惡的知識的惟一代表嗎?學術權力日益縮減為一種專業評判與學術道德維護之權力,就是因為多元主義及反權威之觀念在20世紀中后期以降的再度強大,導致引導與安排他人人生的傳統權威被消解的緣故。某種古典傳統可以敵視此種進程,但卻沒有能力回答一個神學式的根本問題:誰判斷?誰解釋?(Quis judicabit? Quis interpretabitur?)從現代的視角看,此種權威隱含著權力濫用和專斷的危險;而從古典的視角看,要求此種權力的人,未必是哲人,而更可能是僭主。如果說大學是知識的“共和國”,它有可能通過一種反共和的制度及法律關系得以實現嗎?學生權利的強化必然迫使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都承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以更大程度上形成一種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事業的力量,而不僅僅只產生對行政權力的限制。學生對大學治理的參與權、對學習歷程的選擇權、對教學事務的評判權、甚至對內部事務的決定權的強化,將使得大學內部的權力關系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第三,布魯姆深刻地刻畫了現代大學的轉型,擔憂在此背景下可能出現人文精神和思想道統的淪喪。筆者無意評價這一點在目前的中國是否適用,即使它可能,也不過說明此種道統生命力之脆弱。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一種優秀的思想不是在與其他優秀思想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沒有一種流傳久遠的精華不是經過無數歲月的風吹雨打而得以傳承的;如果連所謂空洞、淺薄的流行意見都無能為力,要依靠權力甚至是專斷的權力才能勉強保有一席之地,是否在當下乃至思想競爭更加激烈的未來還有生命力,至少是令人疑惑的。相反,權力結構的變革和學生權利的崛起,正叩問著偉大思想回應時代、贏得傳承的能力。如果某種偉大的道統未曾懼怕黯淡如夜的宗教裁判所、烽火連年的野蠻戰爭及種種暴政,又如何會在千姿百態的多元性、從更加強調所有人的主體性地位的時代中迷失呢?
大學教育的專業化,乃至所謂“巨型大學”(muluniversity)的出現,是工業化和社會分工高度發達的經濟社會中不可避免出現的現象,這是不以某種傳統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的。在歷史上,現代意義上的權力(power/pouvoir)正是伴隨中世紀晚期乃至近代初期的工業化萌芽而出現的一個概念,與帶有正義色彩的統治(imperium)、法權(ius)或支配(potestas)相比,它可以實現完全的實證化,十分適合于調節復雜的制度分工及關系結構;它只需要正當性資源的適度支持。權利結構的界定,不可避免地需要依托權力的再分配;而權力結構重置的關鍵是正當性資源的再分配。如果在理論上沒有充分承認學生的主體地位,不認為大學是教師、學生(大部分會轉變為校友)、國家和社會的共同事業,制度上的推進只能是零敲碎打的努力。在大學興起之初,無論教師型大學還是學生型大學,都是自發聚集的教師和學生的共同事業,但愿高等教育的這一“初心”未被忘記。
布魯姆教授的憂思使人敬重。他一直致力于維護高等教育的歷史使命,維護大學致力于思想之獨立、深刻思考之傳承以及人本身之完美的目標。但是,在整個權力結構當中,不可能再有單兵突進的空間。在我們這個時代,只有當學生和社會都以主體的姿態參與這一目標時,這一目標才有實現的可能。
參考文獻:
[1]Lucas R. The Right to Higher Education[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70, 41 (1): 55-64.
[2]Guri-rosenblit S. Trends in Access to Israeli Higher Education 1981-96: From a Privilege to a Right[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96, 31(3): 321-340.
[3]Berger E. The Right to Education under 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J]. Columbia Law Review, 2003, 103 (3): 614-661.
[4]Halvorsen K. Notes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uman Right to Education[J].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990, 12 (3): 341-364.
[5]Young D P. Student Rights and Discipline in Higher Education[J].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1974,52(1): 58-64.
[6]《居住法令》Authentica Habita (1158年).
[7]布魯姆 A. 大學的民主化[M]. 應星, 劉云杉,譯. //張輝. 巨人與侏儒(增訂版) —布魯姆文集.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07.
[8] Koeppler H. Frederick Barbarossa and the Schools of Bologna[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939, 54 (216): 577-607.
[9]Riddle P.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University Formation in Europe, 1200-1800[J].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93, 36 (1): 51-52.
[10]蘇宇. 行政權概念的回溯與反思[J].行政法論叢, 2015(17): 96.
[11]方新軍. 權利概念的歷史[J].法學研究, 2007(4): 83.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責任編輯: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