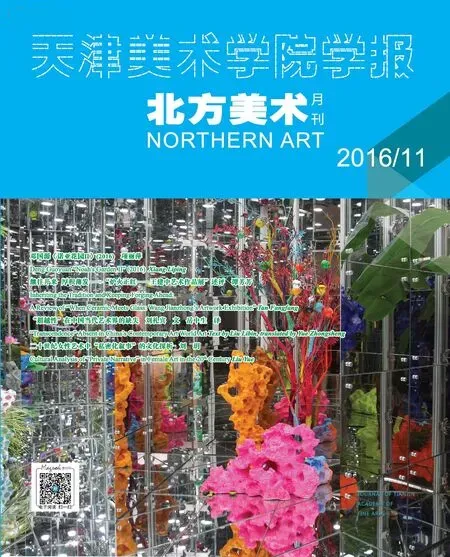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與20世紀早期中國美術史研究
唐 毅/
中國自古以來就不乏美術史論著作,從南北朝始,歷朝歷代都出現過精妙絕倫的畫論著作。近代第一本美術史論專著是姜丹書在1917年撰寫的《美術史》,該書屬“師范學校新教科書”,是受當時教育部委托而編寫的一部教材。此后,從事教育事業的藝術家,如陳師曾、黃賓虹、潘天壽、林風眠、劉海粟、傅抱石、倪貽德、豐子愷等等都有美術史專著問世。民國時期,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方法包括中國美術的通史研究、斷代史研究、分類史研究、專題史研究等等,其中主要以通史寫作為主;從20世紀30年代起,逐漸形成了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第一個高潮,美術(繪畫)通史、斷代史、專題史等都建樹頗豐,如李樸園的《中國藝術史概論》、傅抱石的《中國繪畫變遷史綱》、秦仲文的《中國繪畫學史》、胡蠻的《中國美術的演變》、鄭午昌的《中國美術史》、史巖的《東洋美術史》、俞劍華的《中國繪畫史》等等。這一時期的美術史研究著作受西方進化論影響,不少學者自覺地運用美術進化的理論來闡釋美術運動的變遷、發展。譬如,秦仲文在1933年所著的《中國繪畫學史》就將上古至清末民國的中國繪畫發展史分為萌芽、成立、發展、變化和衰微五大時期,把數千年的中國繪畫發展史看作是一個由生長走向衰微的歷程,這明顯受到了生物進化論的影響。此外,劉思訓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美術發達史》一書的編輯例言中就明確指出:“本書所采材料首重考證,古代美術之無從由遺物考證而只可于典籍的著錄中探尋消息者,則均經嚴密的理智分析,求其與現代知識不相抵觸者采用之。”①另外,從40年代中后期開始,美術史學家開始注重考據、鑒別等方法在美術史寫作中的運用,1947年童書業在《怎樣研究中國繪畫史》一文中說:“研究繪畫史,不但要懂得繪畫的技術,還得有鑒別、考據和著史的知識。”②

圖1 五代回鶻公主像(曹議金夫人像)

圖2 五代曹元忠像

圖3 五代曹元忠夫人像

圖4 張大千 麻姑拜壽 1944年

圖5 張大千 青綠潑墨山水1965年

圖6 張大千 山雨欲來 1966年
美術考古的方法在西方出現得較早,德國美術史學家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則開美術考古著作的先河。中國較早運用美術考古方法進行研究的是王子云,但實際上,張大千在1941年就開始的臨摹敦煌壁畫事件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次美術考古,只不過張大千是一位畫家,他臨摹壁畫的初衷并不在于作美術史研究,因此,學界比較忽略其在美術史研究方面的價值。但不可否認,張氏確實在美術考古上為后人打開了一扇門,對于民國時期的美術史研究產生了影響。
一、美術考古成為美術史研究的新補充
在敦煌壁畫被大規模地發現之前,人們了解古代史的途徑都是通過文獻、史書等。而文字記錄的有限性和抽象性使得人們對百年之前乃至千年之前的歷史形象總是隔著一層紗。圖像是人們了解一段歷史、一場事件、一個人最直觀的方式,但由于中國畫特殊的材料,能夠長時間保存下來的卷軸畫數量非常少,這對于研究中國古代美術史造成了不小的困擾。雖如此,中國自古就有在墓室、寺廟、石窟造像之習俗,這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們研究古代歷史、社會習俗、人文藝術提供了寶貴的圖像資源。尤其是20世紀初,沉睡百年的敦煌石窟藝術再次被人們發現后,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尤其是唐及唐以前的六朝歷史提供了最直觀的圖像證據。雖然敦煌壁畫的產生最初是出于宗教的目的,壁畫所繪制的內容大都與佛教內容有關,但伴隨著各朝各代統治者觀念、社會風俗、審美的變遷,敦煌壁畫中也包含了大量的世俗內容。由于敦煌壁畫存續的時間非常長,從六朝直至元代,其中保存的大量與世俗生活相關的內容堪稱一部中國古代社會風俗史。
張大千來到敦煌后,雖然沉醉于敦煌壁畫精彩的繪畫技法,同樣也十分關注壁畫對于補充中國古代歷史的重要作用。他曾提出:“壁畫可以補正史傳。我國因年代久遠,史籍繁多,就是抄錄多錯,譬如五代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史傳只載了大略,且多舛誤,但敦煌千佛洞和安西萬佛峽都有關于曹氏的材料,若能加以整理,就可以補正史之不足。”③
張大千所說的曹議金是唐末五代沙洲人士,為前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外孫女婿,后來掌政瓜、沙二洲,也成為歸義軍節度使。關于曹議金及曹氏家族的記載,史書文獻中多有出現,但均記錄不詳。譬如,《資治通鑒》中載:“八月,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薨,沙州長史曹議金代領軍府;制以議金為歸義軍節度使。”④這里僅記載曹議金為節度使,其他信息均無。《舊五代史·唐明宗紀》中關于曹氏的記載:“(長興二年春正月)丙子,以沙州節度使曹議金兼中書令。”⑤《宋史·外國傳六·沙州》中關于曹氏家族的記載最為詳盡:“議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建隆三年,加兼中書令,子延恭為瓜州防御使。興國五年,元忠卒,子延祿遣人來貢。贈元忠為敦煌郡王,授延祿本軍節度使,弟延晟為瓜州刺史,延瑞為衙內都虞侯。咸平四年封祿為譙郡王。五年延祿、延瑞為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后,而以其弟宗允權知瓜州。表求旌節,乃授宗壽節度使,宗允檢校尚書左仆射、知瓜州,宗壽子賢順為衙內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軍節度,弟延惠為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⑥這一大段敘述給我們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曹氏家族官位資料,除曹議金外,曹氏家族其余子孫任職過節度使、檢校太尉、檢校尚書左仆射、檢校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衙內都虞侯、衙內都指揮使等官職,有的還被朝廷封郡王爵位,可謂官高爵顯。從史料文獻記載中我們可以了解曹氏家族的人員構成、官職、生卒年等信息,但對于曹氏家族成員樣貌的描繪卻幾乎不可見。曹氏家族長期統治瓜、沙洲一帶,其家族成員之間的關系如何?他們日常生活、飲食起居如何?這些信息在史料文獻中都很難找到。然而這些在五代敦煌壁畫中卻可以清楚地看到,譬如現存的敦煌98窟、100窟、454窟(圖1—圖3)都是集中反映曹氏家族成員的供養石窟,結合《敦煌遺書》中關于這三窟的建造記載,我們可以較為清楚地了解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曹氏歸義軍初建時的內憂外患和逐漸強盛的過程。
在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供養人畫像中,曹氏家族是唯一以家族形式出現的供養人形象,張大千共臨摹了《曹議金像》《曹元忠像》《曹議金像夫人回鶻可汗的圣天公主像》《曹元忠夫人像》。畫中對兩代曹氏家族人進行了詳盡的描繪,從面部五官、發型到服飾等等都嚴格按照壁畫中的人物形象描繪,并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撰述,分兩大階段,前一階段,美術史家繼承古代治史傳統,重視文獻資料,以畫家作為畫史的主人公,以卷軸畫作為繪畫發展的實例,著重筆墨分析,尋求流派的淵源;后一階段,即1949年后,美術史論家除了重視文獻之外,同時將視線轉移向田野考古領域。考古新發現的巖畫,帛畫,現存寺院、石窟壁畫及民間繪畫等等,都被充實到史冊中。自敦煌藝術被大規模地發現后,中國美術史研究逐漸受到來自考古實物的挑戰。以考古實物為基礎、具有實證色彩的美術史寫作模式,是與形式主義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提供了另一種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傳統藝術的視角。
二、“以作品形式為中心”的畫史關注點
傳統的中國美術史研究看重文獻材料,多以繪畫和畫家為中心。過去的著作多以“繪畫史”“畫學史”為名,這表明大多數人關注的重點是繪畫,在他們看來,“筆墨”是中國傳統繪畫的本質要素之一。正如陳師曾在概括文人畫的要素時提到的四點,人品、學問、才情、思想,傳統中國畫史研究是不重視形式問題的,而看重繪畫的“人”。但以畫家為中心的美術史是無法將建筑、青銅器、陶器以及其他工藝品納入自身體系的。因此,傳統的文人畫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與考古實物不相容的概念。“筆墨”“書畫同源”這些觀念已經使中國傳統繪畫形成了一個具有自身特色、有機而封閉的統一體,這種統一性構成了張彥遠美術史模式的基礎。
近代中國的美術史論家較早關注“形式”問題的是留學德國的騰固。受到歐洲當時盛行的形式主義研究的影響,滕固認為,根據現代學術的發展,將考古實物排除在外的美術史是不可思議的,因而放棄那種以藝術家為中心的美術史模式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引入考古實物之后,美術史的統一性,自然就由形式來承擔。這一點在他所著的《唐宋繪畫史》中有充分體現。《唐宋繪畫史》關注的雖然仍是繪畫,還沒有明確涉及太多其他方面的考古實物,卻旗幟鮮明地提出應該以藝術作品本位的歷史來代替藝術家本位的歷史,并強調使用風格分析這種形式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美術史。民國時期,將“形式”分析的方法運用到對傳統繪畫的研究中有著十分現實的意義。張大千一直關注畫面形式的問題,他早期所創作的山水、人物畫其實已經有了突破一般文人畫的野心。尤其是1943年從敦煌歸來后,張大千的畫風有了很大的轉變,最為明顯的就是其人物畫中的“雙勾”線條以及山水畫中的“青綠設色”。這一時期,張大千仕女畫的線條更明確地具有表現形體空間的特征,這無疑是從敦煌的唐代壁畫中總結學習到的。1944年所作的粉本《麻姑獻壽圖》(圖4),用筆增加了力度,清晰地呈現出“提與挫”的力道,行筆不追求流暢感反而有滯留感,勾勒中又明顯注重柔曲中見挺拔的力道。衣紋明顯依著形體轉換而變化,特別是在長線的末梢,稍加力道,使衣裙的形體的空間轉折結構躍然紙上,這是典型的以線條表現形體的結果。
張大千在談論敦煌壁畫時,特別提到“線條”的問題,由此引出白描人物畫,他指出:“人物畫的線條要有剛勁的筆力,一條一條地畫下去,中國有一種白描法,即專門用線條來表現。”⑦可見,在張氏看來,白描人物畫中的線條是傳統人物畫極佳的表現手段,由于在文人畫中得不到重視,這種方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被人所知,當張氏在敦煌石窟中見到了古人表現人物造型所用的就是這種白描人物后,他顯得十分激動,甚至認為“線條被復活了”。從現存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看,他確實將線條運用到極致,尤其是粉本作品中對佛、菩薩、供養人、建筑物、藻井的線描勾勒。
從1941年赴敦煌臨摹壁畫到60年代開創潑墨潑彩風格這段時間,屬于張大千創作生涯的中期,也是他從傳統青綠山水向現代青綠山水過渡的重要時期。在創作方面和藝術史研究的觀念方面,他的嘗試都引發了新的動向。他所創作的青綠山水畫其實是一種現代青綠山水畫,是對傳統青綠山水畫的突破(圖5)。學習古人又不拘泥于古人,張大千基于對中國繪畫史上具體作品的研究,尤其對敦煌的多件壁畫的逐一臨摹,拓展了對青綠山水的創作認知。不受程式與章法的限制,畫面中幾乎不出現具體的景物,在繪畫時,以幾何形對現代青綠山水進行重組,通過點線面的有秩序的組合、色彩的塊面感,來加強畫面的視覺沖擊力。另外,由于張大千長期關注西方現代繪畫藝術,因而在他的潑墨潑彩畫中也可以看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子,尤其是“抽象主義繪畫”。他借鑒西方繪畫的色彩來改革中國青綠山水畫。畫中的墨、色達到了明度、純度、色相的和諧。色彩由單調變為姹紫嫣紅,色塊表現各種具體事物,把它們調節成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山雨欲來》(圖6)是張大千晚年創作的一幅潑墨山水佳作,也是一幅典型的現代青綠山水畫典范。畫中的墨、綠、青、藍雜糅、交融、碰撞,畫面中并無一處具體的場景,但觀者卻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暴風驟雨將要席卷而來,墨色相交,實中有虛,虛中有實,整幅作品透出流光溢彩的色墨淋漓,也是激情婉轉的情感迸發,帶來視覺上無邊的震撼和心靈上前所未有的跌宕起伏。
1946年,《藝術論壇》的主編劉獅在“現代藝術論”專號中刊登了《追記張大千畫展》。文章贊揚張大千敦煌后繪畫“作風亦為之大變,無一畫無出處,無一筆無來歷”。可見張大千對于古代藝術作品的用心借鑒。⑧同時,劉獅的文章探討了張大千從敦煌歸來后,在技法與形式上的問題,他認為張大千在形式上的改變是一種創新,這種創新正好契合了當時中國現代藝術所關注的形式主義問題。甚至還將張大千與黃賓虹作比較,認為黃賓虹“用筆軟,且支離破碎,一點層次都沒有”。⑨《藝術論壇》是介紹現代藝術的一本期刊,主編劉獅曾是決瀾社成員,這本期刊的學術觀點是立足于繪畫的“形式”問題上的,刊載過《現代繪畫運動概論》《卞卡索的藝術方法》《后期印象派的巨像——高更》《關于藝術樣式問題》等一系列介紹西方現代藝術的文章。因此,劉獅在文章中對張大千技法、風格、形式等問題的論述,反映出近代中國對美術史的研究已經開始轉到“以作品為對象的研究”上來。
注釋:
①劉思訓:《中國美術發達史》,商務印書館,1950年,第63頁。
②童書業編:《怎樣研究中國繪畫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3頁。
③引自《張大千畫語》,岳麓書社,2000年,第228頁。
④司馬光:《資治通鑒(252卷)》,中華書局,1956年,第8164頁。
⑤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唐明宗紀》,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第575頁。
⑥脫脫等:《宋史·外國傳》,中華書局,1977年,第14123頁。
⑦同③。
⑧《藝術論壇》1947年第1期。
⑨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