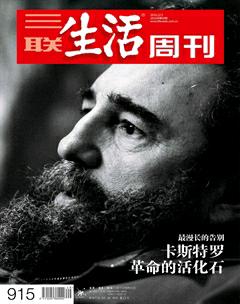郭川:成為船長
邱楊
“當時有人跟我說,你只要堅持到最后從船上走下來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會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國元素,并不是因為實力而入選。“或許有些人覺得這樣的經歷已經足夠,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實。”
失聯
郭川出發前,朱悅濤曾特意飛到北京為他餞行。這天晚上,老大哥放心不下即將遠行的兄弟,不厭其煩地反復叮囑:“大江大海都過來了,你小子一定不能大意,可別成了老水鬼。”沒想到,這一面竟成了他們之間的訣別。
事實上,朱悅濤對這次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并不擔心。相較于三年前持續了138天的單人無間斷環球航行,郭川這次的挑戰難度不算大。他的狀態也很輕松從容,以至于身邊的朋友們并沒有將之視為一次危險的航行。自從10月19日晚上,郭川獨自駕駛著超級三體大帆船從舊金山金門大橋出發后,朱悅濤也沒有像郭川過去單人環球時那樣,密切地關注他每天的實時航跡。直到26日上午10點,一則電話打破了平靜。
“郭川那小子,已經20個小時沒動靜了。”電話里傳來朋友焦急的聲音,朱悅濤心里咯噔一下,趕緊打開網站查看郭川的實時航跡——原本20節的船速已經降到幾節,航跡變動很慢。“會不會是GPS故障?”朱悅濤依然不敢相信出事了,不死心地追問。直到朋友告訴他,美國軍艦已經趕往事發地,究竟人還在不在船上,一切都是未知數。
這并不是郭川第一次失聯,12年前那種刻骨銘心的恐懼煎熬,瞬間從朱悅濤的記憶中打撈出來。2004年9月,是郭川第一次作為船長,從青島遠航至日本下關。就在起航的第二天,他們的船就遇上了臺風。到了下午17點約定好的通話時間,朱悅濤卻怎么也打不通衛星電話。作為這次航行的策劃人,他急得整晚都沒敢合眼,船毀人亡的陰影始終伴隨著失聯的焦灼,就像一顆遲遲沒有爆炸的啞炮。
第二天清晨,天剛微亮,朱悅濤又開始一遍接一遍地打電話。直到7點左右,一直悶聲不響的電話突然被接通了,在聽到郭川聲音的那一剎那,積蓄了整晚的焦慮和擔憂一下子得到了釋放,40多歲的朱悅濤在電話里哭得像個孩子,眼淚按捺不住地往外涌。

2016年9月16日零點48分24秒,郭川帶領6人隊團隊駕駛“中國·青島號”沖過白令海峽終點線,創造了完成北冰洋東北航線的世界紀錄
此刻的他多么希望,這次失聯也像當年一樣,只是虛驚一場。但很快,美軍的前方搜救傳來了壞消息——“青島號”帆船的大三角帆落水,船上并沒有找到郭川的蹤影。人船分離的現實,讓朱悅濤很難接受,他相信一定是在極其意外的狀況下造成的。在他的印象中,從12年前第一次見面時起,郭川就一直是非常嚴謹的人。
“形象船長”
彼時的朱悅濤是青島奧帆委的綜合部部長,正在為全國第一艘無動力遠洋帆船“青島號”尋找船長。見到郭川第一面時,他試探性地問:“你玩過大帆船嗎?”郭川說:“做過,在香港和奧克蘭學過一點兒。”不同于很多人滿嘴打包票的做派,這個老實直白的回答讓朱悅濤心生好感。眼前的中年男人話不多,甚至有些不善言辭,但給人感覺很踏實正派,對人不設防。僅僅第一面,朱悅濤心下就認定,就是他了。
事實上,朱悅濤已經為船長人選犯愁了很久。作為北京奧運會帆船賽事的承辦城市,青島開始提出打造“帆船之都”的城市口號。朱悅濤由此萌生了“航海三步走”的大膽設想:第一步跨洋出海,第二步中國沿海行,第三步環球航行。但在彼時的青島,海面上幾乎看不到大帆船的影子,在中國的沿海城市里,也鮮有停靠遠洋帆船的港池。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2004年的上海船展上,朱悅濤認識了張偉民。后者剛剛買下兩艘美國亨特40遠洋帆船,并成為其在華的商業代理。看準了正在升溫的奧運會效應,在船展上兩人一拍即合,張偉民同意將船停靠在青島,來實現朱悅濤的航海設想——由青島人駕駛遠洋帆船,跨洋出海宣傳奧運會。
這下子船有了,但棘手的是,缺少一個能駕駛遠洋帆船的青島人。在朱悅濤心里,合適的人選除了是青島人之外,還要對帆船航海有熱忱,還得有閑不缺錢,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來遠航。如此苛刻的條件,以至于他找遍了整個青島,愣是沒找到合適的人選。
“我們雖然有全國第一所航海運動學校,但上到教練員,下到運動員,都是玩的運動帆船,這和遠洋帆船完全是兩個概念。他們也不具備遠洋航行的心理素質和技術能力。”朱悅濤打聽到廈門、深圳等地有這樣的航海能人,但青島人的限定條件又把范圍圈死了。
就在這時,張偉民向朱悅濤推薦了郭川,當時的郭川已經在極限運動圈小有名氣。在此之前,郭川一直是傳統意義上的“學霸”:以優異成績考上北航飛行控制器專業,又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第一批MBA畢業生,畢業后在航天部下屬國有企業工作,負責國際商業衛星發射的相關工作。
但在體制內待久了,郭川總有種被束縛的感覺。1999年,34歲的他辭去了副局級的職位,一頭扎進了極限運動的世界里。那時的北京,生活成本并不高,也不像現在有著房子車子等一大堆令人緊張的話題。他只覺得人生還很長,趁著單身,該干點自己喜歡的事了:他學開滑翔機、潛水、滑雪,玩風箏板……嘗試一切有趣的挑戰,帆船也是他的諸多興趣之一。

10月28日,在山東青島奧帆中心情人壩,中國航空航天大學校友和社會各界人士100多人為25日在太平洋海域失聯的郭川祈福
和郭川見面后,朱悅濤當即判斷,眼下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除了郭川是青島人中為數不多摸過大帆船的之外,更打動朱悅濤的是郭川身上的那股韌勁。“說不上來是種什么感覺,就是覺得他這個人挺靠譜的。”他向郭川描繪未來的宏偉藍圖,一定要把郭川打造成青島的第一位遠洋船長。
2004年正好是青島和日本下關建立友好城市25周年的歷史節點,朱悅濤便策劃了“奧運友好使者行”的活動——郭川作為船長,駕駛著“青島號”帆船將青島市市長的信送到下關市。現在回想起來,朱悅濤卻感到后怕:“那時候真是無知者無畏啊!當時的我們對航海根本沒有概念,想得很簡單,反正船沉不了,漂著也能漂到吧。”
當朱悅濤向青島市領導匯報時,有人潑冷水說:“一個浪拍過來不就完了?”但領導最終下了決心,同意朱悅濤用“青島號”的名字,注冊了當時全國第一條無動力遠洋大帆船,代碼“001”。“注冊時,到底是歸體育總局管,還是交通部管,在法律上也是個空白。去保險公司也不讓投保,從來沒遇到過,一切都是新鮮事物。”朱悅濤到企業去拉贊助,“甭管你說得多天花亂墜,也沒搞到錢,最后才拉到了二三十萬元,純粹就是裸奔。”
而郭川去辦簽證時,也遇到了一個小插曲。日本簽證官問他什么時候出發,郭川說9月12日出發,22日到達。簽證官一聽不對勁:“這10天你們在哪兒?”郭川很無辜地回答,在路上。“什么路需要10天?即便坐游輪也要不了這么久。”郭川趕緊解釋是怎么回事,日本簽證官一聽竟然是駕駛無動力帆船前往,就立刻給了簽證。
萬事俱備,但很顯然彼時的郭川尚不具備遠航的能力,朱悅濤對他也沒法兒百分百信任。為此,郭川請來了香港的職業“船老大”保駕護航。出發前,朱悅濤叮囑郭川:“在岸上、在媒體的鏡頭里你是‘形象船長,但一旦上了船出了海,香港的船老大才是真正的船長,你一切都要聽他的。”郭川順從地點點頭,這讓朱悅濤對他的好感又多了一層,“他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不行的時候很謙遜,不爭名逐利”。
2004年9月12日,在青島尚未竣工的奧帆基地施工現場,郭川第一次駕駛著“青島號”帆船出海了。朱悅濤夾在歡送的人群中,站在岸邊久久目送。眼看著船剛剛駛出灣口,卻突然打了個趔趄,停住不動了,遠遠看到船上的人手忙腳亂。朱悅濤心里一緊,趕緊給郭川打電話,原來是船好像撞到了什么東西。他腦門上直冒汗,對著電話嚷嚷:“別停別停,你們趕緊走!岸上的媒體鏡頭還在拍著呢!”直到帆船消失在視線中,他的心才算落地。
可沒想到,當天夜里21點多,“青島號”帆船又悄悄回來了——船艙出現不明原因的漏水,不敢再往前開了。時任青島航海運動學校校長的代志強,特意找了幾名潛水員下水察看,卻也沒找到毛病出在哪里。一時之間,只能僵持在這里。這時,郭川突然蹲下來,舔了舔漏出來的水,發現味道是淡的,也就是說,滲進來的不是海水。眾人順藤摸瓜,很快找到了出水點——原來是出發時的意外碰撞,導致船艙淡水箱漏水。一場虛驚后,船又再次出發了。
在經歷了起航時的意外碰撞、當天夜里的返航,和第二天的臺風失聯事件后,好事多磨的“青島號”首航,終于在10天后順利抵達日本下關。
第二天就是日方的歡迎儀式。由于擔心郭川不善言辭,作為“船長”的發言講不到點子上,朱悅濤頭天晚上特意替他寫好了發言稿。盡管在朱悅濤看來,這篇發言稿盡是“正確的廢話”,但在第二天的公開場合里卻不失為穩妥的保障。他特意叮囑郭川:“一定要照稿子念,千萬別說錯話。”
到了第二天,“船長”郭川在眾人的簇擁下上臺致辭。到了臺上,他顯然有點緊張,肩膀不自覺地往上聳,手也不知道往哪兒放,兩個大拇指硬邦邦地插在褲兜里。看到站相不佳的郭川,臺下的朱悅濤使勁給他使眼色,卻也無濟于事。等到郭川一開口講話,朱悅濤心里就直呼:“壞了!這小子沒按稿子念,連拿都沒拿。”
但出乎意料的是,郭川自己講的,要遠比講稿好得多。樸素又真摯的話語,讓朱悅濤對他刮目相看,在場的日本議長也感動得頻頻點頭。朱悅濤現在回想起來,這段早年的發言,或許就是郭川內心深處,對航海最初的真實感悟——
“6年前我來過日本,當時坐飛機也就是兩個小時的事兒。6年后,在現代交通如此發達的當下,我卻以一種最原始的方式,冒著最大的風險,在海上航行了10天,才又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作為一個信使,通過這種最傳統的方式,來表達一個青島市民對下關人民的真摯情誼。”
受挫的“英雄”
當“航海三步走”面對第三步環球航行時,朱悅濤心里卻打起了退堂鼓——通過前兩次遠航,他愈發感到航海不是簡單的事。在朱悅濤看來,環球航行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出于技術和安全的考慮,他只得暫時擱置,等待時機。
沒想到,時機很快就自己找上門來。2005年的某天,一個商業代理輾轉找到青島奧帆委,向朱悅濤推廣克利伯環球帆船賽。在得知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業余環球航海賽事之一后,朱悅濤的第一個反應是,機會來了。他想借助這項賽事,實現“青島號”環球的設想。
但商業代理一張口就提出了100萬美元的冠名費,這讓朱悅濤傻了眼。政府沒錢贊助,企業不愿贊助,他找了很多奧運贊助商一家家挨個游說,卻一無所獲。他不住地感慨道:“即便是在今天,大家對航海這件事也沒有足夠的認識,更何況在10年前。”
朱悅濤并不死心,他直接給克利伯在英國的市場CEO發郵件,并勸說對方親自到中國來直接溝通。在朱悅濤有理有利有節的游說下,更是在奧運魔力的吸引下,CEO最終同意——青島市以零資金,將克利伯賽事帆船冠名為“青島號”。
接下來,又回到了選人的老問題——當克利伯賽事帆船在青島靠岸時,一定要有一個英雄般的人物從船上走下來。朱悅濤第一個就想到了郭川,他要繼續把郭川打造成青島的“航海英雄”。但不巧的是,郭川當時已經訂好了飛往新西蘭的機票,為戶外媒體拍攝滑翔翼的短片。已經答應的事,他不想臨時爽約。
這天晚上,朱悅濤在咖啡館里和郭川談到半夜。“我跟他說,你一定要繼續走下去。”好一陣動員后,郭川才終于同意了,代表“青島號”參加新加坡站至青島站的比賽。對于彼時的他來說,帆船航海和滑翔翼一樣,與他的諸多其他愛好并沒有太大差別。他之所以答應,或許更多的是出于一個青島人的責任。
2006年1月,郭川作為首位征戰克利伯環球帆船賽的中國人,登上了“青島號”。在船上,他的身份是水手,但他卻覺得自己更像一個“插班生”:“周圍都是素不相識的外國人,而他們彼此間都很熟悉。”所幸大家有著共同的目標,郭川逐漸融入到隊伍中去。盡管曾經有過兩次沿海航行經歷,但這卻是郭川第一次面對真正的大洋。多年后,郭川曾充滿感情地如此回憶:“參加克利伯,是我完成單人不間斷環球航海必須要經歷的第一步。”
當年4月,當郭川隨船抵達青島時,整個青島都為他轟動了。“當我們在家里穿著棉襖,吃著燒雞,喝著咖啡的時候,郭川卻在大洋里戰風斗浪。”在朱悅濤看來,如果說過去的兩次航海,人們的注意力都在“青島號”上,那么這一次,輿論的焦點都落在了郭川身上。當他從船上走下來時,就完成了從“形象船長”向“青島英雄”的轉變。輿論賦予他的意義,結結實實地觸動了青島人心里的柔軟神經。當年,郭川被評為感動青島的十大人物。
或許郭川自己都沒有料到,參加完克利伯回來會是這樣的境況。他還是一如既往,徜徉在極限運動的世界里,帆船航海也并沒有從此變成他的唯一。但朱悅濤卻敏銳地感覺到,或許正是從這個節點開始,作為公眾人物的郭川開始自覺不自覺地背負起一種隱形的責任,盡管這種責任在彼時還很輕微。
而真正對郭川的內心產生巨大沖擊的,則是兩年后的沃爾沃環球帆船賽。為了打開正在悄然興起的中國航海運動市場,沃爾沃環球帆船賽決定在青島設立停靠站,以中國贊助商命名的“綠蛟龍號”也將邀請一位中國選手參賽。得知消息的郭川,這次卻主動提出了申請。在完成從愛爾蘭到冰島近2000海里的測試航行后,船長伊恩決定,郭川入選媒體船員,成為這條船上11名船員中唯一的亞洲人。
但郭川卻有點沮喪,成為媒體船員而不是水手,意味著他將不能參與航行的實際操作,而是負責拍照攝像,記錄航行中的點滴傳回后方。這是他始料未及的結果。在好友黃劍的記憶中,那一天,郭川趴在桅桿上糾結了很久,最終還是決定接受媒體船員的新身份。“畢竟沒有哪個水手能拒絕沃爾沃的誘惑,就像沒有水手能躲過女妖塞壬的歌聲。”而黃劍也加入了“綠蛟龍號”的岸隊。
作為全球頂尖的專業帆船賽事,沃爾沃環球帆船賽有“海上珠穆朗瑪”之稱。一上船,郭川就立刻感受到了差距:船長伊恩獲得過兩屆奧運會亞軍,擁有四個世界冠軍頭銜;值班船長達蒙剛剛獲得巴塞羅那環球帆船賽冠軍,有七次環球30萬海里的紀錄;前槳手賈斯汀是沃爾沃上一屆冠軍隊船員……甚至連其他船上的媒體船員,也都參加過奧運會帆船賽,個個身強力壯,經驗豐富。
好比是“一個小學生面對著十個教授”,無論是駕駛技術、身體素質,還是對航海精神的理解,郭川和隊友們都隔著巨大的鴻溝。完美主義者郭川一下子倍感壓力,甚至壓得他透不過氣來。在完成第一段航程抵達南非開普敦時,郭川曾這樣剖白心跡:“這個航行實在太苦了,如果有十分力氣,那我必須全部拿出來,再加上我對航海的熱愛才能堅持下去。”黃劍在旁邊,能感受到郭川的糾結:“他好像很羞愧,那些藏在他內心深處的恐懼、退縮有時會變得非常強大。”
也正是在這個賽段里,高速航行的“綠蛟龍號”意外撞上一條大魚,20節的速度瞬間停滯,郭川一時控制不住,直接從艙門摔進前艙的垃圾堆中,幾乎把鼻梁骨撞斷。他也時刻擔心自己記錄得不好,會拖這艘船的后腿,也覺得沒面子。作為老友,朱悅濤很能理解郭川此刻的心境:“他是個很要強不服輸的人,盡管不擅長表達,嘴里不說,但常常暗自較勁。更何況,他不愿意在老外面前丟中國人的面兒。”
但壓力往往真的會壓垮人。在接下來的賽段里,郭川開始出現嚴重的失眠,幾十天睡不著覺——“就好像在水里一樣無法呼吸,溺水一般苦不堪言。”在郭川眼里,海上只剩下“熱”和“沒風”,航行已經失去了樂趣。但他仍然咬牙堅持著,就像打仗受傷后爬著往前沖。
當船隊抵達新加坡時,巨大的壓力讓郭川患上了抑郁癥。他站在酒店26層的陽臺上,問黃劍:“我要是現在跳下去,會怎樣?”事實上,他一直在服用隨隊醫生開出的抗抑郁藥物。在黃劍眼里,郭川已經陷入巨大的黑暗之中,“甚至不會笑了”。為了以防萬一,伊恩船長也告訴黃劍,要隨時準備好出發,加入下一賽段。
但是對于郭川來說,如果“綠蛟龍號”在抵達家鄉青島時,自己不能榮耀地站在船頭和支持他的家人朋友揮手,是比死還難受的事。“如果因為現在的困難退縮了,那我就永遠回不到海上了……”船隊從新加坡出發的前一天,郭川要求跟著船隊繼續參賽,他將迎著寒冷的西北風,從新加坡北上青島。事實上,這也是一段艱苦卓絕的航程,有三艘賽船在此賽段中因損壞而退出了比賽。
在抵達青島的那個晚上,郭川和前來迎接他的姐姐在碼頭上緊緊擁抱。對他來說,停靠青島是個坎——當抑郁失眠牢牢纏繞他時,親友和故土的溫暖讓他感到眷戀,甚至一度萌生退意。但“英雄”不能退縮,“一定要在大家的目光中、在媒體的鏡頭前,雄赳赳氣昂昂踏上船再次出發”。盡管心疼郭川的狀態,但朱悅濤依然勸他:“你必須繼續走下去,不然前面所有的努力就都完蛋了。”
為了緩解失眠,朱悅濤陪著郭川徹夜打球。他甚至還給單身的郭川介紹對象,想讓他在岸上有個牽掛,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但見面后,郭川覺得不來電,也就沒成。身邊的家人和朋友們,也都在想盡一切辦法幫他回到正常。
很快就到了重新出發的這一天,郭川再次拒絕了船隊讓他休息一個賽段的建議,咬咬牙繼續航行。下一個賽段是從青島到巴西里約,也是沃爾沃有史以來的最長賽段——1.23萬海里,這意味著他們將在海上連續航行長達40多天。盡管失眠抑郁的癥狀仍未消除,但郭川很清楚,船一旦開走,自己肯定會后悔。
當船越過赤道,郭川的狀態竟然變得越來越好,行至南半球時,他的病癥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好像過了某個時刻,心里所有的負擔就慢慢放出來了。”他終于熬過了這道坎,知道極限在哪里。“當時有人跟我說,你只要堅持到最后從船上走下來就行了,你就是狗熊也不會有人知道。”但郭川心里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中國元素,并不是因為實力而入選。“或許有些人覺得這樣的經歷已經足夠,但我要做到名副其實。”
在此之前,或許帆船航海和他熱愛的其他極限運動并沒有什么差別,但當他沿著隱形的軌跡一步步走過來,郭川越來越清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剛接觸大海時,它給我的感覺就是好玩,那是一種單純的喜歡。當很多其他因素加了進來,包括你的經歷——比如一不留神參加了沃爾沃那次航海賽,在這個過程中,痛苦不堪的那部分,逐漸變成了收獲。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達到一個高度,這個高度已不再是起初那種單純的好玩了。”
“我只是希望把愛好變成一個真正讓別人信服的東西,對得起別人對你的尊重。”這個念頭在他的心里瘋狂蔓延生長,這一年,郭川44歲。
蟄伏的“瘋子”
在沃爾沃帆船賽結束后,郭川突然消失了,從人們的視線中淡出。
他單槍匹馬遠走歐洲,開始按照職業化的方式進行系統訓練。“從一開始,郭川的想法就很明確,只瞄準了單人航海。”曲春是青島航海運動學校的副校長,出發前,郭川曾跟他深入探討。相較于法國,曲春感覺英國的培訓更加嚴謹。但郭川最終選擇了法國,他看中的恰恰是法國在單人航海上的成熟度。“法國有很多針對單人航海的專項訓練,從設備器材到市場環境,都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這里盛產單人航海的冒險家。”
盡管在此之前,圈子里還從未有人敢做這樣的挑戰,但這個決定放在郭川身上,曲春卻并不覺得突兀。早在十幾年前,曲春就認識郭川,在他的印象中,郭川做事從來都是踏實嚴謹。“他很清楚自己的差距,也不盲目冒進,而是一步一個腳印地成長進階,默默積攢力量。”
事實上,從團隊航行轉向單人航行,風險和難度都呈數量級的增長。“比如說睡覺,要訓練每20分鐘醒一次,一般正常人誰扛得住?還有潛水、水下維修、氣象分析、無線電通訊等等專項課程,要求也更嚴苛。”在曲春看來,單人航海對人的綜合能力要求極高,當遇到故障、遭遇兇險時都得一個人去應對,難度之大不言而喻。
更難熬的是心理上的孤獨和恐懼。曲春也曾隨團隊出海航行,“在海上的夜晚,如果沒有月光,那真是漆黑一片。尤其在極度疲勞時,極易出現各種幻覺”。曲春就總感覺前方有一座大山堵住航道,眼看著船馬上就要撞上去。盡管有電子導航設備和雷達,但這種恐懼感卻揮之不去。在蒼茫的大海上,一船人顯得過于渺小,這種恐懼會傳染,時間長了甚至連交流能力都會下降。“更何況是單人航海?幻覺、恐懼、無助會輪番侵擾你的意志。”
航海的人通常分兩種,一種是十年怕井繩,另一種是會上癮。吳亮很能理解郭川對帆船航海的癡迷,他和郭川一樣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名校畢業生,都是在玩遍極限運動后最終停留在帆船上。或許旁觀者很難理解郭川的投入和付出,但吳亮卻感同身受:“內心深處想要給自己一種自由方式,來詮釋對生命的理解和熱愛。”事實上,帆船航海是很孤獨的。“在海上你沒有觀眾沒有鎂光燈,一個人赤裸裸地面對大海,用心在和它對話。”
“世界上有將近1000多個級別和項目的帆船,你能想象嗎?”在吳亮看來,帆船不僅是所有體育項目中最復雜的,也是對人的綜合能力要求最高的。“儀表、風向、水流、機械、電子、力學,這些知識儲備在航海中都很重要。”作為典型的理工生,吳亮越來越發現,之前的積累都仿佛是為了遇上帆船而準備的。這是吳亮的優勢,同樣也是郭川的優勢,其中的復雜和變化對他們來說,有著極大的挑戰樂趣。
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渴望嘗試單人航行,盡管單人航行在航海圈中榮譽極高。“這意味著要放棄正常人的生活,就這一點,99%的人都做不到。”吳亮也暫時沒想過單人航行。“按正常人的標準來看,我們玩船的都是異人,但單人航行,全世界也只有極少數的‘瘋子才會干,這需要更為強悍的意志和能力。”
而郭川恰恰就是這樣的“瘋子”,他背井離鄉孤身一人來到法國艱苦訓練。他曾這樣描述那段苦行僧般的日子:“風景再美,也視而不見。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我得去克服什么——那些孤獨、情感、似有似無的情緒。”對郭川來說,那也像是一種精神上的訓練。他后來之所以能在海上一個人忍受138天,這段經歷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問我會孤獨嗎?當然會,但比你們想象的好得多。”
黃劍在生活中見證了郭川那個階段的“瘋狂”。“郭川是一個很專注的人,在法國為了訓練,他可以天天吃我們看起來會受不了的單調食物,每天只睡五六個小時,腦子還要滿負荷運轉。”黃劍相信,以這樣一種職業態度執著準備的人,成功只是時間問題。跟朋友聊天時,郭川也吐露過想成家。“他說最好是在城市繁華一點的地方,因為航海這些年,總是在荒涼偏僻的荒野,太寂寞了。他也希望家里有個為他熨襯衫的女人……”
幾年后當郭川終于成家時,卻無法與妻子長相廝守。他仍然繼續在法國過著苦行僧般的留學生活:每天早上8點到港口訓練,晚上19點回去查郵件,并給懷孕的妻子打電話。此時的他,仍然在為航海夢想而孤身奮戰。所幸成效已逐漸顯現:他是參加環法帆船賽并首次奪冠的中國人,也是首位參加跨大西洋Mini Transat極限帆船賽事的中國人。
但追逐夢想的路上不是沒有遺憾,郭川甚至錯過了與父親的最后一面。當他在法國為Mini Transat資格賽做準備時,接到了父親在青島去世的消息。在巴黎機場,他一直等到凌晨3點,卻被告知航班因機械故障而取消。那一刻,他知道此生再見父親一面已是奢望。在郭川的記憶中,父親長期臥病在床,嘴上卻總說自己很好,催促兒子趕緊回去做事。“人總要遇到這一關,可我還沒學會怎么面對。父親總是以我為榮,所以我不能停下來。”郭川就像憋著一口氣想要潛到彼岸,“因為一旦停下來,我就會迷失方向。”
138天的修行
郭川是在2010年的春天,萌生單人不間斷環球航行的念頭。心念一旦生發,就難以遏制。對于這個念頭,朱悅濤是強烈反對的:“太危險了!”郭川讓朱悅濤放心,他的決定并不是盲目冒進,經過這幾年的系統訓練和比賽實踐,郭川早已不是往日的他。
在那段時日里,他總是反復向朱悅濤說起一部電影:男主人公也在進行不間斷單人環球航行,但在靠近南美某個島時,他受不了靠了岸,后來他又繼續航行,最終回到了英國。媒體把他稱為航海英雄,但英雄卻一直自責,最終受不了良心的譴責而自殺了。在郭川眼中,單人不間斷環球航行是他實現自我價值的夢想,他不容許自己中途放棄。
郭川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創紀錄。事實上,帆船項目在西方國家開展很早,世界上已經有近70位專業水手駕駛帆船完成過單人不間斷環球航行。郭川需要尋找一個窗口期——他發現在40英尺這個船體級別,國際帆聯還沒有環球航行的世界紀錄。他選擇了一條異于前人的新路線:從青島出發穿越赤道,抵達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然后向東繞過好望角,再穿越赤道從南中國海域回到青島。
事實上,單人環球絕不只是一個人的奮斗,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很多社會資源的整合協助。一向嚴謹務實的郭川很明白這一點,盡管他的性格并不擅長社交。2012年3月,在三亞沃爾沃帆船賽的一次晚宴上,郭川認識了劉玲玲。當時距離他的環球挑戰僅剩8個月,他還在尋找專業經紀團隊的協助。“吹牛的人太多了,我一開始不太敢相信。”這是劉玲玲的第一反應。直到她親眼看到了郭川在法國的訓練,郭川的專注打動了她,臨走時,她決定幫助郭川,成為他的項目管理人。
但找贊助卻遠比想象中困難。朱悅濤也曾經嘗試幫郭川拉贊助,但很多企業都難以理解——“這么個小船,那不是說翻就翻嗎?”擔心航海失敗影響企業形象,縱使朱悅濤說破了嘴皮子,對方也不認可。現在回想起來,這恰恰是郭川航海面臨的現狀。“中國人是不親水的,這種文化基因決定了骨子里不具備海洋意識。哪怕青島人靠著海,還總說別淹著,歸根結底還是害怕冒險。”朱悅濤越想越遺憾,“多少年才出了郭川這么一個人啊。”
盡管喝彩聲寥寥,2012年11月18日,郭川還是獨自駕駛“青島號”帆船離開了陸地,開始了未知的環球之旅。臨出發的這天早上,曲春作為國際帆聯的代表,來為郭川即將創下的紀錄做行前認證。走到船邊他看到,船上只有零零星星幾個人在忙碌,郭川的妻子正對著清單,安靜地整理食物和礦泉水。這個清晨的靜謐畫面,讓曲春印象深刻,恍惚有種夫人送英雄出征的感覺。而郭川則是一貫波瀾不驚的樣子,即便有大事也不輕易表露情緒。
半人高的麻袋堆在船角,里面放著郭川的全部口糧。曲春翻開一看,竟是300多包薄薄的凍干食品,連種類也只有雪菜肉絲面、西紅柿炒蛋飯等三樣。“大半年在海上就吃這個,受得了嗎?”曲春有些訝異,郭川卻默默地憨厚一笑。帶上船的礦泉水,在出海后也將很快喝完,郭川隨身帶了一個海水淡化器,盡管淡化出來的水喝起來味道怪怪的,但這也是唯一的辦法。
參加過各種大小極限帆船賽的郭川,比誰都清楚即將面臨的風險。首先得熬過睡眠這一關,不能進入深睡眠,每睡20分鐘就要醒一次。他和箱子、雜物擠在不到10平方米的船艙里,盡管里面原本有張擔架床,但他卻一直睡在地板上,以便一旦出現狀況,可以迅速翻身起來。海上潮氣侵蝕進來,地板上總是濕漉漉的,他也只得和衣而睡。
在船上,他仿佛始終處于提心吊膽的狀態。“機械故障、電子系統失靈、帆的破損,這些都會帶來令人抓狂的想法——會不會造成連鎖反應?會不會就此結束?”所有問題都可能對他的心理造成極大沖擊,“相對而言,孤獨又算得了什么?”
焦慮如影隨形,郭川聽說過一個在水手間流傳的真實故事。一對法國情侶出海時遇到事故,男人爬上桅桿修理,但下來時卻突然卡住了。這真是最危險的事,上面的人動彈不了,下面的人幫不上忙,只能眼睜睜看著男人掛在桅桿上,被吹成了肉干。
而在海上,任何小問題,都可能演變成無窮大的問題。12月的一天,帆船突然遭遇大前帆破損,船帆墜入水中。郭川只得緊急停船,在漆黑的夜里用了整整一個小時才將帆撈起。風浪中他距離水面僅一步之遙,而人一旦落水,船開走了就幾乎沒有存活的機會。
2013年1月5日,是郭川的48歲生日,也正好是航行的第48天。他打開電腦,和妻子孩子們視頻了一小會兒,彼時他最小的兒子還不到10個月,他給兒子取了一個響亮的名字——郭倫布。他的年夜飯也是在船上吃的,一袋凍干食物、一袋臘腸和一盒罐頭,對他來說半飽半饑是一種常態。他也不怕承認:“在海上我常常流淚,有時候那并不是因為苦,那是一種很復雜的情緒,是一種十年磨一劍終于要爆發的感覺。”
在郭川環球的日子里,朱悅濤一直為他捏著一把汗。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察看郭川的航跡,只有看到軌跡在變化,他才能安心,“起碼說明人還活著”。有時候郭川也會用衛星電話和朱悅濤通通話,但絕大多數時候,郭川在電話里是悶的,偶爾聊上幾句,只有在通過臺灣海峽前,郭川曾和朱悅濤聊起正在猶豫如何穿過海峽。“從海峽外側走安全,從內側走節省時間,但可能遇上臺風。我說你只要平平安安回來,哪怕是用200天、300天都無所謂,都是世界紀錄。”但郭川很有主見,最終還是走的臺灣海峽內側。
事實上,郭川的冒險并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場謹慎的冒險。盡管經費有限,他還是花20萬歐元聘請了全球最頂級的氣象專家,為這場“戰斗”配備了最好的情報機關。氣象專家給出的精準氣象研判,是他做出判斷的重要依據。這也不是他第一次做出類似的決策。郭川拒絕任何浪漫化的意圖,在他看來,運氣也是大自然對團隊辛勤努力的恩賜。
經過長達138天艱苦卓絕的環球航行,郭川和“青島號”奇跡般地回到了出發地。快要靠岸時,他情不自禁地扎進冰冷的海水里,奮力游向岸邊。在爬上岸的瞬間,他長跪不起,深情地埋頭親吻腳下的土地。
停不下來的船長
在朱悅濤看來,單人環球成功后的郭川已經是個登峰造極的人物了,各種榮譽如潮水般涌來。老大哥有時候也勸郭川:“這個年紀了,挑戰也總得有個頭吧。”盡管郭川也袒露過,停下來以后想專門做遠洋的航海培訓。但說這話時,朱悅濤并沒感覺到郭川真有退意。“他骨子里不會停下來,他總是不斷地為自己樹立更高的目標。”這讓朱悅濤有些擔憂,“這家伙早晚是個水鬼。”
而對于郭川來說,嚼過的饃再吃就沒有味道了。接下來他要駕駛一艘99尺級別的三體帆船,挑戰北冰洋東北航線的世界紀錄。東北航線多年來一直被國際帆船界視為“死亡航道”。為了這次航行,郭川對上世紀70年代起至今的全套全球冰圖進行數據分析,經過近兩年的可行性研究,他終于發現了其中的機會——東北航線在某段時日里有20天左右的無冰期,這仿佛是老天為他所開的一扇窗。
不同于以往的單人航海,郭川又一次顯示了他的謹慎,對尚未熟悉的超級三體船,他并不輕易獨自操控,而是率領船隊前往。對他來說,這次航行也是與船不斷磨合的過程。四名來自俄羅斯、法國、英國和挪威的頂尖水手,成為郭川的隊友。在人選的配置上,郭川也有細致的考量,航行途中要經過俄羅斯的軍事管轄地,船員中有會說俄語的當地人顯然要便利得多。
浮冰、狂風、大霧和徹骨的寒冷,在15天的航行中,郭川和他的船員們克服了這些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在極端環境里,人性往往以最原始的姿態呈現,對于郭川來說,如何讓這些個性十足的船員們協同作戰,則是他作為船長的考驗。但此刻的他早已不是10年前那個手忙腳亂的“形象船長”,現在的他已經成為真正的船長,有能力把整條船凝聚在一起。
2015年9月16日,郭川再次創造了自己的職業新高度——實現了人類第一次以不間斷、無補給方式穿越北冰洋東北航道的世界紀錄。這次開拓性的航行在國際上引起巨大反響,帆船界權威雜志《帆船與航行》把年度成就獎授予郭川,并這樣評價:“作為來自帆船航海并不發達的國家——中國的水手,郭川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帆船航海的潛力。”而在中國帆船航海圈里,郭川也逐漸走上神壇,影響了很多后繼者。
但在郭川的內心,挑戰卻是永不止步的。在這次單人駕駛三體船穿越太平洋的挑戰中,吳亮原本要代表國際帆聯,見證郭川沖過終點。在他的印象中,出發前的郭川一直很忙,除了要對船上眾多的復雜細節進行檢查外,還要應對繁忙的媒體采訪和公益活動。“這幾乎是所有職業航海家都要面對的,除非你沒有贊助商,不需要媒體曝光量。”盡管從私心來講,航海家們或許不愿在此耗費過多時間,但對于被貼上英雄標簽的郭川來說,他無疑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他是代表著中國航海界在挑戰,而不是當初寂寂無名的冒險者。
“他也在不斷樹立自己,不斷讓自己的成績與外界的期待相契合。”朱悅濤承認,這些外部的標簽和力量也會影響郭川內心的選擇。但他更愿意將之視為一種精神動力,“如果是包袱,郭川不會越走越高”。盡管如今的郭川在面對媒體時,交流越來越自然,肩膀也不再會緊張地往上聳起,但在朱悅濤眼中,郭川仍然還是當初那個純粹的人。“他只是變得更謹慎,自制力更強。”
反而是家人朋友們一直希望郭川緩一緩。郭川的一位同學曾這樣描述:“我從來沒把他當英雄看待,從來沒有對他說‘加油,也沒有鼓勵他去創造新的世界紀錄。看到他,我不知道為什么就很心疼,我感覺他有壓力,內心有種東西在攪擾他。”
在蒼茫的大海上,伴隨著悠揚的歌聲和兒子的笑聲,結束了一天勞作的郭川手握船舵,凝神望向遠方。夕陽灑在他黝黑泛紅的面龐上,海風微微揚起蓬松凌亂的卷發,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股滄桑孤獨又滿含柔情的味道——這是郭川留給世界的最后一抹影像。在郭川失聯后,朱悅濤常常反復播放這首《Hero》,從歌聲中他仿佛能讀懂郭川的心境。“這或許是一種信號,生活中那些曾經失去的、難以兩全其美的東西,或許他越來越明白航海不是生活中的唯一。”郭川的小兒子已經上幼兒園了,他最羨慕的是妻子能去孩子的家長開放日,這種俗世的溫暖越來越讓他眷戀。而這次太平洋挑戰歸來,原本可能是一個句號。
(參考資料:《郭川的大洋夢》,黃劍著;《郭川:海上138天》,謝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