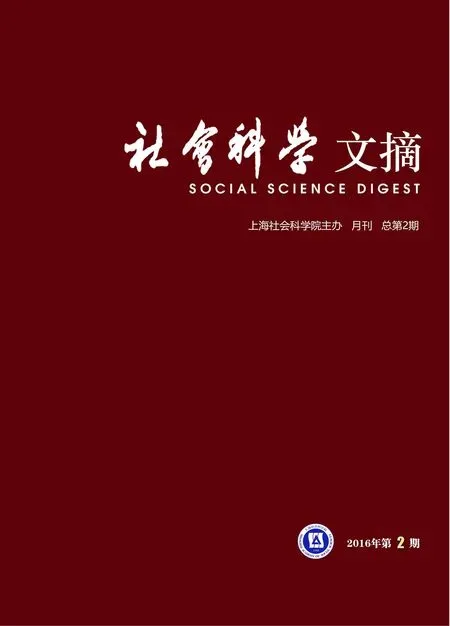思想啟蒙與《新青年》的文學立場
文/劉勇
思想啟蒙與《新青年》的文學立場
文/劉勇
作為開啟中國社會歷史現代轉型的第一刊物,《新青年》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對新舊文化的辨析與傳承,對新思想、新倫理、新道德的關注和討論,是其他任何一個刊物都不能比擬的。在《新青年》開啟現代中國社會歷史轉型、營造強勢的新的文化生態的同時,中國文學也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轉型。《新青年》把新文化與新文學不可分割地凝結在一起。《新青年》本身并不是一個文學刊物,但是五四新文學乃至整個20世紀的中國文學,都與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啟蒙之“徑”:作為切入點的“文學革命”
作為一本綜合性雜志,《新青年》為何會積極推動文學的現代轉型呢?這是我們討論《新青年》與新文學關系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新青年》創刊之初并不旨在建設一種新的文學,而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陳獨秀試圖將《青年雜志》打造成青年群體的精神導師,以實現啟蒙民智的目的。初期的《青年雜志》和當時政論時評類雜志并無兩樣,文學只是作為思想政論時評的一個附屬品和點綴品而已。沒有形成自己特色的《青年雜志》最終不僅銷量慘淡,也沒有產生實質上的影響。
隨著陳獨秀赴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青年雜志》改刊為《新青年》,該刊迎來了自己的重大轉機。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魯迅等一大批北大文科教授的參與,使得這個旨在思想啟蒙的雜志選擇了“文學革命”卷土重來。回首歷史發展之路,無論是中國文學還是世界文學,文學的命運始終與政治思想變革緊密相連。穩定的社會環境會催生文藝作品數量的繁榮,然而文學的高度卻往往誕生在動蕩的時局之中。社會的動蕩、戰爭的殘酷會最大限度地喚起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到了晚清,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之下,爆發得更加強烈、更加集中、更加典型。其實,當時并沒有那么多人真正喜歡文學,而是改造社會、拯救民族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使大家共同匯聚到文學的大旗之下。
因此,與其說“文學革命”是《新青年》精彩的“轉身”,不如說是陳獨秀等人終于為這場蓄謀已久的思想啟蒙運動找到了最合適的切入點和最有力的抓手。這就決定了在《新青年》上所掀起的文學革命,是期望通過文學的力量達到智識啟蒙的目的,最終是為了拯救深陷于內憂外患的民族危機。
啟蒙之“姿”:有用之用的文學
既然一代知識分子都選擇文學來實現開啟民智、實現啟蒙的目的,那么一種什么樣的文學才能擔得起這個重任呢?在《新青年》同仁看來,無用之用的消遣文學必須馬上摒棄,一種全新的文學亟須馬上建立。
這首先體現在《新青年》提倡的是一種現實功用的文學而非審美的文學。無論是陳獨秀在“六要六不要”提出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還是胡適提出的“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都體現出了一種明顯的重“功用”的傾向。從《新青年》引進的小說類型上看,寫實主義的題材居多。但是,對于某些所謂審美性較強的作品,《新青年》則選擇了漠視甚至是批判的態度。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提出著名論斷:“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是‘非人的文學’。”
其次是《新青年》的激進性遠遠大于它的學理性。北京大學作為全國的最高學府,一方面給予《新青年》最深厚的學術支撐;另一方面卻一改以往學院派老成持重、理性穩健的風格,使得《新青年》始終以激進和先鋒的姿態沖擊著當時的文壇和學界。雖然作為新舊之交的時代產物,《新青年》前幾卷還保持著半文半白的表述方式,但這絲毫不影響《新青年》的先鋒性。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表示:“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舉‘文學革命’大旗。”這一大批學院教授、古文大家的“叛變”,自然會讓新文學陣營“浮一大白”,但是也同樣引起了《新青年》與其他保守主義學者的戰火。反對者的聲音,并沒有擊退《新青年》,反而使它集聚更大的能量和更強的火力全力展開攻擊。
再次是《新青年》重文學理論而輕作品創作。王曉明曾這樣評價過五四新文學:“先有理論的倡導,后有創作的實踐;不是后起的理論給已經存在的作品命名,而是理論先提出規范, 作家再按照這些規范去創作。”新文學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得以轉型,不是文學自身發展的結果,而是被“強行設計”出來的。我們看到《新青年》的主要版面都給了“建設一種什么樣的文學”之類的討論,而具體的文學作品發表得比較少。
《新青年》之所以能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發動機,就在于它源源不斷地為新文化運動、新文學提供方方面面的理論支撐。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的“八事”、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提出的“三大主義”、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等,都從理論上將新文學從形式到內容闡釋得非常明確、非常具體。在這些成熟而具體的理論指導下,白話詩歌、白話小說、白話散文以及白話戲劇才逐漸發展起來。就這樣,新文學一邊被這群大學教授系統的理論建構所引導,同時又突破了學院派的限制,自由而迅速地通過《新青年》這個平臺傳播給廣大的讀者,進而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啟蒙之“源”:西方理念的切入和傳統精神的對接
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先鋒者來說,“啟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如何進行思想啟蒙,特別是如何通過文學來進行思想啟蒙,在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中找不到可以借鑒的經驗。殘酷的現實證明,中國自身的文化資源己經無力支撐起復興的歷史責任,他們只有把目光投向先進的西方。西方的民主、科學、人權、自由、進化論等,不僅為他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也為中國的文學啟蒙提供了參照體系。
而《新青年》致力于大量引進西方文學的目的,實際上也不在于讓讀者都能系統地理解西方文學,主要的是借西方文學這種“新”的力量來沖擊國內腐朽、黑暗的文壇。至于這種“新”到底本質上是什么,它是如何發展、如何演變的,在新文化與新文學的倡導者們看來,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對西方的所謂種種的“新”的追根尋源,也并不是《新青年》的根本意圖。當然,從客觀層面來講,想要對西方文化與文學有一個徹底的了解也很難實現。西方發展了幾百年的各種形態的文化與文學在一時間涌入中國。這種“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的迫不及待,往往會帶來一個后果,那就是《新青年》對西方文化與文學的引入往往只能停留在空泛的概念層面,而于其精神本質無意也不可能有深入地理解。
《新青年》最初之所以要建設新文學就是要依靠文學的力量傳遞新的價值觀,以達到啟蒙民眾、改造社會的目的,而非通過審美來洗滌人心。因此,這種強調文學的“功用”性,更大程度上還是承續了中國古典文學的“以文言志”“文以載道”的深厚傳統。因此,由于啟蒙需要順勢而生的新文學,實際上體現的是中國傳統文人“濟世”“救民”的精神和民族憂患意識,《新青年》對于文學“教化意識”與“功利意識”的強調與中國傳統“文以致用”的思想有著深刻的血肉聯系。這樣一來,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一直秉承著西方科學的進化論精神的《新青年》,在向西方各種文藝思潮學習過程中,并沒有選擇當時西方正在流行的“現代主義”,而是選擇了已經“過時”的現實主義。對現實人生的關注,從來都是中華民族文學傳統的重要一環。西方的“現實主義”思潮之所以能在中國形成大勢,主要是因為它與中國傳統的民族性進行了本土性的經驗對接,而當時在歐洲正流行的“現代主義”,卻沒有這種優勢。
無論《新青年》在文化姿態上表現得多么“先鋒”或“西化”,無論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如何決絕,但它在對文學本質認識上實際延續的是傳統文化精神。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形成的慣性,不是《新青年》一時就能夠輕易擺脫的。《新青年》與傳統文學的關系,也絕非“全面反傳統”幾個字就能簡單概括的。
綜上可見,在《新青年》引領下的啟蒙文學,依靠“西方”資源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沒有對外來西方文化與文學的借鑒,中國的文學不可能實現現代的轉型;但是,中國傳統文人的責任感和憂患意識是促進這場啟蒙運動的內在動因,中國古典文學的載道傳統是《新青年》發動的這場啟蒙運動得以與文學緊密結合的根本性因素。
啟蒙之“流”:新文學的發展走向
《新青年》對于新文學所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一個客觀事實是,新文學在《新青年》綻放的時間是比較短暫的。隨著文學革命的漸漸落潮,《新青年》也逐漸失去對新文學的關注。從1920年9月8卷1號開始,《新青年》完全成為宣傳社會主義運動的刊物。但是,一個刊物的價值并不能以它存在時間的長短來評判,更重要的是看它的影響是否長遠。《新青年》在歷史轉型的重要關口奠定了新文學的整體發展走向,它對新文學的建構深深影響著幾十年、甚至是百年以后中國文學的發展。在《新青年》將白話文學、寫實文學、易卜生問題劇等這些理念投放在公眾領域之后,現實主義以其強大的社會批判性和沖擊力,沖破了古典文學的壁壘,成為新文學的主潮。現實人生成為了文學表現的重點,一種“立誠的、新鮮的寫實主義文學”風靡一時。這種以文化批判為指向的寫實主義文學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格調,并整整影響了之后一個世紀的文學發展。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摘自《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