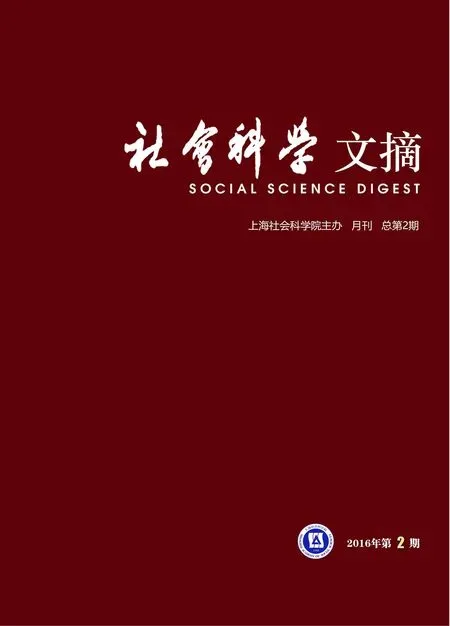知識分子如何避免觀念的陷阱
——從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理性到政治激進主義
文/蕭功秦
知識分子如何避免觀念的陷阱
——從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理性到政治激進主義
文/蕭功秦
近30年以來,知識界對新文化運動的心態發生了明顯的轉向。如果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處于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主流知識界對這場思想文化運動懷有強烈的道德激情與浪漫審美心態,那么,現在更多地是轉向平和、冷靜與審慎的反省。本文即嘗試對20世紀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思想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作進一步反思。
中國激進反傳統主義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獨特現象
眾所周知,發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其內部始終存在著兩種思潮勢力,一種是北方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激進反傳統派;另一種則是南方以《學衡》為代表的,被汪榮祖先生稱之為具有新古典主義的人文主義立場的保守派。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北派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潮是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宣稱,“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也”。這種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想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北派的宣言,這種話語在當時占有優勢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全盤推翻傳統的激進代表人物,以吳稚暉、錢玄同與魯迅三人最為典型。吳稚暉喊出“把線裝書扔到茅坑里去”的著名口號。錢玄同提出要“廢除漢字”,以世界語取而代之。魯迅最著名的觀點是“禮教吃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全盤的反傳統主義思潮對新一代中國人的思想文化與政治選擇,均具有持續的影響力。1917年9月,青年毛澤東在對友人的談話中就鮮明主張:“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從,奴隸性成,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網羅,定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這種激進反傳統主義對于打擊保守勢力有正面貢獻,但也帶來一系列消極后果。激進反傳統的思維方式以人們并不曾意識到的方式延續到文化大革命。
毫無疑問,20世紀初期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獨特文化現象。眾所周知,在20世紀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非西方民族,在走向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都是曾不約而同地訴之于本民族的古老傳統,來強化民族凝聚力與認同感,以此來推進本民族的現代化進程,日本是如此,“復興傳統的土耳其”為號召的土耳其基馬爾是如此,以“印加帝國”作為民族共識的來源的秘魯現代化精英也是如此,而中國的知識界主流,卻選擇了與傳統文化公然決裂的方式,來啟動本國的現代化運動。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激進的全盤反傳統主義思潮?
浪漫主義與進化論:激進反傳統主義的兩重動力
中國的全盤反傳統思潮產生的原因,可以從情感與思想邏輯兩個層面來考察。
在心態情感層面,浪漫主義崇尚自發的沖動、獨特的個人體驗,強調人在沖決世俗平庸生活的規范信條時,在破除習俗、鐵籠般的制度對人心的束縛時,所產生的高峰生命體驗,在他們看來,由此而形成的生命美感體驗要比可能導致的實際后果更為重要。用羅素的話來說,浪漫主義者在推開對人性的種種束縛時,往往會獲得一種“權能感與登仙般的飛揚感”,使他覺得即使為此遭到巨大的不幸也在所不惜。浪漫主義在人類思想解放中,具有重要積極作用。思想解放不可能是冷冰冰的理性判斷的結果,它肯定要伴隨著人們在精神上強烈的對“登仙般的飛揚感”的追求。任何重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都可以看到人類的浪漫主義的影子。而中國近代史上的浪漫主義,是對僵化的、死氣沉沉的、鐵屋般的保守習俗與現狀的一種剛憤的反向運動。
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浪漫主義,不同于18世紀歐洲以“回歸中世紀”為主旨的牧歌式的浪漫主義,這是一種在極端反傳統的快感宣泄中,在與傳統的斷然決裂中獲得精神飛揚感的浪漫主義。
如果說,19世紀末譚嗣同“沖決網羅”的吶喊是中國20世紀浪漫主義思潮的濫觴,那么,鄒容、陳天華等人則是20世紀初中國浪漫主義的開先河者。《革命軍》的作者鄒容鼓吹“非堯舜,薄周禮,無所避”繼之,陳天華以《猛回頭》《警世鐘》再繼之。陳天華對中國人的民族性的判斷,與近代中國人在現實生活中顯示出來的經驗事實并無關系,也完全不涉及前輩知識分子如嚴復、梁啟超等人經常提到的中國國民性的種種負面表現,陳天華對中國民族性的美化還表現在他把西方民主政體視為“珍饈已羅列于幾案之前,唯待吾之取擇烹調,則何不可以咄嗟立辦”。這種浪漫主義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激進文化主義的核心價值。
如果說浪漫主義是心態層次的因素,那么,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則是支撐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潮的學理與思想邏輯層面的因素。根據進化論的邏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那么,由“優者”淘汰并取代“劣者”,就是“物競天擇”的必然邏輯。既然傳統滲透著腐敗與沒落的東西,它扼殺了自由人性,使我們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那么,為了求生存而淘汰它,那就成為一個理性人必須接受的“無上命令”。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激進地拋棄傳統提供了完整的理論邏輯框架。
要看到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劑具有強大摧毀力的話語猛藥,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只有近乎極端的“優勝劣敗”兩叉分類,才具有剛性的話語力量,來摧毀頑固、封閉、僵化的專制文化對人心的束縛,才能砸碎傳統官學的保守壁壘;然而,另一方面,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激進反傳統主義者把自己祖先創造的文化,整體上看作是必須淘汰的“劣者”,使人們進入一種“文化自虐”狀態,這種“文化自虐”心理恰恰是宣泄浪漫主義快感的溫床。可以想象,當吳稚暉、錢玄同與魯迅說出那些極端反傳統的言論時,會產生“痛即美”的快感。事實上,心態上的浪漫主義與進化論提供的邏輯,在此時已經交融在一起了。
啟蒙理性的程序漏洞和兩種啟蒙理性的崛起
傳統乃是一個民族千百年來應對自身的環境壓力與挑戰過程中形成的集體經驗,傳統被打倒后,它們不再成為人們行動的準則與選擇的標準,那么用什么東西來取代傳統,以引導人們作出自己的行動選擇?
在掃蕩傳統之后,填補空白的就是啟蒙理性,所謂的啟蒙理性,就是以普世價值的“第一原理”為演繹依據,運用概念推演得出真知判斷的思考方法。此前大凡人類的傳統制度,都是以千百年來各民族在應對自身環境挑戰過程中形成的集體經驗為基礎的,人們根據這種經驗組織社會生活,形成社會規則與制度,而啟蒙理性主義者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則是可以通過“理性的”“科學的”方法,通過理性的建構,來予以確定并作出選擇。當人們運用啟蒙理性提供的普世價值與組織社會的第一原理,設計出重建社會的施工藍圖,它就進一步發展為建構理性。在建構理性主義者看來,理性人就完全可以如工程師設計機械一樣,設計出理想社會的施工藍圖,建構一個好社會。用建構理性取代經驗有什么問題?以往的人類總是依據經驗來作出選擇,對理性推導能力的崇拜,則讓人的理念具有了獨立性,人們就可以脫離經驗,直接根據理性推導的觀念來重建社會,這就使人們的行動具有與經驗事實脫節的可能性。
激進反傳統主義導致兩種啟蒙理性的崛起。一種是右翼的、以西方地方知識為普世價值與仿效標準的西化自由主義。以個人本位為基礎的普世價值,對于沖擊專制文化造成的奴性人格,固然具有革命意義,但以此為基礎設計好社會,就會陷入全面脫序的困境。
除了這種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啟蒙理性,還有一種是左翼的啟蒙理性,包括工團主義、基爾特主義、安那其主義、暴力革命主張的平等世界論。以上兩種啟蒙理性,都相信可以在脫離本土經驗的條件下,按主體認定的普世性有效的價值,建立起好社會來。這個社會不是根據本民族已往的經驗為根據,而是根據道德理想與美好價值為依據。
雖然,啟蒙主義思潮在打擊專制舊傳統方面有其正面貢獻,然而,由于傳統不能成為中和、緩沖啟蒙理性的中介物,啟蒙理性就會在自身邏輯的支配下,走向建構理性主義,由于理性本身具有的缺陷,會使這種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容易演變成對左或右的烏托邦世界的追求。另一方面,觀念與精神對人心的吸引力是如此強大,又可以使崇尚這種觀念、主義與精神的知識分子成為唯心主義觀念的奴隸,而觀念、主義與現實經驗的完全脫節,又會給社會帶來無窮的災難與始料不及的危險后果。全盤西化論產生的對西方民主的建構主義的追求,以及“文革”的極左思潮對烏托邦極左世界的追求,都是右與左的建構理性的產物,它們也都是觀念的異化的歷史后果。
知識分子與觀念的陷阱
20世紀是思想主義盛行的世紀,是由知識分子創造的各種主義支配人們的歷史行動的世紀。知識分子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們通過自己的思想,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話語的力量,正是這種輿論場上的話語力量,會進一步形成群體性的思潮與主義,認同這種思潮的人們,就會結合起來進行集體行動,并經由行動而形成人類生活中的歷史選擇。
人們相信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比一般人能講出道理來,知識分子也很自信,因為他們覺得讀了書就有知識,對自己往往有很高的估計。然而,人們對知識分子的期望不能太高。事實上,正如歷史上所表明的,知識分子也會造成時代的災難。這是因為,知識分子是運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來進行思考與思想創造的,而人的理性本身卻有著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它有一種邏輯上“自圓其說”的能力,它會編織出一種觀念的網羅,讓人脫離現實,變成作繭自縛的“觀念人”。一般說來,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個人的理性是通過抽象思維,把復雜事物予以簡化。抽象與簡化對于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但簡化的結果往往忽略了客觀事物的復雜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義性。運用簡化的理性思維來作出判斷與歷史選擇,其結果往往是消極的,甚至是災難性的。例如,觀念型知識分子對西式民主具有的普世性的認識,造成民國初年的“舊者已亡,新者未立,倀倀無歸”的社會失范狀態,建構理性簡單地把西方歷史上演變過來的體制搬用到落后的第三世界中來,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舊的傳統體制被打破了,而新的西化的體制卻由于缺乏西方社會的各種條件,而無法有效運行,這種脫序會形成全面的整合危機。又例如,中國“窮過渡”的平均主義,當人們要用全面的計劃經濟這個“完美”的制度,來取代歷史上形成的有缺陷的市場經濟時,往往只想到這種由理性建構的“計劃”的好處,卻忽視了另一面,它同樣也可能產生計劃體制下的官僚主義化,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與創造力,這是左的建構理性的產物。
其次,個人理性的缺陷還表現在,一個社會主體所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全面的,當人們根據這種片面的信息來決定歷史性的行動選擇時,就會導致歷史選擇與判斷的失誤。
再次,主體自身的信仰、激情、人性中的幽暗的心理,以及浪漫心態,這些情感性的非理性因素,如同海面下面的冰山,會不自覺地在人們的潛意識中,支配著顯露在海面上面的理性,主體的理性受感情與其他非理性因素的支配,也就會發生判斷的扭曲與錯誤。換言之,建構理性有許多“程序漏洞”,容易被浪漫主義乘虛而入。當主體把浪漫主義的東西論證為真理來追求,把浪漫主義付諸于社會實踐,就會造成烏托邦的災難。
回歸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
對21世紀知識分子來說,要避免成為“觀念人”,最重要的就是回歸經驗主義。所謂經驗主義,就是尊重歷史中形成的經驗的連續性,就是在嘗試過程當中,在錯誤中不斷地進行糾正,來找出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這兩條理路中,經驗主義比較安全、比較穩妥,知識分子應該用經驗主義來避免“建構理性主義”的缺陷,因為生活太復雜,歷史制約因素太多,我們只有在經驗與試錯中,找出相對而言更適合我們的路徑與制度。
知識分子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應該有一種“同情的理解”態度,知識分子做一個批判者并不難,只要你執著于某種價值尺度,就可以評點萬事萬物,難的是,還要同情地理解包括文化傳統在內的各種事物的多面性,因為人類現實生活永遠是“神魔混雜”的,充滿兩難性與矛盾的。只有具備了這種客觀態度, 才能更客觀地對待傳統,并從傳統中獲得啟示,更務實地、更有效地提出解決矛盾的建議與辦法。
從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人物之一是鄧小平。他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在于,從20世紀初的唯理主義思維回歸經驗主義思維。他的“摸著石頭過河”以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理論,就是回歸到經驗主義哲學,就是尊重事物的復雜性和多面性。通過經驗試錯,來尋找實現富強的合適路徑,漸進地走向強國、富民、法制與民主的目標,實現中國向現代文明轉型。
需要指出的是,單純的經驗主義有其缺陷,我們在經驗摸索過程當中,還需要一種方向感,這種方向感就是追求更美好的價值,這個美好價值是與人類共同的價值相通的。之所以稱之為“方向感”,這是因為,“方向感”意味著, 當人們在堅持追求美好價值的方向時,仍然謙虛地保持著對事物復雜性的尊重,意味著存在著對未來可能性的更大的思考空間。
一個世紀后,當人們對新文化運動進行反思時,應該意識到,對社會進步真正有積極貢獻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尊重事物的復雜性與多面性、警惕意識形態化的啟蒙理性對我們判斷力形成干擾、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者。只有這樣,知識分子才能避免左與右的各種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潮對自己思想的干擾與支配,避免陷入觀念的陷阱;而只有以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為基礎的中道理性,才能客觀認識世界,這樣的知識分子才能擺脫主觀主義,為社會進步作出真正的貢獻。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摘自《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