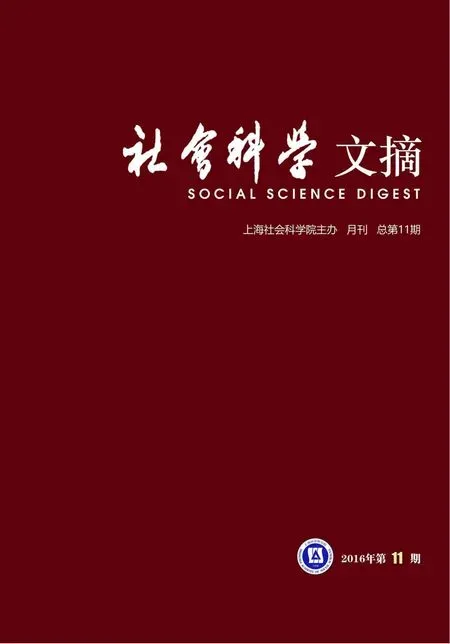擔當精神與古典文學研究的歷史使命
文/傅道彬
擔當精神與古典文學研究的歷史使命
文/傅道彬
從專業出發建構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
擔當精神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的重要內容。擔當,首先是一種政治責任,是一種建立在堅定的政治信仰基礎上的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使命感與責任感。習近平指出:“敢于擔當,黨的干部必須堅持原則、認真負責,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擔當是相對于理想與信念而言的,沒有理想,沒有信念,擔當什么,何以擔當?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所謂“初心”,就是中國共產黨人自建黨之初就樹立的奮斗精神以及所蘊含的赤子之心,就是共產黨人的早期革命理想,是矢志為推翻一切剝削制度建立富強民主、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不懈追求。而這種擔當不僅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學術的、藝術的。對于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而言,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擔當,是一個研究者從專業出發建構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的歷史責任,“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擔當精神是一種深入中國文人靈魂深處的責任意識
學術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學的研究,常常被認為是象牙塔,是遠離現實的純學術。其實沒有脫離時代政治的純學術,所謂象牙塔總是與時代風云聯系在一起的。習近平在2014年10月15日“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別談到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這個人類歷史上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經典時代。經典時代是中國學術思想的起源時期,經典時代意味著一種新的文化精神和學術視野下對傳統文獻的整理與闡釋。美國學者E·希爾斯認為:“原始經文和對其所作的詮釋都是傳統。……圣典本身也是傳統。這種‘傳統’就是對經文積累起來的理解;沒有詮釋,經文將只是一種物件,經文的神圣性與眾不同,但若沒有詮釋,經文便毫無意義。”經典的最終實現依賴于思想的升華,依賴于與時代精神的融合,正如希爾斯所言,如果沒有思想闡釋,“經文只是一種物件”,而有了思想的闡釋,經文才有了靈魂。
春秋時代是經典建立的時代。隨著西周王權的動搖,各個諸侯國實現了城邦自立,王權思想也開始動搖,思想的創新意識不斷增強,春秋士人對經典有了新的視野和目光。典型的是《周易》。《周易》原本是卜筮的著作,而至春秋,以孔子為代表的思想家們完成了對《周易》的哲學改造: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馬王堆帛書《要》之三章
這是關于《周易》研究的重要文獻,標志著《周易》完成了從卜筮向哲學的根本跨越。在卜筮與哲學之間孔子強調的是“后其祝卜”,他重視的是“德義”。這里的德義,不是宗教,不是卜筮,而是思想,是哲學;強調的不是天命,而是人的自身的力量:“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希也”。真正的士人君子求吉求福不是依靠神鬼護佑,而是依靠自身的道德,依靠“德行”與“仁義”。這里《周易》發展史上第一次公開將倫理的意義超越了宗教的意義,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巨大進步。孔子正是將春秋時期進步的倫理思想帶入《周易》,讓古老的卜筮著作融入進步的思想靈魂,使《周易》在新的時代精神下煥發出嶄新的思想光芒。
一些學者試圖將經學研究作為逃避現實的堡壘,其實,經學自其誕生起就有強烈的現實目的和政治寄托,《春秋經》本身就有“懲惡而勸善”、使“亂臣賊子懼”的政治目的。而兩漢經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都表現出經世致用的時代精神,又在流變中不斷融入新的思想精神。乾嘉學術倡導的考證和實學,本質上也具有深刻的經世致用目的和批判精神。顧炎武自稱其代表作《日知錄》包含“經術”“治道”“博聞”三大類,而其學術目的則是“明道”與“救世”。為了“明道”而從經學人手,而“考文”“知音”只是實現“明道”的手段。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顏元激烈地批判宋明理學缺少寄托的空疏學風,只知“舍生盡死,在思、讀、講、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卻堯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藝,不肯去學,不肯去習,那從討‘庸德之行’,那從討‘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千余年來率天下人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在他們看來,離開了現實土壤,離開了實踐功效,所謂學術必然失去生命活力,成為蒼白的心性空談,這一點對我們不無警醒意義。
與自然科學的冷靜與理性不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總體現出研究者個人的情感溫度,體現出研究者的人格力量。研究者的人格精神、思想品味與藝術情趣總是或是鮮明或是潛在地影響著學術的質量與價值。“茍利社稷,生死以之”的名言,是古代士大夫家國情懷和擔當精神的具體體現。儒家學術有強烈的拯救意識和擔當精神,孔子以天下為己任,他一身布衣,幾個弟子,轍行天下,推行自己的仁愛思想,并不是有什么人催促,而是一種自覺的歷史擔當,可以說擔當精神是一種深入中國文人靈魂深處的責任意識。屈原將士大夫的擔當精神化作中國文學的愛國主義的抒情主題,在“信而見疑,忠而被鎊”的坎坷境遇里,仍然自覺地將家國責任放在心中,抒發了“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的壯烈襟懷。對于古典文人來說,愛國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歷史責任的自覺擔當。中國古代文人分為“儒林”與“文苑”兩個系統,兩者在思想性格、專業精神上有許多差別,但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擔當上卻是統一的、一致的。習近平認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擔當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志向和傳統”(《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其實這種傳統也是一種學術傳統、思想傳統。古典文學研究是歷史研究,常常被誤解為“回頭看”的研究。但是回憶過去,并不是回到過去,回憶的目的終究是以獲得前行的力量為旨歸的,古典文學的研究同樣要從現實的土壤出發。
古典文學研究者如何建立以中國話語為本體的中國學術體系
“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沒有科學的高度,一個國家不能走在世界前列,沒有思想和理論的高度,同樣不能實現國家與民族的偉大復興。在中華民族的復興道路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與自然科學工作者一樣肩負歷史重任。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在強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上,特別提出了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與中國文學給予我們精神滋養,給予我們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的同時,也賦予我們不斷創新建構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的歷史職責。當代中國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接近實現中國夢的宏偉目標,因此建立以中國話語為本體的中國學術體系也比任何一個時期都顯得更加急切而重要。對于古典文學研究而言,有幾個問題應該特別引起注意:
第一,學術不是技術,需要先進的思想武裝與理論指導。
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常常把思想方法解釋為“識”。識就是見識,是一個學者對事物的獨特理解。古人論學往往以見識為第一要義,而“識見”其實就是具有一定高度的思想境界與理論視野。學術不是一般性的技術,需要先進的理論指導以及思想武裝。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研究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研究物與人關系的科學,是對人類實踐活動的高度概括,是人類智慧的集大成者。因此,“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著名學者楊公驥特別強調在古代文學研究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他是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研究的學者。結合自己幾十年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經歷,楊先生曾指出:“我不知道還有什么‘主義’或‘理論’能像馬克思主義這樣增強智慧,提高人們的認識能力,幫助人們全面地、深刻地、明晰地辨識中國近幾十年的歷史事件和歷史過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并不是將馬克思主義看作教義,而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的方法,歷史地辯證地分析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實踐,正確的理論指導是中國文學研究取得歷史突破的根本。
第二,無論東學還是西學,目的還是建立中國話語的學術體系。
學術研究不僅屬于理論,也屬于知識。當然所謂理論所謂思想,應當是以知識與學問為基礎的,離開知識基礎的所謂理論創新,理論會變成空理論,問題會變成偽問題。張舜徽先生批評李贄是“史識極高,議論有絕佳處,所憾他讀書不多,見人不廣,識有余,而學不足以相濟”。見識是第一要義,但這樣的見識,應當是學與識相埒,以“學”養“識”,否則“識”就演化成了空論。因此古典文學的研究必須有寬闊的知識視野,不僅注重吸收中國的學術成果,也應該有世界的學術眼光,充分吸納一切人類的學術成果,才能站在學術前沿。錢鍾書先生在學術上強調“打通”,所謂“東學西學,道術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就是打通一切知識壁壘,熔古今于一體,化中西為一爐,創造出以中國話語為本體而又有世界眼光的現代學術體系。
中西學術之爭,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問題。而無論是東學還是西學,有一點是必須要強調的,就是融入世界的目的不是化掉自身,而是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話語的現代學術思想體系。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繼承性、民族性;二是原創性、時代性;三是體系性、專業性。這三個重要特征就是在堅持繼承一切先進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堅持中華民族的文化立場,創造出具有開拓意義的不負于偉大時代、富有專業特征的體系化的當代中國學術。中國話語的學術立場體現了一種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持久而深沉的前進動力。在中國話語學術體系建設中,古代文學研究工作者承擔著特殊的歷史責任。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學傳統和創作,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獨特的詩性思維與藝術境界。激活歷史傳統,獲得前行的力量,通過讓世界了解“文學的中國”,來促進“中國的文學”的發展,是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使命。
第三,為己還是為人?學術研究應當堅守人民立場。
學術是為己之學,還是為人之學,是學術史的一個重要問題。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二程的解釋是“為己,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知于人也”,即為己之學,是充實自身,提高修養;而為人之學,是裝扮自己,取悅世人。但是,如果學術只是為著個人內心的自我修養而沒有大眾的立場,進而忽略了學術的社會擔當與大眾意識,那么學術勢必變成小圈子里的自娛自樂,最終失去生命的活力。如果我們不把“為人”理解為取悅他人的張揚夸飾,而是將學術研究的目標確定為服務大眾服務人民的話,那么為人之學恰恰是應當提倡的。
學術的人民立場一直是共產黨人的主張,馬克思主義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類解放作為自己的價值追求與歷史使命。它堅持人民是歷史活動的主體,承認人民的歷史主體性,也就承認了人民是目的本身,“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我們不能以學術研究的專門性而否定學術的人民性,正像一般群眾并不懂得航天技術,但不能否認航天技術最終一定是要服務人民的。學術也是如此,陽春白雪的學術研究,也應當轉化成滋養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成為服務大眾的精神營養,而不僅僅是個人的自得其樂。
結語
正是從這個角度,習近平強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脫離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就不會有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生命力。”(《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文學上說,人民群眾本身就是文學的創作主體,詩歌、戲曲、小說等文學形式最初來自于人民的創作,抽象的理論批評最終是要促進文學繁榮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古典文學研究也應當堅持人民的立場,盡管它不像文學創作那樣直接面對大眾,但其本質仍然是面向人民的,艱深的古典文學研究依然能夠潛在地曲折地傳達出人民的聲音。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話語的學術體系,是相當艱難的。在世界學術舞臺上,中國的聲音并不響亮。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過,文藝創作上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樣的現象在學術界也普遍存在。而隨著20世紀以陳寅恪、錢鍾書、郭沫若、侯外廬等為代表的學術大師的辭世,學術研究缺少“高峰”的現象也相當突出,這就要求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自覺擔當使命,以沉潛而切實的努力,創造出與偉大時代相稱的學術成果。
(作者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摘自《文學遺產》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