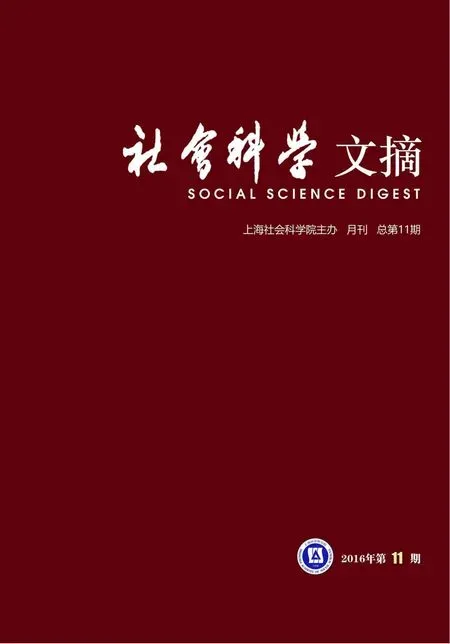歷史何以重提“敘事”?
——論1980年代西方新史學運動的轉向
文/張巖
歷史何以重提“敘事”?
——論1980年代西方新史學運動的轉向
文/張巖
1979年,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L. Stone)在《過去與現在》雜志上撰文,題為《敘事史復興:反思一種新的舊史學》。當時,正值西方新史學運動蓬勃發展,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社會科學化史學業已占據學界主流,這篇批判“新史學”的文章立即引發了爭論。深受實證傳統影響的學者貶之為“不可接觸者”,美國經濟史學家羅伯特·福格爾(R. Fogel)甚至在社會科學歷史學協會的主席演說中宣布將斯通“革出教門”。可是,在隨后的20年間,斯通的睿見漸漸應驗,西方的歷史編撰學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回顧敘事史復興的來龍去脈,深挖1980年代西方新史學轉向的學術語境,有助于我們理解西方史學今日之格局,抑或為中國史學研究范式提供些許啟發。
斯通的“新敘事史”倡導
斯通提出,當時的歷史學家可以劃分為4種:第一種為傳統的敘述型歷史學家,主要是政治史家和傳記作家;第二種是計量史學家,主要工作仍然是數據的搜集;第三種是“頑固”的社會史學家,他們忙于分析“結構”;第四種是心態史學家,他們熱衷于理想、價值、觀念和隱秘的個人行為方式。第二種和第三種歷史學家進行的是一種過時的研究,“經濟和人口決定論者在面對證據時已經無能為力,結構主義者和功能主義者已無更好的建樹。定量分析的方法被證明是一種效力很弱的方法,它只能解決有限的一些問題”。“如果我的診斷正確的話,新史學家發起的敘事史運動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一種趨向對過去的變革做出連貫的科學解釋的努力的結束。”而第四種研究模式則符合新的歷史編撰實踐潮流,斯通將這種潮流概括為“新敘事史”。
那么,這種“敘事”又有何具體含義呢?“敘事被認為是把材料按時間先后順序組織起來,將內容集中合成一個單一的連貫故事,盡管這故事中暗含著作者的情節設計。敘事史與結構史有兩方面的本質不同:其行文布局是描述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其核心關注點是人而非情境。故而,敘事史處理個別和特殊的事物,而不是集合的和可統計的事物。”斯通也認識到,僅用“敘事”一詞是很難概括出當時歷史學的復雜變化的,于是,他又展開性地論及了這種轉向的細節:歷史研究的核心主題是從人生存于其中的環境轉向環境中的人;研究的問題由從經濟和人口轉向文化和情感;對歷史學有影響的學科,已由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轉向人類學和心理學;研究客體上從團體轉到個人;在歷史變化的解釋模式上,從分層的和宏觀的原因論轉向聯系的和多元的原因論;作品組織方式上從分析轉到描述的;在歷史學功能的概括上也由其科學性轉到文學性。總之,斯通暫時用“敘事”一詞來概括新的歷史編撰學在內容、對象、方法和寫作風格上的特點的總合。
斯通的“新敘事史”倡導引發了英國史學界的波動。作為英國社會文化史干將之一的霍布斯鮑姆(E. Hobsbawm)著文回應稱:“不必要以完全否定過去的立場來分析當下的史學潮流。”他認為,不必把敘事史與社會科學化的結構史完全對立起來,更何況,新史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其堅持對社會、經濟等宏觀因素進行分析,并同傳統的敘事史進行直接對抗而取得的。霍布斯鮑姆與斯通對當時西方史學發展前景的認識是不同的,但他們所關注的問題是相同的,即當時在西方史壇出現的這股所謂“新敘事史”潮流的內涵與意義。與此連帶的問題則是,新敘事史與社會科學化的新史學以及更為傳統的敘事史存在哪些關系呢?
新史學困局及其“敘事”訴求
從敘事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新史學運動主要是為解決傳統敘事史的弊端而發起的,新敘事史則是針對新史學的困惑產生的。二戰以來,以法國年鑒學派、英國新社會文化史和美國新社會科學史學為中堅力量的新史學運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對經濟、社會、人口等“結構”和“情勢”的研究,揭示了被傳統史學所忽視的長期對歷史進程起重大作用的因素,而定量分析研究法也將歷史論斷置于更加邏輯化和有說服力的清晰證據之上。但是,過分強調“結構”、“情勢”和“定量分析”等因素時,新史學的不少弊端也就隨之浮出水面。
布羅代爾(F. Braudel)是史學社會科學化的堅定倡導者,他的《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開創了“長時段”理論與實踐的先河。他將歷史學看作一個三層的大廈:在位置和重要性上居第一位的是經濟和生態的事實,然后是社會結構,最后是受制于經濟、生態和社會結構的頂層的心智、宗教、文化和政治的發展。勒華拉杜里(Le Roy Ladurie)、肖努等史學家則將布羅代爾在《地中海》第一部分中所濃墨渲染的“靜止的歷史”的重要性發揮到極致,從而把“長時段”的理論推向盡頭。在他們看來,經濟、社會、心態等“結構”也不夠“長時段”,推動歷史運動的最深層次動力來自于自然地理環境和人類本身的生物機能。1973年,勒華拉杜里代表作《1000年來的氣候史》試圖說明氣候的變化決定了人類的生存境遇,進而改變了歷史的面貌。根據相同的邏輯,肖努認為“古代社會衰落的過程似乎就是一個生物的過程。”總之,“長時段”主宰了歷史,個體的人似乎是裹挾在歷史巨流中的浪花。
英國的新社會文化史看似多一些人文主義關懷,但是,與其說這個學派關注的是具體的歷史的人,倒不如說他們關注人賴以存在的文化。有學者說湯普森的“文化主義特征”是將社會看成一種結構,人所在的階級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變遷相互關聯。換句話說,英國新社會文化史學家眼中的階級、文化和社會也是一種長時段存在的“結構”。
這樣,新史學實際上沒有完全落實以人為核心的新史學綱領。“總體史”、“長時段”的概念應圍繞復數的“人”展開,正如布洛赫說:“歷史學家所要掌握的正是人類,做不到這一點,充其量只是博學的把戲而已。”一方面,研究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和人類本身的生物機能自然重要,但對這些對象的研究絕不能以犧牲人本身為代價,畢竟,人還是一種有主體意識的特殊動物,歷史的發展處處打上了人類的積極能動性的有目的的活動的烙印。如果低估甚至是抹殺了人的歷史地位,就滑向了一種極端化的“自然決定論”。按其邏輯,人的任何作為都將失去意義,因為歷史早已注定,人只是消極、被動地接受控制而已。另一方面,“長時段”之意義被推演到極端之日,是“短時段”意義再度凸顯之時,它提醒新史學的實踐者重新思考“長時段”與“短時段”的辨證關系,重新定位“事件”在歷史體系中的地位。
計量分析方法是新社會科學史的典范實踐手段。“就方法論而言,當代史學的突出特征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所謂的‘計量革命’。”過去傳統史學家經常使用的描述性詞匯被計量史學家換成了確鑿的數字,使讀者看到了更為“精確”的歷史。在美國,新社會科學史學派的學者們將大量的數據輸進電腦,按照他們所編制的程序來研究美國社會、經濟甚至是政治領域的變革。在法國,年鑒史家創造性地將計量方法與“總體史”構想結合起來而發明“系列史”。按照弗雷(Franqois Furet)的說法,不只是數字可以量化,凡是構成系列的史料都可以被系統收集、分析、統計和綜合。比如有人利用一定時期內遺囑內容的系列研究來分析人們對待死亡和宗教的態度。這樣,“系列史”使史料和史學研究領域都大大拓展,甚至有并吞整個史學研究之勢。
然而,計量分析絕非歷史研究的唯一方法,量化也不見得比定性分析精確很多。況且,有些歷史研究對象本身就不太適合量化分析或系統分析,而某些領域內數據的缺失或數據采集的困難都使計量分析難以開展,比如很難用“系列史”方法來研究古希臘的經濟。另外,計量方法被引入史學的初衷,是為了使史學研究的過程更少地受到研究者主觀意識的不利干擾,但實際結果遠非如此。采集數據、選擇程序、制造系列本身就是主觀行為,再加上復雜煩瑣的計量過程中會出現人為疏忽造成的失誤,都會極大地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布洛赫就曾指出史學研究“迷信數字”的危險性。身處年鑒學派第三代計量史學研究熱潮中的勒高夫說:“新史學不應強制計算機去計算因材料狀況和事物本質所無法計算的東西,也不能忽視不能計算的東西,更不應單靠計算機去‘編制歷史’或重溫實證史學的舊夢,讓文獻資料去‘客觀地’制造歷史,而自己則袖手旁觀。”而斯通則更為直接地批評:“在肯定成績以外,不可否認的是,計量史學并沒有實現10年前所提出的宏偉愿望。很多重大的歷史問題依如先前一樣沒有解決。”
史學研究計量化的另一個消極后果就是影響了史學研究成果的交流與推廣。這類史學作品充滿了常人難以理解的圖表、公式、曲線和抽象、枯燥的分析,只能為少數圈內學者所用,史學的審美和社會教化功能便無從發揮。這也是計量化史學作品受到批評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因為新史學在發展深入的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惑,一部分歷史學家才開始對史學社會科學化取向之種種弊端提出了建設性的修改意見。恰逢此時,語言學和人類學迅速崛起,逐漸取代傳統的經濟學和社會學成為對史學影響最大的學科。一些史學家正是借鑒了其中的研究成果用于歷史學的改造:研究對象上抓“小”放“大”,研究方法上嘗試使用具體描述而非傳統的抽象分析,行文方式上也回歸了文學敘事化的傳統而遠離了圖表和公式。
新敘事史的類型及其評價
與當代語言哲學家的研究不同,新敘事史的成長不僅表現在理論建構上,還體現為歷史編撰實踐的具體成果。當代史學家彼得·伯克將具有“新敘事史”特征或探索意味的歷史編撰作品分為5種類型:
第一種是“微觀化”的新敘事史。微觀史學以傳統史學家所忽視的歷史上的小人物、小事件為研究對象來反映宏觀的歷史變革趨勢。在年鑒學派發展的中后期,社會科學化的史學與人類學結盟從而出現了歷史人類學。在這一進程中,曾倡導“靜止的歷史”與“無人之歷史”的勒華拉杜里也創造性地寫出轉型作品《蒙塔尤》。他將中世紀時期法國南部小村蒙塔尤視若“一滴水”,通過顯微鏡般細致的觀察和分析記述村民的居所、勞作、家庭及婚戀、宗教觀,使讀者對于中世紀的經濟、社會、宗教等宏觀抽象的概念有了切實的感受和理解。
第二種是“講故事”的新敘事史。美國耶魯大學史景遷(J. Spencer)教授所刻畫的歷史人物上至帝王,下至士人農婦,都是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懷著強烈的探詢精神重新發掘這些歷史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經歷,通過對大量史料的嚴格考察來探究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場景和細節。有評論家稱其寫作風格兼英國人的嚴謹清晰與美國人的生動幽默于一體。
第三種是“倒敘法”的新敘事史。代表作是諾曼·戴維斯(N. Davis)的波蘭史專著。該著所關注的是“存在于波蘭當下的過去”,作者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波蘭”開篇并由此逐級上溯波蘭的過去,頗有推理小說的意味。這種敘事模式的優點在于“允許讀者或者說是強迫讀者感覺到過去對個人和團體的影響”;缺點則是與相鄰章節之間一環緊扣一環的連貫性作品相比,似乎很難看出其開頭和結尾之間有何種聯系。
第四種是“多調式”的新敘事史。柯文(P. A. Cohen)在《歷史三調》中區分了3個“義和團”:歷史學家敘述“事件”的義和團、歷史當事者“經歷”的義和團、其他人意念中“神話”的義和團。這三者在認識義和團這一客觀的歷史事件時各有短長。柯文對敘事的說明實質上已深入更為深刻的歷史認識論問題,即不同的人會基于各自的時代和生活背景、出于不同的動機和需要來敘事和解釋真實發生的事件。因此,明智的歷史學家應當向讀者坦率地交待歷史學家究竟運用了多少敘事策略來呈現歷史事件,以使讀者對作者的敘事策略有明確預知,由此在閱讀與批判性思考中獲得更多的自由。
第五種是“事件—結構”的新敘事史。此種敘事范式著意解決的是歷史描述中事件與結構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一方面,“事件具有獨特的文化象征意義,事件由文化決定,一種文化的概念和分類塑造著其成員感知和闡釋發生于他們那個時代的事件的方式”。但另一方面,事件也可以改變結構,結構主義史學家也要意識到事件的強大作用。
可以看出,新敘事史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新史學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歷史研究的人文化、主觀化和多元化成分明顯增多。但是,這種對史學社會科學化取向的糾偏,不應視為其在形式上向傳統敘事史的回歸,二者存在著本質差異。首先,從研究對象上看,新敘事史對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感興趣,而這在傳統敘事史學家看來是無足輕重的,后者所記述的是所謂精英人物的歷史。其次,從研究手段來看,新敘事史家并不完全排斥新史學家擅長的分析手法,更準確地說,是在尋求一種將描述性語言與分析性解釋模式相結合的新的敘事模式,而非傳統史學家對歷史作品文學性的單純關注。最后,從研究目的看,新敘事史學家不是為了敘事而敘事,他們對個體的人物和單個事件的描述和分析,是為了揭示其中所隱含的宏大敘事的歷史變動法則。而傳統的敘事史學家大多只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無法深入歷史現象的本質。
作為改進歷史研究的一種有益嘗試,新敘事史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有不少學者對他們的研究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最為合理的擔心就是,新敘事史學家對個案研究的鐘情與對歷史的宏觀圖景的認識究竟有何關聯?過去留下的遺跡本來就十分殘缺,那些幸好保存得完整一些的材料所反映出的歷史事物,難道就具有能夠反映出歷史常態的典型代表性嗎?再有,真實的歷史經歷是歷史敘事者筆下所呈現的那樣頭緒清楚、跌宕起伏嗎?如果讀者僅僅是從新敘事史家那里享受到聽故事的快樂,那么歷史學就成為可有可無的行當了,小說家和編劇就可以代勞。因而,新敘事史的實踐者需要考慮如何將事件與結構協調整合于歷史敘事中,將敘事形式的生動性建立在更堅實的實證性材料的基礎之上。再文學的敘事,都應當是服務于歷史學的敘事。如果新敘事主義者只是關注歷史敘事的主觀化與人文性因素,那么他們很可能會像社會科學取向的新史學家一樣有失偏頗,消解歷史研究的科學性。敘事史“復興”加快了西方新史學運動向新文化史的邁進步伐,重拾歷史學的人文傳統,但同時埋下了歷史客觀性消解和宏大敘事沉默的隱憂。
(作者系吉林省教育學院副教授;摘自《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