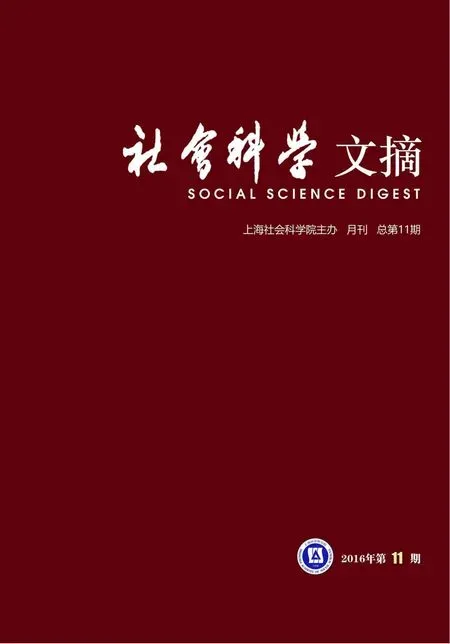城市規模和產業結構如何聯合影響中國的城市勞動生產率
文/陳杰 周倩
城市規模和產業結構如何聯合影響中國的城市勞動生產率
文/陳杰 周倩
引言
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速在近年來有所放慢,引起各界高度關注,并引發不少憂慮。中國要維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前提是要深刻理解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機制,從而為持續提升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找到方向。“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6%,城市經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達到90%以上。為此,提升城市勞動生產率成為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所在,這也是新常態下城鎮化模式轉型的根本要求。
在經濟學文獻中,關于城市勞動生產率的討論往往與“城市最優規模”假說相緊密聯系(Henderson,1974;Black和Henderson,1999;Gabaix和Ioannides,2004),驗證城市是否存在“規模紅利”是經濟增長文獻中的重要命題(Abdel-Rahman和Fujita,1990;Duranton和Puga,2005)。同時,大量研究表明,技術進步和城市勞動生產率也深受城市產業結構的影響(Pavitt,1984;Drucker和Feser,2012)。中國的實證研究也證實,恰當的產業結構調整對勞動生產率具有“結構紅利”效應(毛豐付和潘加順,2012),而工業與服務業如果比重失衡將對城市生產率產生抑制作用(顧乃華等,2006;江靜等,2007;袁志剛和高虹,2015)。結合這些理論背景,可見城市規模和產業結構都是影響城市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因素,但也有理由相信城市集聚的“規模紅利”會隨著城市產業結構的不同而有較大差異,同樣有理由相信產業結構對城市勞動生產率“結構紅利”在不同規模的城市也可能迥然不同。新近文獻中也有提出“城市規模-產業結構”對城市勞動生產率具有協同效應的假說(柯善咨和趙曜,2014),但對城市規模、產業結構和城市勞動生產率三者之間的關聯特征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關聯特點,現有文獻中還缺乏系統的研究。
突破中國城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瓶頸,需要同時考慮城市規模的“規模紅利”和產業結構的“結構紅利”。要實現最充分地利用城市規模的外部溢出效應,不僅要準確度量城市的最優規模,還需要考察在特定的產業結構下,城市規模對勞動生產率有什么樣的不同效益。同樣,辨別清楚產業結構的結構紅利,不僅是簡單找到一個普適的、但可能實際意義不大的最優產業結構,而是要鑒別在不同城市規模下最適宜的產業結構。為此,本文關注,城市規模和產業結構對勞動生產率的聯合作用,以及這種協同效應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在不同類型城市的異質性特點。
本文首先從理論層面討論了城市規模和產業結構對城市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機制和影響渠道,包括關注了中國國情的特殊作用,其次根據我國28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2000-2013年的面板數據,綜合運用GMM、門檻面板模型和空間面板模型等計量方法,實證研究了城市規模和產業結構對中國城市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主要貢獻在于:本文系統地考察了城市規模的“規模紅利”和產業結構的“結構紅利”之間互動關系的非線性特征,包括城市規模對城市勞動生產率的邊際溢出效應是如何受到產業結構的影響,以及產業結構對城市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在不同規模的城市中又有怎樣的不同表現。本文還應用了空間面板模型來控制城市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空間溢出效應,也通過GMM模型等方法盡量去控制了關鍵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在多種模型設定下,主要結果都十分接近,保障了結果的穩健性。
從學術價值上,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與早前Au和Henderson(2006a,b)等基于中國20世紀90年代城市數據的經典文獻的結果作為對照,從而看出2000年以來市場化和快速城鎮化情境是如何影響一個轉型經濟體的城市規模及城市體系的演變。當然,關于城市規模及城市體系合理性的討論并不局限于中國或轉型經濟。但中國巨大的城市規模、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和高速的經濟增長,給予城市規模問題研究一個特殊的實驗性場景來深入挖掘,也提升了這個問題的實踐價值。從政策應用價值來看,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用來評價當前中國整體上城市規模是否合理、城市體系是否健康,同時發現不同類型的城市產業結構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整。具體而言,本文依據計量模型分別對當前中國城市規模的最優容納規模和產業結構的最優結構做了最新測度,以此判斷目前具體哪些城市需要進一步調整城市規模和優化產業結構,可為中國城鎮化發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學的依據。
本文主要發現
本文基于中國地級市2000-2013年面板數據,使用門檻面板回歸、差分GMM、系統GMM和空間面板回歸等方法,分析城市規模和產業結構對城市勞動生產率的聯合作用。主要發現如下:
(1)中國城市規模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可以認為,在城市規模達到最優規模前,中國城市勞動生產率隨城市規模的擴張而提高,在城市規模達到最優容納量峰值后,城市勞動生產率隨城市規模的擴張而降低,也即城市擴張對城市勞動生產率的邊際收益隨著城市規模的上升而下降。但由于樣本中的城市大多數未達到其自身的最優城市規模水平,中國大部分城市都仍有繼續大量吸納勞動力的潛在能力。因此,打破對人口集聚的制度約束,進一步加快勞動力流動,進一步釋放“規模紅利”,仍然是推動城市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必須措施。
(2)產業結構與城市勞動生產率之間也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關系。總體來看,對于中國絕大多數城市而言,第二產業比重越大,城市勞動生產率越高,也即目前中國產業中第二產業相對第三產業來說,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更積極的作用。中國絕大多數城市的第二產業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仍未得到充分發掘,尚未出現下降的拐點,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意味著,對中國絕大多數城市而言,工業化進程尚未完全完成,仍要以工業和制造業強市,還尚不能過早提倡“去工業化”。
(3)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城市規模對勞動生產率的邊際促進作用是趨于下降;另一角度的解讀是,隨著城市規模上升,如果產業結構趨向下降(第三產業相對壯大發展),那會增強城市規模對勞動生產率的邊際外部效益。
(4)此外,我們還發現,樣本城市在既定產業結構水平下,較之2013年數據,總體上城市還可容納約25%的城市規模;而產業結構可調整比例則約為34%。中國目前只有極個別樣本城市略超出最優規模,僅約占樣本總數的4%不到,絕大多數城市仍然有擴大規模的必要性,規模紅利的潛在收益遠未枯竭。同時,從產業結構視角來看,大多數城市,尤其中等規模城市,發展制造業的空間仍然巨大,制造業對提升城市勞動生產率的作用還遠沒有發揮殆盡。但也有少數城市,尤其人口規模巨大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當前迫切需要給服務業更多發展空間來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通過“結構紅利”的更多釋放來提升城市生產率。
結論及政策建議
城市經濟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理解清楚城市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機制,對中國能否實現可持續的中高速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我們認為城市規模與產業結構之間需要十分合理的匹配。基于制造業的乘數效應,城市的“規模紅利”在城市經歷工業化高潮時最為顯著,在工業化啟動階段存在一個門檻效應,在工業化尾聲則會出現下降。另一方面,城市在從小城市到中等城市的發展過程中,主要依賴工業來驅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時創造就業機會和吸引人口,大多數城市不能跨越城市經濟的自身發展規模,跨過工業化就發展第三產業。從國際上看,在國家層面工業化發展不足就進入服務業驅動,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往往也被認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主要成因(王小魯,2000、2010)。但當城市規模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城市自身的發展規律需要產業結構增加第三產業比重,形成合理的二產、三產分工格局,這樣城市規模才能更好發揮對城市勞動生產率的溢出作用。否則,如果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產業結構過度工業化,則會一方面因為服務業配套不足的制約,另一方面因為妨礙城市“規模紅利”的釋放,對城市勞動生產率產生負面作用。
本文有針對性地提出,為充分發揮中國城市勞動生產率潛力,應該分層級、因地制宜和因勢利導地采取促進人口流動的措施,繼續充分發揮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力和輻射力的同時,做大做強中等城市,充分釋放城市規模紅利。這首先需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切實以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作為新型城鎮化的指引方向,促進流動人口的市民化。力推城市群發展,推動城市加強與周邊各類城市廣泛和多樣化的合作協同,以最大化彼此的利益。另一方面,引導城市產業結構順應市場需求及時加快調整。其關鍵點是,開放民營資本進入城市各類服務行業,充分競爭,有利于吸納更多外來人口,為服務業比重上升創造機會,真正擴大內需,同時增加城市三產對二產的支持能力。城市體系的合理優化、勞動力的更自由流動和產業結構的市場化調整,不僅會帶來更強的城市競爭力、更高的勞動產出效率和更持久的經濟潛在增長率,也有利于實現“十八大”所說的包容性增長的踐行。
(陳杰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投資系教授,周倩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投資系博士生;摘自《財經研究》2016年第9期;原題為《中國城市規模和產業結構對城市勞動生產率的協同效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