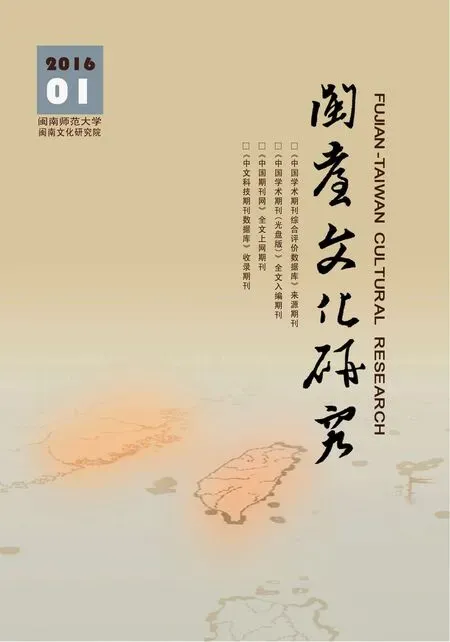19世紀杜嘉德《廈英大辭典》序
Rev. Carstairs Douglas著吳文文譯(閩南師范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363000)
?
19世紀杜嘉德《廈英大辭典》序
Rev. Carstairs Douglas著吳文文譯
(閩南師范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廈英大辭典》是19世紀英國傳教士杜嘉德編寫的一部辭典,將當時的閩南方言詞語逐條翻譯成英文。杜嘉德在自序中對《廈英大辭典》出版的初衷、材料的來源、編寫的過程、編寫目的以及編寫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字典的不足等問題進行了說明。他還從一個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的角度,對漢字與漢語的關系、漢語書面語與口語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饒有趣味的探討。
關鍵詞:19世紀;杜嘉德;《廈英大辭典》;閩南方言
《廈英大辭典》[1]這部字典在編寫的過程中努力做到比之前的字典更便于參考。“廈門白話”之前也被表述為“廈門方言”或“廈門口語”;并且它有一部分和所謂的“福建方言”相一致,如同里弗·麥都思博士在他的四開本《福建方言字典》中所闡明的那樣。但是諸如“方言”或“白話”這些詞語本身往往會導致錯誤的概念。這些詞語所表示的語言不僅僅是指白話式的方言或土話,它既為社會上最高階層的人士所使用,也為平常百姓所使用;它不但為有學問的人使用,也為文盲所使用;有學問的人確實會夾雜著為數不多的一些禮貌式或學究式的語句,但是這些僅僅是可有可無的綴飾(并且甚至這些語句也是以廈門音來表達)。就口語中基本的和常用的部分而言,最有教養(yǎng)、最有學問的人士和那些苦力、勞工、船夫們所說的語言是一樣的。
“方言”這個詞語也沒有傳達廈門話[2]獨有的特點;它不是一些其他語言的方言變體,它是一種獨特的語言,是中國為數眾多且彼此相異的方言之一,根據這些方言可以把中國區(qū)分為不同的區(qū)域。
所謂的中國“文言”的確是在全國范圍內相一致;但與其說它是一種語言,不如說是一種符號;因為這種通行的文言在中國的不同地區(qū)大聲朗讀時是發(fā)不同的音的,所以,雖然寫下來它是同樣的,一旦被讀出來,它就分成了幾種不同的語言。并且,這種文言雖然可以拿著書大聲朗讀,但卻不會在任何地方以任何一種語音形式用于談話。那些有學問的讀書人也從不在日常口語交流中應用這種書面語言,即使是在他們之間也是如此。事實上,它是一種“死去的語言”,它和中國為數眾多的方言口語之間的關系,正如同拉丁語和歐洲西南部語言之間的關系。為數眾多的中國方言口語已經或多或少地被在這個國家中生活的歐洲人或美國人所研究,比如官話、客家話、廣州白話或廈門白話,等等。這些語言源自同一語系,彼此之間的關系類似于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敘利亞語、埃塞俄比亞語以及其他閃米特語系成員之間的關系。
當我們在應用“方言(dialect)”這個名詞應用于這些語言時,有另一個嚴重的缺陷,也就是每種語言內還存在著“真正的方言”[3]比如,官話作為所有方言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內部至少包含三種顯著不同的“次方言”:通行于北京的北部官話;使用于南京和蘇州的南部官話以及通行于四川、湖北等地的西部官話。類似地,為了給其以更好地命名,我們可能稱之為廈門白話(或廈門口語)的這一方言,也包含數種真正的方言(譯者注:也即次方言)。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漳州話、泉州話、同安話以及廈門本地話。在這部字典中,廈門本地腔被作為此方言的標準語音,同時記錄下漳州話和泉州話中與其不同的重要語音差異,并且也注明了為數不少的同安、漳浦以及其他一些地區(qū)的語音差異。
使用廈門話[4](包括上述所說的這些次方言)的人口據說大概有800萬或1000萬。這是有關廈門口語的第一部字典。在此之前,已經存在數量眾多的有關中國書面語的字典。其中一部是麥都思博士所編寫,他的字典為一個個漢字注上了漳州音(更為準確地說,應該是漳浦音)。麥都思博士的字典也收錄了一些俗語,但是相當少,并且完全采自漳州話或漳浦話,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收錄的俗語形式還遠遠不能稱之為精確。唯一一部稍具口語字典形式的出版物是非常簡短的Doty和Macgowan手稿中的詞匯表。
這部字典的基礎是最近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Rev.J.Lloyd所準備的手稿本詞匯表。當我1855年到達廈門時,我抄寫了這份詞匯表便于自己使用。在其基礎上,增加了Doty手稿中另外的詞語,并且,一直以來都進行著增加新單詞和新句子并且重新安排其順序的工作。在抄寫Lloyd詞匯表之后的幾年,我校勘了由倫敦傳教士公會Rev.Alexander Stronach撰寫的手抄本字典。其后,我還翻閱了本地人編的漳州話字典和泉州話字典中的全部詞語,閱讀了一份本地人編撰、嘗試用廈門話來解釋官話詞語和句子的詞匯表。
在這些本土作品中,唯一一部好的作品是漳州音(其實是漳浦音)字典,這部字典被稱為“十五音(Sip-ngé-im)”,這部字典其實也是麥都思字典的基礎。因此,有這三本原始的資料可供參考,我?guī)缀鯖]怎么采用麥都思字典中的材料,因為其中那些未引自《十五音》的白話語句是非常令人懷疑的,同時其中有價值的書面語句子不符合我撰寫這部字典的目標。至于Macgowan的手稿本詞匯表,雖然對于一個初學者而言非常有用,但其對我而言出現的太遲了。我在瀏覽這本詞匯表時,我發(fā)現其中大部分詞語我已經收進我的手稿中了。
沒有人比我更清楚這部字典的不足之處了。最初它只是為我個人使用而準備的。隨著它變得越來越厚,最初我只是希望它或許會以手抄本的形式為廈門語的初學者使用,或為后來的傳教士們所復印、精簡或擴充。在反復地被懇請,乃至最后應廈門三所基督教公會全部成員的正式請求下,我同意將其付諸出版。我為這部字典的全部錯誤和不足表示歉意,它的出現,是為了供急需之用,意在填補一項真正的空白、完成一項真正需要的工作。無論它被取代、忘記或僅僅作為今后某部更為完美、精確作品的基礎而被記住的話,我都會感到十分的欣慰。
當廈門傳教公會要求我為已經編輯好的手稿付諸出版做準備時,倫敦傳教公會的Rev. John Stronach和美國Reformed Mission的Rev.John Van Nest Talmage,d.d.被同時指派協助我做修訂工作。Stronach先生從頭到尾核對了全部內容,但是Dr.Talmage在修訂了十幾頁后由于有其他要務就停止了這項工作。當他們修訂之后,我在謄寫為出版而準備的清樣時,我發(fā)現將全部的內容重新統籌編排和改寫是非常必要的(包括大量的增補內容和他們難以發(fā)現的更改)。因此,這本書的可圈可點之處很大一部分應歸功于我的助手們,同時,我應該為它的全部錯誤承擔責任。
本書最大的不足在于相應的漢字的缺乏。這主要由兩方面原因構成。一是有相當大數量的一批詞語,我們根本沒能找到相對應的漢字,這個數量大概是全部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對我而言十分必要的回國休假期間,要找到這些漢字簡直是不可能的,它們中很多是生僻字,還有一些漢字難以辨別是對應語言中的白讀形式還是對應其文讀形式。二是即使這個漢字被找到,在英國要將其印刷出來也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又必須在回國度假期間將其印刷出來,因為我們在廈門沒有印刷出這么一部書的設備。當我回到中國,我也沒有足夠多的工作以外的時間去其他港口城市完成印刷工作。考慮到這些漢字可能被陸續(xù)找到,這部字典出版期間的兩到三年內我滿懷期盼,一有可能就將這些漢字補充進去。在我因為這部字典中沒有配上相應的漢字而感到深深的遺憾之時,我也在另一種意義上對此感到慶幸,因為這倒可以證明廈門白話是一種獨立性很強的語言,無須書面漢字的輔助仍保持其獨立性。并且我希望許多人由此也獲得學習這種語言的勇氣和信心,因為他們往往在這些復雜而奇妙的漢字面前望而卻步。當然,所有在中國的傳教士和任何一個值得稱之為學者的人,必須學習漢字,因為僅僅靠白話和俗語在長遠看來,是無法了解那些可稱之為文學的漢語作品的。
這部字典讓我深感遺憾的另一個不足是,是非常缺乏有關植物、動物、藥品等等的名稱。時間不夠在這里也是一個借口,我希望讀者能夠給以充分的理解。一些詞條名稱已經從下列這些作品中選出,比如《The Fuh-chau Recorder》,《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The Phoenix》,《Dr.Porter Smith’s Book on Medicines》,以及為數眾多的文言文字書,等等。然而我沒能找到合適的方式對這些名稱加以驗證。
對一些人而言,這部字典沒有英譯漢部分也是一大缺憾。但是這確實是另一項截然不同的工作。漢語的思維以及表達的全部方式和特點,和英語中最為接近的等同詞是如此不同,使得看上去似乎很容易的對譯一部字典的工作,在實際操作上成為一項漫長艱巨的任務。
雖然有上述這些不足,但是我相信,這部書對學習廈門話的人將大有幫助。我的初衷是幫助那些在這個地區(qū)投身于傳教事業(yè)的人;但是,為此目標我想方設法對這一語言作了一個全面的考察,以便我能夠對其開展學習和研究。因此這本書對商人、旅行者、水手、翻譯人員和學生也同樣是適用的。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最為急切地希望能夠學習他們的語言,以便能夠直接和他們交流,而不是用那些難懂的所謂“廣州英語”或“鴿子英語”來交談,也不必時刻借助翻譯開展交往。這將使得因誤解而產生的爭吵和彼此之間的反感大大減少,也讓這些國家之間的交流充滿友好氛圍且能夠互惠互利。
由于后期時間的不足,引言和附錄中的解釋已經被大大地壓縮;我也因此沒能給幾個條目做出一個科學的處理,但我對這些實踐性的字典使用指導將有利于這本字典的使用和這一語言的掌握感到滿意。
最后,我要對英格蘭基督教長老會的外國傳教委員會召集人HUGH M.MATHESON先生和Bolesworthd的ROBERT BARBOUR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同時也感謝C.E.LEWIS先生的慷慨,使得我能夠出版這部書。
1873年,4月4日
再版注:由作者為第二版所做出的改正和補充部分已經被包含進這一次出版中。這些更正和補充共兩百多條。更正的校稿已經由廈門的威廉姆·麥克格雷格先生(Rev.WILLIAM MACGREGOR,M.A.)過目。
倫敦,1899年5月
附錄:詞語條目分類
A.廈門方言
An.or Ank.安溪方言
Bud.佛教的(詞匯)
C.漳州方言
cf對比,比較
Cn.泉州方言
col白話或口語,相對于文言或書面語而言
dis從——區(qū)分出
E.永春方言
esp特別的
F.臺灣所特有的句子
f.外來詞。用來指稱外來事物或概念的名稱或詞語,并且這些詞語只是或主要由那些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所使用。
fig.修飾的
gen.普通的,通常的
H.惠安方言
K.or Kk.Kwan-kow灌口方言
L.南安方言
lit.文言
Mand.官話,或中國北方、中部或西部的白話
opp. opposed to.反義的
P.漳浦方言
R.文言形式
注釋:
[1]杜嘉德這部辭典書名為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內容是將廈門話為主的閩南語翻譯為英語,現通常被翻譯作《廈英大辭典》。欲詳細了解該辭典可看原著或參考馬重奇先生《英·杜嘉德編撰〈廈英大辭典〉(1873)音韻研究》,《勵耘學刊》2014年第2期。
[2]杜嘉德所指的“廈門話”,在概念上實際相當于我們現在所說的“閩南語”。下文同。
[3]杜嘉德所說的“真正的方言”,相當于“次方言”這一概念。
[4]同注[2]。
〔責任編輯李弢〕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Rev. Carstairs Douglas,Translated by Wu Wenwen
Abstract:Carstairs Douglas is a 19th-century British missionary to China, he preached in Minnan region more than 20 years, so many people called“minnan ACT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hich translated Minnan dialect words into English, is written by him. in the introduction ,Carstairs Douglas intradued the publishing of dictionary, the source of the material, the process of writing, writing purpose an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course of the writing, the shortage of the diction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19th century , he also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ten and spoke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esting issues.
Key words:in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Minnan dialect
基金項目:2011年福建省教育廳科研項目:“閩南方言與贛方言詞匯比較研究”(JB11135S)。
譯者簡介:吳文文(1976~),男,江西省余江縣人,文學博士,閩南師范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