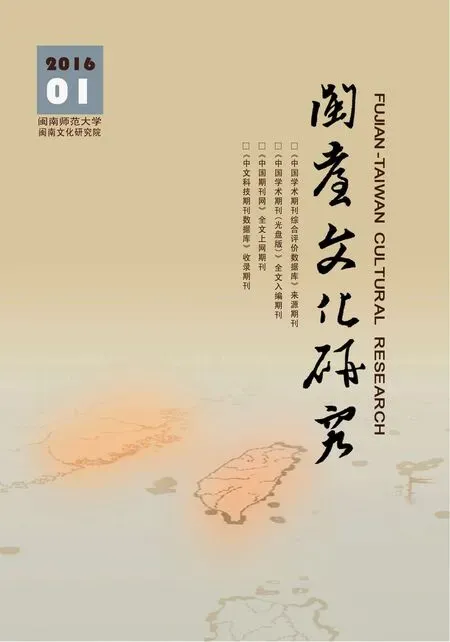閩南王爺信仰流傳馬來西亞的歷史意義
王琛發(馬來西亞道理書院,馬來西亞檳城11600)
?
閩南王爺信仰流傳馬來西亞的歷史意義
王琛發
(馬來西亞道理書院,馬來西亞檳城11600)
摘要:閩南各村鎮王爺信仰一旦落地在馬來西亞,轉化成為南洋當地的王爺信仰,即與閩南、臺灣或其他地區王爺信仰同源不同流,會借助各種熱帶元素維續其精神傳統與生命力,既對原鄉信仰文化飲水思源,又繼承原鄉廟宇的社會功能,依著當地社會文化脈絡演變。各地王爺信仰除了在異地凝聚原鄉信眾,還可能根據當地形勢合祀不同原鄉諸姓王爺,力圖維續閩南認同,還發展出凝聚跨原鄉且跨族群信眾的本土信仰態勢。同時,在社會開拓過程,立廟傳承即表達了集體文化與價值觀落實為當地主權象征,突出表現在廟宇有組織支持本境公共保健醫療。
關鍵詞:諸府王爺;水陸主權;血緣先輩;集體祖神;公共保健
一、重溫各種王爺來歷說法
閩南王爺信仰的共同點,是其廟宇多根據王爺姓氏,稱呼神明為某府王爺或某府千歲。由于王爺信仰過去也在臺灣興盛,20世紀有段時間又是只有臺灣出版物能夠輸入南洋華人世界,因此,目前海外許多相關王爺信仰的說法,很多淵源于上世紀以來臺灣傳媒的傳播影響;研究這些說法,實有助理解漳泉原鄉信仰如何落地臺灣,以及理解閩南神道文化演變為當地本土信仰的過程。但神圣傳說既然本源于閩南,又不僅流傳到臺灣地區,因此各地王爺傳說的演變也就不見得全都受到臺灣的影響,尤應注意王爺信仰流傳各地都會演變出在當地的新神話,如此方才符合民眾公認神跡必定超越地區界限的心態。所以,雖然早在上世紀初,曾有人根據傳說統計總共有360位王爺,臺灣流傳的王爺姓氏達到132種,但這畢竟不等于中國海峽兩岸以至南洋各地的所有各姓王爺。不過,至少單從臺灣的統計可發現王爺姓氏包括:李、池、吳、朱、范、溫、康、關、馬、趙、張、鐘、劉、史、謝、連、蘇、施、許、袁、蕭、崔、盧、潘、郭、邢、姚、金、岳、雷、伍、羅、黃、洪、藍、白、紀、蔡、沈、余、俞、于、虞、陳、包、薛、林、楊、徐、田、譚、封、何、葉、方、尹、高、甘、鄭、呂、章、耿、王、武、華、夏、楚、秦、魯、齊、越、周、殷、韓、魏、陸、唐、陶、宋、胡、狄、駱、韋、歐、侯、柯、萬、江、榮、邱、孟、董、戴、吉、聶、龍、云、游、尤、莫、干、程、倪、丁、元、潘、廉、石、玉、清、將、帥、兵、士、寇、冠、抄、平、順、瓊等姓。[1]
而現今所謂“東南亞”各國王爺信仰,其實也是各有各的造化。各位王爺的香火跨境散播在不同國家的大城小鎮,其中有的王爺被同姓的后裔主祀或附祀在當地宗祠,有的王爺香火則發展成為地方民眾的區域性廟祀;還有些王爺香火遭遇南洋各國長期政治變遷,迄今只能被信眾虔誠供奉在個人家中。因此,自明清兩代王爺下南洋,各國有多少間正式的王爺廟祀?又有多少姓的王爺香火流傳到當地?到現在還是沒有可能明確統計。
至于南洋華人有關王爺香火來歷的信仰記憶,也輾轉流傳著好幾種說法。
民間有一種說法,是把王爺信仰追溯到秦朝,認為他們之間包括秦始皇焚書坑儒埋害的365位儒士,以及權臣趙高謀害的忠臣義士。[2]可是這種說法很容易遭遇歷史考據的困境。問題不在神鬼之有無或是否真有其事,而在于王爺信仰本就是局限在閩南文化影響的范圍;不但唐代以前的典籍,沒有記載過華北到華南出現類似的王爺信仰文化,而且許多各姓王爺廟,廟史都沒有記載王爺是秦代人。何況,王爺信仰的內容甚至不曾從閩南流行至閩中,所以閩南人才有機會附會發展出“王爺入永春,損失十三萬”的流行俗諺。因此,要說閩南當地流傳的王爺信仰源自秦代,畢竟是難以找出時空憑證。
民間第二種說法,則是把王爺和唐太宗聯系起來,說是唐太宗李世民微服出巡遇險,遇上36人救駕有功,唐王因此欽賜36人進士,下旨他們游巡天下。后來36人不幸集體墜海罹難,太宗于是追封他們為神靈,繼續代天巡狩。[3]可是這樣的傳說既然只適合說明36人,便難以對照臺灣本土姓氏多達132種的王爺。
民間還有第三種說法,是把王爺起源說成是唐玄宗開元年間的事,說是皇帝或奸臣做了壞事,主張把一批士子關入地牢吹奏絲樂,以此“怪音”試驗張天師能耐,要他施法停止音響,導致天師奉皇帝金口誅滅360名士子。這造成日后鬼魂游走皇宮哭訴冤情,玄宗后悔,下詔天師設壇,敕封這些亡靈成為王爺,敕賜彼等巡察天下“游府吃府,游縣吃縣”的特權。[4]
另有第四種民間說法,則認為王爺其實是明思宗末年的360位進士,在明朝滅亡后,不肯仕清,自盡殉國。民間以玉帝敕封王爺為由,香火祭祀,并賦予大眾對忠臣的期望,希望他們死而為神,奉玉帝旨意巡按天下,賞善罰惡。[5]
但以上第三與第四兩種說法,且不說在傳說所指時代或者稍后的文獻都難以找到根據,重要是傳說中的人物身份都是無法戰陣的文舉“進士”形象,畢竟無從吻合民間的王爺信仰印象,難以對比解說為何人們供奉的許多位王爺都不是士子裝扮,反而以戎裝將軍面貌受到供奉。
臺灣當地還傳承了老臺灣歷代記憶,認為民間曾頂著清政府高壓,假托王爺信仰以奉祀鄭成功祖孫,如連橫《臺灣通史·宗教志》便曾提及此段說法,解釋道:“時已歸清,語多避忌,故閃爍其辭,而以王爺稱”、“雍乾之際,芟夷民志,大獄頻興,火烈水深,何敢稍存故國之念?”若按其說法,王爺廟稱為代天府、代天巡狩,乃因鄭成功“開府東都,禮樂征伐,代行天子之事”。[6]連橫也因此指說,臺灣“池”府王爺信仰極盛,是由于部份“池王爺”廟,背地假借“池”與“鄭”的泉語發音相近,暗喻“鄭王爺”。[7]另外,也有認為,鄭家被明朝皇帝賜姓朱,因此“朱王爺”暗喻鄭家。[8]但此說若真,畢竟也只能說明某些廟奉祀“王爺”是假托閩南王爺之名,延續對鄭成功的忠烈崇拜。也正如連橫《臺灣通史·建國紀》所載,到1875年,欽差大臣沉葆楨按照清朝鼓勵忠義政策,請奏朝廷在臺灣開建延平郡王祠,配祀明季忠義之士百十四人;當時,祭祀鄭成功變為朝廷鼓勵之舉,當然就不需要再假托于王爺信仰了。[9]只是,有多少假托“王爺廟”實為鄭成功廟祀,是難以重新正名,也難以考究了。但反過來,筆者在臺灣安平的田野調查,也曾聽聞日本在1895年殖民臺灣以后壓制漢族民間傳統信仰,曾使得臺灣一些池府王爺廟假托“鄭王爺”,說自己供奉著日本人強調為“日本后裔”的鄭成功。
其實,不論是在臺灣或南洋,民間許多王爺廟,最盛行的說法都是王爺為著老百姓“殺身成仁”的故事,認為廟里所祀奉的王爺系古代的數名士人,途中見水井中有疫毒,自行投身井中,警告鄉民不能飲用,救人性命,以積下的大功德感動玉帝,升天為神。當然,這樣的說法還是無從解說所有王爺的來歷,也還是說不通那些戎裝的王爺如何歸類,但至少反映了人們心目中王爺信仰往往反映神明生前“義烈”的價值特征。
綜觀上述各種相關王爺來歷說法,雖說都無法總結整體王爺信仰,但仍可理解它們的信仰精神有著共同內涵,幾乎一致繼承著華夏傳統文化處理信仰生活的思路,首先視王爺為維護傳統價值的殉難者,然后又將原來橫死性質的“厲鬼”類型死者,按照生前所做功德大事“化厲為神”,成為人們崇功報德、慎終追遠的對象,讓傳說中的殉難事跡交織出萬人膜拜的威嚴,成為世人學好向善的楷模。
另一方面,有些學者主張王爺的原型本是瘟神,或是由原來的瘟神信仰演變而成。臺灣學者提及這種主張,所依據早期文獻,是在1722年清廷平定朱一貴起事以后,御史黃叔璥記載其巡視臺灣所見,在《臺海使槎錄》卷二《赤嵌筆談》“祠廟”條提及:“三年王船,備物建醮,志言之矣!及問所祀何王,相傳唐時三十六進士為張天師用法冤死。上帝敕令五人巡游天下,三年一更,即五瘟神。飲饌器具悉為五份,外懸池府大王燈一盞。”[10]以后又有兩位乾隆年間到臺巡查御史,范咸與六十七,共同纂修《重修臺灣府志》,其卷十三《風俗》載:“臺俗尚王醮,三年一舉,取送瘟之義也,附郭鄉村皆然。境內之人鳩金造木舟,設瘟王三座,紙為之,延道士設醮。……跪送酒食既畢,將瘟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財寶,無一不具,送船入水,順流揚帆以去。”[11]由此而發展至王爺本為瘟神之研究論述,到1938年便有前嶋信次最早發表《臺灣の瘟疫神、王爺と送瘟の風習に就いて》,以后頗有學者據此論述,影響很大。[12]其中如劉枝萬,即以為王爺包括許多姓氏,是發生大瘟疫造成大量死者,形成雜姓群聚的厲鬼靈魂崇拜,經歷不同演化階段演變為逐瘟之神、護航之神,由此逐漸擴大神圣職能,成為醫藥、保境安民的神明。[13]
但是,如后來康豹(Paul R.Katz)在《臺灣的王爺信仰》的研究指出,瘟神通常只包括五瘟使者和十二值年瘟王,和一百三十二姓王爺是有差別的,后者大部分和瘟神也沒直接關系。[14]而且,供奉諸府王爺的規格,顯然不是祭祀無主厲鬼的一般壇祠。更何況,王爺信仰最早不是源于臺灣,因此也就不宜單以臺灣的一些廟宇作為論證整體王爺信仰起源的范例。若根據民間后期流傳的《五府千歲真經》所說,民間對王爺的情感,正好與上述清廷官員的記錄相反,并不是說諸府王爺本身是瘟神,而是說明在天上神祇的相互關系之間,瘟神與王爺可以形成互相對應的系統。如果說《五府千歲真經》畢竟是20世紀中葉以后臺灣神道界編整神啟的手筆,那么再按照據說在馬來西亞吉蘭丹州流傳了兩百余年以上的池、朱、榮、莊、楊、溫等諸府王爺請神咒,諸府王爺帶領數萬兵馬代表玉帝巡視人間、斬妖捉邪,形象顯然很早定型定性。[15]
從民間相信玉帝領導諸神主掌三界事務、賞罰人間善惡的角度,瘟神與王爺都屬天庭體制諸神,負責天庭賦予的不同職司,雙方會有互動也是可以解說。如果瘟神使者是奉著玉帝命令懲罰地方造惡、到凡間施放瘟疫,王爺之所謂“代天巡狩”,則是獲得玉帝欽賜權力去監察與重審凡間事務,在瘟神下降前后事先巡察以及糾正地方善惡,因此亦有代民眾向行瘟使者說項的職權,禮送這些瘟君離開本境。另外,王爺既然被賦予巡狩權力,也就有足夠權能調兵遣將對付、鎮壓和押送那些散播瘟疫的神煞和妖魔鬼怪。過去王爺信仰活動的最大特點是“送王船”,由于最后要載著瘟神,所以也確有稱為“瘟神船”;人們誤以為王爺是瘟神的原因,也是由于瘟王亦稱“王”。但“送王船”是由民眾為他們心目中看顧當境的諸府王爺備船,目標明顯是以大木船支持王爺送走瘟神,而不是期待王爺隨著送走王爺船從此消失,讓王爺廟就此關門。正如楊國楨曾引證的大英圖書館館藏乾隆乙丑(1769)海澄道士《送船科儀》,漁村為海船人員禳祭,舉行“送船”,目的是將傳播瘟疫的神煞押送出境,符合農漁社會驅病除災的心理本質。[16]
臺灣民間會有認王爺為瘟神,也許是源于臺灣海峽兩岸的地理與風向使然,造成閩南信徒送走的王船往往有機會漂流到臺灣西南方。這很容易造成某些鄉鎮接到王船,懼怕瘟疫,也要建起王爺廟或作醮普渡,并且再舉辦送王船,以期送走上岸的瘟神。這種信仰實踐,無形中會隨著王船漂泊,把王爺信仰向著王船擱淺的鄉鎮推廣;但同樣情形,又極容易讓人們把王爺與厲鬼、瘟神角色聯系起來,甚至等同,看見王爺作為船主的名號,就以為備船送瘟神出海的船主是瘟神,也以為送船出海的村鎮是把瘟神送到其他不認識的村鎮,隨著王爺船在他人岸邊擱淺。其實,乾隆二十九年王瑛編纂《重修鳳山縣志》,便曾置疑過這種說法,認為不合理且不可置信,這本縣志提到說:神(王爺)聰明正直,怎么到了異鄉就變成厲鬼?而人類何必作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17]
若據黃文博《臺灣民間信仰與儀式》,臺灣人所謂“王爺”既然本是一般神明的統稱;那么,通稱王爺的神靈,其實來歷不同,應有分類,分別為戲神系統、家神系統、英靈系統、鄭王系統、瘟神系統。黃文博書中提及“家神”性質的王爺,尚包括1952年謝世的謝水藍,因在臺南永康貢獻極多,死后被地方民眾奉為“謝府千歲”,以至曾有其同宗候選人打著其名堂參加立委選舉。[18]只是,根據這樣的分類,論述王爺信仰其實不應一概而論。如考慮到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地閩南先民流傳的信仰印象,各地共同擁有之狹義的王爺信仰,應該還是人們心目中具有“代天巡狩”職司的諸姓王爺,他們到了各地,因各種因緣演變,受到不同群體供奉,可以是五姓組合,或三姓組合如林郭馬、朱雷殷、朱李池、杏莫蘇、朱邢李等,還有單姓王爺。這其中,有像吉蘭丹巴西嗎(Pasir Mas)地區華人社會,其《池府王爺咒》尊稱地方集體供奉的池府王爺為各村落的“祖王爺”;[19]有的王爺固然以防治瘟疫聞名,也有的王爺廟是因應著地方民眾要求,“巡狩”的事務不同,不一定要定期對付瘟疫。
二、王爺香火凝聚先民主權意識
如果追問馬來西亞諸府王爺的歷史與祖廟淵源,馬六甲與檳榔嶼的王爺廟也許最早設立香火,兩地既有漳州王爺,也有泉州王爺。值得注意的是,在馬來西亞的王爺信仰,往往是由下南洋的閩南宗族群體組織集體香火,供奉與延續原鄉王爺廟分香,并俗稱神靈為“祖佛”。有時,地方上的王爺信仰又可能表現為合祀多位王爺的形式,由華人開拓聚落的一些民眾共同發起建廟,集體供奉地區先民各自從不同原鄉帶來的二位以上王爺香火;當地閩人也往往會因此把王爺香火結合說成“兄弟有序”,并以王爺作為地方安靖保護神,把落地生根的王爺群祀視為源自不同原鄉民眾在地結合的歷史象征。[20]而且,根據各地廟史,這些王爺除了有名有姓,當地也重視王爺化身為神以前的身份來歷,或從王爺香火遷移說明先民如何從原鄉帶著文化與傳統價值觀念南遷墾荒。廟史,也就支持了地方華人歷史的有根有據。
正由于漳、泉兩地航海下南洋海路遙遠,而且可能有許多風險,人們常要依靠神靈維持信心,馬來西亞華人信眾所供奉的王爺,幾乎都源于先輩為了沿途自保而親身攜帶原鄉親切的神明香火,其中一些閩南宗族村落先人更將村中供奉的同姓王爺視為血緣先輩,成家立業后也會把香火分香到居所奉為家神,自認家中供奉的王爺是血緣先輩當中成神的人物。因此,馬來西亞華人王爺信仰不僅是地方廟祀,也常見于宗祠主祀或附祀,甚至普遍被人們家里當成祖先神,或信眾會一邊尊奉王爺為他姓的先人英靈崇拜,一邊又將其供奉為家居保護神。[21]
根據英國人S.M.Middlebrook撰寫的《Ceremonial Opening of a New Chinese Temple at Kandang, Malacca》,他在1938年到馬六甲干冬(kandang)參觀當地朱府王爺“代天巡狩”新廟落成建醮,得悉本廟香火最初由漳州漁民攜帶上岸,放置在一所小亞答屋供拜,以后才由信徒擇地建廟崇祀。按S.M.Middlebrook當時記錄,舊廟歷史可能要回溯兩百余年以前,乾隆年間,馬六甲尚在荷蘭殖民時期,華人已經供奉來自漳州的王爺香火。[22]再據蘇慶華《代天巡狩:勇全殿池王爺與王船》,馬六甲萬怡力(Bandar Hilir)勇全殿的池府王爺,源自信徒從泉州府同安縣(今隸屬廈門市)馬巷的池王宮元威殿奉引王爺香火南下,1811年建廟于現址。[23]因此,馬六甲勇全殿和臺灣200多座“池王爺廟”,擁有相同祖廟,此地相傳神明身世的版本,也和臺灣海峽兩岸流傳的版本大同小異、故事主線還是集中在“救瘟”:池王爺名然,是明代南京武進士,蒞任漳州府道臺,赴任至南(安)同(安)交界處的小盈嶺驛館,聞三小鬼將往漳州投毒“裁減人口”;池道臺為救萬民,設計奪取瘟藥自服,面焦氣絕。玉皇得報,感其精誠,特賜“玉旨敕封代天巡狩總巡王”,其香火后來發展各地,“漳州既獲庇蔭,泉郡亦沾恩澤”,受泉州人立廟奉祀。
如此一來,馬來西亞固然還有些王爺廟迄今保留送王船的記憶,或有的廟至今還會延續燒送王船的傳統,但此地鄉鎮最早的王爺金身或香灰幾乎都是信眾親身從閩南故里懷抱過來,從來不可能遇上福建王船千山萬水漂來,故而也就難有可能流傳王爺船上岸的事,或者會把自己抱來的神明視作瘟神上岸。馬來西亞的王爺信眾,一旦遇上其他地區將王爺說成瘟神信仰,或者把“十二行瘟王”也看待成同屬“代天巡狩”,確會感覺到格格不入,覺得這些文字和他們的信仰經驗存在很大差距。
事實上,先民在南洋各地供奉諸府王爺香火,流傳類似閩南故鄉的神話版本,通過集體在新的聚居地點延續家鄉信仰,往往有利大眾消減對新土地的陌生,而生起異地重建故鄉的認同凝聚力。據王琛發《代天巡狩下南洋》,早在1814年,便有檳城蔡姓宗親從海澄縣三都鐘山社故里家廟“水美宮”迎請到二位“蔡王府王爺”香火,供奉在有許多捕魚和務農的族人散居的浮羅池滑(Pulau Tikus)地區,以后又經歷過其他鄰近開拓民合祀各姓王爺、接著再分開香火到其他開拓地區的過程;最終,原地水美宮依據祖先同源發展為供奉二位蔡王爺與辛、柯王爺的“辛柯蔡宗祠”,而其他各姓信眾則捧走辛柯蔡以外的王爺香火,在灣島(Tanjong Tokong)地區重建另一僅僅供奉朱池李三王爺的“水美宮”,交托“福建公司”管理。[24]
再如馬來西亞華人人口最稀少的吉蘭丹州,在巴西嗎地區,當地鎮府宮的楊府二王爺原來是在巴西嗎彭家蘭巴西村子,由人們稱為“大伯壽”的一位父老“王壽”帶來,地方人士在1940年代才開始為王爺建廟,以后形成與鄰近甘榜古丹、登籠、紗卡、十三行等十幾地區的信眾聯系;而巴西嗎當地的華人,除了稱彭家蘭巴西的楊府王爺為“二王爺”,還互相稱呼楊府王爺對岸河邊Aur Duri村的蘇府王爺為大王爺,又稱江沙村的池府王爺為三王爺,村民年年互相到鄰村參加三位王爺誕會,促進各村來往。[25]至今未為池府王爺建廟的江沙村,到目前猶保持地方王爺信仰的最早組織形態,是依靠各家各戶每年擲笅選出值年爐主,由值年爐主盡義務把和鄰村楊府王爺歷史同樣悠久的神像帶回家中供奉,以服務本村和鄰村信眾一年祭拜公眾保護神的需要。這也算通過敬神完成睦鄰。
以上足以說明,馬來亞本土的華人很早就延續清朝乾嘉年間福建原鄉盛行的王爺印象——王爺常被宗族村落認為是本族有名有姓的先人,除了作為宗族家神,也會發展成其他人共尊同祀的英靈崇拜。一旦王爺下南洋,他們既可以成為保護宗族下南洋開拓宗姓新領地的祖先神,由先行者供奉的一位或數位王爺,也可能統合成為鄰近數個互相依賴村落的集體保護神。
當然,自19世紀中葉以來,人們陸續從中國閩南各村鎮攜帶香火南下馬來西亞,到達南洋以后的廟祀格局也不盡然仿似原鄉,而是各有演變。例如:其中也有不少王爺廟的池府王爺香火,并非來自泉州馬巷,而是源自南安廿九都遼陽山上的靈應堂的分脈。這些由南安靈應堂南傳東南亞各地的香火,如檳城大路后與芎蕉芭兩處靈應堂,廟號沿用“靈應”而供奉祖廟孫、佘、池三王爺;北海拉惹烏達(Raya Uda)靈應社增奉雷府王爺;北海雙溪浮油(Sungai Puyu)單獨供奉佘府王爺;檳城峇六拜(Bayan Lepas)過山孫劉二王府,一同供奉靈應堂三王府所供奉的孫王爺與不同來歷的劉王爺。另外,還有像威北日落斗哇(Teluk Air Tawar)的天地堂三保宮,是供奉了由緬甸商船傳進來的七府王爺。[26]
上述提及的各地王爺廟,雖說僅是全馬王爺廟的小部份,但是他們的歷史淵源,確可以反映馬來西亞王爺信仰的多元淵源。同一位王爺香火可以因其本身在中國早已分香不同地方,依各位信徒的原鄉淵源被帶進馬來西亞。來自不同原鄉的王爺,也可以因各地群體在當地互相結合,形成地方上新興的廟祀組合,流傳演變。唯一難以變化的共同點,是各地廟祀畢竟都表達在中華故里神明南渡,地方華人在當地建廟崇德報功,為著感恩神明、學習神明教義而結社,重要目的在于轉化神明歷史與傳說作為時人典范,異地重建符合祖先文化思維的倫理綱常,確保社會大眾求安身立命。
崇德報功與慎終追遠的目標,本來就是為了完成民德歸厚,不論個人是否站在血緣立場,沒有人會反對其他人以崇德報功與慎終追遠的同理同情對待自己心目中的“血緣先輩”,也沒有人會忽略神道設教的重心不能局限在神靈與個人的親屬關系,人們反而重視神靈象征的價值觀念能否感應而內化于人心。由此,各府王爺可以因為是自己同姓后人的“血緣先輩”被稱“祖王爺”,也可以被他姓乃至他族信眾基于英靈崇拜而尊稱“祖王爺”。這才是閩南各村鎮王爺信仰能夠在南洋各地以各種形式延續、組合、發展、演變的根本原因。
上述諸府王爺的“香火”,最初下南洋,當然也不一定以神像或香爐南傳,信徒所能攜帶的,可能僅是一小包掛在脖子上的香灰,或把小香包縫在衣領內。可是,在先民眼中,不論神像、香爐、香灰,俱可視為延續與再現原鄉廟祀的神圣象征,確保大眾有信心落腳新天地。王爺崇祀至遲在荷蘭人統治馬六甲的年代扎根馬來西亞,各地廟祀多從木架茅棚一路發展到廟宇堂皇,可謂是信仰活動承載著閩南文化傳播到南洋植根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地傳播的后果,又帶出各廟共有的常見現象:大家只能確定王爺信仰源自閩南,卻再也無法限定馬來西亞各地方王爺信仰純屬閩南人后裔崇祀;而王爺信徒甚至包括地方上其他族群,又似乎更說明王爺作為當地先民集體祖神的正當合理。
神道設教的成功,也表達在人們對神明冥冥中的威靈顯赫有所期盼。灣島水美宮廟前對聯以“水美”二字為冠首,概括神明功能“水陸兼權憐赤子,美靈特赫慰蒼生”,大致可反映大眾心目的神圣印象,認為王爺作為原鄉祖廟之英靈,降臨于萬里航路現場,是會保佑過去在原鄉保護過的子民和他們的子孫,尤其照顧著南洋群體既要開拓內陸莽荒,又要依賴海港經濟謀生。王爺既然“水陸兼權”,正如馬國流傳的池府王爺請神咒,咒文有謂“收斬天下邪魔鬼,縛治妖魂不正神”,就表明著神明威權是發揮在驅邪、除妖、治病,以及確保包括各種煞神和魔怪不會跑到船上或岸上,并以“送船”儀式押送各種災病離境。馬來西亞早期王爺廟祀多在海水或河流岸邊,恰恰反映著信徒集體期待神靈水陸兼權能照顧合境平安。[27]群體祖神在群體灑下血汗的當地“水陸兼權”,當然也反射出群體對周遭環境具有水陸主權意識。
正因在南洋的王爺信仰表達了人們通過異地重構信仰重建新的故鄉感覺,因此人們從集體生活所及范圍想象著王爺廟“水陸兼權”,總涉及神圣領地的邊界概念。不論王爺廟或其他神廟,其延續閩南民間道教的信仰觀念,還表現在以廟宇作為聚落空間的信仰中心兼文化特征。立廟除了祭祀神靈,還需以鄉鎮或廟宇為中心,依照“中央—四方”布局,設立有形的“五營”神兵祭祀,建立起護衛有形人畜世界兼無形鬼神世界的邊境意識。若追溯先秦兩漢以降的文化觀念,現在神廟構建“五營”信仰的觀念來源,實源于結合“中央—四方”維護華夏文化勢力范圍的多元一體模型:中央三秦在關中,四境服裔的東九夷、南八蠻、西六戎、北七狄,與之形成互相支援的政治兼軍事體系,維持天下穩定的大一統;這種五方秩序的軍事理想演變為信仰觀念,早期曾被漢晉道教壇制轉借使用在護壇儀式,后來被各地民間道教與法派吸收,形成神廟護境兵將群的觀念。[28]到了閩南民間道教信仰,則以張、蕭、劉、連四圣者守東南西北四營,輔助哪咤為中壇元帥。根據這種觀念,正當19世紀的南洋華人非常重視講究地方幫群實力,廟中安“五營”,每月例常初一、十五在廟宇鄰近四方準備糧草飯水,為肉眼看不到的本廟神明兵馬舉行“犒軍儀式”,不止能界定廟宇在鬼神界與人間的影響所及。“五營”的外營令旗能離廟多遠,也被視作廟宇和信眾群體勢力影響的象征。
按民間的信念,諸府王爺生而為人,義薄云天,正直忠勇,歿而成神。諸千歲能廣受四方香火,得授代天巡狩之職,掌握“過州食州、過府食府”大權,其因緣殊勝在他們的道德取向,生前以舍己救人的人格化身出庇佑天下之神格。諸府千歲以后貴為天神,擁有代天行事的權能,更有條件繼秉與擴大生前驅邪除魔、保境安民的道德,成為南洋華人遷州過府、開天辟地的精神典范。一旦先民在新土地廟祀家鄉英靈,把熟悉的故鄉色彩帶進日常信仰生活,又以神明名義確定安放和祭拜“五營”的最遠邊界,并主導神明例年“巡境”,就代表著王爺信仰象征的文明“綱常”落地實踐,王爺信仰承載的華夏文化也通過廟祀活動重復在地方上演練。南洋先民其實就是憑著集體長期拜拜王爺,將每一處“當地”轉化為人神共享、神佑人旺的王爺巡狩之“境”。
先輩墾荒開拓、除瘴消癘、建綱常、開海運,本有功于當地而無愧于天。是故,南洋諸處之王爺廟,可謂先輩衣冠南渡之紀念,是中華閩南民系開拓異境的歷史與精神象征。
三、王爺廟祀提供地方醫療支持
再回到先輩在南洋墾荒的歷史場景,很多時候,南洋各地王爺廟宇的社會功能之一,是支持地方公共衛生與治病救人。地方衛生條件落后,肯定造成開拓群體眼見心思的集體生存危機,王爺信仰傳統以來作為對抗瘟疫的象征,也必然使得人們對王爺的信仰要求,離不開通過神圣威靈與廟宇設施保障大眾平安,尤其對抗古人列入“瘟病”范圍的各種傳染病癥。
從防治疾病的角度評價燒送王船,王爺信仰出現燒送王船活動,其實涉及公共衛生,在集體信仰活動當中兼顧整個社會防治瘟疫的安全。但送瘟船最初不一定關系諸府王爺。回顧閩浙盛行的送瘟船習俗,《閩雜記》卷七雖把福州和漳州等地“出海”送瘟船混為一談,但所提及福州地區,其實并非閩南王爺“不入永春”之散布區域。再以乾隆版《泉州府志》為據,其卷二十《風俗》記載:“五月無定日,里社禳災,先日延道設醮。至期以紙為大舟,送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備,陳鼓樂儀仗百戲,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29]這份文獻重要在它提到較早期泉州地方上燒送王船,較為節約,不像后來浪費金錢制造大型木船漂浮出海;而且,文獻也證明送瘟神不一定相關王爺,不必選擇王爺誕辰,多是選擇農歷五月夏季多雨濕熱之際。可見,閩南人盛行祈請諸府王爺送走瘟神,是想額外憑借“代天巡狩”權勢,加強信心效果。以閩南人過去應付溫帶與亞熱帶氣候交界地區的經驗,農歷五月常是多種瘟病流傳季節;應崔寔《四民月令》提到的農歷五月“陰陽爭,血氣散”,[30]南朝梁人宗懔《荊楚歲時記》所說“五月俗稱惡月,多禁”,[31]“送王船”可視為人們從民俗角度理解與對應,提出如何對付可能發生傳染病的環境。可以考慮,所謂閩南王爺巡境與燒送王船儀式相結合,包括大眾事前事后清理街頭,將各種容易腐爛的物質包裝上船送入鹽性海水,沿途燒放大量鞭炮以火藥硫磺殺菌去瘟,以及用大量藥香結合火燒王船對付水域邊的濕氣,不見得是全無醫藥知識而僅是表面熱鬧的神秘儀式活動。
當然,其他地區送瘟未必要依靠閩南諸府王爺,但是閩南到南洋各地形成王爺壓陣的傳統,其實以神威添勢,更大動員整個鄉鎮,寓集體保健于信仰活動。
若從神廟設施對應民眾日常保健需要,古人造香,基本目的在抑制霉菌、驅除穢氣,一般常見制香原料,不一定單純使用榆樹皮、柏木、柳木、杉木等木屑、葉屑精磨成粉,也不一定要用檀香、沉香、蕓香粉末,很多時候反而是注重藥物配方。明代醫家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線香”入藥,有說:“今人合香之法甚多,惟線香可入瘡科用。其料加減不等,大抵多用白芷、獨活、甘松、三柰、丁香、藿香、藁本、高良姜、茴香、連翹、大黃、黃芩、黃柏之類,為末,以榆皮面作糊和劑。”[32]李時珍還記載了用線香“熏諸瘡癬”方法,是在桶中點燈,燃香以鼻吸煙咽下。而中毒或生瘡的患者甚至可以到廟中吞香急救,“內服解藥毒,瘡即干”。[33]包括王爺廟,任何廟宇,只要有信眾燒香,廟里有隨時供大眾取用的香灰,對鄰近地區的居民,神廟就是大眾小病防大病、急病求緩和的場所。
站在傳統中醫立場,不論是燒香或者香灰,確實有藥用價值。以藥制香,燒出香灰稱為“爐丹”,不單純是美化的稱呼,是歸功為著神明保佑大眾而尊稱。從中藥藥性去分說,爐丹,實屬草木灰,味辛,微溫,入肝、腎二經。《本草綱目》除發現草木灰味道辛,微溫,還說香爐灰可治“跌撲金刃傷損,罨之,止血生肌。香爐岸,主疥瘡”。[34]若按現代化學分析,香灰主要成分是碳酸鉀,碳酸鉀是強堿弱酸鹽,其中有鉀,鈣最多,磷次之,也含有少量鎂、硫、鐵、銅、鋅、硅、硼、鋁、錳、鉬等微量元素。中醫經典說香灰的內服外用治病功能,包括:清熱、利濕、殺蟲、去瘢風、去黑子、去疣,息肉,疽蝕疥瘙、治大骨節病、蝕癰疽惡肉、止血生肌、去瘡疥。如《本草綱目》提到的草木香灰外用方法,就是把香灰和酒加熱,敷在被狗咬傷口,可以腐蝕諸癰疽惡肉;《本草拾遺》還建議說,香灰和醋弄熱了熨胸部和腹部,可以對付心腹冷氣痛及血氣絞痛。還有些民間土方,又主張用香灰加麻油,可以涂抹在湯水灼傷的皮膚,作緊急處理。古人或純粹使用廟里爐丹,或者針對不同疾病配合其他藥材,并非全無符合現代醫療的根據。
香灰泡水當藥,不僅治人病,也能治動物病。人們經驗上,會根據《本草綱目》記載,利用味咸的草木灰,沉清液,醫治耕牛吃草后的胃痛和脹風;民間過去缺乏獸醫,農村也常取新鮮香灰,用溫開水攪拌均勻,浸泡四分之一個時辰,過濾、去渣、澄清,再讓畜生服用,以治療家畜翻胃吐草、大便秘結、肺寒胃冷、滑腸。由此可見,神廟對農牧村鎮的重要,不純粹是信仰需要,也涉及人畜安全。
所以,古人經營廟宇,不單是設立神像和修造硬體,還得摸熟地方各種病癥,注重地方制香配方。古代人在廟里廟外拜神燒香,是真正在神前做有效大眾保健的功德事業,燒的香,有利環境殺菌,有利大眾吸香煙保健,剩下的香灰也是造福人畜的健康;廟宇香火可謂是日常防治村鎮人畜瘟病災難、急救各種傷病的第一道防線。各地神廟鼓勵信眾燒香,在香爐中保留香灰,并允許人們請香灰回家服用,是人們把功用濟世利民的好事,感恩奉獻神靈,而以神明的名義,推崇照顧大眾保健和地方安寧。這就是古人的謙虛,為善而不居功,又歸功神靈慈悲關懷,因此而推崇神道設教的社會風氣。有錢的人燒多一把香,沒錢保健治病就不怕缺乏資源。
再按道醫通源說,神廟以靈符救世治病,也并非虛言。《本草綱目》言:“諸紙,甘,平,無毒。楮紙:燒灰,止吐血、衄血、血崩、金瘡出血。竹紙:……止虐。滕紙:燒灰,敷破傷出血,及大人小兒內熱;衄血不止,用古藤紙(瓶中燒存性)二錢,入麝香少許,酒服。草紙……最拔膿。麻紙:止諸失血,燒灰用;紙錢:主癰疽將潰,以筒燒之,乘熱吸患處,其灰止血。”[35]南洋神廟傳統用的符紙,原料不外清熱解毒的竹紙、滕紙,還有蔗紙。符紙是藥,符紙染色劑是藥,畫符用的朱砂或墨汁都是藥。青符用竹葉染青,為的是竹葉能對抗煩熱、風痙、喉痹、嘔逆等癥,以及對治咳逆上氣、溢筋急、惡瘍,并有殺小蟲的作用;黃符常用黃姜染黃,就是由于黃姜有效活血化瘀,通經止痛,功能祛風、治氣滯、癰腫、風痹、跌打等。而按《新修本草》總結:朱砂或稱“丹砂”的功用是在“主身體五臟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通血脈、止煩滿、消渴”;[36]墨汁味道辛苦,其性平,是以入心、肝二經為要,以達止血、消腫、治吐血、衄血、崩中漏下、血痢,癰腫發背。[37]可見,各色神符用墨書寫再蓋朱砂,其實具備成藥性質,兼顧各種常見病癥。一般人體發熱,或因熱病而囈語,見神見鬼,符藥往往不離符紙和符色的原料結配,以朱砂鎮心火安神、清熱解毒,以墨汁通經脈、祛內傷、解郁悶,又根據符紙原料祛風、清熱、鎮痛或消炎。人們到神廟討取的神符結合各種單味藥微量元素,固然不見得符合中醫精致層次講究“君臣佐使”配方,尚可能不是對癥下藥,但肯定能樸素而有效穩定病人情緒,發揮刺激人體調節功能的引子作用,至少舒緩痛苦或減輕惡化。其中訣竅,又在于某些符紙必須低溫燒成堿性白灰,配合陰陽水發揮效用。純粹把靈符作用看成神跡,或者片面以為只具信心療法的功能,反而掩蓋信仰文化綜合各種醫藥知識的智慧。
至于馬來西亞王爺信仰衍伸的藥簽文化,包括馬六甲勇全殿、檳城靈應堂、威省靈星堂等,流傳著信眾求問藥簽傳統,亦應受到重視。藥簽的由來,其實是當地神廟根據神靈保護黎民疾苦的慈悲,基于地方常見病癥,尋找懂得醫理的先進,總結地方上平民經濟能負擔、鄰近容易尋找的藥物,編寫各種微量藥物復方。藥簽作用,在于藥物能對應身體心肝脾肺腎五行各系統,無病作用少,有病則溫和刺激患病系統,達到治療效果。神廟要啟用或改寫藥簽,一般都要先以擲笅等方式祈求神靈恩準,才開放給信徒求用。分析百年藥簽,不僅可以發現當地舊時的常見疾病,還可以根據沒有具體出藥、只是教訓求簽者改過遷善的“空簽”,發現過去的地方倫理議題,看到“空簽”如何警惕信徒轉變心態,以達到治病也挽救人心。
嚴格的說,神廟的原有功能本來就包括處理社會集體醫療的需要。尤其王爺信仰的重大特征,就在于人們相信王爺是照顧當地人民除瘟祛病的神靈,供奉者若是同姓宗族,更覺得王爺是最接近也可以依靠的神明兼長輩。在醫藥落后、平民百姓無法為小病而遠途耗時耗錢醫治的年代,神廟文化擁有燒香、香灰、符紙、藥簽等等元素,無疑支持了大眾避免耽誤病情,讓大家就近尋求病,從淺中醫。馬來西亞許多百年以上王爺神廟的廟宇文化包括各相關醫療的內容,可說是地方先民開辟鄉鎮過程缺乏醫療的艱辛見證。他們依靠著神道信仰與神廟組織支撐集體生活,百年不懈,為子孫安居樂業奠基。
四、后 語
馬來西亞王爺信仰畢竟是在自己土地上延續與發展,因此本土王爺信仰相對于其他地區的王爺信仰,可能出現別人缺少的內容,也可能缺少其他地區普遍的內容。例如,馬來西亞的王爺信仰活動,往往看不見演變自古代戰陣的陣頭表演,有的王爺神廟自20世紀至今長期不再燒放王船。從歷史角度,這樣的在地演變都不是壞事。如果鄰近區域一般友善互動,大家相安無事,原來借著神誕舞刀弄槍演練陣勢,反而會引來不必要的顧忌,當然可能式微。而地方公共衛生長期基本穩定,醫藥進步,就會致使地方大眾調整對王爺信仰功能的側重面向,轉向關注海陸經商安寧繁榮等等領域,甚至還有爺爺奶奶祈求王爺保佑后人讀書考試。這比起爺爺奶奶小時候看不起醫生,找王爺求藥簽、取爐丹,反映著拜神的群體生活在進步。人們對神明功能有了新的共識、多元的要求,其實也能反射大眾繼續傳承舊有信仰的熱誠,信心不變。
總結地說,馬來西亞王爺信仰文化是以各地崇祀諸府王爺的廟宇組織為載體,承載著華夏傳統具有閩南地方色彩的價值觀,落實影響各地華人社會,維續其民族文化認同;各地王爺神廟,是有責延續華人先輩文化與價值認同的社會組織,同時也曾通過神明名義提供各種神符與藥簽,在地方上發揮過維護社會公共衛生的效果,有益治病救人。當然,隨著當代社會中西醫等各源流醫學繼續進步、醫療機構相繼普遍、交通發達、治療許多疾病的時間成本與經濟成本降低,王爺神廟維護公共衛生和治病救人的實質功能日益降低,是必然的。但,時勢演變,何嘗不是朝向王爺信仰除瘟救病的原來理想?當代王爺信仰也許應結合社區營造的理念,從施醫贈藥轉進增多普及醫療保健知識的活動,乃至創辦醫療機構,繼續發揚神道精神,擴展王爺信仰強調安靖地方、除瘟祛病的歷史本色。
(注:本文根據口頭發言講稿整理。最初發表于馬來西亞檳州北海雙溪浮油靈星堂主辦“第一屆國際孫佘池三王府文化聯誼研討會”,2014年1月31日。)
注釋:
[1][日]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臺北:捷幼書局,1993年(原版于1919年),第35~37頁。
[2][3][5]劉昌博:《臺灣搜神記》,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第140頁,第140頁,第39頁。
[4]姜義鎮:《臺灣民間信仰》,臺北:武陵出版社,1985年,第38頁。
[6]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04頁。
[7][8]石萬壽:《王爺信仰與延平王君臣關系之探討》,載《臺灣文獻》第60卷第1期,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2009年,第206頁,第225頁。
[9]連橫:《臺灣通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2頁。
[10](清)黃叔璥:《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八·臺海使槎錄》卷二,第三十一頁;China-America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 Identifier-access: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06044602.cn;版本亦見(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第45頁。
[11](清)范咸、六十七:《重修臺灣府志》,http://guoxue.r12345.com/tw/03/105/021.htm;另參:(清)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第60~61頁。
[12][日]前嶋信次:《臺灣の瘟疫神、王爺と送瘟の風習に就いて》,日本民族學會編輯:《民族學研究》季刊第4卷第4期,東京:日本民族學會,1938年,第25~66頁。
[13]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第225~232頁。
[14][美]康豹(Paul R.Katz):《臺灣的王爺信仰》,臺北:商鼎文化公司,1997年,第6頁。
[15][19]參考《吉蘭丹巴西嗎鎮府宮發起人之一林朝板手抄咒簿》,1962年。
[16]楊國楨:《閩在海中:追尋福建海洋發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50~151頁。
[17]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原刊于1764年),第58頁。
[18]黃文博:《臺灣民間信仰與儀式》,臺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8~43頁。
[20][21][24][27]王琛發:《“代天巡狩”下南洋——馬六甲與檳榔嶼閩南先民印象中的王爺信仰》,載金澤、陳進國編:《宗教人類學》第一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82~305頁,第288~291頁,第291~292頁,第298頁。
[22]Middlebrook, S.M., Ceremonial Opening of a New Chinese Temple at Kandang, Malacca, in December, 1938.JMBRAS Vol.XVII, PartI, 1939,p.98.
[23]蘇慶華:《代天巡狩:勇全殿池王爺與王船》,馬來西亞:馬六甲怡力勇全殿,2005年,第26頁。
[25]馬來西亞吉蘭丹《鎮府宮楊府二王爺廟史》,廟方根據地方口述歷史記錄整理的手抄藏件。
[26]《第一屆國際孫佘池三王府文化聯誼研討會》,檳城:雙溪浮油靈星堂,2014年1月3日,第14~19頁。
[28]李豐楙:《“中央—四方”空間模型:五營信仰的營衛與境域觀》,載《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0年第一期(總15期),臺北: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0年6月,第34~38頁。
[29](清)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纂:《泉州府志》卷二十,載《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志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492頁。
[30](后漢)崔寔撰、石聲漢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4頁。
[31](梁)宗懔撰、宋金龍校注:《荊楚歲時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頁。
[32][33][34][35](明)李時珍編撰,李經緯、李振吉剪輯:《本草綱目校注》,沈陽:遼海出版社,2001年,第560頁,第560頁,第283頁,第1332~1333頁。
[36][唐]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安徽: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第86頁。
[37][清]汪紱《醫林纂要》所說墨塊藥用功效是針對古法以松煙、骨膠、香料制墨而言,內容轉引自http://cn.zmfp.com/ health/news_13/138769.html。
〔責任編輯鐘建華〕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the Spreading of Wangye Belief in Malaysia
Wang Chenfa
Abstract:Although the local Wangye belief in Malaysia has inherited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Wangye temples which originated in various clan villages in southern Fujian of China, such belief was actually reconstructed by the pioneers of their new settlements with the support of tropical local elements for the sustenance of its traditional values, spirit and vitality. Some of these local Wangye temples may become an icon for the disciples from the same homeland which will also continue to serve as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ir new settlements, and others may help the unification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by the combination of Wangye worships from various origins to strengthen their sense of solidarity. Though the local multi-cultural society gives rise to a new situation that some of Wangye believers may not be Chinese, yet the local Wangye temples never stop their efforts of keeping the southern Fujian’s identity. And the Wangye temples always perform as the vehicle of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common value system for the enhancement of pioneers’sovereignty in their new settlements, as well as the community center for local public health care.
Key words:Wangye from different clans, pioneers' sovereignty in new settlements, consanguineous ancestor, collective ancestral deity, public health care
作者簡介:王琛發(Ong Senghuat,1963~),男,馬來西亞人,宗教學博士,醫學博士,馬來西亞道理書院、道教學院董事會主席兼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