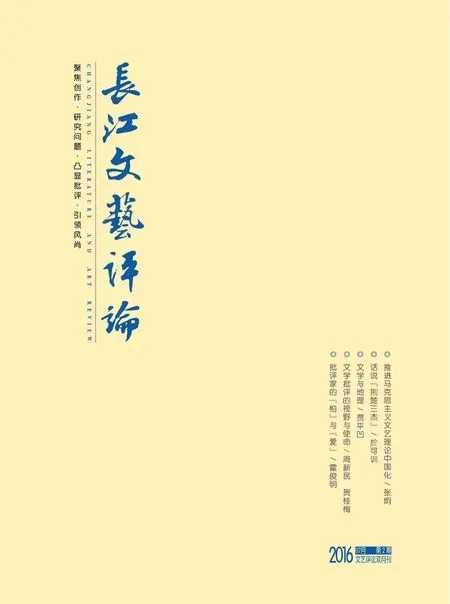文學與地理
◎ 賈平凹
文學與地理
◎ 賈平凹
人類依賴著天和地而生存延續,天上有太陽月亮星星,提供光明與黑暗,有雨,有風,風流動著叫風,風不流動了叫空氣;而地上提供了水,食物,住所,這住所包括你活著的住所和死亡后的住所。中國人歷來講究風水,風就是代表了天,水就是代表了地,于是就有了天文和地理,天上的星空劃分為分星,地上區域劃分為分野,分星和分野是對應的,人就“仰觀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就是說,人的所有象征,精神,信仰都來自天上,而生活的一切技能都是從地上的萬物上模仿學習中獲得。
今天我們先不說天上的事,故宮里有一個匾額,寫了四個字:諸神充滿。諸神都在天上,天上的神我們說不了,說了就是神話,我們今天說地理,當然我們做什么,說什么,天上的神都在看著。古語里講,目妄者葉障之,口銳者天鈍之。意思是你如果太狂妄,什么都看不起,那么上天會飄來一片樹葉就把你遮擋了,讓你成為一個瞎子;你如果口若懸河,胡說八道,那么上天會把你變成啞巴。所以,我們說地理,說地理比較神話而言,應該是人話,但地理我們也根本說不清,僅就以地理與文學這個小角度的話題,我們說一說一些極其淺陋的認識吧。
什么樣的時代出什么樣的作家,什么樣的經歷出什么樣的作家,什么樣的特質出什么樣的作家,同樣的道理,什么樣的地理也是出什么樣的作家。
有一句俗語,說一方水土養著一方人。養什么?養人的相貌,養人的性情,也包括氣候、物產,從而形成的語言、習俗、宗教和審美趣味。之所以有歐洲、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各色人種,那都是地理不同形成的,中國有某某地方出美女,某某地方出文官武將,那都是地理不同形成的。海邊的人長得有魚的形象,山區的人長得有羊的形象,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陜西的蔥半尺高,山東的蔥二尺高。大山里有各個溝岔,各個溝岔里都有動物,有的溝岔肥沃有森林,生長了老虎獅子一類的大動物,有的溝岔貧瘠干涸,生長了一些山羊羚牛,有的溝岔是梢林,擁集了大量的飛禽。我常想,歐洲人就像那些大動物,這些大動物多是獨來獨往,平日沉默,行為直接,但都有侵略性,掠食時極其兇猛。亞洲人都是小動物變的,中國人或許更像飛禽,喜歡聚堆,愛說話,吵雜聲不斷。但小動物因為小,要生存,就敏感,警覺,緊張,多疑,狡猾,而且身上有毒,能長毒刺,能噴毒液,使強用狠,顯得兇殘。
我當年為了修煉我的文學語言,曾把一些好聽的歌曲拿來分析為什么好聽,其音符怎樣搭配了形成怎樣的節奏了就好聽。我列成表格,標出線條。陜西北部和南部都有非常著名的民歌,分析了它們,結果發現,陜北民歌標出的線條和陜北的地貌形狀一模一樣。陜北民歌平緩、雄渾、蒼原,陜北是土溝土梁土峁,一個一個不長樹的山包連綿不絕。而陜南民歌節奏忽高忽低,尖銳高亢,陜南是秦嶺和大巴山,峰巒一個緊挨一個,直上直下。秦嶺的最高峰是太白山,我登過,在山腳松柏成林,常見有數人合抱粗的高達幾十米的,可到了山頂,那些松長了千年,卻是盆景那么大。我到過青海西藏,看那些神圣的山,為什么就神圣呢,是真的山上有神嗎,但它確實使山下的住民有過許多奇異的生活現象,但同時我也想,那么大的一座山,一半插入云中,長年積雪覆蓋,它肯定影響氣候,氣候的變化必然會使許多奇異的發生。在我的家鄉,秦嶺深處,小盆地被山層層包圍,以前偏僻封閉,巫的氛圍特別濃,可以說我小時候就生活在巫的環境里,那里人信儒釋道,更信萬物有靈,什么神都敬,除了上廟進觀拜那些佛呀菩薩呀老君呀關公呀,還有龍王山神土地灶爺牛馬爺樹精狐仙,蛇蝎蜈蚣蟾蜍烏龜也都敬。村里經常鬧鬼,有各種精怪附上人體,村里沒有醫生,卻有陰陽師,有了病,治疼的方法很多,如火燎,鍋蓋,放血。那是在深山里,偏僻,霧氣大,人又稀少,所以才產生這些東西,我后來到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幾十年,就很少聽說鬧鬼。我在廟里問過一個和尚,因為他說他常在廟的院里見到鬼,都沒有頭,是些兇死鬼,來廟里求超度的,我問我能不能見到?他教我的辦法是晚上兩點后,坐在沒人的十字路口,腳面上蒙上草皮,頭頂塊草皮,在草皮上插上香,然后想著你要見死去的某個人,那鬼就來了。我沒有去做,我有害怕,更重要的是城市里根本尋不到沒有人的十字路口。
現在蓋房子,買房子,布置房子,都講究風水,風水最基本的常識,就是你感覺到舒服就是好風水。這如同蓋房子,蓋得周正,能向陽,能通風,這房子也堅固,你如果房子蓋得彎彎扭扭,就向不了陽通不了風,當然也不會堅固。人也是這樣,某個人長得漂亮,此人肯定性情陽光,很聰明,也長壽。長得丑陋,不是蠢笨,就是心理容易扭曲,身體也不健康。但為什么常是漂亮人成不了大事,而往往丑陋人能成大事,其實是漂亮人受干擾的多,因為聰明,什么都一學就會卻不堅持深究,丑陋人或性格偏執或經歷坎坷,反倒他堅韌不拔。風水還有一部分是心理作用,比如,你一旦覺得家里某個地方沒有布置好,心里老糾結,那你就一定得去重新布置。我琢磨過我家鄉的那個陰陽先生,村里婚喪嫁娶,蓋房安灶,都要他選方位擇日期,常常是按他的意見辦了就平安吉祥,沒按他的意見辦,就出事。他沒有多少文化,對易經呀堪輿呀并不怎么懂。我想,他幾十年從事這樣的職業,或許就有了神氣,他這樣認為,身上就有了煞氣。廟里的佛像是人塑的,一旦塑成,塑佛就得跪下磕頭。從事某一種職業久了,這個職業就影響了從業者的氣質,甚至相貌。當然,文學作品也講風水,這就是結構完整不完整,情節安排得合理不合理,是一般性的正,還是正中有奇,奇中有正;是一般性的平衡,還是亂中有序,險中求穩。再是它的基調,它的硬軟度,它的色彩聲響和味道。所有這一切,就構成了一本書的命運。人是有命運的,書也是有命運的。
地理在文學中似乎是一般問題,其實可以說它是作品的基點和定位。這如同你一旦系上了一條什么樣的褲帶,那么你就配上什么樣的褲子,有了什么樣的褲子,就有了相應的襪子、鞋子、上衣、帽子,以及你背的包,坐的車,要去的地方,要見的什么人,說的什么話。我們常說這部作品有特點,有味道,至于什么特點什么味道,這都首先從作品中的地理開始的。我們讀拉丁美洲的文學是一種味道,讀俄羅斯的文學是一種味道,讀日本的文學又是另一種味道,讀中國古典作品,《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金瓶梅》各是各不同。尤其戲曲,梆子戲和越劇黃梅戲不同,同是梆子戲類,秦腔和晉劇,評劇又不一樣。過去的各個省會都是不一樣的,不說它的物產,語言,習俗,單就建筑都不同,而現在可惜的都在趨同化,這個城市與那個城市差不多了,年輕人又都說普通話,你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好象還在你生活的地方。因此,我們現在的一些作品,就越來越失去原創性,失去獨特性。
我在初學寫作的時候,寫作的欲望強,見什么都新鮮,聽什么都好奇,就拿來寫,跟著風胡寫,就象一只蝌蚪,跟著魚游,游呀游,魚還是魚,我的尾巴卻掉了,游不動了,成了一只青蛙。當初還很得意我寫了一大堆作品呀,一整理,是那么淺薄,無聊,可笑,是一大堆的文字垃圾。我就覺得我這是文學上的流寇,我得寫我最熟悉的,我沒有文學根據地,就回到了我的家鄉,先后三次,一個縣一個縣走,一個村鎮一個村鎮地走。從此就以我的家鄉商州為我的文學根基,開始了我的鄉土寫作。也體會到一個人,無論干什么,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角色和現狀,不了解就不可能自由,就不可能駕馭自己,就變成社會的思潮中別人左右自己的那種力量的奴隸或玩物。
除了八十年代我三次大規模走商州外,每年又多次回去,作品都寫的是故鄉的人和事。在我的理解中,故鄉是什么,是你的血地,是你身體和靈魂的地脈。那時,我的父母還在,故鄉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以父母存在而存在。在那時的返回,不僅是為了文學,更是為了生命和靈魂的安妥,它的意義就和一般的采風不一樣。這如同你因干別的事餓了一天肚子的饑和家里沒有糧食吃了上頓還不知下頓的饑是兩回事。
我的故鄉商州,在秦嶺深處,在商於古道旁。陜西的關中原是八百路,商於古道是長安城通往東南的唯一之路,是六百里。戰國時代,它是秦楚交匯地,秦強了我們屬秦地,楚強了我們屬楚地,號稱是秦頭楚尾,文化上有中原之雄沉渾壯和楚的綺麗鐘靈。我們的那個鎮是古驛站,歷史上的韓愈、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蘇軾等等都曾居住過,留下詩文。宋元之后,長安遷都,這地方逐漸荒蕪,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這里仍是山高林深,交通不便,封閉落后,淪為國人很難知曉的地方。我寫商州的時候,那里還叫商洛,商州是商洛在古時的稱謂,連大多商洛人也不知道商洛還曾經叫做商州。現在商州的名聲是大了,商洛市所在地也改名為商州。對于商州,這四五十年里,什么都在變,社會體制在變,由政治革命到經濟建設,山水在變,或山青水綠或殘山剩水,但有一點始終沒變,那就是人的感情。那里太熟悉了,無論那里發生了什么,我稍一知道,就能明白事情的根源是什么,會有什么樣的過程和結局。我說過這樣的話:我是站在西安的角度上回望商州,也更了解商州,而又站在商州的角度上觀察中國,認識中國。
我寫作品,有這樣的習慣,就是在醞釀構思時,腦子里首先有個人物原型為基礎,哪怕這個人物是我從眾人的身上集中起來的,也必須先附在某一個人的身上,以他為基礎。再是以我熟知的一個具體地理作為故事的環境,比如一個村子,這村子的方位,形狀,房舍的結構,巷道的排列,誰住哪個院落,哪里有一棵樹,哪里是寺廟和戲樓,哪里有水井和石磨。這兩點先確定下來,就如蓋房子打下地樁,寫起來就不至于游移、模糊。然后寫起來了,再根據內容需要刪增、取舍、夸張、變異、象征、暗喻,才創造出一個第二自然,經營出一個文學世界。每一個作家創作時,人物可能是集中融匯的,故事可能是無中生有的,但地理環境卻一定是真實的,起碼是他熟知,在一處扎住,進行擴展、改造的。從真的自然所提供的素材里創造出另一自然來,大自然的素材被改造為完全不同的東西,優越于自然的東西。對于我本人,我作品中的地理,則是非常真實的。我之所以喜歡這樣,我想讓我的作品增加一種真實感、可信感,尤其當我以所寫的人物和故事指向了多義,表達出我的意象時,越是地理環境上我越要真實。這就是我一向都在提的以實寫虛。
真實的地理是創作的一個基本規律,它的好處是寫時不至于游離,故事如孤魂野鬼它得有個依附處,寫出來的作品,能讓讀者相信,而進入它的故事中,但是,這樣也常常帶來麻煩,尤其給作者本人。我在這方面吃過苦頭。80年代我走商州后寫了《商州初錄》,文學界評價還非常好,但因縣鄉是真名真地理,村鎮是真名真地理,當地人就對號入座,其中寫到落后的東西,那時政治解讀的氣氛濃,就指責我誣蔑農民,把農民的垢甲搓下來讓農民看,結果商洛地區宣傳部組織了批判會,寫了材料上告省委宣傳部,上告中國作協和發表此作的《鐘山》雜志。寫了《廢都》,對號入座的更多,有人控告我,就在前年一個還見了我罵我,我說我沒寫你,他說明明在寫我,連我家那條街那條巷那個寺廟你都寫得真真切切,你不是寫我?寫《秦腔》后,我不愿把書給老家人看,擔心被攻擊,一度不敢回去,后來他們還是看了,沒引起什么風波,我這才回去了。
由此,我得到一個問題,紅學家考證《紅樓夢》,考證地理是對的,而對于故事人物,連同一些細節也考證,這就覺得不對了。小說中的情節,人物,那是經不起考證的,一考證就錯了。可見這些人自己沒有寫過小說。現在許多人在電視上講歷史,引用的材料來自《史記》《漢書》《資治通鑒》或一些志書,這還是可以的,而有的從文學作品上找,就不靠譜了。
說到這里,我還要強調的是,講地理與文學,文學中的地理,并不是寫地方志。地理一旦寫進了文學,它就融入其中,不再獨立存在,或者說它就失去本身意義。寫所見的世界,并不是你所見的世界,而是體驗的世界。塑佛像時用鐵用石用木用泥,一旦塑成就是佛了,再也沒了它是什么鐵什么木什么泥了。我們在說地理對于文學的地方性、個人性的重要時,如果在一部作品中所要求分析的地方的、個人的習癖愈多,這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可能竟會愈少,一部作品應高高超越個人生活領域,他不是一個賦有地方性和尋求個人目的的人,他應該是一個更高層次的“人”,一個“集體的人”,傳遞著整個人類潛意識的心理生活。
我在九十年代寫過一個文章,說:云層上邊盡是陽光。意思是,民族有各個民族,地方有各個地方,我們在重視民族和區域時,一定要知道任何民族、區域的宗教,哲學,美學在最高境界是相同的,這如同我們坐飛機,穿過了各種各樣的云層后,云層上面竟然是一派陽光。這就需要我們在敘述你這個民族你這個地方的故事時,也就是說當你看到你頭上的那朵云時,你一定要想到云層上邊都是陽光,陽光是統一的,只有云朵是各式各樣。人類在認識上,感情上有共通性。任何文學和藝術不是麻痹思想的娛樂消遣,它是人類精神世界向未知領域突進的先聲,是人類中最敏感的一小部分人最敏感的活動。舉個例子,當你坐一輛旅游車,中午十二點時你讓司機停車說肚子餓了去吃飯,大家這時肚子都餓了,你的提議大家都同意,如果你十點鐘要停車吃飯,那只是你個人餓了,得不到大家的同感。文學是你一個人寫的故事,你的故事在寫一個人的命運,而這個人的命運和這個社會,時代的命運有了交集重合點,你就不是你一個人,是集體的人,你的命運就不是你的,是社會的時代的,那么,這個故事就偉大了。
所以說我們講地理與文學,僅只是講地理在文學中的重要,還都屬于基本的東西。寫什么取決于你的膽識和見解,怎么寫取決于你的智慧和技巧。從整體上說,作品取決于作者的能量和品格,取決于文學背后的聲音和靈魂。
賈平凹: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一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