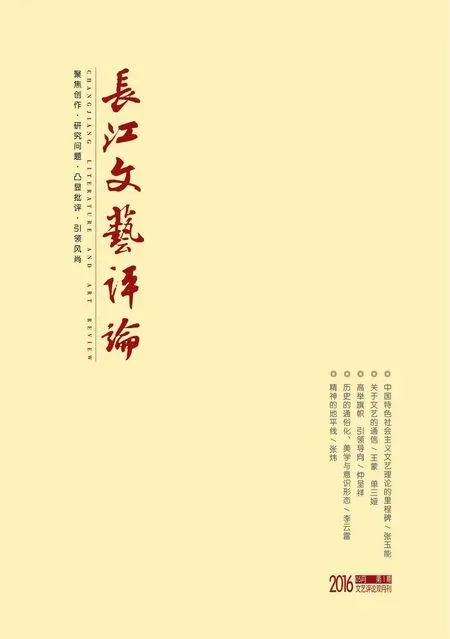我選擇那條少人走的路
——我的文學批評觀
◎ 楊光祖
我選擇那條少人走的路
——我的文學批評觀
◎ 楊光祖
楊光祖,男,漢族,1969年生,甘肅通渭人,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評委、甘肅省領軍人才、甘肅省文化宣傳系統“四個一批”人才、甘肅省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中組部“西部之光”訪問學者、魯迅文學院第五屆高級研討班(全國中青年文學理論評論家班)學員。現任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當代文藝評論中心主任,教授、碩士生導師。
1990年開始文學創作,已發表散文等各類文學作品百余篇,有多篇散文多次入選全國年度散文選。從2003年起主要從事當代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已經在《人民日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文學評論200多篇。有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等轉載、收錄。出版專著四部:《西部文學論稿》《守候文學之門——當代文學批判》《楊光祖集》《回到文學現場》。曾榮獲甘肅敦煌文藝獎一等獎、甘肅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甘肅首屆黃河文學獎文學評論一等獎。
一
2013年8月的某一天,我們大學畢業20年后重回母校,在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會議室里,面對著趙逵夫等幾位當年的老師,我作為班長發言,其中我說到了一句話,大家都笑了。這句話是:想當年,我瞧不起搞現當代文學的人,我覺得那里面沒有學問,可光陰流轉,如今的我已經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10年了。
世事滄桑,造化弄人,大學時代的我是以“楊古典”而馳名全班,教授《古代漢語》的甄繼祥老師在課堂上公開說,讀書當如楊光祖,還把這句話寫到黑板上,并說,我可以不上《古代漢語》。我感謝甄老師的厚愛,但課還是一直在聽。
那時候的我,最喜歡的是古代漢語、唐宋文學,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是每期必讀的。大學時期撰寫的幾篇作業畢業以后也都公開發表了。進入21世紀,當年教授我們唐代文學的楊曉靄老師,還幾次請我加入唐代文學研究會。但我只笑笑而已,我哪里還有那個資格?
大學畢業后,一直很迷茫,幾次想考研究生,但懶惰占了上風,無事可干,于是寫散文,那幾年與詩人張哲交往,倒是發表了很多散文,大多都是報章體。如今看起來,也就是作文而已,學生腔太濃,羞于提起。我真正的散文創作是2007年以后了,這里暫且不提。
寫了幾年散文,也還是感覺很無聊。1998年,當時在慶陽工作的馬步升到省委黨校培訓。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了他的散文集《一個人的邊界》,非常喜歡,那種粗野、恣肆、洋洋灑灑、大氣磅礴懾服了我。于是,主動跑到他的房間,認識了他,并為他寫了幾篇小評論。未料從此就走上了文學評論之路。
其實,我的骨子里,更喜歡古典文學、書畫藝術,亦喜歡哲學,雖然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差,但那種喜歡是壓不住的。2000年和2012年前后兩次跑到北京大學、中央黨校進修、訪學,名義上在中文系,其實每天都在哲學系聽課,主要是聽西方哲學。我感謝北京大學西哲老師,比如陳嘉映、靳希平、趙敦華等老師,他們的演講、課程,給了我人生旅途中極其深厚的喜悅。而在書畫一途,研習多年,每每感覺到一種幸福,陳傳席、梅墨生兩位先生惠我甚多,我的朋友楊海燕在書法領域造詣很深,朝夕相談,受益匪淺。
因為有了這樣的知識視野、藝術興趣,反過來看現當代文學,尤其當代文學,有時候,就很有一種不滿足。現當代文學領域,我最佩服魯迅先生,他的道德文章,他的文字功夫、思想境界,至今無人企及。在我眼里,當代文學還無法與現代文學相比。我說過,文學不是拔河,哪邊人多,哪邊就贏了。當代文學就小說而言還無人能夠超越魯迅,散文方面還無人可以超越周氏兄弟,你就不能說你超過了現代。當然,我對那些在文學領域默默耕耘的作家抱以真摯的敬意。
從事文學評論也近十載,但說實話,快樂著,并痛苦著,無聊著。有時候,也會問自己,什么是文學,什么是好的作品?我也不知道。面對一部作品,我沒有理論,或者說,不用所謂的理論生搬硬套,我只是用我的心去感知,去體悟,然后把這種感知、體悟形成文字。我不是那種可以面對任何文本而洋洋灑灑寫萬字長評的人,我只對感動了我的作品才有話可說。但這并不說明,我不喜歡理論,我每天讀理論書的時間更多。
我深知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艱難和危險,如果你還想說真話,按你內心的真實感覺去說。所以,從我出道以來,我很少主動為認識的作家寫什么文字,馬步升是一個例外。也很少通過我評論的作家去發表文章。我不愿意那樣做,覺得很丟人,甚至可恥。我評論的很多作家,我至今還不認識,從來沒有見面,即便偶爾碰面了,我也裝作不認識,從不談及這個問題。有時參加全國文學會議,我也不會跑到他們的房間,說,我給你寫過評論。一個評論家也有一個評論家的尊嚴和自由。2007年在北京開全國青創會,紅柯正好坐在我的旁邊,而我剛好在《文藝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嚴厲地批評了紅柯的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我剛一落座,略有尷尬,不料他主動說,你的文章我看了。我說,不好意思。他說,沒關系,你能主動去買我的書,并認真讀完,然后撰寫那么一篇文章,我很感謝,這才是真正的讀者。
可是,這樣優秀的作家在當下的中國并不是很多。有些作家邀你寫他的評論,你拒絕幾次,人家仍然堅持,你就不好意思再推辭,于是,你就寫了。結果,人家看了,很不高興,嫌批評太多。其實,因為都是熟人,你已經很客氣了,批評也藏得很深。但人家還是不高興,于是約去的稿子就沒有了下文。有些一開始就告訴你,你馬上寫,一周交稿,某大刊下月要出,于是,你什么都扔下了,寫完了,人家說,你還是不懂我的作品,于是,也沒有了下文。后來,你遇見那個大刊的編輯,人家說,嘿,根本沒有這個事。
有些作家希望評論家評論他們的作品,也比較喜歡看你把某某批評得體無完膚,但當你批評到他的時候,他就無法容忍了,而且你還只是勸百諷一。這些作家最拿手的武器就是:你沒有讀懂我的作品。聰明一些的會稍微改變一下語意:你批評的是我以前的作品,我某某年之后的作品已經沒有這些缺點了。其實,你批評的正好是他某某年之后的作品。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告訴我,我的作品你讀得太少了。我就問他,你有多少作品?他說,100篇左右。我就正告他,我最少看了你80篇。面對這樣的作家,作為評論家,你覺得很無奈,很可恥。因為這是對一位嚴肅的評論家的一種羞辱。他開始懷疑你工作的態度了。
我喜歡那種和你講理的作家。你說他的作品有什么問題,他可以與你講理,或者不理睬,也可以,各寫各的,評論家從來不是作家的附庸,或者奴才、丫鬟,要看作家的眼色行事。不要說“你沒有讀懂”,你可以說那些地方“你沒有讀懂”,簡單的謾罵或否定,都是一種不負責任。
二
當然,在評論的過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文學,怎么樣才算優秀的文學?并對文學批評本身也進行嚴厲的反思。評論家有自己的職業尊嚴,但也有自己的職業操守、職業底線。只有你嚴守底線,有尊嚴地進行批評,真正的作家才會尊重你,包括尊重你的工作。
馬克思說,資本在狂歡。隨著資本的大幅度進入許多領域,藝術也難免其災。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城市的崛起,中產階級的開始形成,大眾文化一枝獨秀,新媒體的迅速發展,傳統的時空秩序被打破,以往的經驗方式已經落伍了。
文學藝術,也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
什么是藝術?如何鑒賞和評價藝術?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大眾文化的時代,倘若以大眾的標準來衡量一部作品,那么,誰的讀者多,誰就是老大,或者說,誰的粉絲多,誰就最優秀。問題是,大眾靠得住嗎?藝術,也和政治一樣,人人都有一票嗎?民主的普選制,是否適用于文學藝術?如果以粉絲數量來評價,章太炎絕對不是于丹的對手。如今的中國,有幾個人能絲毫不費勁地閱讀和理解章太炎的著作?
另外一個問題,評論家評價一部作品以什么途徑,或者用什么武器?大家都認為評論家必須要庫存很多理論,然后憑借那些理論來評價作品。我們的批評家確實也是如此,區別只是有人只有一個理論,有人有幾種理論。但拿一套理論評價一部作品時,它的功效如何呢?以前我們用庸俗馬克思主義理論評析作品,使得讀者倒了胃口。現在很多人用海德格爾理論來評析作品,如果依然是庸俗的、不及物的,那么同樣倒人胃口。當評論文字只是滿足于從概念到概念,這種碰碰車式的概念游戲,又有什么意義?
多少年來,我們依靠“理論”進行文學“批評”,誤人誤己呀。我這樣說不是否定理論,理論很重要,但理論必須通過學習化為自己的血液,然后通過“直覺”表現出來。張愛玲在《私語》中說:“一切要讓人在切身體驗中發現它”,可謂至理名言。當代作家,還有批評家的最大問題,不是沒有理論,而是沒有感覺,沒有對文字的直覺。我經常說,文字必須要經過人的身體,成為一種生理的東西,沒有疼痛感的文字,是無生命的。當代中國,借來的理論太多了,可以說是理論過剩,甚至理論恐慌。但是,理論真正起作用,還必須與自己日常生命的存在性發生關聯,作為一名評論家,你必須對你使用的理論有感應,最好有一種浸潤。然后,用你自己的話說出來,而不要做那種吃力不討好的搬運工。我們很多學院派評論家做的就是西方理論的搬運工的工作。我雖然也經常閱讀西方理論,但我不屑于做搬運工,我總是力求用自己的理解,直接進入文本,跟著感覺走,而不是理論走。
我一直覺得審美直覺才是一個批評家最重要的素質,就是面對一個文本,你有沒有感覺,從心理到生理,有沒有觸動?不管是反感,或者感動,都必須要有。如果沒有一點感覺,只是生硬地搬用一些理論來言說,我覺得這樣的批評家非常恐怖。高爾泰在一次訪談中說:“批評家最主要的素質是審美素質。要求評論家必須有羅丹的技術才有資格評論羅丹的藝術,這樣的要求是荒謬的。”牟宗三認為中國的學問是生命的學問,“生命之學問,總賴真生命與真性情以契接。無真生命與性情,不獨生命之學問無意義,即任何學問亦開發不出也。”而“真生命與真性情”,也就是“存在之感受”。就文學批評而言,我喜歡做那種“創造性的批評”,我也努力做一名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我對瑞恰茲那種精密的、原則的,甚至科學的文學批評,不太感興趣。當然,我也知道這似乎是目前的趨勢,但我不愿走那條路。
本雅明認為“光韻”是古典藝術與現代藝術的標志,古典藝術是光韻的藝術,而現代藝術是復制藝術。“光韻”就是作家充盈和獨特的審美體驗內化于作品之中,此乃真正的藝術本性之所在。它是揮之不去的生命呼吸之馨香。本雅明最為看重的就是人與自然的神交階段的自然關系。他說:“藝術作品的機械復制時代凋謝的東西就是藝術品的光韻。”只要生命的原真性存在,生命之光韻才不會消失。而如今的藝術多的是人造的光環,光環與光韻之區別,是它更多的在文本之外,比如藝術家的頭銜、名聲、地位等等。
現代藝術中光韻的日漸減少,主要原因是現代藝術生產的制作與復制技術的發展。而時代的巨變,也結構性地改變了人,大多數讀者、觀眾已經無法看到古典作品中的光韻了。朱寧嘉說:“現代藝術培養起來的接受者,由于影像的連續刺激,更多時候對藝術的欣賞采用的是反射性感知,即本雅明概括的渙散消遣式,因而,往往感受不到存在于藝術中的靈韻,尤其是古代藝術中的靈韻。”“現代藝術培養起來的感知方式,不只讓人無法感受傳統藝術中的光韻,往往也致使人們與現代藝術中潛藏的靈韻擦肩而過。”以本雅明的這個理論看待中國當代文學,也是極其中肯。當代文學,尤其那些走市場的,只是技術品而已。那里可能最多就只有復制了,光韻之類,真的是很難看見了。
數字時代的到來,網絡閱讀、電腦閱讀、iPad閱讀、手機閱讀的迅速普及,3D、4D、5D電影(影院),尤其7D電影(影院)的誕生,直接將電影與游戲結合,還有微博、微信成為人類日常化生活,都不斷地加劇了淺閱讀的步伐,和視覺娛樂的發展,原來那種帶神性的深度閱讀,人與神合一的體驗完全消失了。已經很少有人有耐心去認真地閱讀古典作品,尤其那些大部頭的著作了。他們連讀一首短詩的時間、精力、感覺都沒有了。現代藝術日益成為一種可制作的快餐藝術。
在這個大眾文化盛行的時代,藝術迅速淪落為商品,“文人,一如依賴華美的衣著裝扮而可以更好出賣自己肉體的妓女,以美的幌子向人們出賣靈魂并兜售虛假的幸福。”(朱寧嘉:《藝術與救贖——本雅明藝術理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那些生產者的作家也是如此,他們被資本綁架,以碼洋為評價標準。在這樣的文學氛圍中,作家如果還要試圖保留批判立場,那將是一個很不好的結局,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商品化社會機制。
在這樣的時代,從事文學藝術的評論,就是一種冒險,也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作。對于評論家來說,有時候真不是一種快樂的審美體驗。
三
古人說,天地人神。可是我們遠離天地太久了!一個文化人如果一不知天命,二不接地氣,那他的文字就只能是溫室中的花,好看而不中用,根本經不起風霜的打擊。我一直在批評學院派的所謂文學論文,有某知名學者撰文批評我,說我因為沒有受過嚴格的學院訓練,因此才仇視學院派。其實,我也在高校從事教學工作,我也是一名教授。我只是對文學過分學科化、技術化、工匠化看不慣而已,并沒有仇視。我以為文學更多的是人類的一種生存方式,一種存在狀態,孔子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我覺得是很好的。詩人阿信說:“我擔心會讓那些神靈感到不安。它們就藏在每一個詞的后面。”
我們現在的學院派由于學科體制的需要,在所謂學術的名義下,屠宰文學,摧殘文學,使得我們的學生越來越不知道文學為何物。閱讀他們的文學論文,滿篇是后現代名詞,到處是德里達、海德格爾,其實,他們對這些扎根于西方文化厚土的大師了解多少真需要質疑。這種教條主義的態度,與當年毛澤東批評的黨八股,“言必稱希臘”,并沒有多少差距。中國的文化創新、中國的文學創作,還是要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厚土里,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魯迅說,從文學概論里走不出作家。我認為也走不出優秀的文學批評家。一名文學批評家,他們必須把根扎到民族的大地去,一個與本民族的文化聯接最緊密的人,才能知道它的疼與愛,才能與它生命相關。我們必須向別的民族、國家學習,這種學習也不能限制在幾個名詞上,而是要觸到他們文化的生命線上。
在10多年的文學評論實踐中,我也積累了不少的個人體驗。新世紀以來,是文學評論日益學院化、技術化的時期,文學評論文體日益規范化,或者日益課題化,語言日益教條化。但我一直在抵制這個傾向,我頑固地認為文學評論必須首先是美文,而且必須與你所評的作品息息相關。我們有些學院派的文學評論,其實把文章中的作品換一個別的作品都依然可以說得通。王朝聞說,一個美學家必須掌握一門藝術,這樣才能深入美學的堂奧。從事文學評論的人,從事一下文學實踐對于體悟作品的細微之處,非常有好處,因為道心惟微,藝術的奧妙就在它的微細之處。我個人本來最早就是寫散文的,前后發表了200余篇。后來從事文學評論,散文的寫作就很少了,但依然在堅持。近幾年,已經在《華夏散文》《西湖》《雨花》《作品》《延河》《書屋》《海燕》《飛天》《黃河文學》等雜志發表了幾十篇,并被圈內朋友所認可,多次入選全國散文年選,和各種散文選本。就我個人來說,對我的部分散文我還是很珍愛的。
很多人說我的評論與眾不同,一是隨筆化,二是太刻薄。我寫評論文字,總是盡量散文化、美文化,而不愿意太學術化,干巴巴地讓讀者為難。至于批評我為文太刻薄,缺乏對作家的同情之了解,我一直不十分認同。年初,美國的一位朋友陳瑞琳女士,也是一個優秀的作家、評論家,她看了我的那篇關于西北中短篇小說的文章,給我發來一個短信:“你這文章能發表,那編輯真是開了宏恩!你手上那把刀子總是扎到作者的痛處,作者叫痛,編輯也不好受,我讀著都心驚肉跳。”看了之后,我才第一次認真地反思,難道我的文章真得這樣厲害嗎?最近幾年,我在西北文學方面下力甚多,尤其陜西文學,當然主要以批評為主,包括對賈平凹、陳忠實老師.我一直奉守“我尊重,我苛求”的宗旨,我認為對自己喜歡的作家,進行廉價的吹捧,是一種褻瀆。古人說,“恒稱其君之惡者為忠臣”,我愿意做一個如此的批評者。
我曾經在《南方文壇》2012年5期的“今日批評家”發表短文《我的批評觀》,其中說:
文學批評,是批評家與作家的靈魂交流。面對優秀的杰作,心有靈犀,拈花微笑,那當然是最高境界。但面對一些粗制濫造之作,或者反人性、反人類,價值觀錯位,低俗無聊之作,也需要當頭一棒,禪宗所謂棒喝是也。不過,肯定,或批評,文學批評家都是必須用“心”的,不能胡來,成為圈子批評、哥們批評,或者批評棍子,也不能將文學批評僅作為一種工具,一種謀生的工具。新世紀以來,學院批評的崛起,在強化文學批評理論性的同時,也降低了批評的尺度。學院式批評的最大特點,就是用西方人的一兩個“理論”寫一本書,或一篇論文,但其實與文學文本沒有關系,是一種不及物批評。
當學院派用一套一套的所謂理論“研究”那些文學作品時,“文學”就不存在了,在他們那里“文學”早成為了“尸體”。他們指手畫腳,說這是“后現代”,這是“后殖民”,這是“新歷史主義”,云云,很喜歡分類。這種“文學批評”至少產生兩個結果:一、只有“理論”,所謂“文本”隨便換一個都無所謂的;二、沒有“文學”,也沒有“批評”。利維斯說,所謂批評,就是一種差別意識。但在學院派批評家眼里,所有的文本都是一樣的,沒有什么差別。這種文學批評,其實更像是把“文學”當做了他們馳騁“理論”的“資料”而已。
在那篇文章最后,我還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批評者往往是非常合格的讀者,也是作家真正的知音。作為一位批評家,對那些聲明赫赫的中青年作家,尤其要有一種批評意識。這是對他們的尊重,對他們的致敬。”
美國文學理論家海澄·懷特說,文學在西方被認為是高級文化,或者說是高級文化的最直接的表現。因為文學代表著文化。所以文學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對文化未來的爭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從事文學評論也是一項非常愉快,而且充滿冒險、懸念的工作。我喜歡它。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有一首名詩《未選擇的道路》,他說:
樹林中岔開兩條路,而我——
我選擇那條少人走的,
而這已造成重大差別。
楊光祖: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