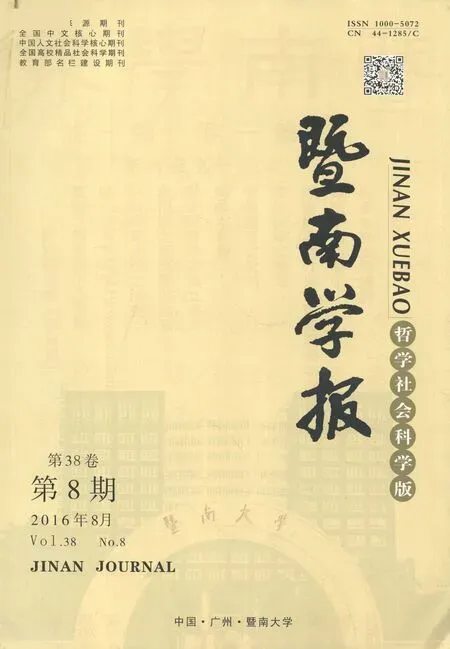一元股東權利配置的內在缺陷與變革思路
汪青松
(西南政法大學 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
一元股東權利配置的內在缺陷與變革思路
汪青松
(西南政法大學 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
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制度以一系列強制性規范為主體,形成了實質上的法定一元化配置模式,相應的股份類型也僅表現為單一的普通股。這種股東權利配置模式的邏輯基礎包括抽象資本層面的股份平等、股東同質化假定、基于兩權分離的代理理論以及股東權利結構完整性原則。但法定的一元化配置模式也存在著諸多內在缺陷,諸如股東權利配置無法體現公司自治理念、單一股份類型無法滿足股東異質偏好、股東權利行使結果與平等初衷相背離以及中小股東權益保護源頭機制的缺失。因此,推動股東權利配置模式從一元走向多元應該成為中國公司法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內容。
股東權利;股份公司;類別股份;公司自治
一、引 言
中國《公司法》通過一系列強制性規范確立了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的一元化模式,即每一股份所附隨的權利都是與其所對應的資本成比例的、無差異的。從形式上說,這種法定的一元化股東權利配置模式符合平等原則的基本要義,也與公司法保護股東權益的制度目標高度契合。但這一表象卻與兩方面的客觀現實不符:其一,一元化股東權利配置模式下的中小股東權益實現與保護的狀況并不盡如人意,中國上市公司的分紅情況就是最好的例證;其二,全球范圍內的公司法變革浪潮正在不斷拓展股東權利配置的自治空間,域外市場實踐中股份類別的現實樣態豐富多彩。制度表象與客觀現實的鮮明反差應當引發我們對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模式的反思。本文正是沿著這一反思路徑,首先對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模式的制度框架與邏輯基礎進行簡要梳理與闡釋,進而著重分析一元化股東權利配置模式所存在的主要缺陷,最后提出推動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模式從一元走向多元的制度變革思路。
二、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的制度框架與邏輯基礎
中國《公司法》2005年的修訂在去規制化方面作出重大的努力,也明確表示要為股份公司創制多種類別的股份提供制度支持。但相應的配套制度時至今日仍沒有出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公司法中一系列的強制性規范對股份公司的股東權利配置形成剛性約束。因此,中國股份公司的股東權利配置制度實質上仍屬于典型的法定一元化模式,相應的股份類型也僅表現為單一的普通股。①目前僅有少數公司依據中國證監會2014年3月21日發布的《優先股試點管理辦法》開展了優先股的試點。當然,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和公司法理能夠為這種法定一元化模式提供相應的邏輯基礎。
(一)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一元化配置模式的制度框架
首先,公司法總則中確立了股東權利構造法定化的基本原則。《公司法》第4條關于股東權利的總括性規定實際上包含著以下幾點內涵:其一,股東所享有的權利是由法律規定,而非章程約定;其二,股東所享有的權利應當是無差異的,或者說僅有與出資相對應的量的區別,而無質的不同;其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應當是每一股東都享有的基本股東權,不能夠通過章程或其他方式予以限制或取消。
其次,公司法對于股東權利中的參與性權利與經濟性權利的配置采取的是以出資為基礎的比例性原則。《公司法》第98條首先規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由全體股東組成”;隨后在103條規定“股東出席股東大會會議,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決權”;《公司法》第166條第四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該規定雖然賦予了公司章程對于紅利分配方面的自治空間,但對于能否通過章程規定不按同一順序進行分配的問題則未置可否。另外,《公司法》第186條第二款規定股份公司清算后的剩余財產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并沒有賦予公司章程另行規定的自治權。
再次,公司法對于股東權利中的處分性權利作出一定的限制。在這些限制性規定中,一些是針對具有特定身份的持股者在一定期限內轉讓股份權利的限制,如中國《公司法》第141條就對發起人、董事、監事和高管人員持股的轉讓作出限制。這種限制具有較為充分的正當性基礎。本文所要重點關注的是關于公司回購股份的限制。《公司法》第142條規定,除少數幾種法律明確列示的情形之外,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股份。這一禁止性規定使得股份公司無法在股份發行之初就對其附加上回購條款。換言之,《公司法》沒有賦予股份公司對其股份持有者的處分權進行章程限制或者說約定限制的自由。
最后,公司法為股東權利的多元化配置預留了制度空間,但缺乏具體的引導性規則。《公司法》第131條規定:“國務院可以對公司發行本法規定以外的其他種類的股份,另行作出規定。”但除證監會的《優先股試點管理辦法》外,國務院至今尚未正式制定頒布股份公司發行類別股份的具體規則。同時,“一股一表決權”“按出資比例分配剩余財產”等強制性規定也對類別股份的發行構成障礙。
值得說明的是,公司法在具體股東權利的行使上對于中小股東的弱勢地位給予了一定程度的矯正。例如,《公司法》第105條規定的累積投票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小股東將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推選進董事會、監事會的可能性。但由于該制度并非強制實施,因此其積極功能的發揮受到較大的制約。同時,對于大型公眾公司中持股比例極小的眾多公眾股東而言,即使采取累積投票制,其投票對于選舉結果也幾乎不會產生實質影響。另外,《公司法》第106條也規定了股東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東大會會議和在授權范圍內行使表決權,從而為中小股東分散表決權的集中行使提供了可能。但實踐中,表決權征集和代理往往是作為大股東或管理者進行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工具。
(二)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一元化配置模式的邏輯基礎
1.抽象資本層面的股份平等
梁彗星先生曾明確指出,平等性和互換性構成了近代民法制度和理論的基石,民事主體在平等性上的不足將會因互換性的存在而得到彌補。②梁彗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20世紀民法回顧》,梁彗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34頁。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在分配利益和負擔的語境中可以有兩種意義上的平等對待:一種是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這種平等對待要求將每一個人都視為“同樣的人”,要使每一個參與分配的人都能夠在利益或負擔方面分得平等的“份額”,因此要盡可能地避免對人群加以分類。另一種是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這種平等對待要求按照一定的標準對人群進行分類,只有被歸入同一類別或范疇的人才應當得到平等的“份額”。①王軼:《民法價值判斷問題的實體性論證規則——以中國民法學的學術實踐為背景》,《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傳統民法中的強式平等原則在公司法中的最集中體現就是股份平等原則,或者謂之股權平等原則。由于這一原則在公司法律制度中具有相當于首要原則的重要功能,因此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司立法一般都直接或者間接地承認該原則。在德國舊的《商法典》關于股份公司的條文中,最初并未規定股權平等原則,但在1978年修改《股份法》時增列了第53a條,明文規定了股權平等原則。②1993年修訂的德國《股份公司法》第53a的表述為:“股東在同等情境下應當被同等對待。”2010年12月的修訂沿用了這一表述。歐盟在其第2號公司法指令的第42條中也明確要求各成員國的法律應當確保處于相同地位的全體股東能夠獲得相同的對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1999年5月發表的《公司治理準則》(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的第2章中也非常明確地規定了股權平等待遇原則。中國1993年頒布實施的原《公司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股份平等或者股權平等原則,但卻設有不少體現了股權平等原則的條款,比如該法第130條第1款關于同股同權和同股同利的規定、第106條第1款關于一股一個表決權的規定等。股份平等原則在股東權利方面的具體體現主要集中于對公司收益、凈資產以及公司控制的比例性利益。③[韓]李哲松著,吳日煥譯:《韓國公司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頁。
2.股份公司股東同質化假定
傳統公司法理對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資合性”特質的強調實際上體現出對股東的一種“同質化”假定,即忽略股東之間的實然差異,而僅僅將他們視為無差異資本的載體。同樣,股東們所擁有的股權也是同質的,即可以“將公司的股權看作是被切開的餡餅。就餡餅而言,那些吃它的人可能得到的大小不同,但是每一塊的內容都應該具有相同的性質。……就股份而言,這意味著與企業的財富有關的一套相同的權利。”④[加]布萊恩R.柴芬斯著,林華偉、魏旻譯:《公司法:理論、結構和運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09頁。股東“同質化”假定下的股份公司內部權力分配的一個核心原則就是“一股一票”原則。按照傳統的公司理論,股東有權控制公司,因為他們擁有公司剩余索取權,所以股東對最大化公司剩余利益有著同質的需求。而“一股一票”原則無疑是將股東的“同質性”偏好集合成公司集體偏好的最佳方式。每一股東就每一股擁有一票,如此一來所有股東就擁有了與他們的剩余利益相當的投票權,這將為所有股東提供適當的激勵去參與公司事務。
3.基于兩權分離的代理理論
經濟學所關注的代理問題產生于下述兩種情形:當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期望或目標沖突時;當委托人難以證實代理人實際在做什么或者證實成本昂貴時。⑤Kathleen M.Eisenhardt,“Agency Theory:An Assessment and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14,1989,p.58.在代理理論的視野中,股份公司的股東是公司的唯一所有者和剩余索取權擁有者,⑥Michael C.Jensen&William H.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3,1976,pp.305-360.其基本特點是:股東不被要求在組織中擔當任何其他角色;它們的剩余索取權可以不受限制地讓與;允許在股東中不受限制地分擔風險。⑦Eugene F.Fama,Michael C.Jensen,“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Journal of Law&Economics,Vol.26,1983,pp.301-325.代理理論將股東定位為公司的所有者和剩余索取者的理念在傳統公司法理論和制度中也得到了明確的貫徹和體現。傳統公司法理論認為,作為股東出資的對價,股東應當享有從公司中獲得經濟利益和參與管理的權利。
4.股份權利結構完整性原則
立足于股權平等和股東同質化假定,傳統公司法理論進一步發展出了股份權利結構完整性原則,即在處理股權經濟性權利與參與性權利的關系時普遍采取了禁止分離的默示規則,該規則在傳統公司立法中一般被表述為“比例性原則”或“一股一票”原則。“比例性原則”被歐洲委員會界定為“所有與控制之間的均衡配置”。在這一語境下的“所有權”被限定為“現金流權利”。①關于該原則更為完整的定義可以參見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Group of Company Law Experts of 2002,該報告中指出:“最終的經濟風險與控制權之間的均衡性意味著股權資本擁有一種參與公司利潤或者清算剩余分配的不受限制的權利,并且只有這種股權資本能夠正常地附有與其所承擔的風險相均衡的控制權。”不過,在傳統公司法的體系下,股權權利禁止分離規則的內涵遠比“一股一票”或者“比例性原則”的字面所傳達的意思要豐富得多。首先,股權具體權利不得與成員資格相互分離。德國學者萊塞爾等在論及股份公司的成員權(即股東權)時也強調了“與成員權相關的各個權利的一個最重要的基本特征是,這些權利是不能與成員資格相分離的。”②[德]托馬斯·萊塞爾、呂迪格·法伊爾著,高旭軍等譯:《德國資合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04頁。其次,經濟性權利與參與性權利不得分離,特別是股權的經濟性權利與參與性權利不能相互分離而單獨轉讓。美國一些州的公司法明確禁止出售投票權。美國德拉華州1958年的Hall v.Isaacs一案就明確表示了公司法禁止股東在不同時轉讓其在公司剩余財產中的利益的情況下單獨出售其投票權。③Hall v.Isaacs,146 A.2d 602(Del.Ch.1958).美國《紐約州商業公司法》第609(e)條規定:非經本條以及本法第620條授權,股東不能為任何數目之金錢或者其他有價物而向任何人出售其投票權或者簽發投票權代理。伊斯特布魯克和費希爾從理論上將公司法關于股權的經濟性權利與參與性權利不得分離的規定概括為“投票權附隨于公司剩余利益”。④Frank H.Easterbrook&Daniel R.Fischel,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73.最后,股權經濟性權利與參與性權利實行比例性配置。
三、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一元化配置模式的內在缺陷
盡管傳統理論為股東權利一元化配置模式提供了形式上的邏輯合理性,但這種大一統的股東權利構造模式的實際運行效果并不盡如人意。以中國股份公司的現狀為例,許多家族公司面臨著外部融資需求與控制權保留的沖突困境;上市公司中享有投票權的中小股東普遍表現出“理性的冷漠”,分紅權也難以得到充分實現;立法所提供的股東權益救濟機制的保障作用也無法有效發揮。這些現實都充分折射出法定的一元化股東權利構造模式存在著諸多內在缺陷。
(一)股東權利配置無法體現公司自治理念
傳統代理理論認為公司可以通過契約實現自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將公司法律也作為一種契約看待的。但是,代理理論者自身所面對的解決代理人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的難題,以及隨后的理論研究者們所揭示出的人的有限理性、管理層機會主義、不完全契約理論、中小股東理性的冷漠、資本多數決原則下的多數暴政和訴訟救濟中的少數恐怖主義等一系列現實問題,都阻礙了契約化公司治理的優化目標的實現,這又使得公司治理不得不借助強制性法律規范來矯正。于是,保護股東利益以及克服市場失靈就成為公權力在公司治理領域大舉登堂入室的“通關文牒”,并借助其自身特有的自我膨脹能力不斷拓展其作用界域。這種結局應當是與代理理論者的初衷背道而馳的。傳統公司法的強規制化之表現可謂俯拾皆是,而關于股份類型的一元化安排也是公司法強制性的一個顯著表現。法律對公司內部關系的過度干預也必然大大減損公司章程在實現公司自治上的“憲章”性作用,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一種形式化的擺設。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公司缺乏合乎自身需要的獨特的股份類型設計,完全由立法統一打造的單一股份權利構造與公司自治理念相去甚遠。
(二)單一股份類型無法滿足股東的異質偏好
按照諾思的闡釋,在經濟社會中,“制度是為約束在謀求財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個人行為而制定的一組規章、依循程序和倫理道德行為準則”。制度的功能在于“提供人們在其中相互影響的框架,使協作和競爭的關系得以確定,從而構成一個社會特別是構成了一種經濟秩序。”①[美]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27—228頁。而就某一社會或者說某一種經濟秩序而言,制度并不應當是單一的和僵化的,而應當是多元的和靈動的。因此,法律在公司內部關系中的“大一統”努力往往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一廂情愿,它沒有充分考慮到公司各成員間的多樣化需求。這種單一的立法模式必然會引發制度供給不足。在中國公司法中,制度供給不足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因公司法未對股權內容的自治性配置予以明確規定而導致的股份制度供給不足。②任爾昕:《關于我國設置公司種類股的思考》,《中國法學》2010年第6期。這種一元化股東權利配置制度所引發的現實后果必然是:某些投資者所看重的某些權利因為保障不足而難以充分實現,另一些權利則因缺乏行使積極性而淪為虛設。
(三)股東權利行使結果與平等初衷相背離
在股東權利一元化配置模式下,每一股份所對應的權利是相等的,作為公司的出資者,中小股東與控制股東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一致的,他們都是公司的股東,都享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內容相同的股東權,包括自益權和共益權。但這種權利配置實際上在一開始就注定了中小股東在公司治理中的弱勢地位,特別是隨著公司資本基礎的擴大,股份日益分散化,小股東越來越遠離公司的最終控制權。股東地位強弱分野的不斷加深是有著其深刻的現實根源的。首先,股東之間在經濟實力上存在著不對等。特別是在大型公眾公司中,中小股東的經濟實力與其對應的控制股東的經濟實力往往是天壤之別的。其次,股東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信息不對稱。中小股東的信息弱勢不僅大大削弱了其參與公司事務、影響公司決策的共益權行使能力,也會使其在自益權受到侵害時面臨證據不足等種種維權難題。最后,股東之間向公司轉嫁成本的能力不同。小股東的先天弱勢加之控制股東的義務缺失極易導致公司實踐中的控制股東侵害中小股東權利的案件不斷發生,其對公司制度的負面影響甚至超過了傳統理論一直重點關注的兩權分離所引發的代理問題。有研究表明,全世界的大型公司核心的代理問題是限制控制股東對小股東的盤剝,而非限制不對股東負責的職業經理人王國的構建。③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 De Silanes&Andrei Shleifer,“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Paper,No.1840,1998.
(四)中小股東權益保護源頭機制的缺失
在由法律強制規定的一元化股東權利配置模式下,中小股東權益保護只能通過事中的權利行使和事后的補償性救濟,而無法在事先獲得更優的衡平性權利安排。從交易自由的角度來看,強行采用股東權利一元化配置直接制約了中小股東的選擇權,即中小股東在投資時僅能選擇出資與否,而無法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股東權利構造。這種形式上平等的初始權利安排使得中小股東不能在源頭通過更為合理的出資對價條款來強化自身的利益訴求與保護手段,加上公司運行過程中行使權利所面臨的諸多障礙和結果的不確定性,權益極易遭受損害。而中小股東利益一旦受損,就只能單純依靠立法提供的事后救濟,不僅要耗費大量精力,其結果也難以預料,即使僥幸成功,對中小股東利益的直接作用也極其有限。
四、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制度的變革思路
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制度的變革正在受到內外兩個方面力量的推動:一方面,現行股東權利配置制度的內在缺陷構成了推動變革的內在力量,中國公司立法亟須對現實需求作出回應;另一方面,全球公司法改革浪潮中所表現出的擴大股東權利配置的自治空間的趨同性特征構成了推動變革的外部力量,中國公司立法亟須對世界潮流作出回應。因此,推動股東權利配置模式從一元走向多元應該成為中國公司法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內容。
(一)推動公司法基本理念與原則的演進發展
首先,關于股東平等內涵的認知應當從資本層面向主體層面演進。法定的一元化股權配置模式所堅持的股份平等實質上只是一種資本層面的平等,而沒有關注到資本背后的出資主體在市場地位、信息獲取、權利行使等能力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異。立足于抽象資本層面的股份平等在兩個層面上易于對中小股東權益造成損害:一個層面是直接制約了中小股東的選擇權,即中小股東在投資時無法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股東權利構造;另一個層面是間接損害了中小股東的投票權和收益權,因為在“資本多數決”的股東大會決議規則下,不僅中小股東的投票權形同虛設,其收益權的實現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這種出發點“平等”、結果卻不平等的制度悖論在傳統的以比例性為原則的一元化股東權利配置的制度框架下無法得到有效解決。而主體層面的平等則體現了對主體之間差異的關注、對主體個性化需求的尊重、對結果平等的追求等實質平等的基本要義。
其次,關于股東投資目標的界定應當從同質化假定向異質化現實轉向。傳統公司法理借鑒理性“經濟人”假設而將投資收益最大化視為所有投資者的共同偏好,以此進一步推導出股東是同質的。但從現實層面看,股東之間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①George W.Dent Jr.,“The Essential Unity of Shareholders and the Myth of Investor Short-Termism”,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ol.35,2010,pp.105-111.而是多元的、異質的。股東作為主體的異質性對于公司立法所帶來的啟示是:公司立法在進行股東權利配置的制度設計時不能僅從資的視角將股東視為無差異資本的載體,而要從人的視角關注股東之間在穩定收益、強化控制、減小風險等方面的不同偏好。
再次,關于公司自治原則的解讀應當從治理層面向股東關系層面拓展。近年來,在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演進中,趨同的力量正在壓倒存續的力量并將最終戰勝后者。②孫光焰:《公司治理模式演進趨勢之爭的方法論檢視》,《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而趨同性所凸顯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不斷放松對公司的強制性管控、拓展其自治空間。中國《公司法》2005年的修改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一變革方向,特別是對于有限公司的內部關系安排大量采用了章定條款。③錢玉林:《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檢討》,《法學研究》2009年第2期。不過,該次修法在貫徹公司自治原則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突出表現在:一是關于股份公司的制度設計仍然是以強制性規范為主;二是關于公司自治的拓展主要體現在公司治理層面,對股東關系層面的延伸較為有限,特別是未能在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制度上真正構建起多元化體系。公司法下一步的變革應當將拓展股東關系層面的自治空間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允許公司與股東對作為出資對價的權利構造進行自主安排。通過這種自主安排,股東個性化的投資偏好將能在股東權利構造中得到更好體現,股東的投資收益不確定性風險將能夠通過事先的制度安排加以減輕。
最后,關于股東權利保護機制的設計應當從事后救濟為主轉向注重全程保護。現行公司法在形式上為股東權利的保護提供了一系列事中行使保障和事后救濟措施,但這些保障和救濟途徑的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有學者通過對中國上市公司的研究認為,盡管小股東保護被官方認為是證券市場規制的主要目標,但小股東在實踐中并沒有獲得很好的保護。影響障礙主要來自國有股的獨大、小股東利益在實踐中并沒有被置于優先位置、小股東的力量微弱、民事救濟的不充分以及獨立董事的功能缺陷。④Roman Tomasic and Neil Andrews,“Minority Shareholder Protection in China’s Top 100 Listed Companies”,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sian Law,Vol.9,2007,p.88.實際上,導致股東權利(主要是中小股東)保障不足的重要原因還在于權利的源頭配置的不合理,即立法沒有賦予股東對于適合自己的權利構造予以自主協商與選擇的權利。按照科斯定理,由于交易費用的客觀存在,不同的初始權利界定和分配,會帶來不同效益的資源配置,所以初始權利的合理配置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相比法定的一元股東權利配置模式,多元化配置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對股東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風險通過事先的安排加以減輕。只要法律確保這些安排在公司運營中能夠得到很好的履行,就能夠為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提供強有力的保護。這種保護力要遠遠勝過內涵較為模糊的信托義務體系和旨在間接保護股東利益的派生訴訟制度。
(二)推動公司股份類型制度供給方式的變革
在中國現行公司法體系下,單一的股東權利構造形成了以強制性規范為主體的股份類型供給方式,這種單純的法定供給方式已經明顯表現出與現實需求的不適應性。盡管所有法律都需要基于公共性維度來證成其自身的合法性,①熊偉:《法律合法性的公共之維——基于歷史類型的考察》,《河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但從客觀上說,與股東權利相關的法律制度的公共性并不意味著當然的普適性。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立法者不應當置契約自由于不顧而試圖促使公眾公司股權結構標準化,畢竟沒有哪一種模式能夠具有普適功能。②Caspar Rose,“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One Share-One Vote’controvers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closure and Governance,Vol.5,2008,pp.126-139.按照公司契約理論,公司是一種合同的聯結或者說是合同束。如果從投資者以其投資為對價獲得股東權利的角度看,將股東權利配置理解為一種契約是非常合理的。不過股東與公司之間的契約并不必須是單一的權利義務構造模式,因為股東的投資偏好與需求是異質的,因而股東權利配置也可以是多元的。實際上,即使在美國這樣“一股一權”原則曾占據重要地位的法域,權利構造各異的類別股份形態也極為豐富,關于公司創設不同種類股份的規定已經打破了稱謂、概念上的局限,促成了公司融資最大限度的靈活性與適應性。③于瑩、潘林:《優先股制度與創業企業——以美國風險投資為背景的研究》,《當代法學》2011年第4期。
關于公司立法,公司契約理論所表達的核心觀點是:公司法應該是開放式合同,在這種合同模式下,公司參與各方在利益驅動下可以對公司法進行增刪修改,在一定情況下甚至可以選擇“退出”公司法規則。④[美]伊斯特布魯克、費希爾著,張健偉、羅培新譯:《公司法的經濟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譯者序。因此,公司法的主要內容不應當是強制性的。強制性規范適用的邏輯基礎是所調整對象涉及第三方利益(包括社會公共利益)。但僅就公司內部關系、特別是股東之間的權利配置關系而言,幾乎不涉及股東之外的第三方利益。對于這些問題,利用強制性規范要求所有公司、所有股份遵循一個權利構造模式,既無正當性依據,也無現實必要。相對于股東而言,債權人在公司關系情境下似乎更需要強制性規則的保護,既然債權人都可以通過初始的契約條款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股東更應當擁有實現自己投資偏好的自由。換言之,股東權利不應當被視為公司法的創造物,而應當是公司參與方之間的契約的創造物,公司法所需要做的,除了嚴格限制的公平性評價之外,就是對這些契約安排予以確認和保護。因此,中國股份公司股份類型制度供給方式應當從單一的立法供給向立法供給與章程供給相結合的方式轉變。立法供給的主要任務是確定股份類型創制的原則、邊界與保護手段;章程供給的主要任務則是創制適合本公司情況和市場需求的具體股份類型與相應的權利構造。
(三)推動股東權利配置具體立法規范的變革
盡管股東權利的內容十分豐富,但最為基本的是三類權利,即以分紅權和剩余財產分配權為代表的經濟性權利、以表決權為代表的參與性權利以及處分性權利。域外公司立法與市場實踐的經驗表明,要推動股東權利構造走向多元化,相應的立法規范就需要在上述三類權利的制度設計上進行變革。
首先,將“一股一權”由強制性規范改為默示性規范,允許通過公司章程予以排除適用。通過這一變革,公司將能夠根據特定股東的需求而對表決權重新加以配置。盡管表決權被視為股東享有的最重要的權利,①張民安:《公司股東的表決權》,《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一股一權”也被視為股份平等的當然要義,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作為公司法的基礎制度安排,表決權規則的設計更應本著效率之理念進行。②羅培新:《公司法學研究的法律經濟學含義——以公司表決權規則為中心》,《法學研究》2006年第5期。實際上,在現代公司中,表決權基本上已成為爭奪控制權的基本工具,中小股東的表決權往往只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在控制權爭奪中其表決權的作用不能充分實現,其利益容易受到損害。在這種情況下,通過事后的表決權信托固然是為中小股東利益保護提供了一種較好的外部機制,③胡智強:《論表決權信托——以小股東利益保護為背景展開的研究》,《現代法學》2006年第4期。但表決權信托往往并不能直接實現和增進中小股東的實際利益。因此,在配置股權內容時提供多樣化的權利構造組合,允許中小股東以放棄表決權為對價而獲得經濟性權利的優先或增強,應當是一種更有效的保護機制;同樣,也應當允許有意加強對公司控制的股東用其經濟性權利或者對公司發展的特定貢獻來換取更多的參與性權利。
其次,對于經濟性權利的配置,明確允許公司章程在權利計量標準、權利行使順序等維度上作出差異化安排。現行公司法僅明確了股份公司章程可以規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紅利,在此基礎上,應當對《公司法》第166條和第186條作出修訂和完善,進一步明確公司章程可以規定在股東之間不按同一順序分紅、不按同一順序分配剩余財產。
再次,對于處分性權利的配置,明確允許公司章程在約定的基礎上作出附條件或附期限回購、限制轉讓等規定。除現行公司法所規定的法定回購情形外,應當允許公司發行可回購股份;也應當允許公司以股份作為激勵,在授予員工股份時附加一定的業績或者任職期限等限制處分條件。
最后,應當以行政法規形式盡快出臺股份公司發行類別股份的具體規范。出臺該規范的目標是為了變革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的單一模式,為股份公司直接進行股東權利多元化配置提供規范性路徑,促進“市場促生型類別股”的生成和良性發展。由于股東權利配置主要屬于公司自治范疇,相應的條文設計應當盡量減少強制性規范,多采用授權性規范和默示性規范。建構的重點包括股份公司股東權利差異化配置的自治邊界與基本原則,股份公司能夠發行的類別股份的范圍,以及各種類別股的法律界定、權利構造、權利行使、權利處分和權利保護等相關制度。
五、結 語
法律規制與公司自治的關系是公司法理論與實踐中一個亙古彌新的主題,也是公司法律制度演進變革的一條基本邏輯脈絡。二者的關系不應當被理解為相互排斥、相互替代,而應是相關補充、相互協調。當然,針對不同的公司關系情境,法律規制與公司自治的位次關系也應當有所不同。對于屬于公司內部關系范疇的股東權利配置,以公司自治作為制度供給的主要路徑已是全球公司法變革的共識。本文關于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模式的反思性研究期待著能為后續的理論研究和立法變革提供以下共識性結論:第一,股東權利的初始配置是一種議價締約的結果,而非法律賦權的產物;第二,擁有完整權利構造的普通股只是公司法供給的標準化契約,公司各相關方可以在協商的基礎上創制具有不同權利構造的類別股份;第三,中國股份公司股東權利配置的多元化變革應當以法律規范為引導,以市場創制為基礎。
[責任編輯 李晶晶 責任校對 王治國]
D922.291.91
A
1000-5072(2016)08-0064-08
2015-10-10
汪青松(1974—),男,安徽懷遠人,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從事民商法學研究。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經營者集中的附條件批準制度研究》(批準號:12CFX068);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營商自由與商事主體制度研究》(批準號:15SFB2032);西南政法大學引進人才項目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