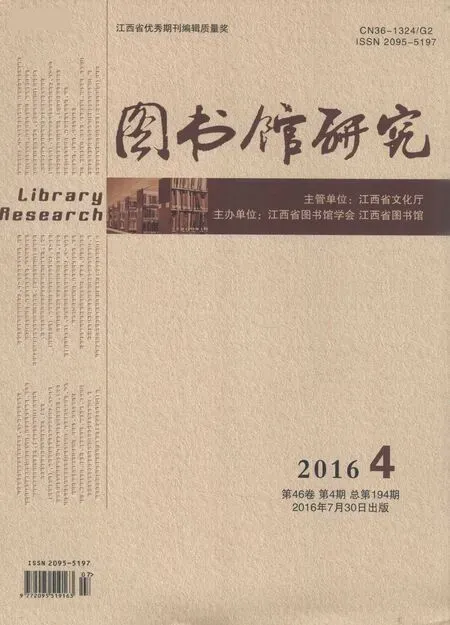《綠窗新話》勘正
齊心苑
《綠窗新話》勘正
齊心苑
(山東大學文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綠窗新話》是宋代說話人的參考資料,它與羅燁《醉翁談錄》不是轉引或被轉引的關系,兩書成書時間相近,《綠窗新話》稍早一些。新見到的黃孝紓遺稿《〈綠窗新話〉校釋引言》為解決《綠窗新話》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按照黃孝紓文中線索,對比《藝文》連載之《綠窗新話》與兩岸通行的排印本《綠窗新話》,發現排印本擅自改動底本,從版本介紹到文本順序都存在疏漏。
綠窗新話;醉翁談錄;話本;黃孝紓;周楞伽
1 《綠窗新話》為說話人參考書
“綠窗新話”最早見于宋·羅燁《醉翁談錄》:“引倬底倬,須還綠窗新話”[1]。研究者多據此判定《綠窗新話》的性質為說話人的參考書,如胡士瑩、黃孝紓、程毅中等。后來逐漸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如:周楞伽以為《醉翁談錄》所謂“綠窗新話”,意為“當代風月佳話”,不是書名;凌郁之認為,《醉翁談錄》所言“綠窗新話”是書名,但不一定是今天的《綠窗新話》,“《綠窗新話》的性質可能是類書,殆與《侍兒小名錄》《姬侍類偶》諸書性質差近。”[2]
《綠窗新話》是說部重要典籍,書中故事多經精簡,但詩詞都是完整收錄,可以說是一本說話開場、結尾詩詞大全。上文提及的周、凌二人的觀點都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二者對“綠窗新話”的理解都過于片面。雖然“綠窗新話”字義上可以泛指風月故事,但不能因它字面多義而否定它是書名的可能。何況,《醉翁談錄》中“綠窗新話”,是同《太平廣記》《夷堅志》等并列出現的,就句法上看,應該是書名。凌郁之對“新話”的理解也不準確,在宋代“新話”可特指當代故事,但在實際運用中意義更靈活,如南宋陳善《捫虱新話》內容是詩話,論述范圍不限于宋代。其次,凌郁之因《綠窗新話》故事形式上以類相從就將之定為類書過于武斷。類書分力求廣博的綜合性類書和功用突出的專門性類書。《綠窗新話》顯然不是前者。雖然其內容大都關乎風月,但書中故事與祖本相比,刪繁錄要,僅存梗概,多失卻了原有的曲折動人的特點。這樣顯然不能滿足普通讀者對故事情節的要求,所以,《綠窗新話》也不是專門的風月故事類書。
宋代說話家數很多,故事取材廣泛,僅小說一家就有靈怪、煙粉、傳奇等諸多門類。說話人雖然各有專長,但對于貴在“尤務多聞”,“說收拾尋常有百萬套,談話頭動輒是數千回”的小說人來說,說話者需要具備多種題材類型的知識儲備。可想而知,滿足他們需要的參考書既要囊括眾多故事,又要方便檢索記憶。將同類主題的故事集合一起不僅利于翻檢查找和閱讀記憶,而且方便說話人選擇與正話相關的入話,提起話頭,漸進地切入正題。由此便可理解何以《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均有類書門類清晰的特征。二書的組織形式,和說話慣有程式息息相關。形式上與類書有相似之處,但功用卻不同。所以將《綠窗新話》視作說話人的參考資料和底本合情合理。
黃孝紓 《〈綠窗新話〉校釋引言》:“羅燁所說‘引倬’、‘底倬’,當屬宋元時的市語,現今雖不可通曉,但從字面推闡,‘引倬’,可能是入話的引子,‘底倬’,可能是收場唱詞,按之《綠窗新話》,附錄大量詩詞,從而得到著落和答案。”[3]“倬”,有“美好”“俊俏”之意。“引倬底倬”,指開頭好、結尾好。說話開始先有一段押座文或定場詩,既能穩定聽眾,又可為正話作鋪墊;說話結束時,常用韻文總括正話、點明主旨。對說話人來說,在故事梗概之上添枝加葉不在話下,但創作與故事相關的詩詞殊為不易。《綠窗新話》正可解決這個難題。書中故事簡略,相關的詩詞卻大都著錄完整。若說話人掌握了書中詩詞,何愁說話沒有精彩適用的開場、結尾詩詞呢?
2 《綠窗新話》早于《醉翁談錄》
《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體例相似,且內容有交叉。二者成書先后直接關系到《綠窗新話》的性質。如周楞伽便由二書交叉部分判定 《醉翁談錄》成書在前,《綠窗新話》是得名于《醉翁談錄》之“綠窗新話”:
本書所節引的故事,往往與《醉翁談錄》同,但《華春娘通徐君亮》開頭相遇一段,《醉翁談錄》卻存闕,足證本書問世在后,為《醉翁談錄》編者所未及見,因而本書編者頗多轉引《醉翁談錄》,而《醉翁談錄》卻不能據本書補足全文[4]。
此說不通。今本《醉翁談錄》未存《華春娘通徐君亮》開頭,并不意味著書問世之初這則故事就是殘缺的。查影印“觀瀾閣藏孤本”《醉翁談錄》,《崔木因妓得家室》一頁內容竄入華春娘故事。華春娘故事的闕文當是原書完整的一頁或幾頁。這說明羅燁編撰之時這則故事本是完整的,也許是流入朝鮮時缺頁,也許是日本影印時漏掉一頁,導致了今日看到的《醉翁談錄》華春娘故事的殘缺。事實上,《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二書所記故事多有不同程度的縮減,根本無法以存闕詳略定其成書先后。
周楞伽先生所說“本書編者頗多轉引《醉翁談錄》”也不符合事實。《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故事對應如下表1所示。

表1 《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故事對比
前6條,大體上《醉翁談錄》比《綠窗新話》詳細。如華春娘故事,《醉翁談錄》文字雖然有缺,但對華春娘父親的籍貫、官職,母親的姓氏等都有交代。
第7、8兩條,《綠窗新話》稍詳。《綠窗新話》中韓翃柳氏故事仔細交代了李生贈柳氏的過程;楚娘悔嫁故事,楚娘為媒人所陷嫁與村夫,被里中少年嘲笑憤而求離。《醉翁談錄》沒有這些細節。
第9到12條,兩書出入較大,顯然編撰者依據了不同的祖本。如伴喜故事,兩書結尾不同;第11條,兩書故事人物姓名不同,但是情節和細節卻驚人的一致,而且《綠窗新話》所載的三首詩全見于《醉翁談錄》(這是《綠窗新話》為說話人參考書的最好證明:故事僅存梗概,詩詞記錄詳細。因此出現了二書中同樣故事人名不同、地點不同,但是所引詩相同的局面)。
第13條蘇軾判和尚犯奸一組,兩書文字幾乎全部相同。出現這種情況,要么兩書取材來源一致,要么是一書抄了另外一書。鑒于上文對第9到12條的分析,后一種情況不太可能,所以極有可能是兩書編撰者選錄這則故事時使用了相同的祖本。
綜合以上可知,《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之間不是簡單的轉引和被轉引的關系。兩書都記載了當時頗為成熟的一些故事,因編者剪裁原則不同、依據的祖本不同,便呈現出了種種差別。又因成書時間接近,參照同一祖本的可能性較大,所以會出現對同一故事的記載如出一轍的情況。《綠窗新話》所載故事以北宋為主,涉及南宋的,據黃孝紓斷定有兩篇,一是《孟麗娘愛慕蔣芾》,一是《楊生共秀奴同游》。前者文中有“往行都赴省”句,“行都”是南宋對杭州的稱呼;后者敘楊廷實“久寓都下”,最終同秀奴赴江而死,故事中的“江”,當是杭州錢塘江。且書中引用了多則楊湜《古今詞話》中故事,這說明《綠窗新話》成書必定在《古今詞話》之后。楊湜書成于南宋初年,且《綠窗新話》并無元人事跡,其成書時間應在南宋,不會晚至元代。《醉翁談錄》乙集《吳氏寄夫歌》和《王氏詩回吳上舍》都涉及元代人物,書中偶有追思故宋的口吻,對此,鄭振鐸、胡士瑩等都認為是元刊的明證。也有學者認為這些內容系后人摻入,書原成于宋代。筆者認為,《醉翁談錄》一書雖然名目清晰,但是其分類并不嚴謹,各卷情況也不一致,書的編撰當不是一氣呵成,作者極可能是由宋入元的遺民,書成于元初。可以肯定,《綠窗新話》成書早于 《醉翁談錄》,《醉翁談錄·小說開辟》提及的“綠窗新話”確是指今之《綠窗新話》。
3 《綠窗新話》排印本的問題
對《綠窗新話》感興趣的學者頗多。據黃孝紓先生《〈綠窗新話〉校釋引言》可知,其好友夏敬觀也曾對此書作過考證,本打算連載在《青鶴》上,可惜因為抗戰而未得發表。黃孝紓先生的校釋和夏敬觀先生的考證今日都無從見到。現有的幾個經整理的排印本包括: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本、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古典文學出版社)本以及臺灣世界書局《增補中國筆記小說名著》本(與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本相同)。以上三個版本都出自周楞伽先生之手。1991年本是在1957年本的基礎上,體例稍有改善,版本介紹、篇章目錄等也有改動,但仍延續了舊版的某些疏漏和錯誤。
3.1交代版本來源有誤
1957年《綠窗新話》[5]排印本的《后記》和1991年排印本的《前言》在述及整理《綠窗新話》所依據的底本時都存在著問題:
寧波天一閣藏書中,也有這書的抄本,趙萬里曾據以輯楊湜古今詞話的佚文。一九三五——三六年藝文雜志曾分期刊載此書全文,共一百五十四篇,較董康所抄目錄多三十五篇,當是足本,據說它所根據的是嘉業堂抄本。(《后記》)
本書因從未付印,長期湮沒不傳,僅吳興嘉業堂、寧波天一閣有抄本,一九三五年上海《藝文雜志》曾據抄本分兩期刊載全文,我于一九五七年就根據《藝文雜志》所刊加以整理。(《前言》)
周楞伽先生所說的“《藝文雜志》”,實際上是《藝文》雜志,《前言》標點錯誤。《綠窗新話》系黃孝紓先生從嘉業堂借抄,付《藝文》刊載。黃孝紓先生遺稿《〈綠窗新話〉校釋引言》對此有專門說明:
《綠窗新話》二卷,舊題皇都風月主人撰,不著姓氏。傳世無刻本,吳興南潯劉氏嘉業堂有明抄本,系得自鄞縣天一閣。較武進董誦芬《書舶庸譚》記在日本書坊所見到同一內容改題 《綠窗新語》者,篇目增多三十馀篇。海內抄本當以此為最完善了。
遠在一九三四年,與亡友夏吷庵、盧冀野合編《藝文》雜志,曾向嘉業堂借抄,付藝文雜志分期刊載。吷庵、冀野及余,并錄有副本,吷庵并有考證,擬交《青鶴》雜志登載,后以抗戰軍興未發表。
由黃先生手稿可知,《藝文》連載的 《綠窗新話》,抄自劉氏嘉業堂本,而劉氏嘉業堂本得自天一閣本,所以嘉業堂本和天一閣本是同一本。《藝文》刊載時并沒有說明這種情況,因而周楞伽先生整理時尚不知道兩個抄本是同一本。
黃孝紓先生手稿中,提到與夏敬觀、盧前合編雜志,分期登載的時間在1934,而周楞伽先生《后記》說是1935-1936,《前言》說是1935,誰是誰非?經查找發現,《藝文》創刊號發行于民國二十五年(1936)四月一日,如此一來,分期刊載之事絕不可能在1936年4月之前。黃孝紓先生手稿作1934年,可能因為時隔過久,記憶出了偏差。但是周楞伽先生曾認真查閱過《藝文》雜志,為何也會記錯?仔細翻閱《藝文》原刊后發現,問題出現在《藝文》的最后一期。《藝文》雜志一共刊行了6期。創刊號刊于1936年4月1日,原定是雙月刊,但發行后大受歡迎,于是第2期于5月10日提前發行并公告說改為單月刊。但改為單月刊后銷路并不理想,后幾期發行所間隔的時間越來越長。第3期發行于6月15日,第4期發行于8月10日,第5期發行于10月20日。問題就出現在第6期也是 《藝文》的最后一期,雜志刊行時間居然顯示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日。這顯然是印刷錯誤,因為這期末頁還為出版于當年4月16日的 《食貨雜志》做廣告,中間還刊有紀“丙子七月二十七日”事的作品。正是這處印刷錯誤導致了周楞伽先生誤會《藝文》連載《綠窗新話》的時間是1935-1936。
3.2記錄分期錯誤和文本順序顛倒
周楞伽《前言》云“上海《藝文雜志》曾據抄本分兩期刊載全文”,實際上,《藝文》雜志共分5期連載了《綠窗新話》:上卷載于第2、3、4期,下卷載于同年第5和6期。《前言》中“分兩期”之說不知從何而來,在先前《后記》中,刊載情況還是“分期”,而非“分兩期”。且不論差錯的釀成是出版社的粗心還是作者后期誤改,單就版本介紹看,1957年版《綠窗新話》比1991年版更為準確詳細。
排印本《綠窗新話》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極少為人注意。《藝文》分5期刊載了全部《綠窗新話》:第2期共16條,從《劉阮天臺仙女》到《張俞驪山遇太真》;第3期共33條,從《韋生遇后王夫人》到《周簿切脈娶孫氏》;第4期共23條,從《薛媛圖形寄楚材》到《唐明皇咽助情花》;第5期共41條,從《韓妓與諸生淫雜》到《虢夫人自有美艷》;第6期共41條,從《袁寶兒最多憨態》到《蔣氏嘲和尚戒酒》。將此與排印本《綠窗新話》對比發現,排印本卷下,顛倒了《藝文》原刊第5期和第6期的內容,這樣一來,排印本《綠窗新話》卷下便是以《袁寶兒最多憨態》開始,以《虢夫人自有美艷》結束。《綠窗新話》是按故事類型分類的,《袁寶兒最多憨態》和《虢夫人自有美艷》都屬“麗人”之類,然因排印版倒置了第5期和第6期,導致了兩篇原本相鄰故事首尾遙遙相望。
3.3改底本不作說明
《綠窗新話》排印本體例難以稱善,這個問題石昌渝等編著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譚正璧《話本與古劇》等已有述及。雖然后出的排印本已經對前一個作了不少改進,但仍存在許多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對原文作刪改或修改卻不注明。如《王軒苧蘿逢西子》,原文共11行,排印本竟少了從“軒知其異”到“西子已在焉”近5行的內容;《劉浚喜楊娥杖鼓》,排印本少末句“素娥以此詞,名振京師”。這種情況實在讓人難以理解。《藝文》原文校對不精,錯漏很多,周楞伽先生整理時一律直接改過,其中自然有誤改的地方,如 《柳家婢不事牙郎》,排印本將評語“嘗觀柳仲涂為叔母穆夫人墓志”一句中“柳仲涂”改作“柳仲郢”,整段評論因這一誤改變得脫離上文、難以理解。有些原書評論文字混入作者注釋中,如《張倩娘離魂奔壻》和《灼灼染淚寄裴質》,原小故事后有秦觀文或詞作為評論,而在排印本中,秦觀詞文都被置于作者按語中。這些刪改都沒有相關說明。
通觀排印本《綠窗新話》,轉錄《藝文》所刊載的出處時也偶有改動。如《楊妃竊寧王玉笛》的出處,《藝文》、黃孝紓先生手稿和董康 《書舶庸譚》(董康《書舶庸譚》記有在日本見到的《綠窗新語》目錄,經對比分析,《綠窗新語》即《綠窗新話》。)都作《詩話細覽》,排印本卻改作《詩話總龜》;《藝文》所載《蔡文姬博學知音》末有小字說明出自《列女傳》,排印本卻說未注明出處。
綜上,排印本有失底本原貌。盡管周楞伽先生的校補,采輯資料眾多,為后來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但如果拋開《藝文》原刊,僅就排印本進行《綠窗新話》的研究,難免會出現偏差。
[1]羅燁.醉翁談錄[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2]凌郁之.《綠窗新話》平質[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5):56-59.
[3]黃孝紓,齊心苑.《綠窗新話》校釋引言[J].文史哲,2016(1): 59-69.
[4]皇都風月主人,周楞伽.綠窗新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皇都風月主人,周夷.綠窗新話[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Survey about New Words by the Green Window
QI Xin-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New Words by the Green Window is the reference of Speaker in Song.Its generation time is earlier than Conversations with a Drunkard.Introduction to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New Words by the Green Window written by Huang Xiao-shu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to solve related problems about this book.According to the trail in Huang's paper,we can compare the edition serialized in Art magazine and the prevailing typographical book.The prevailing one tamper original text,and the order of text is wrong.
New Words by the Green Window;Conversations with a Drunkard;Huaben;Huang Xiao-shu;Zhou Leng-qie
G256
G256
A
2095-5197(2016)04-0125-04
齊心苑(1988—),女,在讀博士生,研究方向:元明清小說與詩歌。
2016-05-10(編發:王域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