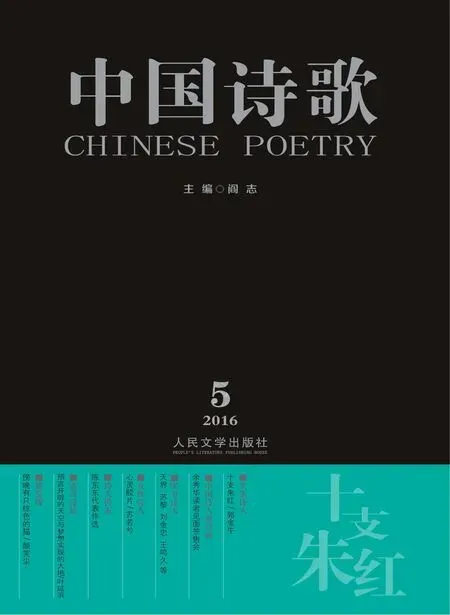預言開辟的天空與夢想實現的大地
——吉狄馬加和他的長詩《致馬雅可夫斯基》
陰葉延濱
預言開辟的天空與夢想實現的大地
——吉狄馬加和他的長詩《致馬雅可夫斯基》
陰葉延濱
中國新詩誕生百年之際,世界正在用驚奇的眼睛關注著一個東方大國的復興。中國新詩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正是在一百年前世界大變革的風暴中,迎著世紀的曙光沖向天空的雛鷹。一百年的中國新詩對于有悠久歷史的中華傳統詩詞,今天仍是一只雛鷹,但在東方文明的天宇,百年風雨,每一次歷史重大的變革中,我們都看得見中國新詩的身影。中國新詩也用優秀詩人的名字和不朽的詩篇,構筑了中華民族精神殿堂復興與重建的基石。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回顧百年新詩歷史,中國新詩是兩條大河滋養的精神家園。這兩條大河,一條是中華文化之河,源遠流長,其滋養如乳汁,使中國新詩有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另一條是世界文化之河,一百年前,那些睜眼看世界的先賢們,開辟了與世界對話,并且努力學習各國優秀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之旅。百年的跋涉,讓“同時涉過兩條大河”的中國新詩,神話般又現實地站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回望百年歷史,我們在向傳統致敬的同時,也在向那些世界大師致敬,因為有他們,中國新詩才可能成長并留下一篇又一篇與史同在的經典。
當代詩人吉狄馬加發表在《人民文學》2016年3月號的最新長篇力作《致馬雅可夫斯基》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的向巨人致敬的新作。讀吉狄馬加的這部長詩的時候,我的腦海里出現了一長串的名字:但丁、哥德、普希金、惠特曼、馬雅可夫斯基以及他的同行者“還有巴勃羅·聶魯達、巴列霍、阿蒂拉、奈茲瓦爾、希克梅特、布羅涅夫斯基、不能被遺忘的揚尼斯·里索斯、帕索里尼”(引自《致馬雅可夫斯基》)之后,我們還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在這個長長的名單中,吉狄馬加曾先后寫過許多向他們致敬的詩作,比如翁貝爾托·薩巴、薩瓦多爾·夸西莫多、耶胡達·阿米亥、塞薩爾·巴列霍、巴勃羅·聶魯達、米斯特拉爾、胡安·赫爾曼、托馬斯·溫茨洛瓦、切斯沃夫·米沃什、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等。我認真閱讀后感到,吉狄馬加這首《致馬雅可夫斯基》,有著詩人更深的思考與更投入的情感。
馬雅可夫斯基是世界級的大師,他在中國曾有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同時也受到較多的誤解,并且一度被中國讀者遺忘。馬雅可夫斯基是我最早認識的詩人之一。那還是1950年代末,讀小學的我剛認識寫《金魚和漁夫的故事》的普希金,又在母親的桌子上看到了厚厚的馬雅可夫詩集,我還讀不懂里面的詩,但我記住了其中一首詩《不準干涉中國》。這首寫于1924年中國大革命時期聲援中國工人的短詩,讓我記住了馬雅可夫斯基這個名字。以后在我從事詩歌寫作的早期大量經典閱讀中,馬雅可夫斯基也就進入了我向大師致敬的視野。馬雅可夫斯基青少年時代,投身反對沙皇專制統治的革命宣傳,被沙皇政府三次逮捕投入牢獄。他在牢房里開始了詩歌創作。馬雅可夫斯基1912年在“未來派”發表宣言,要“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22歲的詩人在《穿褲子的云》里喊出了他與舊社會的決裂:“打倒你們的愛情,打倒你們的藝術,打倒你們的制度,打倒你們的宗教。”他曾預言1916年將出現革命,當1917年轟擊冬宮的炮聲響起,他首先張開雙臂歡呼十月革命的到來。他說:這是我的革命!他把自己的創作與人類歷史上偉大的變革聯系到了一起,藝術上的先鋒銳意創新與激進的社會變革理想,推動他站到了時代的巔峰。標新立異,獨樹一幟,同時走向廣場和民眾,他忘我地和所有的敵人同時戰斗。他熱情地擁抱革命,用詩歌冒犯一切陳舊的陋習,也無情地挑戰自我。最后他用自殺這種反抗方式,留給了這個世界無數的思考。在他去世86周年之際,在近一個世紀的歲月里,世界風云變幻,圍繞著他的話題始終未曾停止。我認為,不同立場的藝術家至少都有了這樣的共識:馬雅可夫斯基是那個風云聚會的大時代偉大的激進派的詩人,同時他的作品讓那場震撼世界的革命,在人類精神高度上得以達到空前的高度。
《致馬雅可夫斯基》是中國詩人吉狄馬加以詩歌為橋,走近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并與他并肩站在時代高度,審視自己面對的時代。“馬雅可夫斯基,不用其他人再給你評判/你就是那個年代——詩歌大廳里/穿著粗呢大衣的獨一無二的中心/不會有人忘記——革命和先鋒的結合/是近一百年所有藝術的另一個特征/它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就是在/反越戰的時候,艾倫·金斯伯格們/在紐約的街頭號叫,但在口袋里裝著的/卻是你炙手可熱的滾燙的詩集”。吉狄馬加在這里經典性地點明了近百年所有藝術的另一個特征:“革命和先鋒的結合”。這是馬雅可夫斯基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同時也是我們理解《致馬雅可夫斯基》這首長詩的入口。是啊,我們回首百年新詩,以及百年的世界藝術史,那些成為經典的偉大作品,正是時代偉大變革與藝術偉大創新的有機結合。“你的詩,絕不是紡毛的喑啞的羊羔/是涌動在街頭奔跑的雙刃,堅硬的結構/會讓人民恒久地沉默——響徹宇宙/是無家可歸者的房間,饑餓打開的門/是大海咬住的空白,天空牛皮的鼓面/你沒有為我們布道,每一次巡回朗誦/神授的語言染紅手指,噴射出來/階梯的節奏總是在更高的地方結束/無論是你的低語,還是雷霆般的轟鳴/你的聲音都是這個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僅次于神的聲音,當然你不是神/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你的/一生都在與不同的神進行徹底的抗爭/你超自然的朗誦,打動過無數的心靈/與你同時代的聽眾,對此有過精彩的描述/馬雅可夫斯基,我們今天仍然需要你……”吉狄馬加在與馬雅可夫斯基心靈對話的詩句中,不僅讓我們重新清晰地看到了那個時代巨人般的詩人,同時也喚醒了詩人的神圣職責:讓沉睡者醒來,讓匍跪者站立,讓喑啞的羔羊吶喊,讓詩歌在街頭一起和民眾奔跑!是啊,詩人是時代的驕子,但詩人如果不關心這個時代,不關注門外的世界風云,那么詩人只會成為沙龍里的寵物和仰人鼻息的侏儒。吉狄馬加作為一個詩人,他熱情地投身于中華復興的社會實踐,同時又冷峻地審視這個時代的各個角落:“馬雅可夫斯基,并不是一個偶然的發現/20世紀和21世紀兩個世紀的開端/都有過智者發出這樣的喟嘆——/道德的淪喪,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精神的墮落,更讓清醒的人們不安/那些卑微的個體生命——只能/匍匐在通往靈魂被救贖的一條條路上/馬雅可夫斯基,并非每一個人都是懷疑論者/在你的宣言中,從不把技術邏輯的進步/——用來衡量人已經達到的高度/你以為第三次精神革命的到來——/已經成為了不可阻擋的又一次必然/是的,除了對人的全部的熱愛和奉獻/這個世界的發展和進步難道還有別的意義?”認識馬雅可夫斯基與他所處的時代,是為了認識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并且解決好與時代和民眾的關系。吉狄馬加在這里,不僅讓讀者重新認識馬雅可夫斯基,同時也將成為一個偉大詩人所需要解決的與時代的關系中許多重大的課題,擺在每個有良知的中國詩人面前。
《致馬雅可夫斯基》這部向大師致敬之作,又是詩人與詩人心靈呼應的紀錄:兩位詩人隔著一個世紀的歲月,告訴他們親愛的讀者,詩歌何為?詩人何為?詩歌的力量何在?“沒有人真的敢去否認你的宏大和廣闊/你就是語言世界的——又一個酋長//是你在語言的鐵氈上掛滿金屬的寶石/呼嘯的階梯,詞根的電流閃動光芒/是你又一次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形式/掀開了棺木上的石板,讓橡木的腳飛翔/因為你,俄羅斯古老純潔的語言/才會讓大地因為感動和悲傷而戰栗/那是詞語的子彈——它鉆石般的顱骨/被你在致命的慶典時施以魔法/因為你,形式在某種惟一的時刻/才能取得沒有懸念的最后的引力/當然,更是因為你——詩歌從此/不僅僅只代表一個人,它要為——/更多的人祈求同情、憐憫和保護/無產者的聲音和母親悄聲的哭泣/才有可能不會被異化的浪潮淹沒……”這就是馬雅可夫斯基給予吉狄馬加的啟示,也是吉狄馬加揭示出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成為巨人的秘密。一個優秀的詩人必然是宏大廣闊的語言世界的酋長。吉狄馬加在許多場合,十分清楚地表明他認為,一個詩人必須重視詩歌藝術,關注詩人更要了解他對于語言的掌控能力。然而擁有高超的語言才華,對于一個詩歌巨匠還遠遠不夠,他必須為他自己和這個時代創造新的語言形式。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式的詩行,搭起向上伸往古老傳統寶庫的通道,向下伸向民眾,承接無數無產者吶喊和母親的眼淚。偉大的詩人總是和民眾在一起,當然他必須有征服人心的天賦,他是語言王國的酋長,又是創造新世界的超人;他是街頭奔跑人群中的一員,同時又是所有母親的兒子:“在勞苦大眾集會的廣場上/掏出過自己紅色的心——展示給不幸的人們/你讓真理的手臂返回,并去握緊勞動者的手/因此,詩人路易·阿拉貢深情地寫道:/‘革命浪尖上的詩人,是他教會了我/如何面對廣大的群眾,面對新世界的建設者/以詩為武器的人改變了我的一生!’……”這是最深刻也最樸素的真理,與大地在一起,會獲得大地的力量。在長詩中對話馬雅可夫斯基,吉狄馬加特別地引用了另一位杰出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名言:“力量——在那邊!”這是對那些沉溺于沙龍和小圈子的詩人所說的名言,詩歌是在馬雅可夫斯基那邊有了力量!對于那些混跡于詩壇的庸人,吉狄馬加尖銳地指出:“那些沒有通過心臟和肺葉的所謂純詩/還在評論家的書中被誤會拔高,他們披著/樂師的外袍,正以不朽者的面目穿過廳堂……”吉狄馬加的這種清醒,對我們認識今天的詩壇大有益處,同時,正是這種清醒,讓他對馬雅可夫斯基的評價,更具有辯證而冷靜的力量:“對一個詩人而言,馬雅可夫斯基/不是你所有的文字都能成為經典/你也有過教條、無味,甚至太直接的表達/但是,毫無疑問——可以肯定!/你仍然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的公民/而那些用文字沽名釣譽者,他們最多/只能算是——小圈子里自大的首領!”詩人何為?詩歌何為?詩歌的力量何在?吉狄馬加用這些精彩的華章般的詩句,告訴了他親愛的讀者。
《致馬雅可夫斯基》是吉狄馬加用心靈點燃的詩句之炬,引領他的讀者走向大師。從馬雅可夫斯基所處的那個時代,人類又走過了百年的歷程。今天的人類社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巨變,資本的全球化,信息時代帶來的技術革命,讓曾經那么浩瀚的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世界越來越小了,然而人心之間的距離卻更加深遠難測。人類已成為命運共同體,然而共同的精神家園,卻在戰爭炮火和精神霧霾的籠罩下漸行漸遠:“這個把所謂文明的制度加害給鄰居/這要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更加無恥/這個世界可以讓航天飛機安全返航/但卻很難找到一個評判公理的地方/所謂國際法就是一張沒有內容的紙/他們明明看見恐怖主義肆意蔓延/卻因為自己的利益持完全不同的標準/他們打破了一千個部落構成的國家/他們想用自己的方式代替別人的方式/他們妄圖用一種顏色覆蓋所有的顏色/他們讓弱勢者的文化沒有立錐之地/從炎熱的非洲到最邊遠的拉丁美洲/資本打贏了又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總有無數的個體生命付出巨大的犧牲/沒有別的原因,只有良心的望鏡——/才可能在現代化摩天樓的頂部看見/——貧困是一切不幸和犯罪的根源”。站在全人類的高度,詩人吉狄馬加呼喚詩人的良知,也是呼喚人類賴以共存的良知:“是的,除了對人的全部的熱愛和奉獻/這個世界的發展和進步難道還有別的意義?”正因為如此,重新面對馬雅可夫斯基就有了世界性的意義:“馬雅可夫斯基,新的諾亞——/正在曙光照耀的群山之巔,等待/你的方舟降臨在陸地和海洋的盡頭”。在這里,吉狄馬加抒發了一個東方詩人的自信與堅定,他對詩歌的信心也就是對人類良知的信心,更是對未來人類命運的信心:“詩沒有死去,它的呼吸比鉛塊還要沉重/雖然它不是世界的教士,無法赦免/全部的惡,但請相信它卻始終/會站在人類道德法庭的最高處,一步/也不會離去,它發出的經久不息的聲音/將穿越所有的世紀——并成為見證!”吉狄馬加是大涼山彝人之子,也是中華文明培養的杰出詩人。偉大的彝族文化是他成長的乳汁,中華文明豐富深厚的傳統使他在改革的大潮中成為優秀的中國詩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始終堅持向世界各國的文化大師學習,早在吉狄馬加青少年大學求學期間,他那時的詩作就看得出受非洲詩人桑戈爾的影響。之后他的成長幾乎是一個與世界文化大師對話的漫長歷程。他的詩集已在全球十多個國家翻譯出版,成為在世界上最受重視的當代中國詩人之一。這首長詩《致馬雅可夫斯基》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力作,他寫出了一個中國詩人面對時代風云的堅守與良知,也向世人展示了在東方土地上生長的夢想與信心,這部長詩是時代大潮拍擊一個杰出詩人心田激蕩出的心聲——
那一個屬于你的光榮的時刻——
必將在未來新世紀的一天轟然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