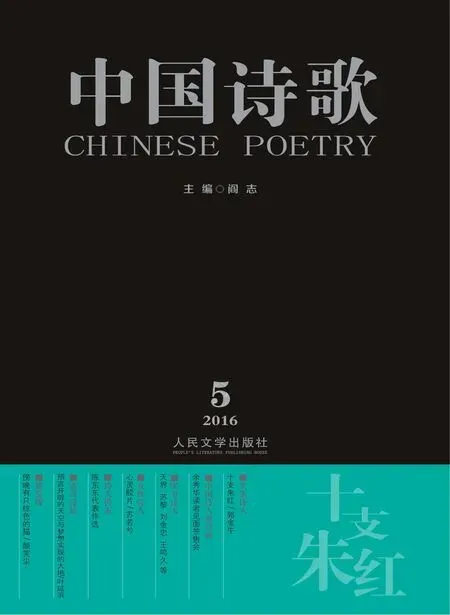詩學觀點
陰孫鳳玲/輯
詩學觀點
陰孫鳳玲/輯
●羅麟認為,詩歌經典是凝聚了人類的美好情感與智慧,能夠引起不同時代讀者的共鳴,藝術上具有獨創性,內容上具有永恒性,能夠穿越現實與歷史的時空,經受得住歷史滌蕩的優秀詩歌文本。一方面,詩歌經典本身必須在內容、藝術上質量過硬,那些不嚴肅、不真實或是在藝術創造性上乏善可陳的詩歌作品,是不可能成為詩歌經典的。另一方面,詩歌經典必須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或者說具有某種歷史性,比如新詩草創時期的一些經典作品,放在今天或許在藝術性上并不出眾,但由于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在特定歷史時期內和條件下特有的開創性,而具有了無可取代的經典性。也就是說,沒有相應的一段比較長的時間的藝術沉淀,詩歌經典的生成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去考查,當下詩歌因為在時間沉淀的條件上無法滿足要求,是不太可能產生詩歌經典的。在時間距離過近的環境下,所謂的“經典性”的生成往往是自封的,也是站不住腳的。
(《21世紀:詩歌接受的“窘境”》,《文藝爭鳴》2016年第1期)
蔭王士強認為,個人化寫作本身當然是值得肯定的,詩人作為獨立的個人而不是作為群體、集體、理念的代言者,個體生命的價值與尊嚴才能夠得到保障,這本應該是寫作的基礎與前提。……但是,個人化寫作同時也是艱難的,絕不是沒有邊界和標準的隨意亂寫,它雖然高度尊重個體的獨立性、個性,但這一切均需在尊重藝術規律的前提之下進行,藝術本身便是在重重的不自由中尋求自由。就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詩歌寫作而言,它一方面存在過度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不足的問題。個人化寫作的“過度”主要體現在詩歌作品的過于自我、私密,從而割斷了與廣闊的生存世界的關聯,僅僅成為了知識的中轉、思想的演練、語言的煉金術、修辭的自我循環等等,從而導致個人化有余而公共性不足。
(《重審20世紀90年代詩歌的個人化寫作及其內在分歧——從羅振亞〈1990年代新潮詩研究〉談起》,《當代文壇》2016年第1期)
蔭蔣藍認為一個人在文字上的亮相儀態,幾乎就決定了其后來的言說方式,就像你無法改造自己的聲帶。采用轉喻和口語的融合語態,為情緒加入冰塊,對不斷敞開的日常經驗進行寓言化處理,一次寫作就是一次回憶,往事在一種克制陳述的語態里復蘇曾有的花香和枝蔓,那既是寫作者的自畫像,也是為生存完成的一次照亮。
(《圈內圈外的成都詩人》,《星火》2016年第1期)
蔭周慶榮認為,對詩歌中的“分行”和不分行的散文詩,我從未把兩者相隔離,我個人以為二者都是詩,是“大詩歌”。散文詩的敘述性和藝術的延展空間似乎更大,正因為更大,它需要寫作者哪怕在手法的隱喻、模糊時,也要能把現象背后的本質性思考清楚,它不允許過分掩藏,而分行詩的魅力之一恰恰在于掩藏。我認為優秀的詩人,只要覺得敘述需要,在自由度、空間感或完整性需要進一步釋放時,都會感受到思想性、敘述性和詩性真正結合后的美好,像昌耀后期的散文詩。現在有許多以分行詩寫作為主,但散文詩也極其優秀的詩人,如:胡弦、徐俊國、雷霆、王西平、宋曉杰、金鈴子等。
(《詩與遠方——關于深度、理想、宏大敘述的詩歌對話》,《揚子江詩刊》2016年第1期)
蔭劉向東認為,從根本性上來說詩歌無疑是想象和虛構的藝術,有一定鑒賞力的人,大體不難區分側重于存在的具象的詩歌與側重于虛構的想象的詩歌。我們的文學觀里多年以來一直滋生著這樣的一個念頭,說是不能與現實靠得太近,太近了,其作品的文學性就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受到質疑,因為我們很多文壇的老前輩是有教訓的。我覺得根本問題不是離現實近不近的問題,也不完全是方法問題,說到底是襟懷和氣度問題。
(《重溫田間的〈抗戰詩抄〉》,《詩選刊》2016年第1期)
蔭田原認為“流暢性”是評價詩人的標準之一。這里所說的流暢性跟當下詩壇提倡的“阻拒性”并不矛盾,一首具有流暢感的詩中同樣可以存在“阻拒性”。但如何在一首文字有限的詩歌作品中做到“流暢性”和“阻拒性”共存的平衡,我認為至關重要。對于內行讀者,二者或許都很必要,但對于更多的一般讀者,“流暢性”似乎更為重要。一首詩中,阻拒也許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很多的阻拒并非詩歌空間天然所致,而是作者的思維不通才華不夠所致,甚至是做出來的,像腦血栓一樣,這樣的人為故障式的阻拒不是詩歌所需要的。即使是阻拒性的文本也應該是文字字面上的阻拒,而讓讀者感受到的那個生命也應是流暢的。
(《流暢與差異——吉狄馬加其人其詩》,《時代文學》2016年第1期)
蔭張曙光認為詩人必須研究技藝,使之嫻熟精準。但詩人不應僅僅滿足于技藝,更要發掘人類更為內在和隱秘的情感,以揭示時代本質的特征。現在寫作的一個誤區是,詩人認為寫作的個人化就是單純地表現個人的情感,而很少能夠將個人情感上升到一個普遍的高度。同樣,詩人們以語言為工具,但語言并不僅僅是工具,也代表著詩歌本身。因為詩歌中的技藝、情感或經驗最終是以語言來呈現的。詩人不僅要善于使用語言,更要為語言的凈化和豐富盡到力量。
(《著名詩人與優秀詩人》,《詩林》2016年第1期)
蔭李以亮認為支撐和成就一個藝術家(包括作家、詩人)的,首要的是他身上整體的直覺,混沌卻鮮明的傾向和意識,而非那些東拼西湊、亂七八糟的知識、概念、偽裝、姿態、立場。而直覺背后,是獨特的人格、熱力、氣質,是整個的人,是小宇宙,是他對世界與人的全部確信或無知。凡是能夠解析的對象,都是貧瘠的和乏味的。藝術的想象,無疑具有輕靈、拔地而起的能力,這使它好像跟實在的現實沒有關系。不對,想象雖然離開了那個具體、不能溶解于藝術的實體的現實,想象卻必須關照、回顧、反哺那個現實。否則,想象不可能走多遠,那樣的想象也沒有什么意義。
(《沉默與言說——2015年札記》,《詩歌月刊》2016年第1期)
蔭牛學智認為,徹底的口語化用詞、徹底的日常化句式,包括徹底的日常生活形式框架,都不是評價一首詩是不是壞詩的首要根據,標志一首詩是不是壞詩、非詩,甚至流水賬、廢話的,是詩人是否胸懷天下,是否真的用真切的生命體驗觀照外部世界。這時候,任何理由的時髦價值、任何圓熟的前衛技術,都必然首先為詩對世界、對社會現實、對無數個人的遭遇孤注一擲,去賣命、去咳血、去痛苦、去孤獨、去寂寞。否則,讀者便沒有任何動力放下手機、放下鼠標,為一個與自己無關的文字游戲去無聊地消耗時間。
(《寧夏“60后”作家的三副面孔》,《朔方》2016年第1期)
蔭張曉琴認為,網絡時期精英知識分子被進一步推擠,大眾知識分子開始一統山河,“人的文學”已經演變為“身體寫作”、“欲望寫作”。就像福柯所說的那樣,人被知識、欲望終結了,傳統意義上的神性寫作者徹底死了。也正是因為他的死亡,舊的寫作倫理才被打破,新的寫作倫理得以確立,而新的書寫者也才產生。這便是大量網民的書寫。從圣人移到精英知識分子,最后到大眾,這顯然是一種下降的趨勢。作者在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死亡方式,而其每一次的死亡,便是文學的新生。大眾書寫的網絡時期,作者已死,無數的書寫者誕生。書寫者不再聽命于神的召喚,也不再堅持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而是隨心所欲地書寫,是娛樂書寫。
(《表象的恐慌與本質的自由:對新媒體時代文學境遇的另一種思考》,《創作與評論》2016年1月下半月刊)
●喬葉認為任何身份都會帶來限制,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沒有完美的身份。而寫作的張力也恰恰來自于限制。至于歷史觀,我不覺得一個作家應該有一個歷史觀,那是政治學家或者歷史學家的事。作家關心和體現的應該是人,歷史中的人和歷史中的人性。寫作說到底是個人的事,也都是拿作品說話的事,讀者不會因為你是70后就會格外厚待你,也不會因為你是90后就特別縱容你。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我覺得最根本的敵人永遠是在自己內部,有個詞叫禍起蕭墻,我認為最根本的挑戰就是“戰起蕭墻”,是自己對自己的挑戰。我覺得最關鍵的是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清楚了這個,所有的沖擊都不足為懼。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文學的財富——對話喬葉》,《江南》2016年第1期)
蔭歐陽昱認為,要“把你寫進詩”就是把人寫進詩,包括素不相識的路人,即凡是能讓我產生詩意的人,尤其是平頭百姓。詩是什么?從這個意義上講,詩就是一個既要讓詩人活、讓大人物活,也要讓名不見經傳的人見經傳,通過我詩而活下來。一個帶著語言行走的人,所到之處、所到之國,都會自覺地把注意力轉向該國的語言,并將其與自己的母語和父語(我個人的獨創)進行對比,令其入詩。
(《把你寫進詩:漫談詩歌的全球寫作》,《華文文學》2016年第1期)
蔭艾偉認為,六十年代作家在中國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作家的童年記憶是十年“文革”,然后在他的少年、青年及中年經歷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因此這一代作家身上有非常特殊的氣質。年少時,因革命意識形態喂養,他們具有宏大的“理想主義”的情懷,又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見證了“革命意識形態”破產后時代及人心的陣痛,見證了“信仰”崩潰后一個空前膨脹的物欲世界。這些經歷讓這一代作家建立了雙向批判的目光。它既是“革命意識形態”的批判者,也是“市場欲望”的批判者。
(《生于六十年代——中國六十年代作家的精神歷程》,《花城》2016年第1期)
蔭阿來認為,古代是一個詩歌時代,中國外國都是詩歌時代,外國包括描述他們宇宙觀的《失樂園》那些都是,講述歷史的也是詩歌。文字越普及越發達,詩歌的受眾肯定越強些。但是從消費主義開始,詩歌更多的是一種自我滿足,敘事文學有吸引更多讀者的可能性。任何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中國大概到唐宋時期,敘事文學就開始發展,其實是因為城市的發展,消費的發展而導致的。中國敘事詩不強大大概是和漢語的功能有關系。西方詩歌,尤其是現代派意象派之后,西方詩歌也變得慢慢向中國詩歌學習,中國詩歌也向西方詩歌學習,所以變成全球的一體的詩歌狀態,西方詩歌雖然有敘事傳統它也停止敘事。
(《文學總是要面臨一些問題——都江堰青年作家班上的演講》,《美文》2016年第1期)
●關晶晶認為,藝術創作是體驗、感受、自我探索的過程,藝術不是思想,它可以是思想性的,或是前思想的,但它必須以不同于思想的特征來呈現。任何關于精神的活動都可以是“思想性的”、“前思想的”,它只是描述了一種向度,但它不能區別不同的精神活動。藝術作品可以因創作者而帶進一些思想性、宗教性或者科學性,但它們只在藝術創作中作為遙遠而深蓄的背景存在。藝術就是藝術,藝術本體不應該也承載不了思想、宗教或者科學。我覺得生命的體驗、感受,生命的狀態要大于作品,大于思想性、宗教性、科學性。
(《關晶晶:從來就是這樣》,《青年作家》2016年第1期)
蔭曾蒙認為,把詩人經驗改寫為公共事件或者把對公共事件的觀點切換成為個體的思考,這或者是一種寫作才能,更是一個詩人成熟成為標新立異的創作沖動。種種道德約束、人為的成見都不會成為阻擋寫作的動力。有時候我們看到小詩人的作品單獨拿出來,比大詩人的要完美得多,但大詩人有一個明顯的優點,那就是他總是持續地發展自己,一旦他學會了一種類型的詩歌寫作,他立刻轉向了其他方向,去尋找新的主題和新的形式,或兩者同時進行。不斷地轉變、突圍,不斷地試驗,以語言作為盾牌,又使得語言成為語言。寫作的難度被不斷超越,不斷形成新的難度,不斷地突破自己。這是個周而復始、沒有終點的圓周運動,哪里都是起點,這也是詩人不斷創造的源泉和秘密。
(《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禮》,《青春》2016年第1期)
●陳仲義認為,現代詩經典化是時代語境、文本屬性、審美習慣、接受口味、價值觀念等諸多因素博弈與合力的結果。現代詩經典化的“大指標”應充分考慮時空維度下的原創性、影響力與超越性三種。現代詩經典化需要漫長時空的篩選、甄別與耐心等等。它是集體記憶表層與深層銘刻的共同產物,其最顯著標示是“流傳”。現代詩經典化不同于詩歌標準的理性、抽象的“說教”,而是充滿活的感性的形象化的“外延”。現代詩經典化意味著承認詩歌某些恒久性元素及其合法性,它們的留守與變異是繼續重鑄經典的支柱。
(《現代詩:不可或缺的經典化》,《南方文壇》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