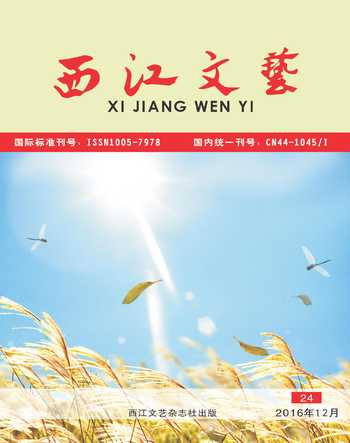蒼涼莽荒之原下的群像
李萌
【摘要】:《呼蘭河傳》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來敘述小城的風土人情,沒有主角,卻寫了很多普通人,通過這些普通人的群像,塑造出整個呼蘭河的氣息。和藹厚道的祖父、淡漠疏離的其他家人、悲慘的小團圓媳婦、老胡家的惡婆婆、“神婆”、“云游真人”、古怪的有二伯、堅韌的馮歪嘴子和他可憐的媳婦、周三奶奶、王寡婦、看戲的姑娘姐妹們......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們的行為,向讀者展示了呼蘭河人們的品質和精神風貌,向我們展現(xiàn)了一幅呼蘭河特有的“人情”圖。而我們對人物的分析也不能僅是停留在他們說了什么話、做了什么事以及由此反映出他們的性格特征這樣的層面上。透過人物的表現(xiàn),透過呼蘭河獨有的民俗活動,他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狀態(tài)是一個引發(fā)我思考的問題。我認為不能概括地用“荒蕪一片”來形容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他們的精神世界是需要我們去關注和研究的。因此筆者在通過具體的人物、事件、場景,分析研究了這些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之后,更進一步思考,對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進行研究,通過分類和舉例來進行具體的闡述。
【關鍵詞】:天然式“過活”;迷信鬼神;畸形心理
《呼蘭河傳》是蕭紅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蕭紅的巔峰之作。它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有著獨特的重要地位,許多文學評論者都給予其較高評價。小說以散文化的語言講述了作者的童年故事和家鄉(xiāng)風物,渾重又輕盈,以兒童視角的敘事方式將呼蘭河的風土人情娓娓道來,平鋪直敘的方式使呼蘭河以一種古樸寧靜、蒼老神秘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描繪出一幅呼蘭河的風土人情畫,寄托了作者對故土的思念和懷戀,也寄托了作者濃重的悲觀主義情懷。它的成功是多方位的,不僅文本內容本身具有極高的藝術審美價值,在敘事的語言上、敘事的方式方法、小說的精神內涵等方面都獨具特色。茅盾先生曾這樣評價這部作品的藝術成就:“它是一篇敘事詩,一片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這部作品的成功之處在于它將蕭紅的鄉(xiāng)愁、孤獨、坎坷匯聚成最冷靜的筆尖,淡然地書寫落寞與蒼涼、可悲與苦難,無聲之處盡是聲嘶力竭的吶喊。筆者在讀了文本多遍之后,選擇去研究總結呼蘭河人們的精神世界。原因在于這部小說令人感覺到一種溫吞,甚至靜默的悲傷,作者的用字用句是一部分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小說的內核帶給人們的觸動,于是筆者想透過文本去研究更深一層的---呼蘭河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通過研究,筆者認為他們的精神世界并非“空洞貧瘠”一詞便可窮盡,有很多細微且深刻的東西值得讀者去深挖,去思考,去剖析。了解呼蘭河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狀態(tài),并作以分類和總結,以得到更為客觀全面的認知。呼蘭河的人們大都質樸,但沒有明確積極的生活目標,缺乏知識和思考,處于一種“天然式”過活的狀態(tài)、對待他人的苦難有一種畸形的心理、守舊麻木、愚蠢封閉、所有的民俗活動都脫離不開鬼神,迷信且誤人誤己。整體的精神狀態(tài)可以用“荒蕪不自知”來形容,但仍有些特別的形象跳躍出來,成為呼蘭河人們精神荒原里的點點綠洲。
一、生活中反映出的呼蘭河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
從整體來看,呼蘭河人們的生活平靜封閉。而它的平靜源自于它的封閉。封閉有兩個原因:一是地理環(huán)境因素所致,它處于東北小城,閉塞落后。二是根本原因,封建落后的思想統(tǒng)治著這里的祖祖輩輩。人們以他們祖先留下來的方式生活,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自然而然受到局限。書中有很多描寫呼蘭河人們生活的畫面,通過他們日常生活的行為和方式,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
(一)生存的意義——生活還是過活?
呼蘭河的人們處于一種“集體的無意識”[1]的生存狀態(tài)之中。所謂“集體無意識”,簡單而言,“就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無數(shù)同類經(jīng)驗在某一種族全體成員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傳,正因為有著相應的社會結構作為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支柱。”[2]呼蘭河的人們簡單地日復一日地重復著體力勞動和生理功能的運轉,對于生活的目的和意義從未進行過思考,因此也沒有明確的認識,祖祖輩輩習慣于這樣付出體力卻不經(jīng)思考的生活,所以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過活狀態(tài)。有學者提出,呼蘭河人們的這種生存方式是“天然式生存”,“天然式生存,就是把生命隨意地安放在自然環(huán)境之中,雖然利用天然的生存資源,卻又毫無人工培育痕跡,毫無生存目的而存在著的一種存在狀態(tài)。”[3]呼蘭河人們的生存狀態(tài)的確是這樣,對生活只有最低的要求,缺少思考規(guī)劃,仿佛被蒙著眼睛拉磨的驢一樣,只是單調地重復而不去尋求其意義所在。由于整個群體都處于這種麻木與閉塞之中,導致他們形成了強大的集體無意識的狀態(tài)。作者在書中并沒有直接提出對呼蘭河人們生存意義的追問,但從很多細節(jié)的描寫中是體現(xiàn)出呼蘭河人生存意義的虛無以及作者對此的失望與無奈。
書中有段話對這種狀態(tài)進行了描述:“生、老、病、死,都沒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長去;長大就長大,長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沒什么關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聾了,就不聽;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動了,就癱著。這有什么辦法,誰老誰活該。病,人吃五谷雜糧,誰不生病呢?死,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親死了,兒子哭。兒子死了,母親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來哭。”在他們眼里,生活就是活著這件事,就是吃飯穿衣,度過一個又一個年頭。他們根本不知道理想、信念、信仰這些東西,也許有,也是繞不開吃穿生老病死的念頭,再有別的什么的話,就是鬼神了。這是一極其消極閉塞、被動麻木的生活態(tài)度,也許跟他們談論生活態(tài)度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對于這個層面的理解,呼蘭河的人們是空白的。
(二)“輕如草芥”的生命不被尊重
小城里有很多卑微的小人物:失獨的王寡婦、街邊的叫花子、寄人籬下地位卑微的團圓媳婦、混生活的有二伯、低微苦命的馮歪嘴子和他的妻子王大姐......
這些人物都具有悲慘的命運,而呼蘭河的人們對待這些不幸者的態(tài)度則是:剛開始同情,轉變?yōu)槁槟静⒁詾檎勝Y,更甚則是踐踏。“他們常常喜歡把一些不幸者歸在一起,比如瘋子傻子,都一律去看待。”“偶爾在秒臺上或是大門洞里不幸遇到了一個,剛想多少加一點惻隱之心在那人身上,但是一轉念,人間這樣的人多著哩!”“或是做著把瞎子故意領到水溝里邊去的事情。”“人們對待叫花子們是很平凡的。”由此可見,人們對待這些不幸者是有一種畸形的歧視的,偶爾會有一絲惻隱之心,但也迅速被麻木和取笑代替。
以王寡婦為例,她痛失獨子后就瘋了,發(fā)瘋的時候會在街上狂哭一場,哭過一場之后還是平靜地去賣豆芽,回家吃飯睡覺,活著。沒有人關心她孤苦悲慘的生活和內心世界,只是把她當做瘋子傻子對待,覺得這樣不幸的人很多。時間久了,她自己也習慣了人們一貫的麻木,自己也變麻木了。無論你痛苦與否,有多痛苦,這個世界照舊平靜,無人施舍于你同情或愛。這里的王寡婦讓我想起魯迅先生筆下的祥林嫂,同樣的悲劇人物,被一群麻木無聊、比自己好一點的人反復咀嚼著悲慘的遭遇,歧視多過于同情,被逼瘋、逼死。這反映了呼蘭河人們精神上的頑疾,是存在于封建社會的國民劣根性[4]的體現(xiàn),是一種“看客”的姿態(tài),是一種旁觀心理和勢力的心理。他們不懂得尊重生命,反而去嘲笑輕薄不幸者,可惡、可笑、可悲。
(三)欺人且自欺
小城的人們,不僅騙別人,也欺騙自己。欺騙別人也許只是不想讓他們獲悉真相,而欺騙自己卻是為了獲得精神慰藉,為自己的目的冠以借口,說服自己。是國民劣根性中“瞞和騙”的典型,類似于阿Q精神。
大泥坑在呼蘭河人們的生活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第一是常常淹死牲畜,供大家消遣,以此為談資。第二就是供人們自欺欺人,變“瘟豬”為“淹豬”,讓人們大方的地去吃瘟豬肉。人們明明都知道這青紫色的豬肉是“瘟豬”,但正因為有了這個能夠淹死牲畜的大泥坑,所以可以騙別人這是淹豬,免去了嘲笑,又能說服自己,從而安心吃肉,一舉兩得。小孩子一不小心說出實話還要挨打,這很可笑,畢竟大家可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去自欺欺人的。呼蘭河的人們貼膏藥主要是講究能貼多久,貼的越久的膏藥,越覺得錢沒白花,哪怕貼了半個月還不見好,甚至還腫得更大了,但到底用了那么久也值了。這種自欺是愚蠢的,畢竟花錢治病講究的是藥到病除,越快越好。
(四)“重死輕生”的生死觀和敬畏鬼神的神鬼觀
呼蘭河的人們相當迷信。與人當前的生存狀態(tài)、生活質量相較,他們更重視人的身后事。活著的時候空洞無聊,除了吃飯穿衣和必要的勞作、迷信活動外,再無追求,就是之前所說的“天然式”過活,但卻非常重視身后事,各種儀式場面,應有盡有。此外,扎彩鋪里的別墅、別墅里的傭人、廚子、各種家當、庭院、馬車、牲畜、管家......替死人考慮的十分周到,要是真有陰間,死人可比活人幸福的多。這反映了呼蘭河人們“重死輕生”的生死觀。他們不去盡力改變現(xiàn)狀,而是將它們寄托于一個虛無的世界,愚蠢懶惰。
呼蘭河的人們對鬼神是絕對的敬畏和盲目的迷信。他們的民俗活動無一不跟鬼神有關。在生活中,家里老人孩子身體不好不去請大夫看病,而是請“大神”來跳一跳;兒媳婦孝敬婆婆也是給婆婆請個“大神”跳一跳;因為迷信,把小團圓媳婦折磨致死、還有各種荒誕的迷信傳說......他們敬畏鬼神,將一切苦難都跟鬼神掛鉤,從而用迷信的手段“解決”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過度迷信鬼神的原因,物質狀態(tài)上是由于落后,科學無法普及,精神上則是源于人的一種逃避懶惰、不自信,安于現(xiàn)狀。
(五)看他人“受難”時的畸形心理
呼蘭河的人們有一種奇怪的癖好—看別人“受難”,幸災樂禍、欣賞、興奮的同時,還夾雜著一絲憐憫,是一種很畸形的心理。
小說里面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受難”場景就是給小團圓媳婦“跳神”。“因為老胡家跳神跳得花樣翻新,是自古也沒有這樣跳的,打破了跳神的紀錄了,給跳神開了一個新紀元。若不去看看,耳目因此是會閉塞了的”、“老胡家跳大神,就實在跳得出奇。用大缸給團圓媳婦洗澡,而且是當眾就洗的”、“她在大缸里邊,叫著、跳著,她像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邊站著三四個人從缸里攪起熱水來往她頭上澆......”事實上小團圓媳婦根本沒毛病,就是被她婆婆打的得了心病,但大神非說是狐仙讓她去出馬,要給她洗澡。呼蘭河的人們能來的都來看熱鬧了,其實是看小團圓媳婦怎么受折磨的。小團圓媳婦被撕了衣服扔到開水里,沒有人阻止,而是想看她會怎樣。尤其是第一次洗澡結束后,有的人覺得無聊想要回去,“大神”趕緊說要洗三次,人心就再次振奮,這些都說明了人群都是來看熱鬧的,看小團圓媳婦如何受到虐待,來滿足自己看人“受難”的變態(tài)的欲望。
人們此時的心理是很畸形的,他們內心是希望看到小團圓媳婦被折磨的。在洗澡的過程中,“幫兇”很多,小團圓媳婦不肯脫衣服,幾個人把她的衣服撕了,小團圓媳婦想從大缸里爬出來,但很多人按著她......但也不完全是幸災樂禍的心態(tài),因為跟他們自己并沒什么關系,就是一種“看客”的心態(tài),好奇、殘忍、麻木、偽善。在小團圓媳婦被燙暈之前沒有人幫她,在她被燙暈,有人以為她被燙死后,大家都跑過去拯救她,還有人流下淚來,這種虛偽的憐憫之心也是看客們畸形心理的一部分,既看了熱鬧滿足了自己的畸形欲望,又適當?shù)谋硌萘艘环@示一下自己的憐憫之心,是一種矛盾、畸形的心理。呼蘭河的人們看他人“受難”時的心理很畸形,是封建社會國民劣根性的一種。
二、民俗中反映出來的精神世界
“精神生活是人類內在創(chuàng)造、傳遞和體驗精神價值的心意活動,而民俗則是人類日常情境中,代表了民眾群體的精神意愿,展現(xiàn)這類精神生活的基本形態(tài),呈現(xiàn)為精神生活的獨特風景線。”[5]簡單而言,二者的關系是:民俗活動反映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狀態(tài)決定或促進民俗活動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
(一)跳大神—誤人、害人的“愚眾游戲”
跳大神這個封建迷信色彩最重的活動是貫穿整部小說的,被提及多次。跳大神這種迷信的民俗活動,并不是呼蘭河的特產(chǎn),它又叫“薩滿舞”,薩滿是滿族的巫師,薩滿舞也就是巫師在祈神、祭禮、祛邪、治病等活動中所表演的舞蹈,是封建時期東北農村所盛行的一種民間活動。[6]但在呼蘭河,人們卻把它當做正事,生病了不去請大夫,而請“大神”來跳一跳,跟看戲似的,“大神”演的好,觀眾們也看的盡興,時間久了耽誤了治病,誤病誤人。小團圓媳婦剛來的時候是一個不怕羞、很健康的孩子,其實后來就是被婆婆整日地打罵虐待,有點兒嚇著了,心里難受,所以有點兒顯得抑郁,她婆婆就說她有病了,要給她跳大神。自此就開始百般地折騰團圓媳婦:跳大神、亂喝土方子藥、用開水燙她......最終好好的一個孩子被折騰死了。但呼蘭河的人們不知道事實,小團圓媳婦不是被狐仙抓走了,也不是病死的,而是被這種封建迷信的活動害死的。人們抱著看戲的態(tài)度,也懷著對鬼神的敬畏之心,被封建迷信操縱著,一起害死了小團圓媳婦。
說它是“愚眾”游戲,是因為它占據(jù)了呼蘭河人們的精神生活,人們覺得這是場盛大的儀式,從不懷疑它的真假。媳婦給婆婆請個“大神”來跳,別人就說這媳婦孝順。書中描寫的大神和二神形象很生動,生龍活虎,煞有介事,作秀感十足,但人們仍對此深信不疑。這也說明了人們精神世界的空虛,因為他們沒有知識和信仰去做支撐,才會來者不拒,相信這些愚昧的東西并以此為支柱。
(二)孟蘭節(jié)放河燈、娘娘廟大會—精神生活的荒蕪和寂寞
呼蘭河的人們對死亡沒有恐懼,就像他們對活著本身也沒有珍視一樣。除了鬼神之事,他們再無別的可以稱作為精神世界的其他東西,因此他們的精神世界是荒蕪一片的,空虛寂寞。
孟蘭節(jié)在呼蘭河是個盛大的節(jié)日。小說用了很大篇幅來描繪孟蘭節(jié)放河燈的盛況,熱鬧非常。孟蘭節(jié)是俗稱的“鬼節(jié)”,書中說放河燈是為了讓孤魂野鬼拖著燈去投生。這承載著呼蘭河人們的善良心愿,但卻是寄托在鬼神之說之上,這樣的節(jié)日,跟如今承載著美好傳說、繼承著良好風俗的節(jié)日和民俗活動相比,是缺乏內涵的。看河燈的人們的心態(tài)也是發(fā)生了一連串的變化:“從上流的遠處流來,人們是滿心歡喜的,等流過了自己,也還沒有什么,唯獨到了最后,那河燈流到了極遠的下流去的時候,使看河燈的人們,內心里無由地來了空虛。”看河燈并不是積極向上、有趣的民俗活動,也無法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感動感染或是慰藉,畢竟它立足于封建迷信舊習俗之上,也不像如今的清明節(jié),至少寄托了對亡人的思念和美好的希望祝愿。娘娘廟大會是呼蘭河另一個獨特的節(jié)日,大家去娘娘廟祈求多子多孫。在這個節(jié)日中,仍舊是場面大過于祈福本身,也反映出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這樣的節(jié)日盛況空前,反映出人們精神世界的荒蕪空虛,沒有其他更有意義的活動,聊以慰藉枯燥的生活。
(三)野臺子戲—女性單調的生活和被操控的命運
人們以看戲為由頭,聚在一起,有不同的目的和消遣。女人精心打扮,盛裝出席說明她們平時這種機會不多,平日里依附于男人,重復著冗雜無趣的生活,在這個時候才得了空,成了主角,借著野臺子戲,出來看看姐妹們,也讓別人看一看,互相比一比。但她們的命運并不會發(fā)生什么改變,等戲唱完,她們還是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一切都沒什么改變.......即使遠嫁的女兒向母親哭訴自己的不幸,母親也只是說“這都是你的命,你好好地耐著吧”。這些女人,都處于被動的地位,服從于封建男權,因為她們之前的世世代代都根植于這樣被封建男權控制的土壤之中,她們不懂得反抗,即便反抗,也會被當做另類。呼蘭河的女人們,依附并屈服于男權,被掌握、被操控,這是封建頑疾之下,呼蘭河女人平淡無奇且悲哀的命運。
三、精神荒原中的點點綠洲
以上兩部分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代表了呼蘭河大部分人的精神狀態(tài),是愚昧、麻木、虛無、可笑的,但并非所有呼蘭河的人們的精神世界都是如此,例如“我”、爺爺、馮歪嘴子這些角色都是呼蘭河里特殊的形象,讓我們看到了呼蘭河人精神荒原中的點點綠洲。
“我”是清醒的,一邊懷念呼蘭河的樸素和溫情,懷念它的一條街道一個泥坑,一邊冷眼看著它的蒼涼衰落,麻木和無知。“我”也極具智慧,有一種“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大智慧。表面淺淡地娓娓道來,但對于呼蘭河的一切,“我”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認知。也正因為“我”的思考,才不甘于俯身于這樣的生活之中,“我”敢于叛逆,有獨立的人格個性。 “我”能夠以孩童的角度和語言洞察事情的真相,是清醒的,同時也是克制自知的。
爺爺明理和善,不同于愚昧麻木之眾,是小說中被提及次數(shù)最多的人物,不僅因為爺爺是最疼愛“我”的人,不重男輕女,給了“我”的童年最溫暖的回憶,同時也因為爺爺是一個拿主意的人,受人尊敬。爺爺在呼蘭河應該是很有地位的,這從書中很多地方都有跡可循,但他不擺架子,無論是對老廚子還是有二伯都很客氣,體現(xiàn)了他有修養(yǎng),并沒有一般地主的惡劣習氣。爺爺教“我”詩歌,說明他有文化有知識并且不反對女孩子讀書,這樣的眼界在呼蘭河已是難得。更值一提的是,當他知道老胡家打小團圓媳婦,折磨她的時候,并未袖手旁觀,一直告誡他們不要打她,在告誡無果時決定讓他們二月搬家,說明爺爺很有正義感。爺爺雖然清醒,但他還是沒有和大環(huán)境抗爭,這這個形象的局限性。
馮歪嘴子是整部書里面最打動我的角色。他出身卑微,命運坎坷,但他勤勞、不放棄不沉淪,努力生活。在婚姻被包辦的社會背景下,他和王姑娘自由戀愛,敢于追求愛情和幸福,勇氣可嘉。他不向磨房女主人低頭,為妻兒另尋住處,妻子病中對妻子很好,體現(xiàn)了男人的擔當。妻子去世后,別人都覺得他要撐不下去看他笑話的時候,他沒有一蹶不振,頑強地堅持下來了,照顧孩子,堅強地活著,不放棄努力,這讓讀者看到在落后蒼涼的呼蘭城里,也有拼搏抗爭的精神,與命運和災難抗爭,與封建思想抗爭。他的孩子發(fā)育的不好,但當他的孩子會走路后,他還是滿足地笑了,人物形象在這里再次得到升華,他有著寬闊的胸懷和一顆知足感恩的心。所以,馮歪嘴子雖然在呼蘭河是被別人嘲笑指點的,但他在精神和人格甚至人生追求上,都勝眾生太多。
結語
呼蘭河的人們大多數(shù)是樸實,循規(guī)蹈矩的,但他們守舊迷信、愚蠢麻木、自欺欺人,總體上是僵硬病態(tài)的,他們的精神世界是虛空荒唐、甚至他們有畸形的心理,但仍有跳躍出來的人物,他們清醒、勤勞、有追求,成為呼蘭河這片蒼老土地精神荒原上的點點綠洲,散發(fā)著希望的光芒,也讓呼蘭河這片土地在作者的心中充滿溫情,散發(fā)著特別的魅力。
注釋:
[1]榮格:《論分析心理學與詩的關系》
[2]百度詞條:“集體無意識”的學說發(fā)展。
[3]史杰:《論<呼蘭河傳>中的天然式生存》,載《作家雜志》,***年**期。
[4]繆軍榮:《看客論——試論魯迅對于另一種“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
[5]陳勤建:《民俗——日常情景中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載《民俗研究》,2007年03期。
[6]“跳大神”:百度百科詞條。
參考文獻:
[1]王金成:《精神反樸與靈魂挽唱——<呼蘭河傳>新論》,載《北方論叢》,2003年。
[2]李莉:《論<呼蘭河傳>的民俗內涵》,載《呼蘭師專學報》,2000年3期。
[3]馬芳芳:《從民俗鏡象看<呼蘭河傳>眾生的性格與精神世界》,載《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2008年第10卷,第3期。
[4]劉麗麗:《"性格"人物與"群像"人物——談蕭紅<呼蘭河傳>中的人物形象》,載《青年文學家》,2011年6期。
[5] 榮格《論分析心理學與詩的關系》 ,王艾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6]百度詞條:“集體無意識”的學說發(fā)展。
[7]史杰:《論<呼蘭河傳>中的天然式生存》,載《作家雜志》,2010年第10期。
[8]繆軍榮:《看客論——試論魯迅對于另一種“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
[9] “跳大神”:百度百科詞條。
[10]陳勤建:《民俗——日常情景中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載《民俗研究》,200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