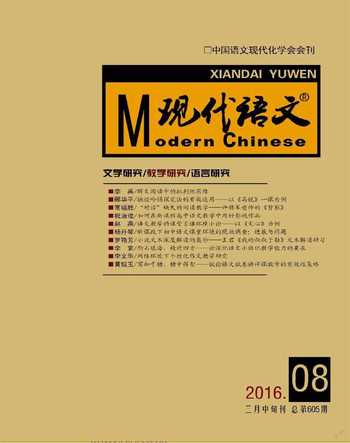小論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知北游》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莊子為何以天地為美?莊子“美”的標準是由其思想的核心“道”所決定的。“道”是自然無為的,因此在莊子看來美也必須是自然無為的,自然無為即是美,而且是至美。《天道》中說:“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靜而圣,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虛靜、恬淡、寂漠、無為”是“萬物之本”,同時也是美之本。因此,萬物所存的“天地”也就具有了自然無為的根本特征,從而成為了美的集中代表。《莊子》中曾多次出現對“天地之美”的贊頌:“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1]“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2]
天地不但美,而且是“大美”,是至美。莊子對“美”和“大”作了區分,“美則美矣,而未大也”,他認為“大”高于“美”。之所以如此,在于“大”體現了“天道”的無為而又無不為,體現了不為一切有限事物所束縛的最大的自由。而在莊子學派看來,“人的自由的表現正是美”[3]。莊子所贊頌的自然無為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悠游于這廣闊無垠的背景之中。《逍遙游》和《齊物論》中各有一段對“神人”的描寫: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
“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傷,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天地”、“四海”為莊子所創造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呈現的空間。而“神人”之所以與廣闊天地共現,原因不僅在于只有天地之大才能襯托出“神人”、“至人”擺脫一切束縛的最大自由,更在于這些“神人”、“至人”是通過“吾喪我”將自身化于自然之中。他們舍棄了社會性,以自然無為作為人世生活的根本原則,達到與大自然融通相與的境界,即與自然、宇宙相同一,“與天為一”(達生)、“與天為徒”(人間世)后,才獲得了絕對的自由,成為“神人”、“至人”的。
莊子有云“夫道,覆載萬物者也”(天地),道生萬物而又附著于萬物之上,宇宙萬物因有道才得以產生和發展,正所謂“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知北游)。由于道在萬物,而“萬物與我齊一也”由此觀之,人是可以通過對自然的觀察去了解道,尋求美的。并且在人為物役的世間,通過體察自然而求得美也就成了唯一的途徑。人只有通過“原天地之美”(知北游)、“判天地之美”(天下)、“法天貴真”(漁父)才能使自己“不拘于俗”而“備于天地之美”(天下)。由此可知,天地因符合自然無為的“道”而“大美”,人若使自身合乎了自然無為,那么也將獲得美,成為自由無待的“神人”、“至人”。
如上所說,人之美可由“備天地之美”而得來。那么美是否可為人所創造呢?有一種觀點認為莊子“否定美和藝術,否定人的技巧智慧,要求從根本上消滅人的認識能力,包括審美能力”[4]。的確,莊子認為禮樂文章有失性命之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天地),要“塞師曠之耳”、“膠離朱之目”(胠篋)使人復歸其真。但《莊子》同樣也有“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達生),以人力而造出“天工”之作的故事。那么莊子對美的創造到底是持什么態度呢?格式塔心理學派(gestalt)在美的創造問題中曾提出“同構說”,用主客體的同構來解釋美的根源。他們認為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有一種結構上的對應,因為這種對應在人的大腦引起了相同的電脈沖,所以人們在特定的對稱、比例、節奏等因素影響下,會產生相應的知覺感受,從而獲得美感,即人的內在情感與外界物質的審美特質的某種契合。這種契合源于人類悠久的生產勞動,人類在長期的實踐中,主體日漸有了普遍合規律的形式,實踐客體的自然秩序、形式規律也漸為人所熟悉、所掌握,這些自然事物也就與人類產生了同形同構,于是具有了審美性質。[5]這一觀點與莊子的不同之處在于它視美存在于自然與人的互動中,而莊子則強調必須舍棄人之為人的社會性,使自然性完全不受社會性的影響,只有徹底融入自然宇宙之中才可獲得美。但他們對獲得美的過程的認識卻有著相似之處,都認為人要在長期實踐中把握住自然的規律,這樣才能吻合客觀的自然,從而獲得美。《天運》中的“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一般被看作是說明應時而變的道理的,但從中也可看出美不能光看表象而要深究其所以為美的規律。莊子在講悟道時常說“坐忘”、“心齋”,但這些都是有前提的,要“有數存焉于其間”。這與后來的禪宗在日常生活中體道有相通之處。《莊子》的“庖丁解牛”一段即可看為是這一思想的體現: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余地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庖丁在長期的解牛實踐中透徹把握了客觀對象的規律,解牛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從而能達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的與道相合的境界,于是“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余地”獲得了完全的自由,進而形成了“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的美感。當然這里的規律不止包括平常所說的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還包含著人與自然之間那種不可言傳的契合,這種契合即使在今天、在同構學說中依然是無法用科學解釋的。總之,在莊子看來,合于“天地之美”的規律是人創造美的前提。對于它的把握必須通過個體的親身實踐,因為這種感受是直觀的、感性的,無法經由他人來獲得,只有自身能有“與道冥同”的體會,能有“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余地”的自由感受。“這種自由形式,才是美的創造或美的境界”[6],于是庖丁可以“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從中得到至樂的享受。《天道》中進而將這種體會與語言相聯系:
輪扁曰:“……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
輪扁也是技進乎道的典型,他的“數”可以看作是數十年實踐所沉淀下的無意識,不可以喻其子。這也從一方面說明了莊子為什么提倡“不言”。關于規律的體悟、契合是純個人的感受,而語言是人們交際的公共工具,有群體所共同遵守的普遍規則,因而,莊子認為要真正把握那種有規律的契合,依靠這種共同遵守的規則是不可能的,只有憑個體的親身感受、領悟、體會才能得以實現。因此,莊子中關于“言不盡意”的表述隨處可見,諸如“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天道)。從另一方面看,莊子認為雖“言不盡意”但還必須依靠語言,這一矛盾決定了他“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天下)的風格。在莊子看來,語言對感受自然之美是有妨礙的,對人也是有束縛的,也是需要人擺脫、突破的對象。他期望以自己特殊的言語表達出自己所意識到的“大美”,在他看來,正是通過這些荒唐之言使人們沖破原來言語規范的束縛,去把握、體驗真正的“大美”。
綜上所述,“天地”因其“無為無不為”而大美。人則一方面因“備天地之美”而使自身能“游于無窮”,獲得完全的自由和美的享受;另一方面因“依乎天理”而能“以天合天”創造出“驚猶鬼神”的似天工之作。“天地之美”因其自然無為、“自美不美”而不愿言,因其混沌無限、變化無常而不可言,創造美的過程也因其強烈的個人性、感受性而無法言說。由此,天地雖有大美但不愿言、不可言,也無法言。
注釋:
[1]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北京大學哲學系教研室編.中國美學資料選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張利群.莊子美學[M].南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 .
[4]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5]李澤厚.美學三書[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6]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白雪 北京外國語大學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