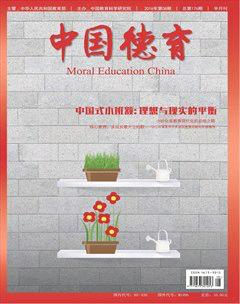治事以畜德
1949年初,年屆七旬的柳詒徵先生,將國學圖書館珍貴的藏書清點造冊、整理裝箱,送進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地庫封存,然后辭去館長職務。五十年間風云變幻,柳先生目睹滿清、北洋政府、國民黨政權的覆亡,更以切膚之感,經(jīng)歷文化形態(tài)的劇烈轉變。抗戰(zhàn)期間,柳先生任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研究所導師,為研究生講授“教授進修課程”“比照西學西史剖析國史之精義”,撰成《國史要義》凡二十萬言。《國史要義》一書為柳詒徵先生晚年重要著作,與《中國文化史》一起,奠定了其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地位。
《國史要義》何為而作?
中國古代雖有典制之學,但并無撰述專題歷史的傳統(tǒng),“學術既不專門,自不能發(fā)達。”柳先生在日本學風影響下,較早的接受現(xiàn)代學術分科,并在國內引領風氣。1948年柳先生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成為國內史學界僅有的兩位既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又是教育部部聘教授的學者,另一位是陳寅恪先生,學界有“北陳南柳”之稱。
柳先生出身經(jīng)學世家,少習經(jīng)史詩文,對傳統(tǒng)文化飽含熱忱。但他并非盲目排斥新學之人。他晚年曾這樣反思:“我數(shù)十年來,能以舊學貫通科學方法,乃是與許多留學生相處得的益處。”可我們觀察《國史要義》的思想內涵,完全以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為本位,與“中體西用”之說大不相同。柳先生四十年代初在給學生王煥鑣的書信中說,“洋奴之習不蠲,中夏之道不明”,已將“中夏之道”作為治學目標,此乃柳先生一生學術之大轉變。
這種思想傾向的轉向,源自于感觀上的切膚之痛。抗戰(zhàn)爆發(fā),南京淪陷,柳先生押送圖書避禍興化,又輾轉江西、貴州等地,期間之艱苦不難想象。1937年冬柳先生有《雪后泛舟入興化城》詩,曰:“江南江北率土焦,流亡載道淚如潮。只堪畫里逢佳境,璧月瓊花廿四橋。”以悲涼之筆觸,描繪日軍侵略后民眾流離失所、城市破敗的慘景。在流離顛簸之中,柳先生主動反思文化的演進,作了《國史要義》一書。近十年之后,柳先生回憶“詒徵治史學數(shù)十年,以中人之資質,值新舊之演變,每欲有所貢獻于世,恒苦學力不足,則隨時世之要求與學校學者共同研究……避兵入蜀,居中央大學為《國史要義》,私冀世界史家明了此數(shù)千年中吾國史事之真相已而,不敢有所論斷也。”他希望借《國史要義》一書,將本國史學固有的價值體系闡發(fā)清晰,在近代中國每況愈下的社會變革現(xiàn)實面前,作出自己的思考,推動傳統(tǒng)史學的發(fā)展。
以禮治史,申述史原
熊十力說《國史要義》“言史一本之禮,是獨到處。”這里的“禮”,主要指的是《周官》所述之禮。柳先生將“禮”的淵源與功用解釋為兩個方面——“司天”與“治人”。二者相互補充,史出于禮,禮本于天,“從民俗而知天,原天理以定禮。故倫理者,禮之本也;儀節(jié)者,禮之文者。”禮,是天道人倫在現(xiàn)實中的具體落實。“從民俗”則可“知天”,則天道必淵源自民俗,天道必以人道為根據(jù)。“原天理”方可“定禮”,則禮義又必然超越一般民俗,人道又必須上升為天道方可成為人倫大綱。既曰“司天”,則掌禮之史官,其權力乃大于世俗之一般行政權力。柳先生推論,“爰有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法,其初以備遺忘,其后以考得失,相勉從善,屈己從人。而史之監(jiān)察權,由是樹立。”史官著書,雖未必可以沮當世人君之暴行,而必能錄其罪惡以暴之于后世。所謂青史昭彰是也,此史學之可以為德義之府也。
禮學為儒學之核心,《論語》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于文,指廣泛的吸納知識,而各種知識的樞紐,則是作為天道人倫大綱的禮學。柳先生在《國史要義》中多次闡釋“言史一本于禮”的觀念。而“以史言史者未識史原,坐以儀為禮也。”禮,不是儀式,而是在貴族政教傳統(tǒng)中,鍛煉出的歷史文化優(yōu)先意識。這種意識在支配歷史學的德性內涵時,強調的是歷史進程中精神力量的偉大,尤其是強調政教文化所形成的規(guī)范意識,這一規(guī)范意識給人以尺度感,可以阻斷人類社會的墮落與腐化。故柳先生自信“吾國以禮為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歸之于人之理性,非茍然為史已也。”
柳先生一再申明史學與政教之間的關系,“禮由史掌,而史出于禮。則命官之意,初無所殊。”禮的施行與記錄,由史官掌握,史官的思想觀念由禮支配,“古之施行、記述,同屬史官……是則政宗、史體,各有淵源,必知吾國政治之綱維,始能明吾史之系統(tǒng)也。”作為施行、記錄的“史”與作為政教原則的“禮”本是同源伴生,“故禮者,吾國數(shù)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歷史編纂的基本價值維度,也是圍繞禮而演進,“史家全書之根本,皆系于禮。不本于禮,無以操筆屬辭。”
立國立人,申述史義
《國史要義》一書以“義”為題,柳先生堅信“史之義出于天”,治史必須明“史義”,除非“人性必變而惡善善惡,吾國史義,乃可摧毀不談;否則無從變更此定義也。”以善惡為史義,反對將實證研究看成史學全部,或者以史學為自然科學。
實證史學在我國淵源已久,清初顧炎武、黃宗羲倡導實學,乾嘉學派將考史之學發(fā)揮到極致。近代以來受德國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梁啟超、胡適等人認為,向西方實證主義史學靠攏,才是中國史學的出路,力圖將歷史科學化。柳先生并不反對這種科學化的主張,然而,當實證史學的空氣完全彌漫學界的時候,柳先生表示出了強烈的不滿,這種不滿在《國史要義》創(chuàng)作的時代,被視作頑固的守舊派。1942年在致學生王煥鑣的書信中寫道,“今日號國史者,開卷即破銅爛骨,烏知圣哲之大義。教師箸書者若此,又何望于學生及民眾。故洋奴之習不蠲,中夏之道不明。”這里“破銅爛骨”,指的是因甲骨的發(fā)現(xiàn)和殷墟的發(fā)掘,人們只注重地下出土之實物如甲骨文、金文文獻,認為它們能夠證實或證偽古史,而將古代經(jīng)學系統(tǒng)中所構建起來的上古歷史框架,視作“傳說”乃至“偽造之史”。清代閻若璩撰的《尚書古文疏證》認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堯所授舜之十六字心傳,出于偽古文《尚書》之《大禹謨》,根底全失。在柳先生看來,古史辨運動的伎倆并未超出閻若璩,而學術水平反遜于潛丘。攜“洋奴”實證之技,壞“中夏”固有之道。
對于晚清民國的學術,柳先生同樣不滿意。他說,“《書》之失誣,《春秋》之失亂。則清季及民國學者,罔不病此。”以“誣”與“亂”評價晚清民國的學術,認為梁啟超、胡適等人“非儒謗古,大言不慚”;在《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一文批評顧頡剛不明說文義例,妄說大禹為蟲,“就單字只誼,矜為創(chuàng)獲,尠不為通人所笑”。以柳先生為領袖的南雍學派,在近現(xiàn)代學術史上,抵制疑古思潮最力,從學力和學理上來講,也最為成功。在柳先生看來,疑古和謗經(jīng)不過是跳梁之技,并不值得推崇,他特別在意的,仍是史學義理與文化精神的安頓。
為矯正“史學即是史料學”“實證即是史學全部”的偏差,《國史要義》一書,重申“史學所重者在義也。徒鶩事跡,或精究文辭,皆未得治史之究竟。”在事、文、義三者之間,強調“史義”最重。史義的標準是什么?柳先生以“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來形容史義。即史學所承載的是價值指向和精神追求,它沒有必然的剛性條例,只有恰當?shù)木S度和指向,也即是尺度。“擇兩端之中,明相反之義,而后可以治經(jīng),可以治史,而后可以無適無莫,而立人之義于天下。”在學術上,柳先生主張學習古代史著的精神義理,反對執(zhí)念,反對偏頗。
因史返經(jīng),申述史德
前文所述,對于疑古思潮,柳先生并沒有極力抵制,只是重錘響鼓得寫了一篇涉及《說文解字》的文章,薄示懲戒,點到為止。但是柳先生是民國時代為數(shù)不多的學者當中,以治史“心術”來衡量疑古思潮的人。柳先生引龔自珍《武進莊公神道碑銘》曰:“辨古籍之真?zhèn)危瑸樾g淺且近者也”。這不是一種情緒化的借古諷今,而是飽含了學人對于古典所建構出的價值體系崩解的憂慮。
一切價值的源泉,皆來自既有的文化與歷史,以一種歷史文化優(yōu)先的意識。考量現(xiàn)實的不完滿與德性的崩馳。柳先生反復申明“吾國圣哲深于史學,故以立德為一切基本。”以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倫理為基本出發(fā)點的史學,向來秉筆直書、不畏強權。“故治吾國史書,必先知吾自古史官之重信而不敢為非,而后世史家之重視心術,實其源遠流長之驗也。史職重信,而史事不能無疑。故《春秋》之義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對史書的懷疑,尤其是類似于“層累的制造古史”這樣的觀點,若作為基本思想用于指導歷史文獻的考據(jù),則是對一代又一代史學家德性的懷疑。中國古代史學最重史德,若誣以作偽,則齊之太史、晉之董狐,仁人君子蹈死守正之心,一筆抹殺,實堪嘆惋。
有鑒于此,柳先生特別警惕傳統(tǒng)史學在現(xiàn)代學術轉向之時的削足適履、進退失據(jù),“知人論世,在求古人之善者而友之,非求古人之惡而暴之,或抑古人之善而誣之也。”對于近代史學轉向中的德性喪失與史學亂像,柳先生這樣評價:“秉心厚者,則能尚友而畜德;賦質刻者,則喜翻案而攻人。”他反復強調,追問史學研究問題意識中本身所彰顯的“用心”與“目的”,才是史家本身的價值取向。
柳先生還說,“史籍之用,亦視學者之用心何如。用之當則可為人類謀幸福,為國家臻治平。用之不當,則可以啟亂飾奸,如王莽、王安石用《周官》之不得其效。而騖博溺心、嘩眾取寵者,更無論矣。”其中“騖博溺心、嘩眾取寵”顯然是針對當下而言,史學究竟是為“成就事業(yè)”“求知求真”還是“修德修身”?他反對將史學作為對象,成為個人“建功立業(yè)”陣地。若以“事業(yè)心”而故意“索瘢吹垢”,苛求古史古人,則必然引發(fā)史學倫理的崩潰。
何謂史德?柳先生在《國史要義》一書中,借章學誠“敬、恕”二字,作為史德之內涵,并加以發(fā)揮:“敬即慎于褒貶,恕即曲盡其事情。”慎于褒貶,則不輕發(fā)議論;曲盡事情,則以同情理解之心態(tài),以當時當?shù)刂閯荩告付罋v史事件之各種原委,“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真乃史德也。”涵養(yǎng)“敬、恕”之心,以治史之經(jīng)驗,培養(yǎng)德性,也就是“學者之先務,不當專求執(zhí)德以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
治史畜德,因史轉人
在柳先生眼中,歷史學是本乎至誠、達乎人倫的精神源泉。他認為,“史出于禮,為國以禮,為史以禮。”并且相信,吾國政教文化,能歷經(jīng)數(shù)千年而綿延不斷,就在于以禮為核心,以史為載體的史學精神的傳遞。
《國史要義》一書以《史化》為結,并云“史之為化,有因有革”。柳先生寄希望于“史能轉人”,人須“大其心量”而讀史,人因讀史而“畜德”“明理”,最終“合天下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就治學之主張與目的而言,柳先生與新儒家接近。然而從治學的路徑而言,柳先生又與熊十力等人不同。新儒家是由性理之學出發(fā),探尋儒學的前途,其研究范疇仍在道體、本體,知、行之間,其目的仍在由內圣而開出外王。柳先生則以史學為出發(fā)點,以儒學的發(fā)生時代為切入點,拋開性命之辨,丟開天人心性之學,由讀史而直接認知中國文化之內涵,再反身求仁,貫通儒術。
與眾多二十世紀知識分子悲觀的情緒不同,柳先生并沒有因文化的出路問題,而深思焦慮、繞室彷徨,而是以一種自信的姿態(tài)展望,“過去之化若斯,未來之望無既。通萬方之略,弘盡性之功。所愿與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寫下這一段話時,正值抗日戰(zhàn)爭后期。無論外部環(huán)境多么惡劣,他的內心深處仍能保持一份凝重的莊嚴。古典精神支撐下的樂觀,歷覽成敗之后的釋然,于自信之外,彰顯的是學者人格之魅力。
【武黎嵩,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李 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