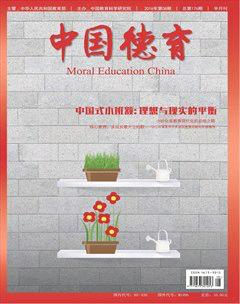娛樂文化對青少年道德成長的消極影響與對策思考
必須在很早的階段,當邪惡還沒有主宰思想時,就諄諄教誨德行。因為如果你不在田地里播撒良種,他就會長出最壞的野草。
近十幾年來,娛樂風愈刮愈烈,加上新媒體不斷推陳出新,娛樂生活毫無爭議的成為可以充分吸引公眾眼球的焦點。尤其是近年來,除了傳統的紙質媒介,如動漫畫報、科幻畫報之外,電視媒介更加迅猛發展,“非誠勿擾”“中國好聲音”“最強大腦”“爸爸去哪兒”等知名娛樂節目席卷而來,開辟了電視銀幕的新時代。而在網絡世界,不僅有大量原創的網絡流行歌曲火爆網絡,還有各種娛樂網站爭奇斗艷,更有各類網絡游戲占據著虛擬時空的半壁江山。傳統媒體和各種新媒體已攜手給大眾提供了一種無法選擇、無法抗拒的娛樂盛宴,我們視之為“娛樂蔓延”現象。
鋪天蓋地的娛樂文化形成了教育發展的一種外部新環境。像所有的文化現象一樣,娛樂也起源于社會實踐,它在與其他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不斷發展和完善,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即娛樂文化。娛樂的本質,“就是把生命(存在)游戲化,它尋求的是短暫的快感和歡樂,并懸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體相關的核心價值。”[1]按照現代人的觀點,“娛樂本身并不屬于價值的范疇。它既包括了消遣又包括了迫切的精神需求的滿足。然而,無論重要與否,它總是心靈的產物。”[2]可是,娛樂是否真的與價值無關?
娛樂文化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實然存在著積極和消極兩維。本文更多以“問題”發現為切入點,深切關心娛樂文化可能帶給青少年道德成長的消極影響,并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向。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3]4波茲曼的這段話,表達出與本文十分相似的焦慮。
一、娛樂文化已構成一種深刻影響青少年成長的“擬態環境”
“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 theory)概念是由美國著名傳播學者李普曼提出的。“擬態環境”是指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后向人們提示的環境。[4]李普曼認為,人們再也不是憑借直接經驗去認識客觀環境,而是通過大眾媒介提供的信息環境即“擬態環境”去把握它。一個不為教育者關注的真相是——對青少年構成分心刺激的,并不是不斷改朝換代的電視、電腦、智能手機……而是隱藏在其背后、萬變不離其宗的娛樂文化。從這種意義上說,娛樂文化已構成深刻影響青少年成長的一種“擬態環境”。
娛樂文化借助多媒介形式,以壓倒性的姿態構成了一種新型的社會和文化環境,它將所有嚴肅的、輕松的,有著不同功能的社會議題都涂抹上一層戲謔的、去中心化的、非主流的色調,再輔之以各類信息的形式進入到大眾視野之中。如此,信息的虛實并不是最重要的,信息以輕松愉悅、無關痛癢的供給方式來呈現成為重要的新常態。而當娛樂文化成為信息生產背后的“潛規則”時,娛樂文化作為一種“擬態環境”事實上就成立了——青少年成長的“媒介環境”等同于“娛樂文化”,娛樂成為認識一切、表達一切的方式,并構成了人類行動的幾乎全部基礎。正如波茲曼所說,“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了表現一切經歷的形式”。[3]114
這是一個媒介娛樂化的時代,快感生產和消費是當下娛樂行為的主體,窺視、游戲和狂歡是其典型形式。大量的娛樂節目以窺視他人的生活、心理和身體為生產素材;以各類游戲節目作為創造歡樂的載體;以各種選秀節目制造出大眾狂歡的場景,這些典型形式不可阻擋地對喜歡新奇事物的青少年的成長產生著深遠影響。娛樂構成了青少年生活的邏輯和內容,青少年習慣性地在娛樂精神中走近各類信息,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由此,娛樂文化沖破了各類媒介技術,讓娛樂功能成為主導現時代所有媒體的“媒介態”,以此遮蔽甚至代替了各類媒體在過去彰顯過的政治、文化和商業等功能,娛樂文化作為一種“擬態環境”,牢牢控制著青少年價值世界的樣態和色彩。
二、娛樂文化使青少年的道德成長走向個體的疏離
娛樂文化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宏大“擬態環境”,它不僅僅是輸出圖像、文字、音樂,更是用這些娛樂形式改變了置身于其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娛樂文化多依賴表演藝術,而表演需要的只是觀眾,而非思想者。當青少年越來越少地思考自己、他人、自然、社會和世界時,將會導致青少年與外界關系的疏離,同時這種疏離還會發生在個體內部,表現為內在世界中個體對自我的疏離。
(一)遠離思考的青少年:被動接受信息的“新式文盲”
觀察娛樂生活中的青少年,我們發現了特征鮮明的“后兒童時代”現象——一群本該漸漸長大的孩子卻在剛剛告別童年的某一天突然停止生長了,三十多歲的人仍把“我們女孩子”“我們男孩子”時常掛在嘴上。他們膜拜《快樂大本營》主持人何炅式的娃娃腔、范曉萱式的“脖子扭扭屁股扭扭”、阿雅式的“咕嘰咕嘰咕”、周星馳式的“無厘頭”文化……人們不禁驚嘆,嬉皮士已經老了,雅皮士也落伍了,頑皮士來了!
對于這一狀況,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有有識之士對此表示過擔憂。克里斯托弗·賴許曾尖銳地指出,“我們文化的危機產生于一個虛妄信念:我們的社會僅僅需要有一定的頭腦,去創造和操作機器,還要有足夠的新式文盲,以便對付其他的機器——我們大眾媒體的機器——以便利用。這或許就是人才方面最昂貴和最浪費的社會形式。”[5]428賴許十分明確地指出了新式文盲與大眾媒體的關系,“現代社會制造了各種新式文盲。大家逐漸發現,自己無法自如而精確地運用語言,無法重溫本國歷史的基本史實,無法進行合乎邏輯的推論。”[5]429由賴許的這段經典的擔心,我們了解到娛樂時代給各個國家的人才培養都造成了相似的困擾。人們普遍擔心娛樂文化會降低人們累積了若干世紀的文明水平,甚至會生產出新式文盲。游走在現代社會中的新式文盲習慣被動地接受訊息,被動地接受下一個生活瞬間中的偶遇或安排,而不是主動地思考問題和尋求新的發展機會。于是,令我們深感擔憂的是,當青少年遠離了思考,他們何以在紛繁復雜的日常生活中鍛煉自己的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能力,又如何磨礪出堅毅的道德品志?
(二)充當看客的青少年:受控于“惰性思想”的道德冷漠者
娛樂文化讓青少年習慣于被動接受海量的信息,這導致現實生活中不斷發酵和蔓延出“惰性思想”。惰性思想會左右青少年遇事做事的狀態,在事情面前,青少年持一種普遍的退縮態度,逐漸遠離了本性中原有的勇氣和擔當,習慣性地充當“看客”。無休止的媒介爭論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青少年的“惰性思想”,諸如在“老人倒地要不要扶”的問題上,青少年逐漸失去了關心和耐心,以及彌足珍貴的道德勇氣。
湖南衛視晚間7:30新節目《噗通噗通的良心》是一檔發現美好的社會道德實驗節目——通過還原社會新聞中的某個事件,以尋找在當別人身陷困境時能主動伸出援手的溫暖的人。節目將新主題鎖定社會敏感話題“老人扶不扶”。測試當天,節目組安排了一名專業的老人演員。測試開始后,路邊正好有一對情侶經過,看見摔倒的老人,男生比較警惕,冷眼旁觀暗示女孩不要管,女生卻充滿愛心毫無顧忌,以瘦弱的身軀努力攙扶起老人,還要將老人一路護送至附近診所。事后,演員爺爺和導演組大發感慨夸贊連連:“真是個好女孩啊。”[6]
這是一個利用媒介做積極價值宣傳的電視節目,盡管如此,仍然改變不了其所具有的“娛樂化”的本質。正像波茲曼試圖努力例舉一些電視節目中的“嚴肅”話題,但最終發現仍舊擺脫不了娛樂化的魔咒。“娛樂是電視上所有話語的超意識形態。不管是什么內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視角,電視上的一切都是為了給我們提供娛樂……我們知道‘新聞是不必當真的……播音員的姣好容貌和親切態度,他們令人愉悅的玩笑,節目開始和結束時播放的美妙音樂,生動活潑的鏡頭和絢麗奪目的各類廣告——這一切都告訴我們,沒有理由為電視上的不幸哭泣。”[3]114-115
“它們不過是一些新聞和故事!”“社會這么大,發生這些事太正常了。”“即使我不幫助,也會有其他人相助的。”這些彌散在青少年群體中的想法,像一張巨大的網,不僅束縛了青少年的道德情感,更熄滅了青少年本應有的道德勇氣,以及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道德行動力。無處不在的娛樂精神和娛樂文化,讓許多青少年不斷長大、不斷冷漠,成為一群受控于“惰性思想”的道德冷漠者。
三、娛樂文化下的德育選擇
如何減輕娛樂文化對青少年道德發展所造成的困擾呢?盡管娛樂文化帶給了我們諸多挑戰,但它不完全只是危機。對于道德教育而言,娛樂文化像一朵朵罌粟花,它嬌艷欲滴的花朵讓走近它的人都沐浴在芬芳中,但同時,罌粟花的果實又會讓人們步入迷途。在這則比喻中,罌粟花的美麗是道德教育應當看到娛樂文化中也有美的地方,罌粟花的危害是需要我們立足于教育來做更多“文化”上的治理。
(一)道德學習是一種“修行”?
娛樂文化是一種文化現象,反映了文化生產者既定的思想、情感和行業模式。事實上,道德教育也是一種文化生產,也涉及到符號的運用、交換以及傳播。只是道德教育依賴的技術是口耳相傳的引導,而娛樂依賴的技術是廣播、電視、智能手機等等。我們發現,娛樂之所以能吸引青少年自愿卷入其中,可能并非僅僅是技術上的差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娛樂文化的本質是能帶給人快樂和自由,是一種所謂的“娛樂感”。
娛樂感,首先是一種感知到的自由,其次是誘發個體對行動的渴望。具備了這兩點,娛樂感便自然而然地讓置身于其中的人處在一種“自由”“滿足”的精神狀態中。道德教育應如何借鑒娛樂文化中的“娛樂感”元素?我們可以從改變道德學習的狀態做起。日本學者佐藤學十分贊賞圣·維克多修道院一位名叫休的人關于學習的論點。在休看來,“學習”是指體悟和認識自然本性與自然秩序,認識自身的本性。通過這種學習活動,認識自己是不完善的存在,從而治愈自己的欠缺所在,成為更完善的存在。也就是說,不是借助知識去控制和支配外界與他人,而在于治愈并豐富自己內部世界所欠缺的部分。這是一種“修行”的學習、“矯治”的學習。所謂學習就是自我的內心世界之“旅”,是自身智慧的“上下求索”,是同自身內心世界的對話。[7]道德學習若能貼近休所言的“修行”,實現道德學習者不斷進行與自身內心世界的對話,那么,這何嘗不是道德教育中對“娛樂感”的一種捕捉,也能夠讓道德學習者體會到“自由”和“滿足”。
提倡修行式的道德學習,一方面試圖改變的是道德學習者的“內環境”,另一方面則是期待能夠進一步優化學校、家庭、社會進行道德教育的方式。修行式的道德學習,是希望能夠讓道德學習者敏感于自身的道德需要,自愿審視和澄清一些道德困惑和價值選擇,這既能帶給個體類似娛樂感的“自由”與“滿足”,同時又能促發青少年道德發展所需要的思考力和行動力。調動了道德內需的道德學習,會讓青少年養成運用心和腦進行思考的習慣,并享受這種習慣,進而建立起自己與外界、自己與自己之間人性、完整的聯結。
(二)家庭能否成為另一個“擬態環境”?
在教育學邏輯中,我們期待的積極影響主要來自三種外部環境:家庭、學校、社會。其中,學校主要是幫助兒童啟智和促進社會化發展的場所,青少年身在其中會更多受到“他律”的學習文化的影響,因此青少年在學校生活中建立的各種關系相對而言是一些弱連結,包括與同伴的交往。而在社會方面,社會又日趨為娛樂文化這一“擬態環境”所包圍。于是,我們寄望家庭這一陣地,期待新時期下能更多釋放和發展家庭的道德影響力。
歷史發展表明,家庭所能夠給予青少年的道德影響在各個方面都是最強大的,我們現在希望做的是讓這種影響也能成為最優質的。家庭最早介入了青少年的成長,并伴隨一個穩定的漫長陪伴期。然而,在強勢的娛樂文化包圍之下,家庭這一過去相對清凈、單一的交往圈也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手機、電腦、電視等媒介讓家人之間的交流逐漸減少,親子之間的耐心也逐漸消散,相互之間的興奮點更是時常不在一個頻度上。這種情形下,亟需家庭作為青少年成長的重要環境,變被動為主動,反求諸己,積極建設一種主動、健康、有序的成長環境——對話、關心和共同活動。這種對話的、關心的、有著共同活動的家庭氛圍一旦建立起來,另一種本質上的“擬態環境”隨之建立起來。在這種“擬態環境”下,通行符號是人與人之間的默契與擔當,這本身就是一種最優質的道德影響力。為此,我們期待陪伴青少年成長的千千萬萬個家庭都能回歸到一種真誠對話、相互關心和尋求更多共同活動的生活狀態上來,用另一種原初、素樸、人性的“擬態環境”來制衡娛樂文化的虛幻狂歡。
在重訴家庭的道德影響力時,我們不禁想起17世紀夸美紐斯的一段話,“必須在很早的階段,當邪惡還沒有主宰思想時,就諄諄教誨德行。因為如果你不在田地里播撒良種,他就會長出最壞的野草。如果你想要開墾它,你只要犁地、播種、在早春松土,你就可以容易做到這點,并有更大的希望獲得成功。”[8]我們有理由相信,家庭會成為能夠為青少年奠定良好道德基礎的另一個“擬態環境”。
參考文獻:
[1]朱人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樂[J].文藝爭鳴,2007(6):3-5.
[2]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470.
[3]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4]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27.
[5]克里斯托弗·賴許.正規教育與新式文盲[M]//楊自伍.教育:讓人成為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位中閣.《噗通噗通的良心》測試老人摔倒驚現最美女孩[EB/OL].(2015-02-11)[2016-02-03].http://gb.cri.cn/27564/2015/02/11/1042s4871846.htm.
[7]佐藤學.學習的快樂——走向對話[M].鐘啟泉,譯.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7-8.
[8]夸美紐斯.大教學論[M].傅任敢,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24.
【張志坤,首都師范大學兒童生命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責任編輯/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