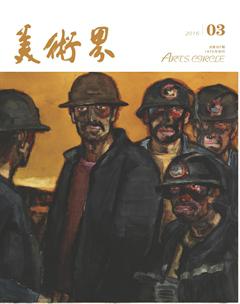淺析顧愷之的“傳神論”及其對后世影響
[摘要]東晉顧愷之不僅是中國繪畫發展史上優秀的藝術家,更是一名杰出的繪畫理論家。他是中國最早系統地提出“傳神論”繪畫思想的,對后世的影響極大。本文將從自己的角度簡要分析顧愷之的這一理論思想及其對后世繪畫理論的影響。
[關鍵詞]顧愷之;傳神論;繪畫美學
說到魏晉,我最先想到的便是“魏晉風度”“玄學”“清談”“人物品藻”等這些雖零散,卻能代表這一時期典型特征的詞語。這一時期,雖戰事頻繁、生靈涂炭,但也許正是因為現實的苦痛才促進了人們精神生活的高速發展。這時的名流、士大夫們思想開放,各種文化百家爭鳴,毫不夸張地說這是個人性自覺、充滿個性的時代。顧愷之所生活的這個時代,正是人物品藻風氣盛行之期,這種環境對他繪畫理論的提出是具有推動作用的。
在繪畫產生的初級階段,最初的畫論是主張繪畫要像形的,如《爾雅》中所說:“畫,形也。”到了魏晉時期,人物肖像畫的發展較之前有了很大的進步,加之這一時期的人們在人物品藻時更加注重人物的風格、韻度,用周積寅的話說便是“把一個人的思想性格,才能氣質的總和表現在外部,則形成一個人的精神面貌”。這些對當時的藝術家,尤其是肖像藝術家產生一定的影響,此時的他們不僅僅要做到人物肖像外形的相似,更要表現人物內在的品質。
正是這一時期,顧愷之第一個提出了人物畫要“傳神”的觀點。《世說新語·巧藝》篇中記載:“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就是說顧愷之畫人物,有時幾年不畫眼睛,別人問其原因,他回答說,作畫重要的不是四肢與樣貌的描繪,關鍵在于眼睛的描繪,即“傳神”。雖然顧愷之強調“傳神”的重要性,但并不是說他忽略對“形”的描繪,在“傳神寫照”中,“寫照”是“傳神”的基礎,只有做到恰到好處的“寫照”后,才能達到“傳神”的地步。也正如他所說:“若長短、剛柔、深淺、廣狹,與點睛之節,上下,大小,濃薄,有一毫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可見顧愷之并不是忽略了“形”的作用,而是覺得“形”與“神”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對“形”的嚴格要求是為了更好地“傳神”。“形是神賴以存在的軀殼,形無神不活;神是形賦予生命的靈魂,神無形不存。”這段對形神關系的表述,我認為也正是顧愷之想要向世人傳達的。
“傳神”是顧愷之繪畫美學思想的核心。《世說新語·巧藝》中載:“顧虎頭為人畫扇,作嵇、阮,都不點眼睛,便送還扇主,曰:‘點睛便能語也。”顧認為作畫要把握人物最傳神的部位,而這部位便是“眼睛”,通過對眼睛、眼神的描繪,可充分體現出人物的內在品質、精神。點睛便能說話,可見,顧愷之那個時候便已認識到“眼睛是心靈的窗口”這句話的深刻內涵。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日:‘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顧愷之在裴叔則的頰上添上三根毛,顯然并不是為了形的需要,顧這是為了傳神,通過裴叔則頰上的三根毛來體現其富于清談的性格特征,以達到傳神之效果。《世說新語》中又載:“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云之蔽日。”顧愷之想畫殷浩,但因為殷浩瞎了眼睛,不想讓顧畫,顧明白殷浩是因為在意眼睛的問題才會這樣,于是用飛白的技法,這不僅可掩蓋其眼睛的缺陷,還能營造出一種有如輕云蔽日之效果。這不僅表現出顧愷之對傳神的熱衷,更體現出藝術家卓越的造型能力以及精湛的藝術修養。此外,顧愷之還說“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這仍然是強調“傳神”的可貴。正如他在《論畫》中所說:“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他之所以認為人物畫最難,是由于人物畫要達到“傳神”的境界,這不僅僅要具備“寫照”的扎實功底,更要有能抓住繪畫客體典型特征的能力。
顧愷之的“傳神”理論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直接受此影響的便是南齊的謝赫。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著名的“六法”理論,而這“六法”中擺在第一位的便是“氣韻生動”,即要求藝術家在創作中要把人物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生動形象地表達出來。謝赫所處時代的繪畫主要是人物畫,表現人物的精神和性格顯得尤為重要。謝赫將“氣韻生動”作為“六法”中的第一法,顯然是受顧愷之的影響,且與顧所說的“傳神”是一脈相承的。
到了唐宋以后,“傳神論”已不僅僅是在人物畫中受到影響,而是浸入到繪畫的各個門類。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卷一》中說:“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道,空善賦彩,謂非妙也……”從張彥遠的這段話便可看出,他認為作畫的關鍵是要傳達出“氣韻”,“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只要畫中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繪畫客體的神韻,那么形似自然也就在作品中體現出來了。這里的“氣韻”與顧愷之所說的“傳神”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他們都在強調藝術家作畫時要能準確地描繪出所作對象的神韻、氣度。
北宋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卷五《故事拾遺·周昉》中記載:韓干與周昉為趙縱畫肖像,雖然兩個人都將趙的外貌描繪的很像,然而韓干“空得趙郎狀貌”,周昉則“兼得趙郎性情笑言之姿爾”。顯然,韓干在作品中缺少對趙縱內在精神、個性的表現,只抓住了他的樣貌,周昉不僅得其樣貌,更是體現出趙縱“性情笑言之姿爾”。簡單說,周昉不僅做到了所繪對象的形似,更是抓住了其神似,而“神似”顯然要比韓干空有“形似”更高一籌,周昉抓住了人物畫的要領——傳神。
到了元明清,顧愷之的“傳神”理論更是被藝術家們發揚得淋漓盡致。“元四家”之一倪瓚的“逸筆草草,不求形似”;明代徐渭的“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栽”;到清代石濤的“不似之似似之”;以及近代齊白石所說的“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等等。這些后世藝術大家的繪畫理論思想究其根源都是來自顧愷之的“傳神”理論。從時間上講,顧愷之“傳神論”的影響從東晉到明清,甚至近代,這一千多年中受顧愷之“傳神論”影響的藝術家有很多,足見其影響的深遠。“傳神”理論的發展不僅遍及中國畫的各個領域,更是成為中國繪畫美學中經久不衰的話題,甚至成為中國繪畫的核心,其影響是極大的。
[宋志敏,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