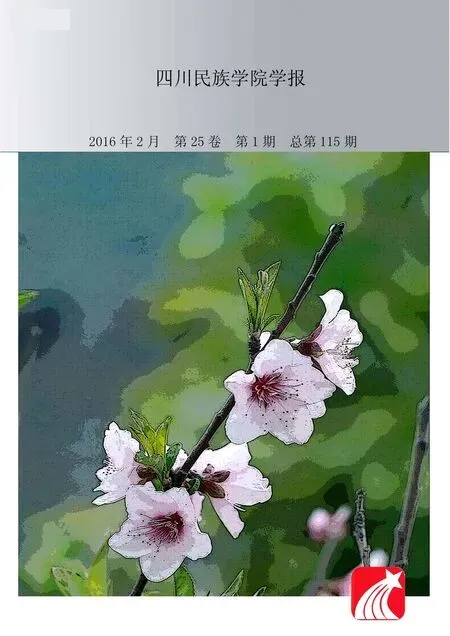河南省葉縣司莊村蒙古族族源、族風、族稱恢復芻議
郭新榜
?
★民族研究★
河南省葉縣司莊村蒙古族族源、族風、族稱恢復芻議
郭新榜
【摘要】元朝的建立與覆亡過程中,有不少蒙古族散居河南境內,發展為現今的河南蒙古族,平頂山葉縣便是河南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該地司莊“易漢”之蒙古族在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深受當地漢族影響,但又有所不同,表明不同民族在民族融合、文化演進后依然會有一定差異性,這種文化差異性反映了民族的不同性。近些年當地村民要求恢復蒙古族族稱的愿望悄然強烈,并得以實現,體現了在不同歷史時期,當地“易漢”之蒙古族在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方面的基本情況。
【關鍵詞 】河南省;葉縣;司莊;蒙古族;元朝;明朝
On the Recovery of Mongolians' Ethnic Origin, Customs and Title in Sizhuang Village in Ye County
Guo Xinbang
【Abstract】In Yuan Dynasty's establishment and fall, many Mongolians lived scattered in Henan provinc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the Mongolian lived is in Ye county. The Mongolians in Sizhuang village is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Han in many ways, such as language, customs and habits. But Mongolians also retain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dicate there will be some differences remained after ethnic fusion. In recent years, Sizhuang villagers have wanted to restore the Mongolian name and succeeded. This reflect Mongolians' basic situation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Han in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Henan province; Ye county; Sizhuang village; Mongolian; Yuan Dynasty; Ming Dynasty
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地帶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蒙元政權建立與傾覆過程中,這里成為根據地、主戰場,蒙古族不斷散居河南。宋金對峙時,河南曾一度為金所轄,蒙古滅金后,“遂留鎮撫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1],使得大批蒙古將士進駐河南。元世祖忽必烈曾向姚樞詢問治國之道,姚樞針對當時的問題,提出了三十條救治意見,其中一條便是“布屯田以實邊戍”[2],并被采納,開始“立經略司于汴”,并“屯田唐、鄧等州”,“敵至則御,敵去則耕”[3],河南成為忽必烈攻取荊襄和兩淮的前線,又有不少蒙古將士屯戍于此。元朝統一后,更有大量蒙古官員長居河南。元明鼎革時,社會動蕩不安,河南又是戰亂頻仍之地,駐守河南的元軍屢有敗跡*比如“至正十一年(1351年)秋,白蓮教領袖劉福通等人打敗元軍,先后占領亳州、項城、羅山、確山、息州(今息縣)、光州(今潢川)、舞陽及葉縣,眾達10余萬人”。見《葉縣志》。,為挽救頹勢,不少高官顯宦被派到河南。然而,明軍的南北夾攻使不少蒙古族官民滯留河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三月,明軍攻克南陽,俘獲元朝將領20余人,時駐守葉縣的元軍,或逃或降”[4]。同年徐達率軍攻占汴梁,黃河以南蒙古官員的北逃之路被切斷,使其既無法南逃又不能北上,君臣離散,民人流亡,只好散竄隱跡于漢人之中,世居河南。《葉縣志》也說“葉縣的蒙古族,是元代遺居本地的蒙古族馬禿塔兒和宣帖木兒的后裔,后改為馬姓、宣姓,多居住在廉村鄉馬莊、宣莊,其語言、風俗、習尚、服飾已與漢族無甚差異”[4]。匡裕徹、任崇岳在《河南省蒙古族來源試探》一文中指出,“平頂山是河南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主要分布在市郊區北渡鄉荊山村、廉村鄉宣莊和馬莊,葉縣仙臺鄉西北拐村和老程莊”[5]。然而,另有一部分蒙古族存在,縣志及兩位學者均未言明,比如平頂山葉縣龔店鄉司莊村的蒙古族。現就該地蒙古族的族源、習俗等方面略加陳述,以求證于相關學者,不當之處,煩請雅正。
一、司氏家族族源簡述
據《葉縣志》載,河南平頂山市葉縣蒙古族多馬、宣兩姓,然而,依筆者調查,除此之外尚有司姓。據司栓修*平頂山市葉縣龔店鄉司莊村村民,在搜集資料過程中,他提供了一些資料和幫助,在此表示感謝。同志講述,司氏家族原系蒙古族,祖籍蒙古大草原,元朝初年遷入中原,后來在平頂山市葉縣龔店鄉司莊村落戶。《河南省葉縣地名志》稱“元朝時,蒙古族司姓居此”,“清代易漢族”*清代,蒙古族與滿族關系密切,無“易漢”之必要,恐誤。[6]。該村“易漢”之蒙古族自元朝發展至今已傳數十代,族眾現已達500多口。
司栓修同志說,司氏家族本不姓司,元世祖忽必烈平金敗宋,建立元朝時,司氏先祖隨同大批蒙古貴族一道進入中原,官封“司農”。當時元朝統治者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漢人,四等南人。這種民族歧視政策致使民族矛盾激化,各族地主與蒙古貴族相互勾結,也可擔任主要官職,擁有大量土地,蒙古族人也會被迫流亡,淪為乞丐,司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由“司農”淪為平民。另外,蒙元政權不能做到輕徭薄賦,以政裕民,致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裂痕不斷加深,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在醞釀之中。
元朝末年,蒙元暴政積攢已久,其統治力每況愈下,受壓迫的各民族不堪摧折之苦,便揭竿而起,密謀反抗,爆發了“紅巾軍”起義。當地盛傳,蒙古統治者為防止漢人反抗,對其實行嚴密控制,只準漢人十家用一把生活用刀,并分派一名蒙古頭領管制,以確保蒙古族統治者的安全。在此情況下,被統治區民眾往往噤若寒蟬,起義軍難以傳遞消息。適逢中秋將至,據說智囊人物劉伯溫獻計,在中秋節互贈的月餅里面夾上“八月十五殺韃子”的紙條,約定在八月十五起義。此法極具殺傷力,大批蒙古人殞命,當時司氏先祖已淪為平民,與漢人關系甚好,被部分漢人藏匿保護起來,幸免遇難。明朝立國以來,由于滯留中原的蒙古人數眾多,且漠北蒙古勢力依然不可小覷,所以,明政府對蒙古族防范嚴密,明政府曾下令禁用蒙古姓、禁穿蒙古服、禁說蒙古語*“洪武元年,詔蒙古服、蒙古語、蒙古姓,一切禁止”。見顧炎武《日知錄》。。滯留在河南的蒙古族為避免民族歧視與壓迫,往往改為漢姓,與漢族雜居而處,互通婚姻,不斷融合。司氏先祖為求生存,以“司農”的“司”為姓,混跡于漢人中,四處流亡,于明朝中期逃至今平頂山市葉縣司莊村。崇禎五年(1632年)發大水,司氏先祖逃難于葉、襄、南陽、漯河、鄭州等地,至第二代世祖時返回司莊,繁衍至今。
二、司氏家族族風考查
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長期融合后,縱然有脫胎換骨的變化,其民族心理、民族習俗也很難有徹底的改變。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司莊村村民在社會習俗等方面受當地漢族該方面影響較大,且其族稱已“易漢”數百年,但其族俗與當地漢族又有所不同。比如,當地司莊村村民“中秋不愿月”(即不過八月十五)、“人死不插影背風”、“不立亡人碑”、“不壓墳頭紙”、“不給死人送盤纏”等習俗與當地漢族迥然相異,《河南省葉縣地名志》也說當地“居民不過中秋節,人死不插影背風”[6]。
我國許多少數民族都過八月十五中秋節,當地蒙古族為何八月十五不愿月呢?正如上文所述,因為中秋節曾是殺韃子之日,為蒙古族的忌日,該節日對漢族等民族來說是團圓之日,而對當地“易漢”之蒙古族來說,則是生離死別之時,對他們而言,八月十五恐怕一度是其揮之不去的夢魘,故不過此節日。當地漢族在喪葬方面有“立亡人碑”、“插影背風”的習俗,而當地“易漢”之蒙古族在喪葬方面則“不立亡人碑”,也“不插影背風”。他們“不立亡人碑”、“人死不插影背風”并非表明其無功祿、無財難立,而是不敢注明或不愿注明司氏先祖前段歷史,說明當地“易漢”之蒙古族對其族源始終諱莫如深。“不過八月十五”、“不立亡人碑”、“不插影背風”在當地蒙古族中代代相傳,時至今日,已由習慣而成風俗。另外,當地漢族在喪葬方面也有“壓墳頭紙”的習俗,即在墳墓的頂端用石塊壓一張16開的草紙作為“墳頭紙”,并在節日、死者忌日以及家族中辦紅白喜事時更換*如今,該習俗漸趨簡化,雖“壓墳頭紙”,但很少去更換。,當地“易漢”之蒙古族在喪葬方面也沒有該習俗。“送盤纏”也是我國許多民族的喪葬習俗,“送盤纏”就是給死者送一些在陰間享用的物品和錢財,通常是在死者出殯后的第二天傍晚,由死者兒女帶著紙人、紙錢等物來到墳前燒毀,意思是讓死者帶到陰間使用,該地“易漢”之蒙古族也沒有該習俗。因為,蒙古族原本信仰薩滿教,雖有人、神、鬼、怪思想,但無陰世陽間觀念,故不會有為死者“送盤纏”到陰間使用的思想。16世紀,蒙古族由信仰薩滿教轉為皈依藏傳佛教,其教義主張“輪回、轉世”,無去陰間生活之說,也不會有為死者“送盤纏”的做法,“送盤纏”到陰間享用與商品意識緊密相連,蒙古族當時尚無此先進思想[7],最終也未形成該習俗。所以,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龔店鄉司莊村蒙古族節日習俗、喪葬習俗方面雖深受當地漢族影響,但在特定歷史因素作用下又有別于當地漢族,表明不同民族在民族融合、文化演進后依然會有一定差異性,這種文化差異性反映了民族的不同性,這些負載不同民族文化基因的民族群體在行為上與當地其他民族多有不同之處。同時也表明,“同化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客觀進程,認同則是對同化結果的一個主觀確認”[8],而認同程度的大小依同化程度高低而定。
三、司氏家族族稱恢復
民族作為社會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屬于歷史范疇,既具有“穩定性”,又具有“變動性”,所以,民族成份和族稱的識別與更改便在情理之中。我國民族識別任務在上世紀50年代已基本完成,但由于諸多原因,需要進行民族成份更改或恢復的客觀情況依然存在。1990年5月10日,國家民委、公安部發布了《關于中國公民確定民族成份的規定》,就更改或恢復民族成份的依據、具體更改辦法等做出了明確規定,成為我國確定民族成份的重要法規依據。由于歷史原因,個別民族被劃為非自身應屬民族成份的,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尊重本民族意愿的情況下,可根據《關于中國公民確定民族成份的規定》予以恢復。在民族識別、恢復過程中既要考慮語言、心理狀態、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又要“對這個民族的長期社會歷史發展情況、民族地區歷史、民族來源和民族關系以及今后民族繁榮發展和民族團結等因素,進行綜合的科學分析”[9],還要堅持民族自愿的原則,以上這些均是民族識別、恢復過程中應充分考慮的,只有這樣方可確定民族的成份和族稱。平頂山市葉縣龔店鄉司莊村村民漢化已久,漢語已是其通用語言,但不能以此將其定為漢族,因為,雖然共同的語言是民族識別的一個重要依據,但是,我國各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一語多族,一族多語的情況均存在,故不可拘泥這一標準。“共同的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長期形成的共同心理狀態,多表現在精神風貌、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集中體現在自己屬于某個民族的心理認知,并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些民族由于共同的民族心理,還會在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進行恢復和強化,以顯示自己有別于其他民族。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龔店鄉司莊村村民有別于當地漢族的習俗,認為自身是蒙古族的民族心理早已引起地方政府的注意和重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葉縣民族宗教局、龔店鄉人民政府多次派人進入司莊村進行調查取證,因前幾年該村對黨的民族政策了解不夠,沒能及時、盡早恢復蒙古族民族成份。近幾年來,隨著黨的民族政策更加深入人心,當地村民要求恢復蒙古族族稱的愿望悄然強烈。在多數族人的要求下,鄉政府、宗教局又重新派人進入該村走訪、調查、取證,宗教局最終行文下發《葉民宗2001》26號文件,恢復了當地司氏家族的蒙古族族稱。自此,司氏族人才算認祖歸宗、正本清源,恢復了本來面目。為紀念這一振奮人心的大喜事,該地族人紛紛捐款,立碑流芳,并于2004年農歷7月初7進行揭碑典禮,參加典禮的有葉縣民宗局領導、龔店鄉人民政府領導、司趙村兩委工作人員及數百鄉鄰及族眾,場面十分隆重。
綜上觀之,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最初往往具有強制性,但隨著歷史的潛移默化作用,會體現出自覺性,甚至表現出強烈的認同感。比如明政府曾下令禁用蒙古姓、禁穿蒙古服、禁說蒙古語,王朝更迭后的蒙古族只得委曲求全。在強制認同下,蒙古族積習日久,又在逐漸實現著自覺的國家認同,比如明朝宣德年間當地蒙古族司齊躋身官場,被封為監察御史,其后世子孫司文舉明末考中進士,進爵翰林院,且被皇帝賜匾:“名著懷清”*據傳巴寡婦清家族世代經營丹砂(提煉水銀的主要原料),相當富有,曾出巨資幫助秦始皇修長城,并為其皇陵提供大量水銀。秦始皇為其筑“懷清臺”,予以表彰。《史記·貨殖列傳》有載:“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故“名著懷清”有表彰功績之意。該匾后來在家族紛爭中被毀,清乾隆五十八年司氏后代又續立,1966年,文革期間再度被毀,現已無存。。司文舉有三子:光有、光良、光士,分為長門、二門和三門,長門、二門還為繼承祖先光耀門庭的這塊匾,互不相讓,對簿公堂,打了三年官司,耗盡家中錢財,門匾被毀,也未能分出勝負,從此過起了清貧的生活,此事集中表現了該地蒙古族對新政權的國家認同感。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家認同過程中,當地蒙古族也在實現著對本民族的自我認同,即民族認同。民族認同多表現為民族的自我認同及個體的民族歸屬感,當地蒙古族村民已易漢數百年,且語言、習俗多已漢化,但該民族群體骨子里始終認為自己屬于蒙古族,自2001年民族族稱更改為蒙古族后,開始不斷地與北方蒙古族建立各種聯系,在習俗方面也開始向蒙古族習俗恢復。
參考文獻
[1]元史·卷一一九·塔察兒[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p2258
[2]元史·卷一五八·姚樞傳[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p2928
[3]元史·卷四·世祖紀一[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p40
[4]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葉縣志[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p14、p537
[5]匡裕徹、任崇岳.河南省蒙古族來源試探[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
[6]葉縣地名委員會辦公室.河南省葉縣地名志[M].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95年,p289、p289
[7]陳燁.蒙古族喪葬習俗中的游牧遺風[J].民俗研究,1992年第4期
[8]楊麗云、董新朝.從經濟活動看民族同化與認同[J].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9]施聯朱.怎樣識別一個民族[J].中國民族,1982年第11期
[責任編輯:古卿]
作者簡介:郭新榜,云南大學旅游文化學院基礎部講師。(云南麗江,郵編:674199)
【中圖分類號】K8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8824(2016)01-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