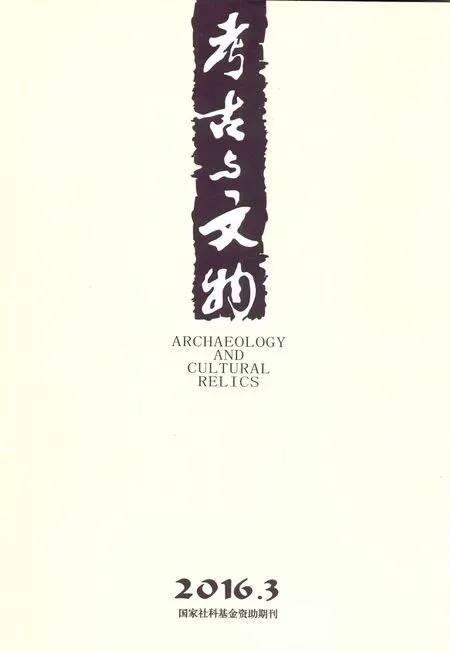秦都雍城姚家崗“宮區”再認識*
王 元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秦都雍城姚家崗“宮區”再認識*
王 元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秦都,雍城,姚家崗遺址區
秦都雍城城址區西北部自上世紀以來相繼發現并發掘出一批重要文化遺存,如銅質建筑構件窖藏、凌陰、建筑基址和陶質建材作坊等,被劃為姚家崗遺址區。早先曾有學者將該區域認定為秦都雍城的三大“宮區”之一,并判定這里即為文獻中的“雍高寢”之所在。近年隨著大遺址考古工作的展開,有了諸多考古新發現,據此我們對該“宮區”的文化屬性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它應是一處專業作坊區,其產品專供雍城相關宮區使用。
姚家崗遺址區地處雍城西部偏北的一處突起臺地上,北距雍城北城墻約1200米,西距雍城西城墻約600米,白起河由其西北向東南流過,注入雍水。臺地北部地勢較高,當地人稱之為“殿臺”[1]。始于20世紀的考古工作,根據當時所取得的重要發現,將姚家崗一帶作為秦都雍城城址的突破口和最為重要且相對獨立的大型“宮區”所在。1959年,當時陜西省考古所鳳翔發掘隊在南古城范圍內進行調查,發現了一些與秦雍城有關的文化遺跡及遺物,并注意到其北的姚家崗一帶也有同類文化遺存[2];1963年,鳳翔隊在對秦都雍城的進一步勘察中,明確了姚家崗一帶,為雍城的其中一個“宮區”范圍[3];1974年后,伴隨著雍城大規模考古工作的開展,姚家崗一帶陸續發現銅質建筑構件窖藏和部分宮殿遺跡、凌陰遺址及大量春秋時期的陶質建筑材料[4],其“宮區”的文化屬性及其重要性愈加明確,甚至有學者提出它“可能就是雍城三大宮區之一的春秋時期秦康公、共公、景公居住的雍高寢”[5]。到了21世紀初,秦雍城考古工作進入大遺址序列,在傳統“宏觀”工作的基礎上,再利用“微觀”的方法和理念,注重文化遺存的點、線、面相互結合的考察研究[6]。在此背景下,考古工作者一方面在姚家崗文化遺存分布區新發現了豆腐村戰國制陶作坊遺址,另一方面還發現了有一道環圍姚家崗遺址區的間斷夯土墻基,并且這道墻與雍城西城墻與北城墻有分別連接的可能性[7](圖一)。因此,如果再仔細考量所有在姚家崗一帶文化遺存的屬性,筆者認為這里不應該作為秦都雍城的“宮區”,而是一處服務于其它宮室的“作坊區”。

圖一 姚家崗遺址區在雍城城址區位置示意圖
一、姚家崗遺址區諸文化遺存內涵
自建國初至今,在姚家崗遺址區內發現的文化遺存主要有銅質建筑構件窖藏、建筑遺跡、凌陰遺址及制陶作坊等。
1.銅質建筑構件窖藏位于今鳳翔縣城關鎮石家營公社豆腐村東南,1973年由當地農民取土發現。陜西省文管會與縣文化館共同組成發掘隊,至1974年在該地調查和試掘了3座窖藏。3座窖穴均為長方形豎穴,窖藏出陽角雙面蟠虺紋曲尺形構件、雙面蟠虺紋楔形中空構件、曲尺槽形小拐頭等各型式銅質建筑構件共10類64件。各類構件在其中擺列整齊,且大部分保存完好,未見灼燒但有打磨、鋸、鑿等制作痕跡。部分構件內發現有朽木遺存[8]。
2. 建筑遺跡位于銅質建筑構件窖藏不遠處,發現有夯土基址、石子散水面、灰坑及陶、玉質遺物等。夯土基址東部已遭破壞,北部未及清理。殘留的夯土臺基西高東低,厚度1~1.2米,西部邊沿殘長2.8米,南邊殘長8.9米,夯土臺基西南角為直角[9]。
3.凌陰遺址位于姚家崗高地的西部,發現銅質建筑構件窖藏后,雍城考古隊發現了該遺址。經兩次發掘清理,形制已基本清楚。該遺址為一處平面近方形的夯土基址,四邊夯筑東西長16.5、南北寬17.1米的圍墻,在基址中部,有一長方形窖穴,東西長10、南北寬11.4米。窖內四壁呈斜坡狀,在窖底,夯筑一周二層臺,臺內鋪一層砂質片巖,主要用來放置儲藏的冰塊,及需冷藏的物品。窖穴四周為回廊,西廊正中有一通道,通道下鋪設有一條水道,與姚家崗西側的白起河相通,東高西低,室內冰塊融化后,即從此水道直接排入白起河。根據文獻記載,這種冰窖古代稱之為凌陰[10]。據計算,這一冰窖初始可藏冰190立方米[11]。
4.豆腐村制陶作坊位于整個雍城城址的西北部,原為高臺地,緊靠馬家莊宮區,范圍約35000平方米,占據了姚家崗遺址區的大部。經2005~2006年的考古發掘,豆腐村制陶作坊遺址內發現了陶窯、深層純凈土采集坑、泥條存儲袋狀坑、為作坊輸水的地下水管道、水窖、陶坯晾曬場地、用于其他拌和材料存放的長方形豎穴坑、廢品堆積坑等一系列與制陶生產、窯工生活相關的遺跡。出土遺物2000余件,主要有陶質建材,如瓦當、板瓦、筒瓦、陶磚、建筑裝飾、陶水管等。在這些遺物中,瓦當尤其是動物紋瓦當的數量特別多,有鳳鳥紋、獾紋、虎紋、鹿紋、蟾蜍紋等。除此之外,還發現有輻射紋、植物紋、云紋、繩紋、素面及文字瓦當[12]。
二、姚家崗遺址區年代
姚家崗遺址區的年代,應結合遺址區內各個文化遺存的年代來判斷。
關于銅質建筑構件的年代,發掘者通過銅構件上的蟠虺紋判斷其屬春秋時代[13]。筆者認為繁縟細密的秦式勾連蟠虺紋來看,與孫家南頭秦墓春秋中晚期的銅器紋飾和馬家莊宮區的蟠虺紋陶范相接近(圖二)。馬家莊宮區先后發現建筑群遺址4處,1981年至1984年清理了其中的一、二號建筑群遺址,詳細調查鉆探了三、四號建筑群遺址,馬家莊一、二、四號3座建筑群遺址的年代均為春秋中晚期[14]。馬家莊三號建筑群遺址的年代上限應相近于一、二、四號建筑群,其下限可能會略晚一點。因此,我們認為銅質建筑構件窖藏的年代當不早于春秋中晚期,或與馬家莊宮區同期。
關于建筑遺跡的年代,從地層堆積來看,第①層為耕土層,第②層為建筑倒塌后形成的堆積,②層出土遺物除筒瓦、板瓦外,還有玉璧、玉玦、玉璜、圭狀石條等遺物,第③層為建筑夯土及石子散水面,與②層包含物相同,③層下為生土。發掘者判斷其為春秋時代[15]。
第②、③層文化堆積出土的素面半瓦當、凹字形板瓦等建筑材料與馬家莊一號建筑群遺址的建筑材料相一致(圖三)。玉璧、玉玦、玉璜等玉質器物則與秦公一號大墓所出同類器物較為相近,只不過在制作和紋飾上略顯粗糙(圖四)。秦公一號大墓是秦景公的墓葬。據目前的研究,可以判斷景公時期秦國已將雍城宮區遷至馬家莊一帶,故該建筑遺跡的使用年代應與雍城春秋時期的馬家莊宮區同期。
關于凌陰遺址的年代,從地層堆積上顯示出其在春秋的文化堆積之下,建筑基址為十分堅硬的五花夯土層。從遺物來看,常見繩紋及三角形紋槽形板瓦、滿飾繩紋和抹光帶相間的筒瓦、通身飾細繩紋的陶質管道等,這些均與馬家莊宮區所出的同類器物接近(圖五)。此外,遺址還出土有銅質建筑構件上的板狀銅條殘段,以及玉璧、玉玦、玉圭等,都是春秋時期秦國常見的器物,在馬家莊宮區亦有發現。故凌陰遺址的年代也當與春秋時期雍城馬家莊宮區同期。

圖二 姚家崗窖藏所出銅質建筑構件紋飾與馬家莊一號建筑群遺址所出陶范紋飾比較

圖三

圖四

圖五
關于豆腐村制陶作坊遺址,從已發掘區域的地層堆積及遺跡分布現象可以顯示出該遺址的始建及使用情況。按發掘者的整理,豆腐村制陶作坊發掘區可分為A、B兩區。A區為當時作坊的生產區,B區是工匠生活居住的區域。A區的遺跡較多、層位關系明確,可以分為4層:第①層屬于近現代耕土層,第②層為唐宋時期文化層,第③層包含有內飾布紋的筒瓦、粗繩紋板瓦、動物紋瓦當、漢代灰陶罐等,為作坊廢棄后在秦漢時期形成的堆積。第④層包含大量動植物紋瓦當、細繩紋筒瓦、鋪地磚、制陶工具等戰國秦建筑材料,該層下的遺跡較多,均與制陶作坊有關,有條狀土溝、各類灰坑、場地、水窖、陶窯等,為作坊的始建時期。第④層文化堆積出土的各類建筑材料均為戰國時期,此外還有大量戰國中期的秦式陶器如釜、豆、罐、盆、盂等。發掘者判斷第④層的年代應為戰國中期,或延續至戰國晚期早段[16]。B區的層位關系與A區類似。綜合上述情況,豆腐村制陶作坊遺址的始建年代應為戰國中期,至戰國晚期或秦漢時被廢棄,前后使用時間與第④層文化堆積時代相符。
三、姚家崗遺址區文化屬性再探討
如前文所述,姚家崗遺址區最初被認為是宮區的主要依據有兩個:一是1963年在豆腐村采集發現的陶制建筑材料,二是1974年姚家崗一帶陸續發現的青銅建筑構件窖藏、建筑遺跡以及凌陰遺址。建筑遺跡及建筑材料的發現可說明其存在宮殿建筑的可能。凌陰遺址、建筑遺址年代相同,均為春秋時期,且處于同一臺地,兩者同屬一個宮殿區當無問題,而青銅建筑構件窖藏也應是這一宮殿區的遺物,故據此判斷三者屬于同一宮區。在此認知的基礎上,韓偉和焦南峰結合《秦記》的記載,進一步推測姚家崗一帶可能就是春秋時期秦康公共公景公居住的雍高寢所在[17]。
根據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和勘探成果,我們認為姚家崗遺址區不是宮區的主要依據有以下幾點:1.早年在豆腐村采集到的建筑材料應是豆腐村作坊生產的建筑材料而不是該區域建筑遺址。2.1974年發掘的所謂宮殿建筑遺跡面積較小,且僅存一角,與馬家莊發掘的布局嚴謹、結構規整的五進院落朝寢建筑相比,其規模可能還達不到宮殿建筑的級別。在對雍城城址區的系統勘探中,該建筑周邊并未發現其它大規模建筑遺存,所以還不能判定這部分建筑遺跡屬于宮室建筑。3.近幾年在雍城城址區東南的瓦窯頭村一帶,勘探出一處與馬家莊朝寢建筑外形相似,多進院落結構的大型建筑遺址,其年代早于馬家莊朝寢建筑,而晚于岐山鳳雛村西周宗廟建筑遺址的年代,屬雍城早期宮室建筑[18]。文獻記載的雍城三大宮區中的早期宮區很可能就在瓦窯頭一帶。對雍城城址區的勘探資料顯示姚家崗區域在雍城早期還位于城外,雍城中期也不處于大型宮室建筑集中分布的內城范圍之內,因此姚家崗遺址區自然就不是宮區,更非康公、共公及景公居住的“雍高寢”了。
如果姚家崗遺址區并非雍城三大宮區之一,那么其文化屬性就需要我們重新進行思考。根據豆腐村制陶作坊遺址的發掘,其出土的大量陶制建材,很多都在雍城城內及郊外行宮建筑遺址上發現過,如槽形板瓦、筒瓦在馬家莊宮區有發現,鹿蟾狗雁紋、鳳鳥紋、鹿紋、單獾云紋瓦當在鐵豐——高王寺一帶有發現,單獾紋、云紋瓦當在鳳翔縣衡水鎮凹里秦漢建筑遺址有發現[19],虎紋、鹿紋、云紋瓦當在孫家南頭秦漢建筑遺址有發現[20]。這些情況說明雍城時期大量的建筑材料可能就來自豆腐村制陶作坊。因此豆腐村一帶明顯不是雍城的宮室所在,而是為雍城宮室服務的官營制陶作坊。
豆腐村作坊遺址東側和南側發現有斷續的夯墻遺跡[21],時代與豆腐樹作坊遺址接近。由于遺跡破壞嚴重,現已不可知其完整形制。發掘者認為這些夯墻遺跡或可與雍城的北城墻和西城墻相接,以此合圍豆腐村制陶作坊及其相鄰區域,在雍城大城圈中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據此,我們可以推定在戰國時期雍城姚家崗一帶已經成為了一處規模較大的作坊區。
而在春秋時期,根據建筑遺跡、銅建筑構建窖藏以及凌陰遺址也可說明其作為一處作坊遺址存在的可能性。
從年代上看,三處遺址均與馬家莊宮區的年代相近。窖藏中青銅建筑構件內的朽木,顯示這批銅質建筑構件極有可能是從其它地方的建筑物上拆下運送至此。韓偉在早年的馬家莊宗廟研究中,曾提出馬家莊一號建筑的毀壞是有計劃拆遷的觀點[22]。據前文所述,馬家莊一號建筑出土的陶范紋飾,與窯藏內青銅構件的紋飾相接近。因此可以推測,馬家莊一號建筑若是拆遷,建筑上的青銅構件極有可能就是保存在這批窖藏中。保存在窖藏里的銅質建筑構件,或與周邊可能存在的鑄銅作坊相關,以供熔煉,或可直接用于新宮室建設。從建筑遺跡出土玉璜、玉玦、玉璧等玉質器物來看,該建筑物的等級較高,可能與管理銅質建筑構件窖藏或周邊冶銅、制玉等作坊的官署有關。凌陰遺址作為一處儲冰場所,主要為王室服務,而該遺址緊靠馬家莊宮區,可為該宮區提供冰塊,發揮貯藏降溫的功能。
此外,雍城城址的西北部,從秦至明清時期,一直都是各種手工業作坊的所在。該區域地勢較高,便于取土,白起河可提供充足水源,使得該地成為城市作坊的最佳選址區域。
姚家崗遺址區作為一個獨立的作坊區,其形成也應該是逐步漸進的。春秋中晚期的姚家崗遺址,規模較小,遺址區發現的銅質建筑構件窖藏、建筑遺址及凌陰等文化遺存,是為雍城宮室服務的不同手工業機構。
到了戰國中后期,隨著豆腐村制陶作坊的出現,姚家崗遺址區的范圍也隨之擴大。姚家崗遺址區在戰國中、后期已形成以豆腐村制陶作坊為主的相對獨立的區域。作坊南部還有工匠居住生活的領域。這些均顯示了雍城此時期的作坊無論是在生產還是規模上已達到了相當專業的程度。
雍城作為秦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從“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到“悼公二年,城雍”,隨著城市的擴建與順應形勢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三大宮區。其中春秋中晚期以馬家莊宮區為主,而到了戰國中晚期,雍城北部的鐵豐、高王寺一帶則成為雍城后期的宮區所在[23]。而姚家崗遺址區作為一處作坊區始終是為雍城宮區即王室服務的。春秋時期規模較小,銅構建窖藏、建筑遺跡以及凌陰遺址均位于姚家崗遺址南部,且離馬家莊宮區較近,應是為馬家莊宮區服務,而隨著戰國時期雍城宮區的北移,姚家崗遺址區也隨之不斷向北發展,形成了生產規模更大、專業化程度更高的豆腐村制陶作坊,為鐵豐——高王寺宮區及郊外的離宮別館提供建筑材料及其他手工業制品的服務。并很可能隨著雍城城墻的修建,也通過修建圍墻而在城區內形成較為獨立的作坊區。姚家崗遺址區在這一時期也發展到了頂峰。至秦國都城從雍城遷出后,姚家崗遺址區逐漸被廢棄,此后也再無大規模的使用。
姚家崗遺址區作為秦都雍城較為重要的作坊區,除了凌陰遺址及生產陶質建筑材料的制陶作坊,還應有冶銅、制玉、制骨等其他作坊存在的可能。而這些則需要我們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進一步的去發現與探索。
本文承蒙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亞岐研究員悉心指導,謹致謝忱!
[1]鳳翔縣文化館,陜西省文管會.先秦宮殿試掘及其銅質建筑構件[J].考古,1976(2).
[2]陜西考古所鳳翔發掘隊.陜西鳳翔南古城村遺址試掘記[J].考古,1962(9).
[3]陜西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鳳翔隊.秦都雍城遺址勘察[J].考古,1963(8).
[4] a.鳳翔縣文化館,陜西省文管會.先秦宮殿試掘及其銅質建筑構件[J].考古,1976(2).b.陜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春秋秦國凌陰遺址發掘簡報[J].文物,1978(3).
[5]韓偉,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發現研究綜述[J].考古與文物,1988(5,6).
[6]田亞岐.秦都雍城八十年考古工作回顧與展望[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刊(總第貳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
[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研究所,鳳翔縣博物館編著.秦雍城豆腐村戰國制陶作坊遺址考古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8]同[4].
[9]同[4].
[10] a.《詩·豳風·七月》載:“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何楷.詩經世本古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b.《毛詩詁訓傳》:“凌陰,冰窖也。”陳應棠.毛詩訓詁新銓[M].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c.《初學記》引《風俗通》云:“積冰曰凌。”“陰,通窖。窖,地窖也。” 應劭.風俗通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d.《周禮·天官·凌人》中云:“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日,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鑒,凡內外甕之膳羞鑒焉,凡酒漿之酒酸亦如之。”鄭玄注:“鑒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溫氣。”賈公顏疏:“冰若有鑒,則冰不消釋,食得停久。”鄭玄等.周禮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漢書·惠帝紀》載:“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顏師古注:“凌室,藏冰之房也。”班固.漢書.惠帝本紀[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1]韓偉,曹明檀.陜西鳳翔春秋秦國凌陰遺址發掘簡報[J].文物,1978(3).
[12]同[7].
[13]同[4].
[14]同[5].
[15]同[4].
[16]同[7].
[17]同[5].
[18] a.田亞岐.秦雍城城址區東區考古調查取得重要收獲[C]//國家文物局編.2012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b.楊永林,張哲浩.陜西秦雍城“微觀”考古新發現“城塹河瀕”實景[N].光明日報,2013-1-8(9).
[19]田亞岐,王煒林.秦都雍城聚落結構與沿革的考古學觀察[C]//慶祝張忠培先生八十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20]孫家南頭秦漢建筑遺址的考古資料尚未發表,標本現存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21]同[7].
[22]韓偉.馬家莊秦宗廟建筑制度研究[J].文物,1985(2)
[23]田亞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J].考古與文物,2013(5).
(責任編輯 楊岐黃)
Qin Capitals, Yongcheng, Yaojiagang locus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signifi cant remains such as the hoard of bronze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ice cellar, architectural foundation, and workshop of ceramic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were found at the Yaojiagang locus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the Yongcheng Qin capital. Previous scholarships often considers this locus as one of the three palace zones of Yongcheng, namely the Yong Gaoqin (雍高寢) mentioned in texts. But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provide new evidence and challenge the conventional viewpoi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locus was a craft production area specialized in architechtural compon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alaces in Yongcheng.
*本文系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重點項目“秦都雍城城址考古調查、發掘與專題研究”(批準號:16AKG00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