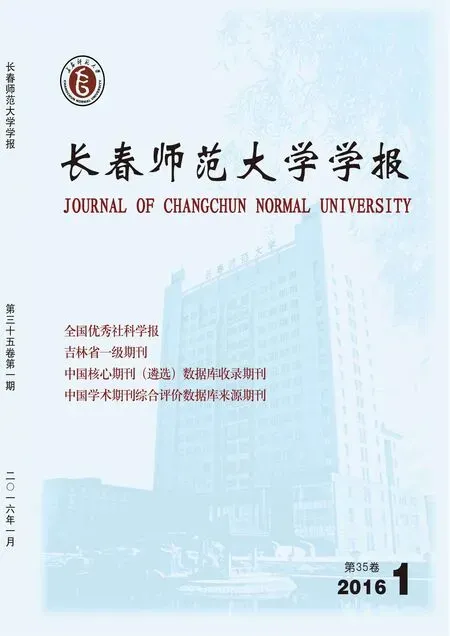賦之源流考
孫語林,吳夏平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
賦之源流考
孫語林,吳夏平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摘要]在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史中,賦體文學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其流變歷來眾說紛紜。本文結合眾家之言論,考述賦之源流,以證賦之源流不為一家之功,實乃眾家之長,歷經時代變遷,最終成為今天我們所熟知的賦體文學。
[關鍵詞]賦;源流;多合一
任何一種文學樣式都有它的源流可探。在我國古代豐富的文化遺產中,賦是一種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學體裁,其起源歷來眾說紛紜。探索賦體文學的性質,首先就面臨著一個正本清源的問題。
一、賦的起源概說
賦,《說文解字》:“斂也。”[1]。古時賦、敷、布、鋪古同聲,韻部亦同,故賦又有鋪陳之意。《現代漢語大詞典》對賦的含義概括為:“我國古代文體,盛行于漢魏六朝,是韻文和散文的綜合體,通常用來寫景敘事,也有較短篇幅抒情說理的;動詞,作:作詩一首;舊時指農業稅;交給:賦予。”[2]單從字面解釋來看,賦的意思多種多樣。賦作為一種文體的起源,歷來備受爭議。
關于賦的起源,舊說紛紜:
(一)古詩之流說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云: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臨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3]
班固《兩都賦序》云:
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夫御史大夫倪寬……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流亞也。[4]18
這兩段話的共同點是認為:詩、賦雖然文體不同,但社會作用是相同的,都用來抒情言志。通看《漢志·詩賦略》,這里的“賦”字可理解為動詞,而非文體。班固《兩都賦序》之說似與《漢志》有所不同,實則互相補充。后者主要是從詩賦的社會作用來說明二者關系,也是對“微言相感”與“賢人失志之賦作”的補充。
(二)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說
《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中明確指出: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隠,韓非《諸說》之屬也;征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5]
此說是對賦的源流研究的重大突破,其貢獻是:不限于從韻文(詩、騷)的角度去探討賦體的形成,而是注意到散文對賦體形成的影響。
(三)本于縱橫家言說
近人章太炎、劉師培均主此說。章《文學說例》云:
“縱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為紛葩,期于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于《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云爾。”[6]7
章說以提出縱橫家之言為賦之先導,后歸結為“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為之賦”。
劉氏之說較為詳盡。其《論文雜記》云:
“詩賦之學,亦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術,流為縱橫家。……蓋采風侯邦,本行人之舊典,故詩賦之根源,唯行人研尋最審。……《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學皆源于古詩。……雖體格與《三百篇》漸異,然屈原數人皆長于辭令,有行人應對之才。……西漢詩賦,其見于《漢志》者,如陸賈。嚴助之流,并以辯論見稱,受命出使。……是詩賦雖別為一略,不與縱橫同科。而考作者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又班《志》有言:‘不歌而誦謂之賦。’案‘登高能賦之言,本于《毛傳》(《鄘風·定之方中》)’,在‘君子九能’之內。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故總名曰德音。而‘登高能賦’與‘使能造命’相次,其為行人之詩賦無疑。……欲考詩賦之流別者,蓋溯源于縱橫家哉?”[7]
劉氏謂周時行人之官與詩人之關系密切,信而有征;謂行人流于縱橫,則似是而非,二者實為不同時代的兩種不同性質之人,只是縱橫家有時亦兼充使命之職而已。但賦中假設對問之體,雖頗受儒、道等諸家著述的影響,而尤近于縱橫家言。劉氏、張氏特別突出它在賦體形成中的作用,仍然是可注意的。張、劉之論證雖未完善,卻是難以抹殺的。
(四)源于隱語說
劉勰《文心雕龍·諧隱》云:“隱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8]122隱語即后世所述之謎語,其源頗古。賦源于隱語,最初是清末王闿運提出來的。其《湘綺樓論詩文體法》云:“賦者,詩之一體,即今迷也,亦隱語,而使人諭諫。夫圣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為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賦因作矣。”這里只謂荀卿本隱語之法以作賦,并未說賦源于隱語。而王闿運之說認為,賦以荀子為“正體”,而以屈原之作為“詞賦”,別為一體。若論師隱之法以作賦,很難說賦體即源于隱語。從現存《左傳》《國策》所引隱語來看,其構思雖巧,但語殊簡質,大抵僅一二語,或二三字,后世且有只有一字者,與賦之為韻語,尚鋪陳殊相遠。竊以為,以隱語為賦之源,反不如說諧言曾對賦體的形成、發展有過某種影響。
二、百川歸海——賦之源流
以上諸說對賦的起源的探討,雖廣度、深度有所不同,然大體各有所主。而其所異,除其他原因外,實與別騷于賦或兼言辭賦有關。這些各有所主的探討,當然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然亦有難于兼賅賦中眾體之偏。清末民初的姚華似欲彌縫其闕,因此提出“賦有三體”之說,其《論文后編》云:
“詩有比興,與賦為三,荀書演賦(荀子《賦篇》),其體益廣。楚辭遞興,繼生宋玉,賦始敵詩,以授漢人。《國風》無楚,故楚辭別行。楚人之辭多矣,而屈原以《離騷》為后人所宗,乃名曰騷。效其體者,語必稱“兮”,緣是生辭,……亦援以入賦。騷者詩之變,而辭賦之祖也,于是騷有三體:其一承詩,其次擬荀,其次宗楚。”[6]9
姚華注意到賦有多源,又注意到賦中有直承詩者,均為可貴。
古人以“六義”注《詩》。《周禮·春官》云:“太師……教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9]《毛詩序》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10]30關于六義的內涵,歷來眾說紛紜,索解為難。一般認為,風、雅、頌為詩體,賦、比、興為詩之用。鄭玄注《周禮》曰:“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詩·大雅·烝民》云:“明命使敷”。《毛傳》云:“賦,布也。”《詩·周頌·賚》:“敷時絳思。”宋人李仲蒙論賦比興三者異同時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他從“情物關系”來論賦比興之差異,認為賦是“敘物以言情”,通過直敘其物來鋪展情感,這是詩經中最常用的創作手法。今人丘瓊蓀在《詩詞曲賦概論》中指出:“賦之為用最廣,而其效亦最宏,所以敷演事理,抒寫物情,匪若比興二者其道最窄。”[11]《詩經》中廣泛運用的“賦”的手法,發展到后來,適應“敷演事理”的需要,逐漸演變成一種獨立的文體,這從荀子的《賦篇》中可見端倪。
荀子的《賦篇》首次將自己的創作命名為賦。以《箴賦》為例,先寫“箴”的來源、用途及秉性,最后引申寓意,諷勸君王應重視賢臣、勵精圖治。從手法上看,層層鋪敘,全面展開,可謂面面俱到,這正發揮了賦“推演事理”的長處。而《蠶賦》是一首詠物抒情的小賦,從創作主旨來說,荀子賦繼承了“詩言志”的傳統。所以,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荀子“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透視荀子賦,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賦在創作手法上繼承了《詩經》的鋪陳手法,適應“敷演推理”的創作需要,逐漸演變成一種獨立文體。當然,荀子賦在文辭上還較為平板,不夠豐腴艷美,內容上也缺乏波瀾起伏的氣勢和一往情深的風采。如果說《詩經》在美學的原則和鋪敘方法上構成賦體文學的先導,《楚辭》則以其瑰麗的人格理想和豐富的想像藝術拓展了賦的境界。
班固乃指出《楚辭》對賦體影響之第一人。他在《離騷序》中說:“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12]4繼班固之后,王逸也在《楚辭章句序》中說:“故智彌盛者言其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10]54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也說賦“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8]60后世也有論說楚辭與賦之關系的人。宋祁在《文章辨體序說》中直接表述“《離騷》為辭賦之祖。”[12]5劉熙載《賦概》亦云“《騷》為賦之祖。”[13]可見,《楚辭》對賦體的產生也有一定的影響。首先,在體制上,賦直接傳承自楚辭。《離騷》和《九章》中以六、七言句式為主,多用“兮”字,常以“亂”字作結,對答的形式經常在《楚辭》中出現。漢賦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這些手法。如賈誼的《吊屈原賦》、董仲舒的《士不遇賦》中都有以“亂”作結的情形,枚乘的《七發》、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中都有對答的形式。《招魂》《大招》等也是后世賦體鋪張揚厲的濫觴。如《招魂》描寫東、西、南、北、上、下六方面環境之惡劣,描述楚國宮室之美、飲食服飾之華、歌舞游樂之盛,都用了鋪張縱橫的手法,對后世賦體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在《管錐編》中,錢鐘書先生說:“枚乘命篇,實類《招魂》、《大招》,移《招魂》之法,施于‘療疾’,又改平鋪為層進耳。”[12]5其次,在題材上,賦體也受到《楚辭》的深刻影響。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辯騷》中所說:“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8]38楚辭涵括了后世賦體所寫的大多數題材源頭。楚辭大家屈原高尚的人格魅力也對賦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濃郁的文人氣質就是賦的典型特征之一。
三體之說似乎彌補了賦中眾體之偏,但賦體文學在表現手法和辭采藝術方面也受到了當時辯說之風的影響。屈原為楚國重臣,宋玉也是一個能言善辯的文士。至于枚乘、賈誼、司馬相如等都曾做過諸侯王的門客或輔佐,儼然有戰國辯士的遺風。賈誼的《過秦論》、枚乘的《諫吳王書》都繼承了縱橫家鋪天蓋地、層層緊逼的言辭藝術。辯士為了說動人主,在說明國勢時,往往對該國的地理、風俗和經濟狀況作全方位的描述,形成鋪排夸飾的敘述藝術。如《史記·蘇秦列傳》:“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馀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14]縱橫家這種輻射型的體物方式,對漢賦的鋪排藝術啟發很大。班固《兩都賦》:“漢之西都……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4]19可以看出,賦的鋪排手法并不完全出于體物,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賦家夸張渲染的需要。這同縱橫辯士說動人主的辯說藝術有異曲同工之處。除此之外,辯士通過逐層深入揭示問題要害,引起君主的重視,這種手法同樣也被賦家吸收進賦體創作中來。例如枚乘《七發》中的吳客。他通過對音樂、飲食、車馬等事物的描寫,由近及遠、由淺入深的啟發太子,讓他在浮華享受中自省。總之,辯說之風同樣滋潤了賦體文學的,促進了賦體文學的產生。
綜上所述,賦作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中介性文體,它的起源不能僅僅從某一方面去探尋。賦這種文體的形成,既有《詩經》、《楚辭》中的一些表現手法,又夾雜了春秋戰國時期辨士的辯說藝術。正是在多股潮流的裹挾下,賦體文學至兩漢時才猶如百川歸海一樣,匯入浩瀚的漢文化海洋中,形成波瀾壯闊的賦體文學主潮,確立了它的體制特點。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賦之源流的認識也在變化。筆者認為,《詩經》、《楚辭》縱橫家辭說、荀子賦都與賦的形成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多者合而為一即為賦之源流。
[參考文獻]
[1]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09:131.
[2]中國社會科學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Z].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411.
[3]劉向.漢書藝文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6:1755.
[4]陳啟天,趙福海.昭明文選譯注[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4.
[5]章學誠.校讎通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6.
[6]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M].北京:中華書局,2011.
[7]劉師培.論文雜記[M].北平.樸社出版社,1928:121.
[8]劉勰.文心雕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鄭玄.周禮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49
[10]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袁濟喜.賦[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12.
[12]謝佩媛 李永田.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3]劉熙載.藝概注稿[M].北京:中華書局,2009:413.
[14]韓兆琦.史記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4722.
[作者簡介]孫語林(1990- ),男,碩士研究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吳夏平(1954- ),男,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602(2016)01-0130-04
[收稿日期]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