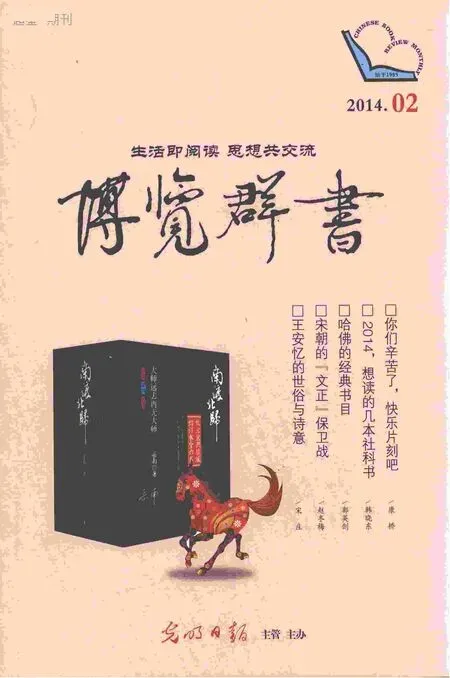關于人類文學經典的沉思錄
范子燁
在文學的天國里,那些璀璨的星辰總是能夠穿越歷史的煙塵向我們發出永恒的光輝;在這光輝的照耀之下,我既珍重現世的幸福,又超拔了塵世的苦難,建立起自我的自由的寧靜的恬美的精神世界。人類需要文學經典,就像需要陽光、食物和水一樣。同時,對文學經典以及閱讀自由、閱讀機會的渴求,也足以代表一個人的文化素養和精神層次,因為這種渴求顯示了人類本性中超越物質層面的精神因素。一個人一群人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的精神特質,實際上就生成于經典閱讀與吸收的過程中。因此,經典的生成問題以及經典的閱讀、傳播和接受問題,實際上也是各個時代面臨的共同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們的時代顯得比較異常。因此,近年來關于文學經典的討論和論爭時有發生,并成為文學研究界普遍關注的熱點。
密切聯系但又超越“三線研究”
2015年7月10日,原國家圖書館館長詹福瑞教授新著《論經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發布會在國家圖書館舉行。而此前半個月,我已經得到了詹福瑞先生的簽贈本。對于同行和友人的新著,我從來都是一拿到手,便認真閱讀,從不含糊。所以,有一次我的同事表揚我,說我經常看別人發表的新成果。其實,在我看來,對職業學者而言,了解相關學術領域的最新進展是自己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前提,即便是賣蘿卜白菜也得了解行情,何況是研究學問!而根據我的了解和觀察,目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明顯呈現出三線分布的研究格局:首先是一線研究,即直接研究作家作品;其次是二線研究,即研究作家作品的傳播史,或曰影響研究或接受研究;復次為三線研究,即是研究的研究,實際是古典文學研究之學術史。這三線研究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形成了當代古典文學研究的多層次格局。而從研究方法和治學路徑上看,當代的古典文學研究也表現在三個方面:理論形態的研究,文獻形態的研究以及理論、文獻兼融的研究。
《論經典》則屬于既與三線有密切聯系而又超越三線的理論形態的研究。這種研究難度很大,當然也很有意義。再不要說應該重視文獻這類廢話了,真正的學者不應該不重視文獻的,因為這是研究的基礎,在我們的時代獲得任何文獻都不成問題,而“應該重視文獻這類廢話”也不應成為理論低能或審美無能的遮羞布,因為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的現實的價值,主要是由理論形態的研究來評判、張揚的。真正的學者必當服務于現實社會,由此而走向未來。實際上,就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而言,我最佩服的是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讀《論經典》一書,對這一點感悟更深,同時也確實遭遇了久違了的文化感動和學術感動:酣暢淋漓的情緒急涌于胸中,仿佛是一曲春江,汩汩而來,勢不可遏。大約在2005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見到詹福瑞教授,當時我開玩笑說:“您到國家圖書館主持工作,全國的讀書人都高興了!”因為我深知,他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一位真正的學者,一位真正的詩人。在我們這個時代,“真正”意味著“罕見”,因為我們的學術隊伍中夾雜著太多的“不真正”。對詹教授十幾年當軸于國圖的成績,業界自有公論,我這里不作評價;無論如何,國家圖書館的領導重任,使他結下了更深的書緣,他對書籍和讀書對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意義的認識,無疑比一般的學者要深刻許多,關懷也要深切許多。面對當代社會傳統文學經典已被邊緣化的殘酷現實,他對文學經典,特別是與文學經典相關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十多年的苦心孤詣凝結為這部《論經典》。
一本關于人類文學經典的沉思錄,兼具現實意義和歷史關懷
《論經典》是關于人類文學經典的沉思錄。“經典,這是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回顧以往的歷史,它已經成為我們深深的記憶。但是,這個名字在今天,有可能漸漸遠離我們,以致我們擔心有一天它會變得異常陌生。經典,自古至今永遠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作者開篇就這樣寫道。隨后,通過對古今中外關于經典定義的回溯和追尋,作者確定“本書討論的經典,亦主要限定在文學經典以及與其相近的人文經典”,顯示了非常清醒的理性意識。在此基礎上,作者展開了恢弘大氣的學術格局,以十章的篇幅逐次討論了“經典之爭”“經典的傳世性”“經典的普適性”“經典的權威性”“經典的耐讀性”“經典的累積性”“經典與政治”“媒體之于經典的傳播與建構”“教育之于經典的傳播與建構”和“大眾閱讀與經典面臨的挑戰”等十個方面的重要問題。顯然,作者建構了一個非常完整的現代性文學經典學理論體系。經典為何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因為“經典常常成為人類思想的策源地,人的靈魂的棲息地”,而這也正是該書的出發點。一代宗師王念孫說:“凡學者著書,必于所托者尊,或后人不能諟正,則董理之。”所謂“尊”,就是研究對象本身具有尊貴性,這也就是經典;至于校勘一道,必須是后人做不了的工作始可為之。真是大格局大氣魄!在王氏看來,學術研究對象和領域的選擇,永遠比為學術研究而付出的努力重要,選擇重于奮斗,這是乾嘉學術史給我們的重要啟示。《論經典》既然以人類的文學經典,特別是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以及相關領域為研究對象,其總體的學術氣象已經籠蓋群倫。因此,《論經典》乃是一部關于文學經典的沉思錄,一部關于文學經典的對話錄,學者的理性、儒者的理想和詩人的激情在此書中融為一爐。王念孫說:“學問須有靈性,苦功而無靈性,是人役也。”苦功與靈性使得這部書亮點密布,讀來饒有趣味,發人深思,引人入勝。這里,我試為讀者揭橥一二,以彰明此書之現實意義和歷史關懷。
其一,于丹緣何把大鵬變成麻雀?
捍衛經典的尊嚴,捍衛文學的尊嚴,這種嚴肅的文化態度貫穿全書。“考察經典與現代大眾傳媒的關系,重要的不是要看大眾傳媒是否傳播了經典,而是看其如何傳播經典。”在此方面,詹福瑞對《于丹〈莊子〉心得》的批評最為典型。對于這本《心得》,詹福瑞指出,“于丹講《莊子》,為了使《莊子》的思想嫁接到當代人的生活實用,則把《莊子》的類似于《逍遙游》中的大鵬之思,降低為枋榆間的蜩與學鳩之飛。”“莊子逍遙游的實質就是要超越現實與自我,而于丹之所講落腳點恰恰正是在現實與人的自我。拋棄眼前的遮目一葉,不過是為了謀取認得更大利益而已。所以于丹教給讀者的不是超越,而是討巧,是謀求更大利益的機心。這豈不與莊子的精神超越和由超越獲得的自由精神南轅北轍!”批評似乎尖刻,但是,他對于丹似乎還有一種“了解之同情”:“從作者的講述中,還是可以看出他們面向的是職場的青年,并且把撫慰這些受眾的職場失意和工作帶來的壓力作為講述的目的。他們既要貼近這些讀者的關切,同時還要照顧其接受能力,因此,盡量做到通俗易懂,盡量用穿插的小故事來調節氣氛,如同戲曲中的插科打諢,都是為了吸引人的眼球,爭取有更好的收視率。而其付出的代價,就是減損經典的內涵,降低思想的高度,甚至曲為之解,把莊子這只薄天而飛的大鵬變成搶樹數仞的麻雀。”偉大作家與偉大作品的精神核心就是其“不可摧毀性”(indestructibility),任何人對經典的歪曲都是徒勞的,譬如,“文革”期間刊行的《論語批判》和《孟子批判》之類,并沒有摧毀這兩部偉大的儒學經典。其實,于丹本人是否有意歪曲經典并具有歪曲經典的能力,我們并不肯定,她的心得也許就是她的真實感悟。故意迎合大眾的心理前提通常是具有與大眾不同的內在體驗,這樣的人常常很痛苦,而于丹的講述似乎并沒有痛苦的意味。其實,誤解經典或曲解經典的過程不僅是媚俗的過程,也是與誨人不倦相悖的過程。
其二,“樣板戲”能夠成為永恒的經典嗎?
“權利影響經典的另外一種手段,是試圖制造經典和神圣化經典。”“在中國,最典型的莫過于上個世紀60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推出的八個樣板戲。”“1966年11月28日,中央“文革”召開、萬人參加的‘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宣布,京劇《智取威虎山》……等八部作品為革命樣板戲。1967年5月,八個樣板戲齊聚北京匯演,直到6月中旬,演出達218場,觀眾達到33萬人。”“時間過去了四十余年,當年紅極一時的樣板戲,今天又被命名為‘紅色經典,繼續在舞臺上演出。”那么,這些樣板戲“今后是否可能成為可以流傳于世的真正的經典”?詹福瑞認為,“要看它是否能夠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是否具有普世價值”,“經典的普世價值在于把一個民族、甚至個人的經驗連接上人類經驗,使經典不僅具有民族性和作者的個人性,同時具有超越民族性和個人性之上的普遍意義。” “作品反映了人類共同關注的問題和表現了人類普適價值的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亞、雨果、歌德、托爾斯泰、薩特、卡夫卡等經典作家,既是西方的,也是東方的、世界的;孔子、莊子、李白、杜甫、曹雪芹、魯迅既是中國的、東方的,也是西方的、世界的,并且是當代的。”這些偉大作家不是哪個政府能夠“領導”出來的,也不是哪個“文化工程”能夠“打造”出來的,他們來自人類的文明社會,他們是人類疾苦、悲哀和不幸的代言人。他們對人類的深切關愛以及相關的文學經典永遠指引著人類文學之輪的航程,他們是人類文學海洋上的永不熄滅的燈塔。這些經典作家已經超越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種種意識形態的藩籬,成為人們共愛共讀共賞的精神財富。正如德國詩人席勒所言:“以具體的意義來說,我們希望成為自己時代的公民;但是在精神的意義上,逃避某一特別國家和特定時代的束縛,成為各個時代的公民,卻是哲學家和有想象力作家的特權和責任。”(轉引自雅斯貝爾斯《當代的精神處境》,黃藿譯,三聯書店1992年版)當然,我們必須看到,即使是經典作品,我們如果長期面對同一部作品,也會產生審美的疲勞、倦怠乃至反感,譬如,你每月把《約翰·克斯多夫》看一遍,每天把貝多芬的《三》《五》《六》《九》四大交響曲聽一遍,看你是否受得了?至于樣板戲在“文革”期間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給人帶來的疲勞和厭煩,當年的觀眾誰都不會忘記,在這種背景之下,《第二次握手》之類的小說自然要被廣泛傳抄了。以權利干預經典的構建與傳播,歷史的教訓既荒唐而又沉重。在這種意義上,《論經典》一書對于當代中國的人文建構,政府的文化決策以及出版事業和文學教育事業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和參考意義。
詹福瑞的文學經典學充滿了辯證法的精神。他分析問題不僅能夠一分為二,而且善于一分為多,尤其善于在動態的變量中尋覓、發掘不變的東西,在不變的東西中捕捉到種種動態的變量。“經典閱讀的關鍵亦是發現,而這種發現即來自閱讀時對前見的證明、更是對前見的打破,為新的前見的建立打開了更深邃、更廣闊的視野。” “如果我們把經典文本稱為經典原生層的話,經典經過歷史累積而形成的讀者閱讀的前見,就是經典的次生層。次生層因依經典的原生層而產生,并且隨著時間不斷增加,僅僅包裹在經典原生層周圍,構成經典完整的生態圈。經典正是在這種不斷的重新闡釋中得以流傳,并且生生不息。” “經典的累積性所造成的閱讀前見,也會影響讀者對經典文本的閱讀和接受。所以就有一個如何對待經典的累積性前見問題。或者剝離外在的前見,回歸文本;或者閱讀經典文本,同時也接受前見;不僅如此,對前見的剝離、接受也總是有所選擇。而讀者在閱讀經典時剝離什么前見,保留或認同甚至強化某些前見,都決定于讀者閱讀時的當下性所形成的與經典次生層的價值關聯。”這些精彩的觀點都顯示了一位杰出學者的卓越智慧。又如作者在探討經典的傳世性問題時指出,一部精神產品能夠成為經典,主要是在經典的傳播與接受過程中,經過兩個以上的文化階段,不同時代、不同時期的讀者克服了閱讀的“時尚性”,達到了對一部作品價值的歷史共識。他舉例說,中國古代儒家的經典《周易》《詩經》《論語》《孟子》和道家的經典《老子》《莊子》歷經千年,流傳至今。儒家經典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作為主流文化直接影響到社會的政治制度,也影響到士人的安身立命。道家經典,則作為與儒家思想并行的思想體系,作用于政治,成為儒家思想的補充。如道家的無為而治政治觀,在不同時期與儒家的積極有為政治觀互為消長,共同構成了封建社會的政治治理理念。而對于士人而言,道家的思想與儒家思想一樣影響深刻,出則為儒,入則為道,幾乎成為大部分封建士人的處世之道。在1911年以后,中國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深刻變化,儒家和道家賴以存在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在,但是儒家經典《十三經》,除《尚書》《周禮》《孝經》等逐漸變為只具有認識價值以外,以上所說的幾部儒家經典和道家經典作為思想資源依然對中國社會發生著重要影響,其經典地位并未因社會變遷而發生根本性的動搖。其原因即在于這些傳世經典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智慧,里邊保存著我們前面所說的超越了時代和意識形態的共識,并且已經滲透到我們民族的血液之中。由此可見,不走偏鋒,遍觀衢路,兼容并包,打通古今中外,將諸家理論融為一爐,并巧妙吸納,出以己意,是詹福瑞治學的突出特征。
總之,《論經典》在學術上有厚度,有力度,有強度。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說:“對于研究者來說,在科學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就是發現問題。但發現問題則意味著能夠打破一直統治我們整個思考和認識的封閉的、不可穿透的、遺留下來的前見。具有這種打破能力,并以這種方式發現新問題,使新回答成為可能,這些就是研究者的任務。”(《詮釋學 》II《真理與方法——補充和索引》,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 2013年版,P65)在文學經典學領域,詹福瑞確實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當然,書中有些地方點到即止,有些地方欲說還休,有些地方化整為零,明眼人均可見出作者的匠心和苦心。真正的文學來自一個有文化信仰有審美追求的人類世界。真正的學術和真正的學者也是如此。《論經典》處處閃耀著文化信仰與學術信仰的光輝,它一定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伴隨著那些不朽的文學經典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