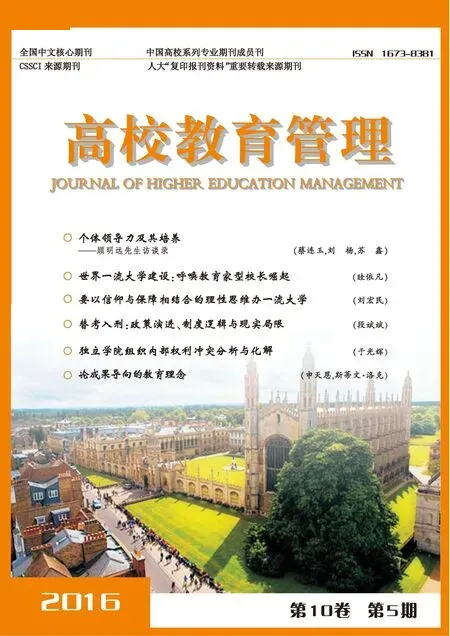替考入刑:政策演進、制度邏輯與現實局限
段斌斌
(中國人民大學 教育學院, 北京 100872)
?
替考入刑:政策演進、制度邏輯與現實局限
段斌斌
(中國人民大學 教育學院, 北京 100872)
替考治理經歷了從“軟性約束”到“替考入刑”的政策轉型,并最終形成了“雙軌制”的治理框架。替考入刑是通過提升違法成本從而迫使人們變成好人的一種制度設計。但從實施效果來看,替考罪的設立并不意味著替考行為的減少或消滅。刑罰可以防止一般邪惡的許多后果的產生,但是刑罰不能鏟除邪惡本身。替考治理需要刑事法律的強勢介入,但更需鏟除替考滋生的社會土壤。為此,除嚴格實施刑罰打擊之外,我們還應淡化考試制度的利益分配器和社會篩選器機能、斬斷替考利益鏈條、健全社會誠信體系以及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
替考作弊;替考治理;替考入刑
作弊之害無需贅言,而替考之弊則不可不言。作為一種實行行為,替考作弊實然侵害考試的公平公正;而作為一種作弊形式,替考作弊則惡劣尤甚、危害尤大。事實上,從2008年甘肅天水替考案,到2014年河南杞縣替考案,再到2015年轟動全國的江西替考案,大規模、有組織的替考案屢禁不止。替考猖獗而治理乏力,刑罰似應成為“最后一道防線”。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明確將國家考試中的替考行為規定為犯罪,這意味著“替考入刑”終于從民間吁求變成國家意志。但正當民眾“口耳相傳”“歡呼雀躍”之時,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替考和泄題丑聞隨即給民眾一盆“當頭冷水”。刑罰可以防止一般邪惡的許多后果的產生,但是刑罰不能鏟除邪惡本身[1]375。顯然,沒有刑法對替考行為的威懾與懲罰是萬萬不能的,但僅僅訴諸刑罰強力又是遠遠不夠的。有鑒于此,文章試圖尋根溯源,探求替考治理的“良方”。
一、 政策演進:從“軟性約束”走向
“替考入刑”的治理轉型
考試與替考似是一對“孿生兄弟”,如影隨形。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考試歷史有多長,替考歷史就有多久。而事實上,替考作弊確是古已有之。史料記載隋唐初創科舉考試之時,就有“承接他名而參調”的冒名頂替者,甚至與李商隱齊名的唐代詩人溫庭筠,就是個著名“槍手”[2]。雖然替考作弊防不勝防、禁而不止,但官方卻從未停下治理替考的腳步。譬如清初就明文規定,一旦發現替考則一律發配邊疆充軍,而乾隆年間則更為嚴厲,替考者將被立即處斬[3]。可以說,替考作弊與替考治理的強大張力構成了考試制度發展的一條主線。但囿于篇幅,文章僅著重梳理恢復高考以來替考治理的政策演進。
(一) 1977—1987年:“軟性約束”的治理時期
1977年高考制度重新恢復,考試取代推薦成為大學新的入學方式。在高考恢復的鼓舞下,華夏大地掀起了一股全民學習的浪潮。發自內心的知識渴望促使人們“真刀實干”地勤奮求知,對替考等作弊行為則極其不屑、避而遠之,而事實上替考行為也確實少見。但在那個年代,國家公職人員在考試中如果出現徇私舞弊的行為則會受到嚴肅處理。山西新絳縣和陜西佳縣在高考中發生的徇私舞弊案件接連受到中央的厲聲呵斥,涉案公職人員也難逃黨紀政紀的開除處分。與之相反,替考行為則被學校僅僅視為個人的道德缺陷,社會輿論對此也相對寬容。面對極少的替考作弊,學校一方面加強思想道德教育和考前紀律教育,重在預防;另一方面,對于作弊學生則主要采取道德教育為主、紀律懲罰為輔的懲治措施。梳理史料不難發現,這一時期不僅替考頻率低,而且替考治理也僅限于個別學校的道德治理層面。譬如某校規定:“學生考試作弊除宣布該科成績作不及格外,并在公布成績時注明是‘考試作弊不及格’,存入檔案。”[4]而作為高考恢復的首屆考生,秦惠民教授不無感慨地談道:“考試是我能夠期盼獲得平等對待的一種最公正形式。考試作為公正價值的體現形式,在中國深入人心。”[5]
(二) 1988—2014年:“行政處罰”的治理時期
考試的“蜜月期”總歸短暫,而替考等作弊行為則開始“初露鋒芒”“嶄露頭角”,到1988年大學生考試作弊已不是個別現象: 一項針對某校大學生的實證研究表明,該校有過作弊行為者高達82.74%[6]。面對日益嚴峻的作弊歪風,教育部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治理替考的規范性文件。1988年頒布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指出:“應考者在考試中有夾帶、傳遞、抄襲、換卷、代考等舞弊行為以及其他違反考試規則的行為,省考委視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警告、取消考試成績、停考一至三年的處罰。”該規定是中央層面治理替考作弊的政策開端。同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管理處罰暫行規定》也指出:“在考試中,夾帶、接傳答案、交換答卷、代考、找人代考、抄襲他人答案或者將自己的答案讓他人抄襲的,視情節輕重,分別給予通報批評,取消報名資格、考試資格、被錄取資格,或者取消入學資格的處罰。情節嚴重的,并給予一至三年不準報考的處罰。”1990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指出:“考試作弊,應予紀律處分。凡屬徇私舞弊者,一經查實,取消學籍,予以退回。”不難發現,此時替考治理在思路上并未嚴格區分“代考”與其他作弊行為。
1992年頒布的《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管理處罰暫行規定》則開了重罰替考作弊的歷史先河。“考生由他人代考的,取消當年考試資格,并從下一年起三年內不準參加全國統一考試”,而其他作弊行為則僅被處以扣除該科所得分的30%~50%、取消當年考試資格、禁考1~2年等處罰。但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和1998年出臺的《教育行政處罰暫行實施辦法》又出現政策反復,再次將替考和其他作弊方式混同處理。“在考試中有夾帶、傳遞、抄襲、換卷、代考等考場舞弊行為的,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門宣布考試無效。”但隨后由于替考作弊屢屢發生,替考再次成為重點打擊對象。2002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堅決制止和嚴肅處理各類高等教育考試中替考等違紀舞弊現象的通知》中指出:“對那些無論用何種形式進行違紀舞弊的人員,尤其是對找人代考的所謂‘雇主’和替人考試的所謂‘槍手’予以嚴肅查處;把替考等違紀舞弊現象的發生控制在最小程度。”面對作弊治理政策的混亂無序,2004年出臺的《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試圖對此進行統籌:“由他人冒名代替參加考試的應當認定為作弊;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參加國家教育考試,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學校按有關規定嚴肅處理,直至開除學籍;其他人員,由教育考試機構建議其所在單位給予行政處分,直至開除或解聘。”該規定實際上是從中央政策層面開了可以開除替考作弊考生的歷史先河。2005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再次重申:由他人代替考試或替他人參加考試者,學校可以開除。2012年出臺的《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則進一步延續了重點打擊替考作弊的治理思路。總之,經過兩次政策反復,嚴格區分替考與其他作弊行為,并加重替考“量刑”的行政治理體系基本形成。
(三) 2015年至今:“替考入刑”的治理時期
2015年再次爆發的大規模高考替考事件,使得輿論嘩然、舉國震驚,乏力的替考治理體系再次成為人們口誅筆伐的聲討對象。江西替考案實際上加速了“替考入刑”時代的來臨。為此,2015年8月2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明確將“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的替考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它指出:“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為他人實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幫助的,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規定的考試的試題、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第一款規定的考試的,處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分析文本不難發現,替考是唯一被納入刑事打擊的作弊實行行為,刑法的規定實際上是替考治理政策的延續。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是指高考、研究生入學考試、司法考試、會計師考試、公務員考試等十幾種考試。因此,只有在這些考試中替考才適用“替考罪”,而其他考試形式中替考則不適用“替考罪”,但這并不意味著替考行為就能逃脫處罰、“逍遙法外”。事實上,在非“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替考的,通常都會受到取消考試成績、禁考1~3年或開除學籍等行政處罰。自此,我國“雙軌制”的替考治理政策正式形成。
二、 制度邏輯:提升違法成本以期威懾并減少替考行為
(一) 替考泛濫且難以遏制是替考入刑的直接原因
近年來大規模替考事件極其猖狂,而替考行為在法律層面卻不能得到有效規制和懲處。甘肅天水替考案、河南杞縣替考案、江西高考替考案,一樁樁替考案的背后不僅拷問著考生的誠信道德,更問責著乏力的行政治理機制。替考行為的泛濫在很大程度上與治理機制的乏力不無關聯,處罰力度畸輕、違法成本偏低為替考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適宜土壤。在“行政處罰”的治理機制中,對(被)替考者通常以行政處罰為主、高校處分為輔,處罰措施也僅限于取消考試成績、禁考1~3年或開除學籍。但是,“替考成功,收費數萬;萬一被發現,頂多就是開除學籍,不是在校生的話,連這點處罰也起不了作用”[7]。對替考者而言,替考成功則收入過萬;而對被替考者而言,替考成功就意味著獲取了稀缺的入學(職)機會。顯然,與替考作弊的巨額回報相比,替考的違法成本明顯偏低。正是違法成本與灰色收益的不成比例,極大助長了人們的僥幸心理。而事實上,行政法律法規在威懾懲治替考作弊方面已難當大任,而刑法規則的缺漏則限制了刑罰效用的發揮,致使替考歪風長期難以遏制[8]。重典治亂、科處刑罰似乎成了替考治理的最后選擇。而替考作弊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教育難題,西方國家也大多采取刑罰手段打擊替考行為。譬如在美國,替考作弊被視作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一旦指控成立將面臨“牢獄之災”以及高額罰金;而在新加坡、日本等國,替考作弊也將面臨刑事指控,違法記錄則會記入考生誠信檔案[9]。應當說,國外替考治理的實踐經驗,無疑為我國“替考罪”的設立提供了某種啟發借鑒。
(二) 提升違法成本以遏制替考行為是替考入刑的制度邏輯
對替考行為實施刑法打擊是訴諸刑法威嚴,給潛在替考者以心理威懾,并給膽敢以身試法者以自由罰和財產罰,從而通過刑法強力打擊替考行為。事前警醒教育和事后教育改造是刑法作用的兩大機制。事前警告教育通過事先公布法律向全社會傳達替考作弊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和應受刑罰懲罰性,在全社會形成一種警示教育,并給潛在替考者以心理警示,從而首先使其不敢替考;其次,大幅提高替考違法成本的制度設計,也使理性替考者不愿替考;最后,事后教育改造則通過對膽敢以身試法者處以自由罰和財產罰,限制或剝奪其行為能力,從而也使其不能替考。可以說,“揚人性光輝、抑人性丑惡”正是“替考入刑”制度的精髓所在。如果說將替考從其他作弊行為中分離并規定為犯罪體現了刑法理性,那么對(被)替考者與作弊組織者、幫助者分別量刑則體現了刑法謙抑性原則。與組織作弊和幫助作弊最高可處七年有期徒刑不同,替考罪的最高刑罰是拘役,甚至情節輕微的將由財產罰取代自由罰。總之,替考入刑是通過提升違法成本從而迫使人們變成好人的一種制度設計。
(三) 侵害他人權益、危及考試公正是替考入刑的法理基礎
替考作弊是對社會公序良俗的公然違反,也是對他人公正權益的侵權損害,更是對有序考試制度的違法破壞。與偷窺、抄襲等作弊形式相比,替考作弊更囂張跋扈、影響惡劣;而與組織替考、幫助替考不同,替考作弊則更直接危及考試本身的公平公正。作為打擊邪惡勢力的最后利劍,刑法在其他治理手段不能有效根治替考行為之時,必須強勢介入。從法理上說,“法無禁止即自由”,法外自由大量存在。但個人自由卻以他人的正當權益和社會的公共利益為邊界,逾越界線勢必引來法律介入和法律責任。替考之所以入刑,正是因為替考作弊逾越考試的自由界限,而對他人的公正權益與社會的公序良俗造成強烈沖擊與實體損害。此外,替考入刑的價值還體現為它能輔助打擊作弊組織。通過曝光的高考替考案不難發現,替考作弊的背后大多都有專業作弊公司的組織、策劃,旺盛的替考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專業作弊組織的“繁榮興旺”。而遵循“沒有買賣就沒有市場”的邏輯,替考入刑也希冀通過重拳打擊買方市場,從而給火熱的作弊市場以變性“降溫”。
三、 現實局限:單純的刑法打擊并不是治理替考的良方
替考罪的設立讓人們對于有效遏制替考行為信心滿懷。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的正式實施效果來看,情況并不樂觀。新法實施不久,不僅研究生入學考試再次發生了嚴重泄題事件,而且替考作弊也未得到有效遏制,據不完全統計,僅北京破獲的替考作弊案件就不下10起[10]。從目前來看,替考罪的設立并不意味著替考行為的減少或消滅。當然,替考入刑的長遠實效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人的有限理性、情感沖動和僥幸心理,無不在啃噬刑法所精心架構的理性制度。正如學者所言:考試難度有多大,作弊技術就有多高[11]。今日的替考入刑,恐怕只會為今后替考“幽靈”的報復性反彈埋下伏筆:將來方式更隱蔽,技術更高超,識別更困難的替考行為或許會再次顛覆我們的傳統認知。而事實上,“替考入刑”不僅提高了(被)替考者的違法成本,其實反之也大幅提升了替考行為的潛在收益,刺激著無法無天者以身試法的可能性。而刑法作為法律體系的最后一道防線, 并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其作用在于“令行禁止”而非“積極預防”。替考治理本質上作為一個社會問題,除了刑法懲治以外,積極預防也必不可少。顯然,替考治理需要刑事法律的強勢介入,但更需鏟除替考滋生的社會土壤。因此,在嚴格執行“替考入刑”政策的同時,積極探尋替考滋生的社會根源,或許才是治理之路的“末端”。
首先,考試制度的扭曲與異化是替考作弊的制度誘因。長期以來,中國的考試制度扮演著分配社會利益的重大功能:司法考試決定了法律行業的準入門檻,影響著千萬法律人的職業未來;而高考成績也決定了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并影響著未來的就業和發展……正是由于考試制度承載并分配重大社會利益,自古以來國人都高度重視考試,由此形成了一種中國特色的“逢進必考”“唯分是瞻”的考試文化。考試神圣化的背后,本質上是對社會利益的瘋狂追逐。但考試尤其是選拔性的升學考試畢竟是一種殘酷的淘汰機制,篩選的巨大壓力導致了“成神教育”被膜拜而“成人教育”遭冷落。功利化的考試和教育評價制度扭曲了心靈,刺激了部分人的僥幸心理,希冀用一時的鋌而走險換取一世的幸福利益。而且考試愈關鍵、愈重要,鋌而走險、以身試法的可能性也愈大。事實上,考試制度在中國已然異化為利益分配和社會篩選的工具。而替考作弊在實質上就是人們試圖用不法方式來攫取本應由其他方式分配的正當社會利益。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替考作弊難以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因此,為有效遏制替考作弊就應當從源頭上首先淡化考試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舍此而指望能根除替考作弊就只能是那“遙遠的夢想”。具體來說,我們應當改革考試尤其是高考制度,破除全社會對分數和學歷的畸形崇拜,確立多樣化的人才觀,設置更多元化的評價標準,逐漸減少考試的范圍和頻率。唯有如此,方有可能松動替考作弊的生存土壤。
其次,作弊組織的幕后運作是替考行為“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從目前曝光的多起高考替考案來看,替考作弊大多涉及專業作弊組織的幕后推動,且公職人員也參與其中。而在分數、金錢的誘惑之下,一條隱于高考洪流之下的利益鏈條事實上已經形成。據《南方周末》報道,河南高考的替考行情是:要將一個替考者平安送入考場,雇主最少都需要付出 10萬元。其中,中介要抽成約2萬元,考場當地的監考方拿到約2萬元,5萬元左右都得用于打通招辦的人,而“槍手”僅拿到1萬左右[12]。不難發現,正是有了替考組織的造假技術支持和幕后人情疏通,被替考者才敢“光明正大”地花錢雇“槍手”考試,替考者也才膽敢“堂而皇之”地走進考場應試;而正是有了巨額暴利的刺激和誘惑,替考組織才敢如此“無法無天”“藐視法律”。恰如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所言:“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13]因此,如果不能銷毀替考作弊組織這只幕后“黑手”,并斬斷替考背后的利益鏈條,單純打擊(被)替考者恐難見成效。
再次,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也是替考滋生的重要原因。急功近利遵循“成王敗寇”的邏輯,追求“短、平、快”的產出和目的導向。如今這種浮躁心態已經滲透至社會的各個角落,影響到各行各業,教育領域也不例外,高中教育則尤為明顯。在“升學”指揮棒的導引下,完成升學指標成了高中教育的中心工作。家長和社會以此評價教育,教育部門以此考評學校,學校以此考核教師,教師以此評價學生,環環相扣最終鑄就了“只看結果,不談過程”的畸形評價體制;而畸形的評價體制也使得學生和教師發展出“為了升學,不擇手段”的扭曲心態和分裂人格。為了升學,一些學生不擇手段、鋌而走險選擇替考作弊;家長明知而不制止,反而為其供幫助;教師知情而不勸誡,甚至暗示學生為之;學校聞之又無奈,睜眼閉眼默許之。可以說,不擇手段的急功近利直接導致了道德底線的失守和法律紅線的僭越,并表現為替考作弊行為的發生。
最后,社會誠信的整體缺失也助長了替考歪風。近些年來,公職人員的徇私舞弊、教授校長的學術造假、坊間充斥的假冒偽劣……無不是社會誠信整體缺失的真實寫照,經濟利益壓倒誠信道德愈來愈成為眾多個體的價值選擇。而替考作弊的泛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誠信水平低下的一種反映:一方面,黑色暴利刺激了替考組織的產生,從而為大規模替考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缺乏誠信的社會本身更易寬容替考作弊,畢竟其在貪污賄賂等惡行面前顯得格外“相形見絀”,今日方實行“替考入刑”,或多或少受到了這種“寬容”亞文化的影響。回顧這些年來,很多教育機構“上梁不正下梁歪”,教授們論文抄襲、學術腐敗層出不窮,這在某種程度上為學生樹立了一個不良榜樣,使得他們也想方設法在各種各樣的考試當中尋找監管漏洞。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我們需要治理的是替考作弊,倒不如說需要治理的其實是整個社會的不良風氣。
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曾說:“刑罰可以防止一般邪惡的許多后果,但是刑罰不能鏟除邪惡本身。”[1]375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曾說:“刑罰的頻繁總是政府衰弱或無能的一種標志,絕不會有任何一個惡人,是我們在任何事情上都無法使其為善的。”[14]總之,作為一個誠信問題,替考治理需要社會誠信的整體重構,也需刑事法律的適時介入;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治理替考既需嚴格執行的刑事法律,更需鏟除替考滋生的社會土壤。為此,替考治理必須深挖根源、對癥下藥、重點打擊、長期施治,如此,方能還考試以藍天碧水的生態環境。
[1]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張東光.唐代科舉考試舞弊的防范與懲處[J].中州學刊,2007(3):182-184.
[3]李國榮.科場與舞弊——中國古代最大科場案透視[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22.
[4]朱從矩.搞好教學管理提高教學質量[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2):118-122.
[5]秦惠民.入學機會的公平——中國高等教育最受關注的平等話題[M]//勞凱聲.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八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0:112-136.
[6]史志英.大學生考試作弊的心理分析[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4):77-85.
[7]練洪洋.對替考“槍手”應大刑伺候[N].深圳特區報,2014-07-09(A02).
[8]李朝暉.建議刑法增設重大考試舞弊罪[J].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4(3):73-75.
[9]陳鵬.考研疑似再次遭遇泄題:研究生招生考試又陷“誠信風波”[N].光明日報,2015-12-31(006).
[10]田珍祥.替考當“槍手”,豈料撞“槍口”[N].中國消費者報,2016-01-18(001).
[11]練洪洋.“考試作弊”入刑相當給力[N].廣州日報,2015-06-26(F02).
[12]文峰.別讓高考作弊成為定時丑聞[N].長沙晚報,2015-06-09(F02).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29.
[14]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47.
(責任編輯馬雙雙)
doi:10.13316/j.cnki.jhem.20160829.002
Surrogate Exam-Taking Taken into Criminal Punishment:Polic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Reality Limitations
DUANBinbin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Governance of surrogate exam-taking has experienced the policy transformation from “soft constraint” to “criminal punishment”, and finally formed the “double-track” governance framework. Taking surrogate exam-taking into criminal punishment is a system design that forces people to become good men by raising the illegal cost. Bu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its effect,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behavior of surrogate exam-taking will be reduced or even eliminated. Punishment can prevent the consequences of evil in general, but it cannot eradicate evil itself. Governance of surrogate exam-taking requires a strong intervention of criminal law,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wipe out the social soil that breeds the cheating. In addition to strictly implementing the punishment, we should also weaken the functions of exam as “interest distributor” and “social filter”, cut their interests chain, improve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purify people’s mentality of flippancy and utility.
surrogate exam-taking behaviors; governance of surrogate exam-taking; criminal punishment of surrogate exam-taking behaviors
10.13316/j.cnki.jhem.20160829.003
2016-04-25
全國教育科學規劃2015年度國家重大課題(VEA150004);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16XNH041)
段斌斌,博士研究生,從事教育法學研究。
G640
A
1673-8381(2016)05-0029-05
網絡出版時間: 2016-08-29
網絡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160829.1108.0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