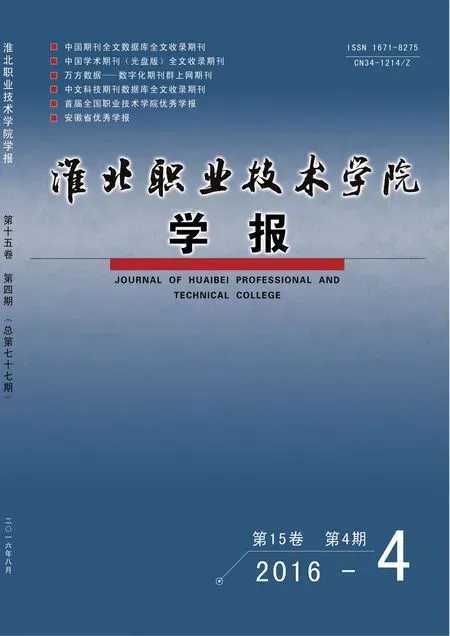先鋒中的“人性”關照——論蘇童小說《我的帝王生涯》
王麗婷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0)
?
先鋒中的“人性”關照
——論蘇童小說《我的帝王生涯》
王麗婷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550000)
摘要: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一批作家以嶄新的歷史觀念和話語方式對歷史進行重新陳述和再度書寫,顛覆了傳統歷史書寫的特定價值和敘事方式。蘇童就是這批作家中的一位。其新歷史主義小說代表作《我的帝王生涯》以民間化的歷史觀、先鋒性的創作技巧,將對“人性”的關照寓于先鋒品格之下,鮮明地體現了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創作特色。
關鍵詞:先鋒性;新歷史主義;宿命感;人性
蘇童創作頗豐,且作品風格各異,他的小說都帶有濃重的傳奇色彩,可讀性很強。作為蘇童新歷史主義小說的代表作《我的帝王生涯》講述了一個帝王傳奇的一生:一個懵懂的皇子在宮廷權利的操縱下成為了“假燮王”,走向人生頂峰,后由盛而衰,皇權覆滅,淪為平民,成為走索藝人,最后在戰亂中出家為僧,走完如夢的一生。
在作者本人看來,《我的帝王生涯》就是“一場很長的白日夢”。蘇童曾這樣評論道“我認為歷史長河中的人幾乎就是盲人,而歷史是象,我們屬于盲人摸象的一群人,……《我的帝王生涯》的寫作大概只是一個很長的白日夢,在北京上學期間我多次去故宮,那里的紅墻綠瓦浮云滄桑誘使你做這種白日夢,這個小說中的歷史是無法對號的,因為是虛構,我寫這個小說的真正沖動在于設想了端白戲劇化的一生,從帝王淪為雜耍藝人,其中的環節創造給你一種推理破案的快感,大起大伏的人生,正好配合我多余的泛濫成災的想象力。”[1]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蘇童將高超的先鋒敘事品格和精妙的故事塑造能力完美結合,在先鋒性的創作技巧下進行“人性”的關照和反思。
一、先鋒手法的運用
《我的帝王生涯》雖然從歷史的角度進行敘事,但作者巧妙運用反諷等藝術手法消解了傳統歷史題材作品的崇高性和莊嚴感。
(一)新歷史主義
中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新歷史主義文學創作是在西方新歷史主義批評理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蘇童作為這一創作流派的代表,其創作印證了新歷史主義小說的發展軌跡。在《我的帝王生涯》中,作者以民間化的歷史觀念、人性化的寫作立場和虛構化的敘事手法將新歷史主義運用得非常到位。
一個虛構的燮國,一個本就不該為王的君主。蘇童用一段我們找不到相對應的歷史國度和一系列歷史事件,敘述了第五代燮王端白傳奇的一生。正如作者在自敘中提道:“《我的帝工生涯》是我隨意搭建的宮廷,是我按自己喜歡的配方勾兌的歷史故事,年代總是處于不詳狀態,人物似真似幻一個不該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個做了皇帝的人最終又成了雜耍藝人。我迷戀人物的峰回路轉的命運,只是因為我常常為人生無常、歷史無情所震懾。”[2]
(二)悲劇化的宿命感
所謂宿命感,是一種無力、無助的感覺,人擺脫不了命運注定軌跡的走向,即便能夠感知命運的結局依然無法控制。《我的帝王生涯》嫁接在具有宿命色彩的人生之旅上,是其先鋒性又一鮮明特征。
父王的駕崩開啟了端白悲劇化的一生,正如端白的師傅覺空所說的:“少年為王,既是你的造化,又是你的不幸。”他的即位便是悲劇化宿命的開始。十四歲的懵懂少年,關注父王的煉丹爐、喜歡玩促織、留心皇甫夫人帶上的玉如意,卻無法履行一個帝王該盡的義務。從此,一個少年天真的人性便因為權力所使而墮落,他不關心朝政,也因為朝政被皇甫夫人和孟夫人兩個女人所把控;他不關心百姓疾苦,他也不關心邊疆戰事,將有功之臣楊松射殺在田野當中。“我不喜歡當燮王,我喜歡走索藝人。”他向往的是走索藝人那看似無拘無束的生活,但宿命的安排卻將他放到帝王的位置。同時,這宿命的安排又是極具戲劇化的,災難拯救了端白,他作為失敗者被趕下了帝王的寶座,他又有了可以完成從前想要企及的生存要求——做一個走索藝人的機會。
這部小說中還有一道極為突出的宿命色彩,就是對災難降臨的寓言式的“咒語”。這個寓言災難的“咒語”多次出現在人物命運和情節發展的轉折關頭,成為支配小說的籠罩性存在。第一次出現在父王駕崩時,一個瘋了的老宮役孫信是這個災難寓言的發出者。煉丹爐大火熄滅時,寓言再一次響起。燮王的殘暴、閹宦得寵、孫信之死、后宮爭斗、南伐兵敗、酷刑至此、燮王荒淫等都引來災難寓言的出現。同時,天上的鳥兒叫著“亡……亡……亡”也是一種寓言化的出現。寓言隱語的反復使用使作品的宿命色彩更加濃郁,是作品先鋒品格的顯著標志。
(三)無處不在的諷刺
反諷是新歷史主義小說中最常用到的一種手法,是用來解構崇高的基本策略,受到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青睞。它用比喻、夸張等手法對人或事進行揭露、批評或嘲笑。《我的帝王生涯》中就無處不運用著各類諷刺手法。
歷史本身就具有很強的諷刺感。在一個女人的權謀之下,燮國上演著一出王位繼承的騙局。皇甫夫人臨終告知端白“你不是真正的燮王,是我把你變成了燮王。”,“我不喜歡端文,也不喜歡你。這只是我跟你們男人開的一個玩笑。我制造了一個假燮王”。與此同時,小說中充滿了對人性的諷刺,“黑豹龍冠已經緩慢而沉重的扣上我的頭頂,我覺得我的頭頂很涼”本不該成為燮王的“我”對于這頂無數人覬覦的王冠卻不屑一顧。面對瘋搶黑豹龍冠的楊夫人,“我”只是說“你想要就拿去吧,我本來就不喜歡”。皇甫夫人和孟夫人,兩個在群臣面前端莊文雅的女人,一個暴虐兇殘,一個粗鄙下流。皇甫夫人教導端白“為王者仁慈第一,千萬不可殘暴兇虐”的場景與小宮女被皇甫夫人壽杖打出包的額頭形成鮮明對比。[3]
這個帝王生涯對于端白來說是一場白日夢,但對于最后將王位搶到手的端文來說,何嘗不是一場白日夢。作者寫端白在位期間種種不理朝政和暴虐的行為,帶著求知心理的讀者讀下去,期望端文的即位會帶來勵精圖治的一面,但作者沒有這么寫。取得最高權力的人首先做的事就是除掉與其一同起兵的西王昭陽,這樣的情節不出意料,因為歷史不乏這樣鮮活的案例。作者的安排更加徹底,讓人們將這場白日夢繼續做下去。端文即位短短幾年便招來鄰國大舉進犯,這個本不存在的燮國真正消失了。彭國同樣是作者虛構的國家,作者沒有寫下去,但彭國將來的命運走向我們也可想而知。這又何嘗不是一種諷刺。
二、人性的剖析
作者依照新歷史觀念和人性觀念巧妙地擺弄著人物的言行和命運。《我的帝王生涯》沒有明確的歷史年代,其中的歷史人物也都是虛構而來,但這些人物卻是中國歷朝歷代,甚至是當今中國很多人性的縮影。小說中充滿了蘇童對人性的失望,無處不是“他人即地獄”的描寫。
親情本應是人與人之間最原本、最溫暖的感情,但親情關系一旦置于王室之中,這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感情就蕩然無存。皇甫夫人是端白的祖母,又是他一生悲劇命運的導演者。身為人子的端白在先王駕崩的那天早晨極不情愿地參加父王的葬禮,“我討厭死者,即使死者是我的父親”。本應手足情深的兄弟之情也是刀劍相向。異母兄弟們“他們用類似敵視的目光望著我”,當聽到“我”被冊封的宣旨,“我”異母兄弟們“臉色蒼白,端軒緊咬著他的嘴唇,而端明咕噥著什么,端武朝天翻了個白眼,只有端文故作鎮靜”,隨后上演的就是圍場捕獵中暗殺的一幕。
少年為王的端白,早已學會了一切帝王的惡習,寵宦、荒淫、殘暴、無信。因厭煩冷宮半夜里傳來的哭聲,憑借著“我有權毀滅我厭惡的一切”權勢,剜去了十一位被廢黜嬪妃的舌頭“那些愛哭的嬪妃們的舌頭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紅鹵豬舌”;將為國出力的楊松連射三箭殺害在田野之中;對農民起義首領李義芝實施猢猻倒脫衣、仙人駕霧、茄刳子、披蓑衣、掛繡球等十一種慘無人道的極刑。聽完燕郎敘述,端白說道“早知這么有趣,我倒會起駕親往觀刑了”。
一國之君尚且如此,后宮中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殘殺可想而知。當“我”即位時,端文的生母楊夫人想要搶走“我”的黑豹龍冠。隨后,被賜死的楊夫人因拒死不從而被十九顆長釘釘死在棺木之中。因為妒忌黛娘能在琵琶上彈奏出美妙音樂,孟夫人割掉了其十指。牡丹園賞花時,出于對受寵的蕙妃的厭惡之情,也因蕙妃的無心之舉,所有人便惡語相向。“瞎了眼的母狗。蘭妃怒目回首,并朝準蕙妃的臉上啐了一口唾沫。”“狐精。菡妃說。”“妖女。堇妃說。”“不要臉的小賤貨。彭王后說。”人與人之間毫無諒解和寬容可言,而是竭盡全力將對他人的侮辱達到了極致。
三、結語
《我的帝王生涯》在先鋒品格的運用和人性的剖析上無疑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作者寫惡并不只是為了揭示惡,寫丑也并不只是為了批判丑。我們所相信,作者對人性進行不斷反思的同時,也將這樣一個批判與期冀的“接力棒”傳給了讀者。
參考文獻:
[1]蘇童.《我的帝王生涯》只是個白日夢[J].文藝理論研究,1997(5).
[2]蘇童.蘇童文集·后宮·序[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3]蘇童.蘇童文集·后宮[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責任編輯:之者
收稿日期:2016-05-15
作者簡介:王麗婷(1989-),女,河北石家莊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14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現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4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275(2016)04-006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