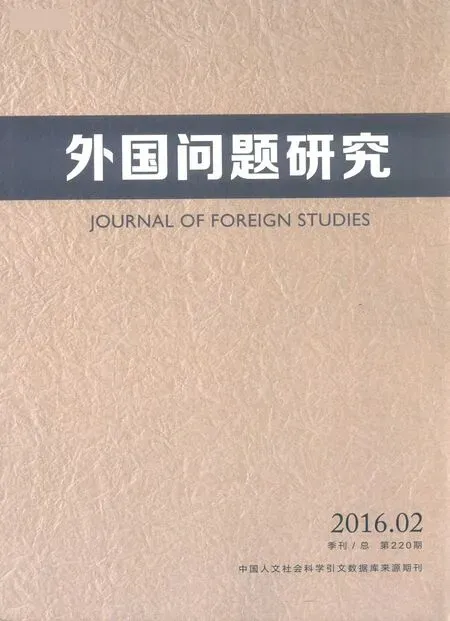《中國孟子學史》韓文版序
黃 俊 杰
(臺灣大學 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臺灣 臺北 10617)
?
《中國孟子學史》韓文版序
黃 俊 杰
(臺灣大學 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臺灣 臺北 10617)
這部書原是拙著《孟學思想史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年)的第2卷,承蒙成均館大學研究教授咸泳大博士的善意譯為韓文,得以向廣大的韓國學界朋友請教,我要首先向咸教授敬致謝意。因為本書內容聚焦在歷代中國思想家對孟子學的解釋,所以韓文版訂名為《中國孟子學史》。我樂于在出版前夕,就韓國孟子學研究的新課題略申管見,以就教于本書讀友。
韓國孟子學研究的第一個新課題是朝鮮時代(1392—1910)儒者對孟子政治思想的詮釋。這項研究課題可以從東亞歷史脈絡來看。在東亞各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儒家經典中的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間有著極其復雜而互相滲透的互動關系。我曾回顧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與朝鮮歷史中,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關系,指出兩者之間具有兩種關系。第一,儒家“知識”與中韓兩國政治權力既互相依賴而又互相滲透;但知識與政治權力畢竟性質不同,在帝國體制之下,皇權是至高而終極的權力,而儒臣的權力則是衍生性的權力,而知識與政治權力也各有其不同的“運作邏輯”(modus operandi),所以儒家知識分子與掌握權力的帝王之間,有其永恒的緊張性。在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與朝鮮都是大一統的政治體制。大一統帝國需要儒家價值系統作為帝國的意識型態基礎,以有效運用各種人力及物力資源;為謀帝國的長治久安,中韓兩國帝王亦須不斷吸納儒家知識分子進入體制中,成為政治權力的執行者。所以儒家的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間,又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近代以前中國與朝鮮歷史上的知識與政治權力之所以既不可分割而又互為緊張,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學經典之特質。古典儒家提出“內圣外王”作為最高的人生理想,認為個人內在道德的修為與外在事功的完成是不可分割的。換言之,內在道德的修養不僅是個人內在思想的玄思而已,它必須進一步落實在客觀的外在環境之中。在“內圣外王”理念下,東亞儒家文化圈中一直潛藏著巨大的將儒家知識落實在政治現實上的動力。儒學知識系統的強烈實踐取向,使儒學經典在近代以前的中韓兩國歷史上必然與權力結構發生深刻的關系。*Chun-Chieh Huang,“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fucian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raditional China and Korea: A Historical Overview,”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 8,No.1,June 2011,pp.1-20.
以上所說的儒家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兩種關系,在《孟子》這部儒家經典的解釋史中,以最鮮明的方式呈現。這主要是由于孟子政治思想以“王道”為其核心價值,孟子痛感戰國時代“霸道”政治殺人無數,起而游說各國國君施行“王道”政治,成為“大有為之君”,一統天下。孟子鼓勵他的時代的國君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堅信:每個人生下來就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心”,他稱之為四種“善端”。孟子說,包括國君在內每一個人只要善自保存并加以“擴充”(用孟子的話)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善端”或“良知”,就可以興發“不忍人之心”,國君只要將這種“不忍人之心”加以“推恩”,加以“擴充”,就可以落實“不忍人之政”,也就是孟子理想中的“仁政”。正如本書第4章所指出的,孟子政治思想包括三項重要主張:一、政治權力的運作以人民的意志為其依歸;二、權力合法化之基礎在于統治者在道德上之成就;三、權力施行的目的在于保障每個人的福祉。這三項主張共同構成孟子“王道政治”的論述。
孟子“王道政治”的理想,對近代以前中、韓、日各國的統治者,都形成很大的壓力,中國明代開國國君朱元璋(在位于1368—1398)讀《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語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黜孟子祠,并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命人刪削《孟子》原典。德川時代講官為日本皇太子講《孟子》,亦以民本政治思想為禁忌。日本儒者批判撻伐不遺余力,指孟子為“亂圣人之道”,*高松芳孫:《正學指要》,《日本儒林叢書》第11冊,東京:鳳出版,1978年,第37—38頁為“仁義之賊,……圣人之大罪人”,*高松芳孫:《正學指要》,第46頁。兩千年來東亞儒者正面詮釋或反面批駁孟子的論著,在君主專制體制下的帝制中國或德川日本或朝鮮時代朝鮮的歷史情境中,使《孟子》這部經典成為為苦難人民伸張正義的福音書,而不是象牙塔里的高文典冊。
《孟子》這部書所揭示的政治思想,不僅在中國與日本激起讀者的驚恐,朝鮮儒者申教善(淔泉,1786—1858,正祖10年—哲宗9年)讀《孟子》時,也提出類似的問題:
問:齊宣王之以湯放桀、武王伐紂謂臣弒其君者,其非歟?孟子以聞誅一夫紂為對,得無過歟?紂雖殘賊,曾為萬乘之主,則謂之一夫而加誅焉,得無迫切歟?*申教善:《讀孟庭訓》,《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45冊,漢城: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1988年,第62—63頁。
申教善生于政治權力一元化的時代,不能理解生于政治權力多元時代的孟子的政治言論。因此之故,后世的經典解讀者就賦古典以新義,企圖愈合他們與經典的距離,例如申教善就將孟子思想別創新解,以響應他自己的設問。*申教善:《讀孟庭訓》,第63—64頁包括申教善在內的東亞儒者解讀《孟子》時,所提出的各種如同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謂的“話語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深深地被權力所滲透,而且互相進行內部的權力斗爭(Michel Foucault,ArchaeologyofKnow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孟子》一書在東亞不僅在各國權力網絡中被解讀,而且不同的《孟子》解讀者之間,也互相進行激烈的論爭。
朝鮮時代儒學取得近乎國教之地位,對朝鮮政治與社會影響深遠。*Martina Deuchler,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 A Study of Society and Ideology,Cambridge,Mass.and Londo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2.朝鮮孟子學源遠流長,從16世紀李滉(退溪,1501—1570,燕山君7年—宣祖4年)的《孟子釋義》開始,釋孟闡孟的論著風起云涌,雖然朱子學是主流思想,例如樸光一(遜齋,1655—1723,孝宗6年—景宗3年)對孟子“浩然之氣”說的解釋完全籠罩在朱子學之下。但是,也有不遵朱注的李瀷(星湖,1681—1763,肅宗7年—英祖39年),甚至也有鄭齊斗(霞谷,1649—1736,仁祖27年—英祖12年)釋孟所顯示的陽明學立場。具有朝鮮文化特色的“人性物性異同論”等問題,也融入孟子學解釋之中。從東亞比較思想史的視野觀之,朝鮮孟子學的發展可以視為朝鮮思想主體性的形成與發展的表現,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發掘其學術研究上之潛力。
關于朝鮮儒者對孟子政治思想的詮釋研究,我們可以聚焦在孟子學的核心概念“仁政”之上。在孟子政治思想中,“仁心”與“仁政”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孟子以“不忍人之心”向外“推恩”,落實而成就“不忍人之政”。但是,孟子的“仁政”理想在兩千年來中、韓、日等國的儒者或儒臣的詮釋中,多屬于蕭公權(1897—1981)先生所說的“政術”,較少屬于“政理”之范圍,*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年,第946頁。也就是牟宗三(1909—1995)先生所謂“治道”遠大于“政道”,*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北:廣文書局,1961年,第1,48,52頁。朝鮮儒者對孟子“仁政”說的論述更是如此。舉例言之,16世紀的李彥迪(晦齋,1491—1553,成宗22年—明宗8年)所撰《進修八規》的第六條就是“行仁政”,但是我們進一步看李彥迪對“仁政”的解釋,他說:
自古人君欲施仁政而害于仁者,有二:刑罰煩,則怨痛多,而害于仁矣;賦斂重,則民竭其膏血,而害于仁矣。故孟子以省刑罰、薄稅斂,為施仁政之本。蓋不能如是,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李彥迪:《疏·進修八規》,《晦齋先生文集》第1冊,卷8,收入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638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427頁。
李彥迪對孟子的“仁政”之解釋,完全落實在具體的政治措施。18世紀的丁若鏞(茶山,1762—1836,英祖38年—憲宗2年)更以井田制度作為“仁政”之確解,丁茶山說:
臣謹案:孟子每以井田為仁政。仁政者,井田也。孟子謂:“雖堯舜,不行井田,則無以治天下”。此圣門相傳知要之言也。井田,如規矩焉,如律呂焉,以譬黃鐘。非臣之言,乃孟子之言也。*丁若鏞:《地官修制田制九》,《經世遺表》卷7,收入茶山學術文化財團編:《(校勘·標點)定本與猶堂全書》第25冊,首爾:茶山學術文化財團,2012年,第126頁。
李彥迪與丁茶山都將孟子的“仁政”解釋為行政措施,固然與他們浸潤在朝鮮時代“實學”思想氛圍有關。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權力是被擁有“終極的權力”的國王所授予的“衍生的權力”,他們不能像孟子一樣地挑戰統治者的政權之合法性(legitimation)之問題。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以上所說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仁政”這個研究課題,涉及很多衍生性的問題,在中國思想史上較為重要的有王霸之辨問題、尊周或不尊周問題、君臣關系問題等,我在本書第4章已有詳細分析。朝鮮儒者金昌協(農巖,1651—1708,孝宗2年—肅宗34年)門人魚有鳳(杞園,1672—1744,顯宗13年—英祖20年)撰有《孟子不尊周論》,*杞園:《孟子不尊周論》,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184集,《杞園集》卷22,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年,第251a—252b頁。洪泰猷(1672—1715,顯宗13年—肅宗41年)也撰《孟子不尊周論》,*洪泰猷:《孟子不尊周論》,《韓國文集叢刊》187集,《耐齋集》卷5,第81d—83a頁。對孟子鼓吹諸侯行王道而不尊周王有所辯論。此外,如管仲論或湯武革命論這一類從孟子“仁政”說所衍生的相關問題在朝鮮時代的發展,也是朝鮮孟學研究中可以推展的研究議題。
朝鮮孟子學研究的第二項課題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主張人生而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四端之心”。孟子心學在中國思想史中從朱熹(晦庵,1130—1200)、王守仁(陽明,1472—1529)、黃宗羲(梨洲,1610—1695)、戴震(東原,1724—1777)、到康有為(長素,1858—1924),到20世紀中國新儒家學者唐君毅(1909—1978)、徐復觀(1904—1982)、牟宗三,均提出理趣互異的新詮釋。我在本書第5、6、7、8、9、10各章已有所討論。孟子性善論在朝鮮時代也歷經新的詮釋。朝鮮儒者取孟子的“四端”與《禮記》的“七情”之說,而對所謂“四端七情”展開辯論,李滉(退溪,1501—1570)、李珥(栗谷,1536—1584)、丁時翰(愚潭,1625—1707)、李玄逸(葛庵,1627—1704)、鄭齊斗(霞谷,1649—1736)、李柬(巍巖,1677—1727)、韓元震(南塘,1682—1751)、李瀷(號星湖,1681—1763)、丁若鏞(茶山,1762—1836)與李恒老(華西,1792—1868)等人均撰文詳加析論。李明輝教授所撰《四端與七情:關于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一書,對朝鮮儒者的“四七之辨”有非常詳細的探討,是這一項議題極為重要的研究論著。
總之,孟子學內外交輝,“仁心”與“仁政”融貫為一,但自從大一統帝國從東亞歷史的地平線升起之后,孟子的思想世界就成為近兩千年來東亞各國知識分子心中“永恒的鄉愁”。東亞知識分子就像生于山澗而成長于海洋的鮭魚,在長大之后奮其全幅生命力游回它們原生的故鄉。《孟子》這部經典,兩千年來一直召喚著東亞各國的儒者,使他們心向往之,起而與孟子對話。我謹以虔敬至誠之心,敬獻此書于韓國讀友面前。如果此書韓文本的出版,能為未來東亞孟子學以及朝鮮孟子學研究的推進,貢其一得之愚,則幸甚焉。
(責任編輯:董灝智)
2016-05-30
黃俊杰(1946-),男,臺灣高雄縣人,臺灣大學講座教授;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A[文章編號] 1674-6201(2016)02-01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