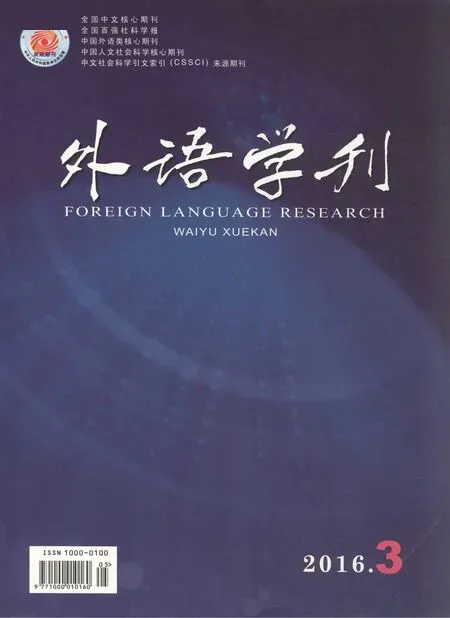邏輯向度與語法向度:13世紀拉丁語語境中《解釋篇》研究*
王建魯
(黑龍江大學,哈爾濱150080)
邏輯向度與語法向度:13世紀拉丁語語境中《解釋篇》研究*
王建魯
(黑龍江大學,哈爾濱150080)
《解釋篇》探討的究竟是邏輯的內容還是語法的內容,是13世紀拉丁語哲學家反復討論的問題。本文主要從3個方面探討:第一,既然Perihermeneias主要關注表述性陳述,那么為什么它被翻譯為DeInterpretatione而非DeEnunciatione,即《解釋篇》的內容究竟是邏輯的還是語法的還是邏輯與語法的聯合;第二,中世紀拉丁語注釋家如何看待亞里士多德在文本中對于名詞和動詞這兩類詞項的處理;第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他們又是如何看待出現在亞里士多德文本中的非限定動詞和名詞的。本文從達契亞的馬丁、羅伯特·基爾沃比、大阿爾伯特以及法弗舍姆的西蒙等人的角度出發,嘗試找出這一時期處理這些問題的異同。
拉丁語;解釋篇;邏輯向度;語法向度
在《解釋篇》(Perihermeneias,DeInterpretatione)的拉丁語傳統評注當中,對于文本的邏輯研究和語法研究之間關系的追問從未停止。在13世紀的拉丁語哲學環境中,追問主要包括著作的主題內容及其在邏輯中的位置等。事實上這些追問最終給后來文本提供引用與詮釋的一系列權威性原則。具體而言,這些追問主要討論前4節的文本內容,它們主要著眼于語言學主題的亞里士多德視角,即邏輯視角,以及普里西安(Priscian,全盛時期在公元500年)的處理方式,即語法視角。
1 《解釋篇》主題:邏輯的抑或邏輯與語法的
在這一時期,盡管波埃修(Boethius,480-524)對于標題名稱的解釋與辯護給予這一時期的評注家們以靈感源泉,但是這些極具個性的評注家多多少少已經與波埃修的評注漸行漸遠,他們關于標題中解釋(interpretatio)含義的闡釋已經不能與波埃修的觀點和諧相處。
在回答表述(enuntiatio)是否是《解釋篇》中主題的時候,達契亞的馬丁(Martin of Dacia,以下簡稱馬丁)引用波埃修的定義:“依照波埃修的觀點,解釋——如同這里所使用的——只是意義來自于自身的口語,在其中要么為真,要么為假”(Martin of Dacia 1961:236)。盡管馬丁引用的第一部分來自波埃修,但是他明顯地加入自己的觀點,這是因為波埃修明確反對解釋必須持有真值。事實上,在闡釋亞里士多德文本的時候,波埃修明確反對將表述等同于解釋,真值是表述的標志,而非解釋。
同時,盡管馬丁贊同波埃修將助范疇詞排除到解釋之外的觀點,但他接著卻爭辯說解釋也排除名詞和動詞,也就是說它排除所有非復合口語,這是因為對于馬丁而言復合性是真值分配的必要條件。因此,盡管馬丁嘗試將解釋的定義與邏輯-語法的區分聯系起來,但是他顯然已經修改波埃修的定義,因此他認為亞里士多德名詞和動詞理論變成解釋的預備性知識而非基本部分。盡管如此,他最終還是將真值加入波埃修的定義當中,表明他希望把《解釋篇》中的方法識別為邏輯的,并且值得用理性科學命名的東西。
與馬丁相反,羅伯特·基爾沃比(Robert Kilwardby)在闡釋解釋的過程中明確提及邏輯與語法以及邏輯與修辭之間的區別。基爾沃比詳細地論述波埃修關于解釋的另一個定義:“我們是依照波埃修來理解解釋的,解釋在這里意味著‘表述意義圖像的口語’。基于這一原因,本書不能被歸類為語法或者修辭,因為‘意義圖像’包含高于‘意義’的東西,也就是說,意義是經由語法學家以及演說家通過適當的、一致的假設來呈現的,一致是由于語法學家,而適當則是通過演說家。《解釋篇》應該同時被放置到理性哲學與語言哲學當中,這是因為理性哲學不能孤立于言語”(Kilwardby 1978:379)。盡管基爾沃比并沒有像馬丁一樣明確提及真值,但他強調邏輯如同語言學一樣都是理性的,它們都履行相似的功能,任何一種理性科學都預設語法和修辭的完構性作為必要條件。
基爾沃比認為語法主要著眼于一致與不一致,而邏輯主要著眼于真與假來審視語言。他認為《解釋篇》中口語的定義(亞里士多德 1990:49)明顯不同于普里西安的定義:“在考慮言語真假的時候,邏輯學家通過意指的事物來定義言語,這是因為真與假是言語中意指的事物造成的;因此亞里士多德說‘言語是有意義的口語。’但是語法學家考慮的是言語中的一致與不一致,他們是通過次序來定義言語的,這是因為一致與不一致是由聯合意指的事物導致的;它們反過來成為事物的結果。因為事物是詞與詞之間結構與秩序的媒介,所以結構和次序都可以歸之于事物。因此,普里西安說‘言語是語詞的一致秩序’”(Kilwardby 1978:4-11)。顯然,基爾沃比已經將評注家的關注點放在真值上,而言語則意指能夠被斷定為真假的事物。
可以看到,評注家們意圖改變波埃修關于解釋的理念來適應邏輯的理性特點以及對于真和假的特殊關注離開亞里士多德關于某些明顯語言學主題的考量,從而轉向對同等邏輯興趣的排除。馬丁和基爾沃比等人也開始簡單地把邏輯識別為理性科學,語言看成語言科學,并且不情愿地把邏輯從語言學藝術中割裂開來。對于邏輯學家而言,在他們專注于把邏輯當成理性科學的同時,如同亞里士多德在第二節和第三節中那樣,他們也意識到文本包含對于語言學現象的考量,這一雙重考量也影響他們對一般詞項(包括名詞和動詞)和非限定詞項(包括動詞和名詞)的理解。
2 一般詞項:邏輯對象還是語言學對象
在《解釋篇》的第二節和第三節,亞里士多德討論名詞和動詞,因此拉丁語評注家基于這兩個小節展開這部分處理方式的邏輯與語法討論。這些討論意在證明邏輯學著作中語法主題考量的合法性以及最偉大的邏輯學權威無法與最偉大的語法權威普里西安在處理相同語言學對象的過程中達成一致的原因。
依照基爾沃比的觀點,語法學家通過分析口語的具體化開始他們對于名詞的處理。他們的分析以理性結尾,即在作為語言學符號的語詞所強加的被意指概念內容中結束;他們主要關注語詞的真實口語結構。邏輯學家則是開始于被意指的概念內容,結束于它的口語符號。(Kilwardby 1978:386) 當然,基爾沃比的觀點并不意味著邏輯學家的終極關懷僅在于口頭表述:事實上,他的斷言反映出亞里士多德在文本中建立的符號關系秩序,這種口頭語詞被視為心靈情感的符號。由于邏輯學家主要關注作為概念符號的語言,于是這種概念構成邏輯的主焦點,它們的口語具體化研究也被引入。在發現語言探究的起點這一差別之后,我們還發現邏輯學家無法簡單地使用名詞和動詞的語法含義作為現成的規則。
事實上,基爾沃比似乎旨在堅持語詞是可構造物,鑒于它們被視為口頭語言;同時它們也是主項和謂項,鑒于它們被視為概念的符號。因此,只要邏輯學家和語法學家從不同的起始點來研究這些相同的客體,那么由亞里士多德和普里西安提供的定義就必然有區別。對于基爾沃比而言,邏輯的名詞與動詞和語法的名詞與動詞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客體,它們只是通過不同的方式被理解;它們定義中的分歧不是由于含混,而是由亞里士多德與普里西安在名詞研究過程中終極目的的多樣性決定。
關于為什么邏輯學家不能簡單地從語法學家那里借用定義,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詳盡地解釋基爾沃比的觀點,即邏輯開始于理性,結束于言語。大阿爾伯特解釋說由亞里士多德給出的名詞的邏輯學定義是一種慣常的有意義的口頭語言,它把口頭陳述視為存在于心靈當中的客體相似物的直接符號。它反過來成為邏輯學家訴諸真與假作為基本原則的基礎,嚴格地說,真與假只存在于知道的心靈當中,它的作用在于復合以及劃分概念以便將它們與已知的事物相符合。語法學家的名詞定義作為“具有性質的質料”徹底忽略語言和心靈之間的關系。鑒于普里西安的定義直接指向事物本身的質料和性質,因此概念性調解使得將真值分配給陳述變得可能。
HCC AM伴IVCTT患者臨床可表現為腰痛。影像學表現可表現為腎上腺區占位伴隨下腔靜脈內充盈缺損,而缺乏肝臟原發腫瘤的表現。或者腎上腺轉移瘤與肝臟病變分界不清。當影像學檢查同時發現肝臟病變和腎上腺病變時,常不易辨別原發灶與轉移灶。泌尿系增強CT或MRI亦有誤診可能。診斷的金標準為活檢或手術切除后的病理確診。患者既往史多有病毒性肝炎感染病史。
對于大阿爾伯特而言,語法學家主要從就它們是事物的直接符號而言來考慮這些符號,因此他說名詞意指具有性質的資料,邏輯學家則說它是慣常的有意義的口語。事實上,大阿爾伯特的解決方案受到一些制約,即我們必須解釋以下矛盾:普里西安在他關于名詞的定義中提及的質料與性質看起來是建立在關于外在世界的形而上學架構之上,而亞里士多德關于名詞的定義以及《解釋篇》的一般方法看起來則是根植于通過概念作為中介的現實意義。但是,如果我們把評注傳統的這些部分看成是一個整體,那么大阿爾伯特的評注就闡明拉丁語作家對待邏輯的語言學方面的方法的普遍特征。
大阿爾伯特關于亞里士多德和普里西安的比較使他得出如下結論,即在語法和外在于精神的現實之間存在比之邏輯和相同的現實之間更強的聯接。相較之下,基爾沃比關于普里西安和亞里士多德口頭言語的定義的比較導向強調邏輯更直接地與符號化的事物有關,盡管對于基爾沃比而言,語法也在最根本上把事物看成是聯合意義研究的尺度。但是當基爾沃比在處理兩個權威在名詞的定義、理性的關系之間區別的時候,作為原則還是作為終點就成為橫亙在邏輯學家與語法學家之間關于語言的視角的重要因素。
3 非限定詞項:排除還是納入
拉丁語評注家接受波埃修的如下觀點,即這些被亞里士多德稱作“不確定的”詞項,確切地說是非限定的,因為它們所意指的是純粹的否定而不是含混。基于這種解讀,詞項“非X”比如“非病的”(亞里士多德 1990:50-51)可以用來表述X之外的所有事物,甚至那些非存在的主體,不過它無法命名被視作X的某些缺乏的特殊處置方式,比如“失明”,它只能有意義地謂指潛在成為X的事物。
法弗舍姆的西蒙(Simon of Faversham,1260-1306,以下簡稱西蒙)爭論說非限定名稱不能作為表述性陳述,因此,非限定詞項無法意指概念性內容,不能被心靈復合或者劃分:“注意非限定名詞和非限定動詞被從邏輯學家的考量中排除出去,這是因為邏輯學家所考量的名詞和動詞必須是表述的部分,但是非限定名詞不是表述的部分,這是因為所有能成為表述部分的事物必須能夠意指心靈中的概念,這是因為對于表述而言這主要是為了求真。不過,它們并沒有被從語法學家的考量中排除出去,這是因為它們通過和其他東西組合起來,于是持有名詞和動詞的那些偶性。”(Simon of Faversham 1957:152-153)。
在這里,西蒙對于文本的解釋存在一個明顯問題。盡管關于邏輯內含物的標準應用看起來并無異議,但是這一應用卻遭遇亞里士多德自己文本的挑戰。當亞里士多德聲稱非限定名詞和動詞在準確意義上并非完全是名詞和動詞的時候,但在第十節中看起來則是在掩飾自己做出的判斷,即他在這里重新斷定說從邏輯上講,非限定名詞是非真的名詞。對于亞里士多德文本更為可能的解釋應該是,他把非限定詞項引入到文本當中是因為它對上反對和下反對理論的邏輯重要性,盡管傳統的希臘語法中這類詞項并沒有相對應的名稱。
基于甚至非限定動詞也是“言說他者的符號”這一觀點(同上:165),西蒙認為它滿足成為表述性陳述內含物的條件。盡管非限定動詞可能無法滿足動詞的規定性定義,但是它們還是具有動詞的偶性,并且一樣可以執行動詞的功能。西蒙“通過非限定動詞能夠與表述中其他事物進行排序”(Simon of Faversham 1957:165-166)來更進一步訴諸意義排序模式。由于非限定動詞保持這一功能,并且由于它并不持有適當地意指言語的任一部分的模式,因此,它能夠被包含在不在場的動詞的模式當中。
大阿爾伯特關于非限定詞項的考量與西蒙的討論大體一致,他也訴諸于語法定義和文本解釋的權威人士。大阿爾伯特不斷提及普里西安的名詞定義即“意指具有性質的質料”(Albertus Magnus 1890:391)來為非限定名詞不是恰當的名詞這一論斷辯護。大阿爾伯特似乎試圖利用普里西安來證明亞里士多德持有非限定名詞不是語法名詞這一論斷,事實上這并不是大阿爾伯特的本意。確切地說,他使用名詞的語法定義來證明邏輯學家的觀點,即非限定名詞意指具有性質的質料的失敗阻止它能夠表述任何事物。
在這一情況中,大阿爾伯特爭論說非限定名詞滿足名詞的語法定義,因為從較弱的意義上講它能夠意指具有性質的質料,但是這一被意指的性質是非限定的,故此它無法命名確定的質料。事實上,這就是大阿爾伯特在早先的段落中拒斥非限定名詞可以在表述中使用的原因。但是,令人沮喪的是,他無法準確地表述名詞的語法定義與邏輯學容忍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由于大阿爾伯特看起來已經發現在詮釋的過程中對語言質料和性質的本體論的語法援引比亞里士多德關于名詞的定義更為合適。我們并不是說大阿爾伯特說非限定名詞的不確定性無法有效地解釋他相信它必須被排除到邏輯學的考量之外:他只是在不自覺地建議說朝向語言的邏輯進途和語法進途之間的傳統劃分是武斷的。
4 結論
13世紀的評注家們以波埃修的思想為起點,評論《解釋篇》中的文本。在評論過程中,盡管評注家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在某些原則性的問題上還是達成一致。這種一致一直影響到后來哲學家評注亞里士多德文本的方式與方法。
首先,拉丁語評注家在關于文本標題以及主題的闡述過程中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并描繪邏輯范圍內推論與語言之間的關系,不過他們在處理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則顯示出很大區別。他們同意這一文本主要關注表述性陳述,但是他們無法形成一種普遍被接受的理論以解釋表述的中心地位,以及名詞和動詞包含在解釋當中的合法性。基于亞里士多德與普里西安的某些邏輯與語法的區別看起來是一種共識:語法關注一致、聯合意指以及語法結構;邏輯則關注真、意義、主體性和謂指性。但是存在于這些評注家之間的差異表現,即使是這些司空見慣的規則也存在著各自不同的理解。
其次,評注家們達成如下觀點,即名詞既是知識的語法對象,又從屬于邏輯學家研究的對象。他們注意到只要哲學的每一個分支保持在自身確定的比率或者獨特視角當中,那么從不同方面考慮同樣問題會產生多個哲學分支。他們因此把邏輯中的主謂項等同于語法中的一致與不一致,并明確地把意義排序的目的認同為它們表述結構的語法規則。他們通過分析兩種藝術對比過程中的常見觀點,介紹精確區分語言學論題中的語法向度與邏輯向度的努力。這一路徑最為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們堅持認為名詞不是一種特殊的語法知識,相反,它僅僅是一種語言學客體;當我們從一種視角觀察時它就成為一種語法知識,但是當我們從另一種角度觀察時,它就變成為邏輯知識。因此,對于這一時期的評注家而言,邏輯與語法中術語的重疊有助于加強兩種科學之間的潛在聯合,事實上,它們是存在于同一種語言學客體中的兩種不同性質。
最后,由于評注家們關于語法-邏輯區別的一般關注點不同,他們得出結論的偏重點也不同。盡管如此,他們還是給出關于非限定詞項地位的令人滿意的答案:即亞里士多德自己評注的原因在于如同“非人”這樣的詞項的不確定性允諾它意指任何存在與非存在。然而,他們并沒有認為亞里士多德在較弱的意義上允諾非限定名詞可以成為語法名詞,而寧可以說,考慮到一些基于心靈假設的潛在主項,它在邏輯中是可被容忍的,因此允諾它意指基于名詞的模式,因此它可以被視為主項和謂項。這就解釋出亞里士多德在《解釋篇》中合法使用非限定名詞的權利,并要求擴大主項化和謂項化的標準以使這一使用方式合法化。由于亞里士多德并沒有將非限定名詞從名詞的邏輯定義中排除出去,因此我們沒有必要通過違反任何邏輯原則的必要來解釋這些邏輯實踐。
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全集[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0.
Albertus Magnus. Expositio in libros Posteriorum Analyticorum[A]. In: Borgnet, A. (Ed.),OperaOmnia[C]. Paris: Vivès, 1890.
Kilwardby, R. Notule super Periarmenias Aristotilis[A]. In: Lewry, P.(Ed.),RobertKilwardby’sWritingsontheLogicaVetusStudiedwithRegardtoTheirTeachingandMethod[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Martinus de Dacia. Quaestiones super librum Perihermeneias[A]. In: Sajó, G.(Ed.),PhilosophorumDanicorumMediiAevi[C]. Copenhagen: Gad, 1961.
Simon of Faversham. Quaestiones super libro Perihermeneias[A]. In:Mazzarella, P.(Ed.),MagistriSimonisAnglicisivedeFaverishamOperaOmnia[C]. Padua: Cedam, 1957.
LogicalOrientationandGrammaticalOrientation:Perihermeneiasin13thCentury’sLatinContext
Wang Jian-l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What Aristotle talks about inDeInterpretationeis logic or gramma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for Latin philosophers in 13thcentury. We will discuss this question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of all, sincePerihermeneiasmainly focus on the enunciative statements, why was it not translated intoDeEnunciationebut intoDeInterpretatione; Second, how did they treat the method that Aristotle deals with normal nouns and verbs; third, especially, how did they treat the method that Aristotle deals with indefinite nouns and verbs.
Latin;DeInterpretatione; logical orientation; grammatical orientation
*本文系重慶市社科基金項目“博弈邏輯視域下的投票理論研究”(2013PYZX0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中東歐邏輯思想研究”(15YJC72040002)和黑龍江大學青年基金項目“16-18世紀漢語語境下的亞里士多德邏輯”(20140041)的階段性成果。
B12
A
1000-0100(2016)03-0024-4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06
定稿日期:2016-03-02
【責任編輯陳慶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