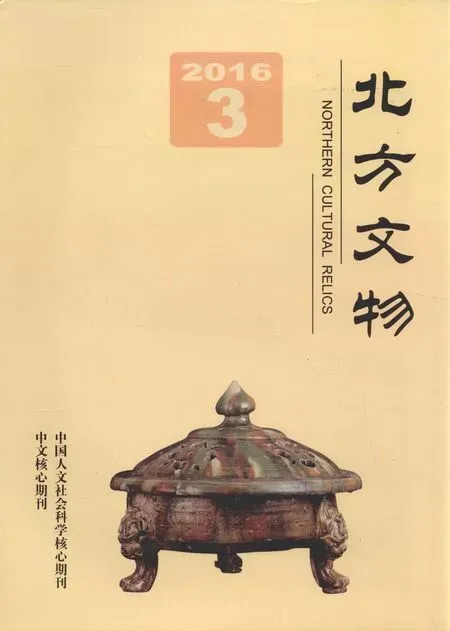遼代官吏贓罪考
鄧齊濱 李沖
遼代官吏贓罪考
鄧齊濱 李沖
贓罪 法律 遼代 官吏
遼代重視用法律的手段懲治貪贓受賄的官吏,對(duì)官吏贓罪的規(guī)定和以贓罪治罪處罰的案例散見(jiàn)于傳世文獻(xiàn)中。遼代官吏贓罪可以歸納為以受賄罪論之“枉法受賕”、 以盜竊罪論之“私取官物” 和以索賄論之“利人誤入、因之取材”三種類(lèi)型,定罪也從貶官、免官到杖刑、黥刑、流刑、死刑不等,處刑嚴(yán)苛,廉察體系具有監(jiān)、刑合一的特色,體現(xiàn)了北方民族的習(xí)慣法與中原唐律的逐漸融合。
“坐贓”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法律中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財(cái)物賄賂的一種罪名,亦作“坐臧”,最早出現(xiàn)于漢代。《漢書(shū)·景帝紀(jì)》有云:“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jiān)、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jì)賞費(fèi),勿論。它物,若買(mǎi)故賤,賣(mài)故貴,皆坐臧為盜,沒(méi)入臧縣官。”《東觀漢記·鍾離意傳》中記載:“顯宗時(shí),意為尚書(shū),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后漢書(shū)·質(zhì)帝紀(jì)》也有記載:“豫章太守虞續(xù)坐贓,下獄死。”漢以后歷代為了政治清明、整飭腐敗,都沿用了官吏以贓入罪的規(guī)定,官吏贓罪逐漸成熟,按贓的性質(zhì)、贓的數(shù)量和官吏的行為與動(dòng)機(jī)來(lái)區(qū)分罪行輕重。唐以后“以贓入罪”的規(guī)定就更加詳盡,《唐律疏議·名例》卷4“以贓入罪”條《疏》議曰:“在律,正贓惟有六色:強(qiáng)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受所監(jiān)臨及坐贓(非監(jiān)主司因事受財(cái))。”遼代的法律制度中,無(wú)論治契丹及諸夷的法律,還是治漢人的法律,官吏贓罪都受到唐律的影響,同時(shí)又表現(xiàn)了北方民族的特色。由于官場(chǎng)腐敗危及遼代政權(quán)統(tǒng)治,遼代統(tǒng)治者十分重視官場(chǎng)腐敗問(wèn)題,遂制定了“因俗而治”的官吏贓罪法律制度和廉察系統(tǒng)。
一、遼代官吏贓罪之定罪
《遼代·刑法志》記載:“先是,南京三司銷(xiāo)錢(qián)作器皿三斤,持錢(qián)出南京十貫,及盜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斤,持錢(qián)及所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①后興宗“好名”,“數(shù)降赦宥”,大赦了很多應(yīng)以死刑判處的罪犯,減輕了一些罪名的刑罰,“枉法受賕,詐敕走遞,偽學(xué)御書(shū),盜外國(guó)貢物者,例皆免死”②,“遼以用武理國(guó),禁暴戢奸,莫先于刑”③,由此推測(cè),按照遼舊律“枉法受賕”、“私取官物”、以權(quán)謀私等官吏贓罪都有判處死刑的情形,均屬官吏犯罪中的重罪。
(一)以受賄罪論之“枉法受賕”
鉤沉遼代有關(guān)文獻(xiàn)史料,遼代官場(chǎng)賄賂腐敗成風(fēng)。遼代初期和中期統(tǒng)治者嫉賢妒能、任人唯親,契丹貴族出身之人只要在“世選”之列,即不問(wèn)德能一概入仕為官,造成了官制的冗濫④。而遼代后期官場(chǎng)腐敗問(wèn)題愈演愈烈,直接演變成為親奸臣、遠(yuǎn)賢臣的政治問(wèn)題,吏治腐敗問(wèn)題也是導(dǎo)致遼代覆滅的重要原因。
遼代初期太宗朝,因?yàn)槟贤醺袃蓚€(gè)刺史貪污腐敗害民,被處以每人杖刑一百的刑罰,又將其囚禁于虞候帳內(nèi),準(zhǔn)備處以“射鬼箭”殺死,太宗于是“選群臣為民所愛(ài)者代之”⑤。景宗朝,“大丞相高勛、契丹行宮都部署女里席寵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勢(shì)薰灼。一時(shí)納賂請(qǐng)謁,門(mén)若賈區(qū)”⑥,貪污納賄之風(fēng)盛行,其中提到的女里“同列蕭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氈裘為枲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為笑。其貪猥如此”⑦。可見(jiàn)這一時(shí)期的社會(huì)矛盾異常激化,因此,如耶律賢適等大臣向皇帝諫言應(yīng)整頓官場(chǎng)腐敗,不見(jiàn)回復(fù),“以病解職,又不允,令鑄手印行事”⑧,這直接促使了遼代統(tǒng)治者對(duì)官吏贓罪的重視。 圣宗即位后,開(kāi)始了職官受賄之罪的明令禁止。圣宗在開(kāi)泰七年(1018年)九月,下詔書(shū)于“內(nèi)外官”,有官吏“因事受賕,事覺(jué)而稱(chēng)子孫仆從者,禁之”⑨。圣宗又在太平六年(1026年)十二月,下詔書(shū),遼代因契丹和漢人分治,所以官吏分南北兩院,“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dòng)有司以達(dá)于朝,惟內(nèi)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茍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問(wèn),具申北、南院復(fù)問(wèn)得實(shí)以聞;其不按輒申,及受請(qǐng)托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⑩。此詔解決問(wèn)題有三:一是契丹、漢人分治問(wèn)題,漢人依照唐律官吏贓罪定罪與處罰都十分明確,而契丹人僅有民族習(xí)慣法作為其規(guī)范,助長(zhǎng)了契丹族人和外戚的貪腐之風(fēng),因此,不論是契丹人還是漢人,只要是“因事受賕”都要經(jīng)過(guò)審問(wèn)定罪,只是契丹與漢人的刑獄要由北、南院分別進(jìn)行,契丹各族依照“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唐律),各依其法;二是貴族與平民一樣定罪,對(duì)于官吏贓罪來(lái)說(shuō),控制了行賄免于刑罰的局面;三是官吏貪求賄賂,為犯罪人開(kāi)脫或?yàn)槠湔f(shuō)情者,以本犯人罪而定其罪,以此來(lái)限制司法官吏的貪污腐敗。圣宗時(shí)期,由于法紀(jì)嚴(yán)明,因此吏治清明。后興宗也多沿用這種“受賕”之坐贓罪名,只是處罰較圣宗朝寬緩。
遼代漢人法律對(duì)職官受賄之罪的規(guī)定依照唐律處罰,《遼史》記載了遼漢人職官接受賄賂被貶職處罰的案例,如同中書(shū)門(mén)下平章事劉六符因受宋人賄賂,被貶為節(jié)度使。
(二)以盜竊罪論之“私取官物”
遼代契丹、諸夷之法與漢律都有關(guān)于職官私取官物、貢物的罪名。
太宗朝,“思奴古多里等坐盜官物,籍其家”。太宗朝法律沿用太祖時(shí)期制定的法律,即契丹人依《決獄法》治罪,漢人依漢律治罪。遼代“籍沒(méi)”刑“始自太祖為撻馬獄沙里時(shí)”,適用范圍主要是皇族、外戚內(nèi)部和官吏等。
興宗朝,“私取官(貢)物”以盜竊罪論處,多處以刑罰并削爵免官。遼興宗重熙十年(1041年),“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而興宗因前世法度酷虐,“迫殞非命,中外切憤”,因此對(duì)盜竊罪也減輕了處罰。《遼史·刑法志》記載:“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即首犯盜竊罪,處以刺右臂的刑罰;第二次犯盜竊罪,處以刺左臂的刑罰;第三次犯盜竊罪,處以刺右頸的刑罰;第四次犯盜竊罪,處以刺左頸的刑罰;第五次犯盜竊罪,處以死刑的刑罰。這與前朝的盜竊“銅三斤、錢(qián)十貫”和“銅三斤、錢(qián)二十貫”就判處死刑相比變化較大。但從史料記載來(lái)看,興宗雖然用法寬緩,但其有時(shí)憑借個(gè)人意志來(lái)決斷,如“南面侍御壯骨里詐取女直貢物,罪死;上以有吏能,黥而流之”,法度不嚴(yán)明,因此政治不清明,一些奸佞之臣趁虛而入,“圣宗之風(fēng)替矣”。
道宗朝,“禁職官于部?jī)?nèi)假貸貿(mào)易”,私取官物或貢物的官員要判處杖刑,有的一并處以削爵免官的處罰,如滌魯因私自盜取了使者的獺毛裘和貢物,“事覺(jué),決大杖,削爵免官”。另外,還規(guī)定私取官物者,允許奴婢檢舉,“詔制諸掌內(nèi)藏庫(kù)官盜兩貫以上者,許奴婢告”。中國(guó)傳統(tǒng)法律文化講究“親親相隱”,雖然遼也曾廣泛傳播儒家文化,并開(kāi)始逐漸將北方民族與漢族互相融合,但是遼代社會(huì)仍然保留著濃厚的契丹北方游牧民族傳統(tǒng),在官吏“私取官物”犯罪中明確允許奴婢和親屬告發(fā)。如道宗朝的蕭術(shù)哲是一位貪官,“清寧初,為國(guó)舅詳穩(wěn)、西北路招討使,私取官粟三百斛,及代,留畜產(chǎn),令主者鬻之以?xún)敗:笞宓芎玫讲堪l(fā)其事,帝怒,決以大杖,免官”。
(三)以索賄論之“利人誤入、因之取財(cái)”
《遼史》記載了一類(lèi)特殊的官吏犯罪,即官吏蓄謀引人誤犯之罪。由于遼代皇帝有春水秋山捺缽習(xí)俗,每當(dāng)圣駕外出至某地停留,必須高高樹(shù)立標(biāo)記,用以禁止行人,但穆宗朝“比聞楚古輩,故低置其標(biāo)深草中,利人誤入,因之取財(cái)。自今有復(fù)然者,以死論”。因此,穆宗詔諭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標(biāo)記,令民勿犯,違以死論”。
遼至道宗、天祚之時(shí),因君昏臣佞,官吏“因緣為奸”,冤獄迭起,吏治走向沒(méi)落。天祚“乾統(tǒng)元年,(蕭得里底)為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余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會(huì)之”。“詔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黨人,(蕭)達(dá)魯古以賂獲免”。耶律塔不也也是耶律乙辛黨徒,“以賂獲免”。
二、遼代官吏贓罪之處罰
遼代刑法創(chuàng)制除了吸收民族習(xí)慣法外,多借鑒漢人法律,即唐律,唐律中的刑罰措施也多被遼法所采納,但其中也雜糅了北方民族特有的刑罰方式,如遼代死刑就多達(dá) 23 種,其中投崖或投高崖、生瘞、射鬼箭等都是與契丹族習(xí)慣法有關(guān)。根據(jù)傳世史料的案例記載,針對(duì)官吏贓罪的刑罰主要有射鬼箭等死刑、流刑、杖刑、黥刑、籍沒(méi)等,還有削爵、免官、貶官等行政處罰,不在此一一贅述,只列遼代官吏贓罪的處罰特殊之處于此。
死刑與杖刑并用。前述三種類(lèi)型的官吏贓罪都可判處死刑,在死刑中射鬼箭是遼代特有的刑罰之一。遼初太宗時(shí)有“南王府二刺史貪蠹,各杖一百……備射鬼箭”。《遼史·禮志三》:“出師以死囚,還師以一諜者,植柱縛其上,謂射鬼箭。” “射鬼箭”原本是軍隊(duì)中出師、還師的儀式,太祖創(chuàng)制法律時(shí)將其作為一種死刑刑罰,與杖刑并用,印證了遼刑罰的酷虐。
死刑的減等。遼中期興宗時(shí)有“南面侍御壯骨里詐取女直貢物,罪死;上以有吏能,黥而流之”。本應(yīng)判處死刑的官吏,因其有為官的才能,因此將死刑減為流刑加黥刑。在《遼史》中有關(guān)于因悔過(guò)自新和賞其賢能而減刑的案例記載,如興宗朝詔曰:“犯罪而悔過(guò)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為辱,朕甚憫焉。”后來(lái)興宗朝的詔書(shū)有:“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官吏坐贓以盜竊罪論處的處罰中黥刑適用廣泛,這種恥辱刑的廣泛應(yīng)用與契丹族保留濃厚的草原文化和奴隸制肉刑殘余有很大關(guān)系。同時(shí),死刑因悔過(guò)自新的原因而減等為黥刑與徒刑,又夾雜著中原文化的影響。
籍沒(méi)與連坐之法。契丹的傳統(tǒng)法里,罪犯有籍沒(méi)家屬的,籍沒(méi)主要屬于財(cái)產(chǎn)刑罰,但也帶有連坐性質(zhì)。契丹所謂籍沒(méi)之事,即收犯者的家屬入瓦里。這里的家屬并非狹義的直系血親,而是泛指其頭下所屬,也就是與其有私屬關(guān)系的部曲,這些“家屬”在游牧民族被視為財(cái)產(chǎn),因此,籍沒(méi)之法實(shí)質(zhì)上是沒(méi)收犯罪者的財(cái)產(chǎn),但也有連坐的性質(zhì)。在契丹法律中,官吏“坐贓”有處以“籍沒(méi)”刑的案例,如前述“思奴古多里等坐盜官物,籍其家”。在契丹法律中,連坐之法也非常突出,“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雖然遺存的歷史文獻(xiàn)中沒(méi)有找到直接對(duì)贓罪連坐的規(guī)定,但根據(jù)《遼史》記載,興宗重熙五年(1036年)詔:“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據(jù)此說(shuō)明,遼代官吏受財(cái)犯罪在興宗以前是處以連坐之法的,自統(tǒng)和十二年(994年)始耶律阿沒(méi)里上奏皇帝,“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之,輒坐以法,是刑及無(wú)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才減輕了連坐之刑的處罰。
八議之法。遼代沿襲唐代八議之法,不僅漢貴族適用八議,契丹貴族也適用八議制度。如遼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坐以禁物鬻入外國(guó),下有司議,法當(dāng)死。乙辛黨耶律燕哥獨(dú)奏檔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朵,幽于來(lái)州”。以此可知,漢律不僅用于漢族,對(duì)契丹族的法律也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這也昭示著番漢法律的逐漸統(tǒng)一,為后世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統(tǒng)治奠定了基礎(chǔ)。
不適用贖刑。契丹舊俗,“殺人償牛馬”,“于厥掠生口者三十余人,亦俾贖其罪,放歸本部”,這些都屬于部落傳統(tǒng)習(xí)俗,故遼代贖刑盛行。中國(guó)古代官吏犯罪也多適用贖刑,但遼代贖刑適用范圍雖廣,卻不包括官吏贓罪,“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tīng)以贖論。贖銅之?dāng)?shù),杖一百者輸錢(qián)千”。這里的公罪是指官吏因執(zhí)行公務(wù)而犯罪,而官吏贓罪屬于與之相對(duì)的私罪,興宗重熙元年下詔“職事官公罪聽(tīng)贖,私罪各從本法”,據(jù)此可知官吏贓罪不屬于贖刑適用范疇。
從以上官吏贓罪的刑罰處罰可以看出,同一種罪名不同處罰的很多,即“遼之世,同罪異論者蓋多”。
三、遼代官吏贓罪之廉察
廉察制度是指國(guó)家對(duì)官員的貪污受賄行為進(jìn)行監(jiān)察,督促官員盡職盡責(zé),以維護(hù)統(tǒng)治秩序的制度。“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而廉察制度本身就兼具糾察“已然”和預(yù)防“未然”的功能,對(duì)于吏治清明尤為重要。根據(jù)《遼史》記載,太祖七年(913年)詔云:“朕自北征以來(lái),四方獄訟,積滯頗多,今休戰(zhàn)息民,群臣其副朕意詳決之,無(wú)或冤枉。”當(dāng)時(shí)派遣北府宰相蕭敵魯?shù)热恕胺值朗铔Q”,而漢人的訟獄或者牽涉番漢的案件則由漢人康默記參酌唐律處理。太宗為澄清吏治曾多次下詔,“北南諸部廉察州縣及石烈彌里之官,不治者罷之”,“大小職官有貪暴殘民者。立罷之。終身不錄。其不廉直。雖處重任即代之”。興宗也曾下詔:“諸犯法者不得為官吏,諸職官非婚祭不得沉酗廢事。”足見(jiàn)遼代統(tǒng)治者對(duì)廉察的重視。
(一)廉察機(jī)構(gòu):常設(shè)機(jī)構(gòu)與臨時(shí)官員的互補(bǔ)
遼代在中央設(shè)立御史臺(tái)、殿中司、樞密院中丞司、門(mén)下省通進(jìn)司及南面官的門(mén)下省和中書(shū)省分別設(shè)左諫院和右諫院,地方設(shè)府州專(zhuān)使,即中央設(shè)監(jiān)察使,五京設(shè)按問(wèn)使,方州設(shè)觀察使,主管糾察百官,肅正朝綱。其中“御史臺(tái)”其下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等職名,石刻補(bǔ)遺所見(jiàn)還有“西臺(tái)御史大夫”、“監(jiān)察御史”;“殿中司”其長(zhǎng)官為“殿中”、“殿中丞”,石刻補(bǔ)遺所見(jiàn)在“殿中司”下還設(shè)有“殿中侍御史”一職,主要負(fù)責(zé)監(jiān)察的職責(zé);“門(mén)下省通進(jìn)司”下有“左、右通進(jìn)”各一人,司監(jiān)察之職;“諫院”設(shè)左、右諫議大夫等官。另外,在石刻文字資料中還發(fā)現(xiàn)有遼代宦官中負(fù)責(zé)監(jiān)察彈劾事務(wù)的職官“行宮御史”。以上是鉤沉和綜合目前文獻(xiàn)資料所載的遼代常設(shè)的廉察機(jī)構(gòu)。除了常設(shè)的廉察部門(mén)和職官,從史料記載來(lái)看,遼代還因案件的積滯而臨時(shí)設(shè)置一些官員專(zhuān)門(mén)掌管廉察職責(zé),以懲治吏治腐敗。圣宗朝的廉察制度不僅有定期的巡察制度,也有不定期的巡檢制度,配合常設(shè)的廉察部門(mén)和臨時(shí)的廉察官員,以懲治貪腐。圣宗朝就有一個(gè)官吏邢抱樸,他被樞密使韓德讓推薦做按察使,監(jiān)察各地方官員是否有貪贓枉法的情況,“黜陟之,大協(xié)人望”。他雖然不是監(jiān)察官吏的官員,但是因其“博學(xué)好古”,做過(guò)“翰林學(xué)士”、“禮部侍郎”、“戶(hù)部尚書(shū)”等職,他的父親又是刑部郎中,皇帝“優(yōu)詔褒美”他,所以他臨時(shí)擔(dān)任了監(jiān)察的職責(zé),糾察地方官吏。
遼代廉察制度多承唐制,需要特別說(shuō)明的是,遼代中前期,政治清明,官吏的貪腐之風(fēng)得到了遏制,監(jiān)察系統(tǒng)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但監(jiān)察系統(tǒng)中有些機(jī)構(gòu)如“諫院”不僅向皇帝諫言,也常彈劾大臣,有時(shí)卻有名無(wú)實(shí),而有些機(jī)構(gòu)如御史也并非專(zhuān)察官吏,也負(fù)責(zé)向皇帝諫言,還有斷獄,為遼后期的吏治腐敗埋下了隱患。
(二)廉察職能:監(jiān)察兼刑獄合一
遼代的監(jiān)察機(jī)構(gòu)兼具監(jiān)察與刑獄的職能,這是遼代監(jiān)察制度的特點(diǎn)之一。穆宗朝的蕭議思、道宗朝的耶律儼和劉伸等,都曾以監(jiān)察官員的身份處理過(guò)刑獄。穆宗朝的蕭議思,任御史大夫,“時(shí)諸王多坐事繁獄”,皇帝認(rèn)為其很有才干,“詔窮治”,徹底深究這些案件。道宗朝耶律儼,“素廉潔,一芥不取于人”,他在大康年間,擔(dān)任都部署判官和將作少監(jiān),既有監(jiān)察之職,又兼斷獄之事,在群臣之中論優(yōu)劣,群臣都說(shuō)他是才俊,因此后來(lái)任職少府少監(jiān)并兼職知大理正,他在大安二年,做御史中丞,詔“按上京滯獄,多所平反”,不僅作為御史中丞擔(dān)負(fù)“繩胥吏,禁豪猾”的職責(zé),還諫言于皇帝,并且掌管刑獄。道宗朝的官吏劉伸,他不僅是三司的副使,還兼諫言之職責(zé),是“諫議大夫”,同時(shí)還是提點(diǎn)大理寺,主管刑獄,他也是身兼數(shù)職,在監(jiān)察官吏腐敗的同時(shí)也處理了貪腐案件。有學(xué)者認(rèn)為,監(jiān)、刑合一的監(jiān)察職能使得遼代的冤假錯(cuò)案減少了,從而達(dá)到了吏治清明、懲治貪腐的作用。
由于《遼史》記載很簡(jiǎn)略,遼代的傳世文獻(xiàn)和碑銘尚不能完整呈現(xiàn)出遼代當(dāng)時(shí)創(chuàng)制的成文法律全部條文,筆者僅從現(xiàn)有文獻(xiàn)記載分析遼代官吏贓罪的定罪、量刑和廉察機(jī)制,恐有片面。但已能從尚有的文獻(xiàn)中發(fā)現(xiàn)遼代比較重視懲貪治吏,同時(shí)對(duì)貪腐者施以重法。“法貴必行”,只有嚴(yán)格的執(zhí)行法律才能達(dá)到法制效果,遼代后期贓罪立法無(wú)法執(zhí)行導(dǎo)致“以賂獲免”的官吏很多,這是遼政權(quán)不能穩(wěn)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遼代法律中表現(xiàn)出的藩漢法律文化的同化價(jià)值為后世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提供了先期實(shí)踐的范例,這種習(xí)慣法與制定法、少數(shù)民族法與漢族法的融合在清朝走向了成熟。
注 釋?zhuān)?/p>
⑥⑧《遼史》卷79《耶律賢適傳》,第1273頁(yè)。
⑦ 《遼史》卷79《女里傳》,第1273頁(yè)。
⑨ 《遼史》卷16《圣宗紀(jì)七》,第184頁(yè)。
〔實(shí)習(xí)編輯、校對(duì) 陰美琳〕
鄧齊濱,女,1983年生,黑龍江大學(xué)博士生,哈爾濱金融學(xué)院法律系講師,郵編150030;李沖,男,1990年生,黑龍江大學(xué)法學(xué)院學(xué)生,郵編150080。
K246.1
A
1001-0483(2016)03-01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