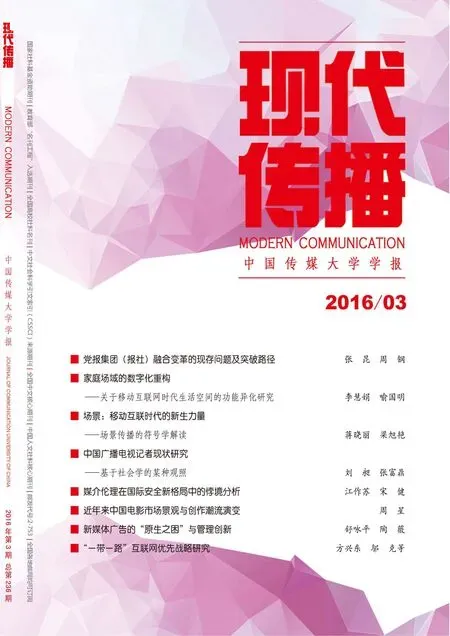多元時代的切片式記錄
——回顧紀錄片《高考》
■ 史 慧
?
多元時代的切片式記錄
——回顧紀錄片《高考》
■ 史 慧
對于紀錄片本體來說,無論什么樣的記錄都是有意義的。對于內容的選擇因人而異,如何記錄各有堅持。但凡能夠記錄下來,能夠保存下來,對于一段歲月和一個時代來說,都可謂難能可貴。更勿論現在科技突破疆界,手機拍攝的紀錄片同樣可以斬獲奧斯卡獎。早年技術與設備圈建的專業門檻,在眾相踩踏中幾乎無蹤可覓。而中國社會的復雜與多義,卻已經在發展和變革的沖動中被一層又一層地構建起來。在這樣一個什么都可以拍、誰都可以拍的時代,紀錄片《高考》選擇了中國教育,來做一次多元化時代的切片式紀錄,以此透視一場考試背后的中國現實。
解剖社會來做一部有熱度的紀錄片。有一種說法把紀錄片分為媒體紀錄片和作者紀錄片。前者有投資、有收益,講究收視率;后者秉持獨立制作、注重表達。作為一支體制內的創作團隊,從投資和播出來看,它所做的工作顯然是媒體紀錄片。但是,媒體紀錄片在商業和宣傳訴求之外,能不能也有一些觀念和表達上的突破呢?或許,《高考》可以看作是以媒體紀錄片的身份來致敬獨立紀錄片式的表達。
一直以來,教育都是社會民生的熱點所在。圍繞這一熱點的各種話題層出不窮,從人大會場到街頭巷尾,牽扯國家發展更關乎個人命運。選擇真正的社會熱點,關心國家發展中的重大議題,從確定“教育”這一熱點,到確定教育熱點中的“高考”,再到廣受爭議的安徽毛坦廠中學、農民工子女的高考、貧困地區的高考、“洋高考”以及高考改革這些分集內容的確定,社會熱點話題一直是選題和內容方向上的錨定。熱點之所以“熱”,話題之所以成為話題,是因為其中有矛盾、有斗爭,它牽扯各方情態,也糾結于社會與個人的道路。社會某一處的景象總不是只有表面,毛坦廠中學極端樣本背后是教育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追求,是被裹挾在快速發展中的集體焦慮。真實記錄下這一景象,是對現實、更是對未來的思考。
馬爾科姆·卡拉克在中國拍片的間隙曾經多次到劇組來,一聊就聊到飯點兒。這位早年以現實題材成名的英國紀錄片導演,對“高考”這樣的中國現實題材異常感興趣。中國紀錄片在國際舞臺上的聲音已經日漸清晰,尤其是現實題材的獨立紀錄片制作,近些年在世界各大紀錄片節展上都建樹不少。但不可否認,在國家媒體平臺的紀錄片中,現實題材仍然相對偏弱。而保存一個時代最真實的現實記憶,恰恰是紀錄片存在的應有之意。
同感式紀錄以還原最真切的現實。各種類型的紀錄片都在追求真實,真實是可以“還原”的,真實也是可以“再現”的。作為現實題材的紀錄片,《高考》堅持的是同感式的貼近觀察與紀錄。這一堅持是絲毫不能被妥協的,從紀錄片的調研階段就已經被確定。
一部紀錄片的創作開端始于田野調查。被描述于紙面的社會熱點話題,背后是沒有面孔的群像,而鏡頭對準的必須是有表情也有內心的個體。《高考》曾經給每位分集導演搭配了一名調研員,在選題方向尚不明晰的時候就開始了調研工作。從選題的可靠性到可執行性、從拍攝人物的選定到拍攝地的采景,調研員既要識人辨事,又要依賴個人判斷給導演組提出專業意見。一份有價值的前期調研報告沒有貼近式的觀察是不可能完成的。最難的是拍攝許可。毛坦廠中學不接受拍攝,北大附中不接受拍攝,衡水的老校長不接受拍攝,正在備考的孩子不接受拍攝……不接受拍攝的理由各種各樣。調研員和導演就像啃骨頭一樣,一個一個做工作,沒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切實有效的溝通實現不了拍攝。可以說,中國紀錄片最缺的,不是資金、甚至不是導演,最缺的是專業的調研團隊。
實際拍攝中感同身受式的紀錄使得鏡頭影像更為真切、也更為細膩。對同期聲的追求是要滿足在沒有解說詞的情況下完成敘述。以一種觀察者的視角來進行同感式的記錄,這樣一種跟蹤拍攝最能契合紀錄片本身的訴求,但是風險和成本也顯而易見。現實和事件發展的不可控客觀存在。拍著拍著這個人物覺得沒戲了,拍著拍著那條故事線索就斷了。這時候,對跟蹤紀實拍攝進行預判就變得那么重要。無論哪種類型的紀錄片都需要劇本,現實題材紀錄片的劇本是對各種故事發展可能性進行的預設以及應對方案。這個劇本往往伴隨著實際拍攝的進行,日日修改,終致面目全非。《高考》素材量和成片的比例是100:1,平均每集的拍攝天數是28天,時間成本的控制毫不遜色于國際制作的水準。
現實題材紀錄片的價值在于影響力。《高考》紀錄片每一集的敘述各不相同,皆可獨立成篇。它們統一在同一個教育熱點話題下,同時在各自的維度方向上追求獨立言說的最大可能。看似分散了影響力,實際卻因為選題的深入和覆蓋廣度集合了力量。
在最初的文案策劃中,對于每個系列單集的設想就是獨立開放的。國家是如此幅員遼闊又是如此復雜多元,貧困與富裕、農村與城市、傳統與時尚,它們很多時候無法調和卻又無法背離。它們既然代表著截然不同的社會切面,就要尋找它們各自適合的表達方式,這是復雜社會生態本身的要求。終至成片,果然每集的結構方式、剪輯節奏都各不相同。它們就如同一套組曲,集合來看有一個統一的藝術構思,分開來看獨立敘述、各自表達。分集既有單故事線,亦有多故事線,每一集的情緒點也各不相同。會寧大山里貧困生劉洋洋的故事單純,卻以情動人;各有追求、看待高考迥然不同的三位校長,呈現出的是觀點的碰撞。影調色彩上的冷峻風格、細節上對于高考話題的頻頻呼應、至精至簡的說明性字幕,可以說是標識系列片為數不多的方式。
《高考》在中央電視臺首播進行到最后一集的時候,劇組同仁發了一條“朋友圈”:塵埃落定。這部紀錄片能夠在中央臺這樣的媒體上順利播出,某種程度上已經是一種圓滿。固然每一種紀錄都是有態度的,但是避免直接評價、適當隱藏態度,或可說是創作上的一種韜光養晦。對于傳播來說,最有意義的是到達。到達更多的人,到達內心,到達觸動改變和重建的另一個維度。國家媒體平臺上的紀錄片表達帶有某種優勢是毋庸置疑的。紀錄頻道的國內觀眾覆蓋超過10億,考量首播收視率和收視份額,至少有1000萬人看到過這部紀錄片。或者是全部,或者是某一集,或者是某一個片段。哪怕內心只是泛起一絲觸動,引發一點的思考,就是有一種力量在作繭繁衍。
2014年拍攝緊張的那段時間,曾經突然接到國外一位華人導演的電話,他在尋找唐慧的聯系方式。湖南永州這個案件的跌宕起伏,在媒體光影中折射出復雜人性與制度迷局,即便遠在美國也被吸引。他感慨于中國紀錄片選題的豐富,也感慨于分身乏術想拍的內容實在太多。其實,現實題材紀錄片永遠都不缺少選題,有人就有故事,一顆人心就能映照世界。致力于把教育創新實驗的張良,曾經把他所理解的教育真諦書寫在教室的最前方,“認識世界,找到自我”。這八個大字,時常在鏡頭中閃現。對于紀錄片來說,尤其是現實題材紀錄片,這八個字同樣能夠成為一種注腳。通過紀錄影像來認識和理解我們身處的現實,也尋找到紀錄片創作者的真正追求和自我實現。
(作者系紀錄片《高考》策劃、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