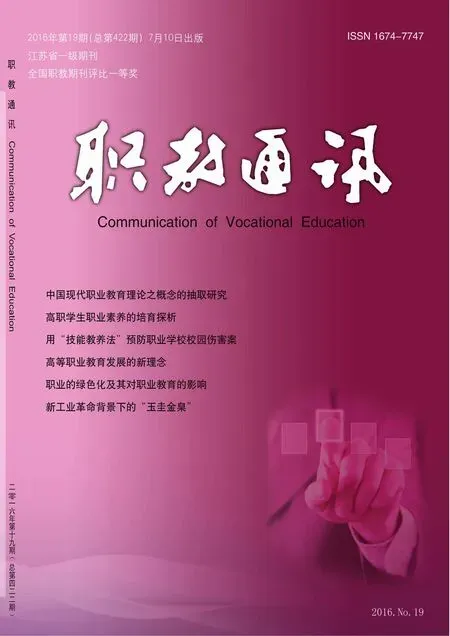“你們全部的觀點,我都不同意”
臧志軍
“你們全部的觀點,我都不同意”
臧志軍
A:“有專家提出,應該把課堂中70%以上的時間還給學生,才能真正提高教學質量。”
B:“這不可能,我們都面臨高考的壓力,誰能保證這種做法不會降低考試成績?”
……
A:“鑒于目前的生師比,以及促進學生社會化成長的需要,分組應該是職業學校教學中的必要策略。”
B:“在普通中學也有小組教學的做法,但一般到初二或高二就被取消了,到高三還是傳統的填鴨的方法。”
……
A:“我們很多老師習慣于把結論直接告訴學生,而不是引導學生探索知識的獲得過程。”
B:“誰不知道探索知識的求解過程是好的,但我們有考試壓力,哪有那么多時間?”
……
以上是一次師資培訓班上的真實對話記錄,A是作為講師的我,B是一位來自一所江蘇職業學校的普通教師。在將近半小時的時間里,她幾乎對我提出的每一個觀點都進行了挑戰,所有挑戰的基本立論都是:我們要帶領學生要參加對口單招考試,你說的那些理念在高考面前毫無用處,所以你說的在現實中根本不可能實現。
這讓我想起了在某門戶網站上一位自稱一線醫生的作者的聲音:“你們全部的觀點,我都不同意!”這位作者宣稱外界的所有對中國醫療的觀點都與現實存在很大偏差,作為一線醫生的他反對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普通病患關于醫療的所有觀點。盡管培訓班上的這位教師并沒有喊出如此對抗性的口號,但顯然也在試圖把作為講師的我與作為聽眾的他們劃入截然對立的兩個陣營——外在于教學實踐的職教研究者和來自職教教學一線的教師。
正因為此,面對來自這位教師的挑戰,我并不感到尷尬:她并非針對我個人提出批評,而是在對脫離實際的思維方式和教育觀念以及持有這些思維方式和觀念的所有人表達不滿。但拋卻個人的感覺,作為職教研究者隊伍的一員,我應該感到沮喪:這些一線教師有時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有時是研究素材的共享者,有時是研究活動的合作者,他們本應與研究者形成共同體,但現在卻成了研究者最大的嘲諷者與對立面。
是什么造成了職教研究者與職教一線教師之間的對立?從上述記錄的對話來看,很可能是由于雙方對各自價值的固守。研究者對職教理論更加認同,哪怕在研究問題,也喜歡把問題納入自己熟悉的理論框架;一線教師更關心如何解決實際發生的問題,對于解決這些問題使用了哪些理論并不關心。因此,雙方形成了方法論上的落差:研究者傾向于以理論為中心重構問題、分析問題并給出解決方案,實踐者傾向于在現有問題情勢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上述的對話中,A總是在堅持理論的正確性,B總是堅持現實的復雜性,雙方的交流演變了不可調和的對話。
美國人利普曼在《大眾輿論》一書中認為,每一個社會和文化群體都對本群體共同認同的價值觀和行為特征有普遍性、概括性的表述,他將之概括為“定勢”(stereotype)。后人還將這一概念繼續深化,形成了“自定勢”和“他定勢”的概念,前者指某一社會群體關于自己的定勢,后者指某一群體對其他群體的共同認定。根據這樣的理論分析,大概可以如此解釋為何B會在培訓班上挑戰A:在長期的實踐中,B總是困惑于一些實踐問題,逐漸形成了自己關于職業教育教學的“自定勢”;她也曾接觸了一些研究者和他們的研究,發現許多研究者討論問題的方式與自己的希望差距甚大,逐漸形成了研究者們“不食人間煙火”的“他定勢”;在培訓班上,A所講授的內容再次強化了她的這一認識,于是更加確信已經形成的關于自己和研究者的定勢,本希望培訓能取得理想效果的B按捺不住開始發難。
文化定勢的研究者們相信盡管定勢是對群體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的客觀描述,但定勢一旦形成也會造成消極影響,即個體會不斷強化自己的正確性,同時,也會強化對其他群體的刻板印象,形成偏見。在本案例中,A和B盡管有對話,但雙方都局限于自己的定勢,并未形成真正有效的溝通、交流,都沒有能夠對對方的觀點產生足夠的影響,而只是在不斷論述自己的正確性而已。
事實上,跳出各自已有的定勢,可以看到雙方都有可檢討之處。對于一線教師來說,自己所認識到的職業教育現狀也許并非職業教育的主流問題,有必要傾聽一下對宏觀問題有更多了解的研究者的聲音,同時,職業教育的未來肯定不會等同于職業教育的現實,今天被認為很重要的問題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變得不太重要,有必要了解一下研究者們根據理論研究作出的對職業教育現實與未來的判斷;而職教研究者也應該認識到目前的職業教育理論研究仍然很不成熟,自己不應成為空洞理論的販賣者,應該學會更多地從問題解決過程中創造理論,而不是從理論中衍生理論。
我原想中立地討論我遇到的這個事件,但寫到這里,發現自己還是跳不出研究者的窠臼,仍然以概念的梳理為起點展開對事件的分析,仍然使用了許多研究者慣用的伎倆來分析問題,可見定勢對自己影響之深。但我們不能因為定勢的頑固而放棄對它的抵拒,希望職教研究者與職教一線教師更多溝通交流,真正形成推動職業教育進步的合力。
(作者系江蘇理工學院職教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