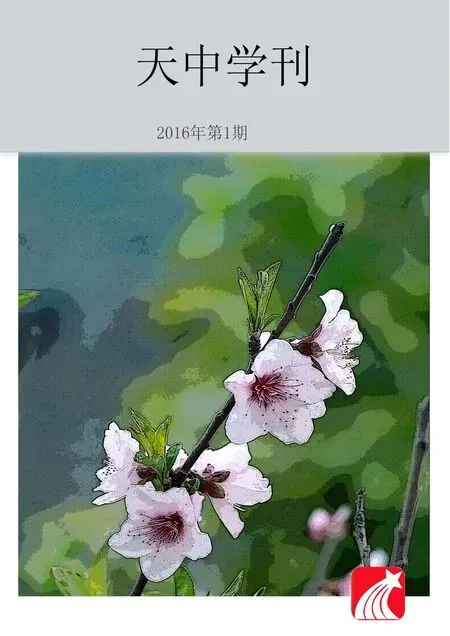論張煒小說(shuō)中的“泥棚茅屋”空間
焦紅濤(平頂山學(xué)院 文學(xué)院,河南 平頂山 467000)
?
論張煒小說(shuō)中的“泥棚茅屋”空間
焦紅濤
(平頂山學(xué)院 文學(xué)院,河南 平頂山 467000)
摘 要:張煒小說(shuō)中的“泥棚茅屋”空間不僅是人物或故事發(fā)生的場(chǎng)所與空間,而且表征著作家建構(gòu)在歷史反思與現(xiàn)實(shí)批判基礎(chǔ)上的人文理想:它意味著道德的高潔和民間智慧的博大精深,是作家試圖超越民間苦難的產(chǎn)物,同時(shí)更代表著對(duì)現(xiàn)代性的反思態(tài)度。
關(guān)鍵詞:張煒;“泥棚茅屋”空間;人文理想
有意無(wú)意之間,張煒在他的文學(xué)世界中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gè)個(gè)形態(tài)近似的空間原型,如玉米地、葡萄園、荒原、樹(shù)林、小泥屋、小茅棚、小石屋等。他筆下那些形態(tài)各異的人物、那些曲折浪漫的故事就展開(kāi)在這些不同類型的空間中。本文試圖結(jié)合具體的文本就其中的“泥棚茅屋”空間進(jìn)行簡(jiǎn)單討論。
一、張煒小說(shuō)中的“泥棚茅屋”空間
從20世紀(jì)70年代開(kāi)始創(chuàng)作,張煒的小說(shuō)中就隱現(xiàn)著這樣的空間原型。這一生存空間或是林中木屋、海邊草棚、田間窩棚,或是小泥屋、小磨屋,但都大同小異,呈現(xiàn)為外形簡(jiǎn)陋、內(nèi)涵豐富的庇護(hù)所的形象。空間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將空間視角引入文學(xué)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眾所周知,文學(xué)的“時(shí)空”是一個(gè)形式兼內(nèi)容的東西,空間可以看作時(shí)間在某一平面上的共時(shí)性展開(kāi)。文學(xué)研究如果缺乏對(duì)空間問(wèn)題的深入認(rèn)識(shí),就不能稱為完全的“時(shí)空”。因此,“泥棚茅屋”空間就不能被簡(jiǎn)單地解讀為文學(xué)發(fā)生的物理環(huán)境,必須從文化的角度予以重新認(rèn)識(shí)。
從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角度看,這種“泥棚茅屋”空間與作家的幼年生活構(gòu)成了某種現(xiàn)實(shí)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張煒曾經(jīng)回憶過(guò)自己早年獨(dú)居叢林的生活,那種生活場(chǎng)景雖然不是小說(shuō)中簡(jiǎn)陋至極的“泥棚茅屋”,但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還是不可忽視的。張煒曾經(jīng)說(shuō)自己寫作中的一類,“就是對(duì)于記憶的那一片天地的直接描繪和懷念,這里面有許多真誠(chéng)的贊頌,更有許多歡樂(lè)”[1]63。然而早就有人告誡過(guò)我們,文學(xué)固然來(lái)自生活,但不僅僅是對(duì)生活現(xiàn)實(shí)的被動(dòng)反映,所謂的“鏡子”理論不僅忽視了文學(xué)的一般規(guī)律,更忽視了作家能動(dòng)的創(chuàng)造性。理解張煒的小說(shuō)世界,應(yīng)該明白張煒筆下的“泥棚茅屋”不是為了佐證那些故事的現(xiàn)實(shí)感而有意加入的“細(xì)節(jié)”,也不是張煒自己對(duì)故鄉(xiāng)地理寫實(shí)性的“致敬”。這其中蘊(yùn)含著作家對(duì)其筆下人物的理解,對(duì)敘事的把握,對(duì)建構(gòu)在歷史與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上的人文價(jià)值的弘揚(yáng),這一切集中體現(xiàn)在作家對(duì)小說(shuō)空間的選擇上。巴赫金在論述拉伯雷時(shí)指出:“一切有價(jià)值的東西,一切優(yōu)質(zhì)的東西,應(yīng)該把自己的優(yōu)質(zhì)體現(xiàn)在時(shí)空的優(yōu)勢(shì)上,應(yīng)該盡可能擴(kuò)展,盡可能存在得長(zhǎng)些;而且真正優(yōu)質(zhì)的東西必然會(huì)有力量在時(shí)空上擴(kuò)展。”[2]356泥棚茅屋作為某種“有價(jià)值”的東西獲得作家刻意的表現(xiàn)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二、“泥棚茅屋”空間多元的文化意蘊(yùn)
“泥棚茅屋”空間在文字上給人的感覺(jué)首先是簡(jiǎn)陋。它因這簡(jiǎn)陋能在文化上輕易占據(jù)一個(gè)優(yōu)越的道德化的位置,從另一層面上彰顯出精神的豐富性。劉禹錫《陋室銘》中云“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但劉禹錫講述的是“往來(lái)無(wú)白丁”的傳統(tǒng)文人曲高和寡的自我滿足,張煒小說(shuō)中的“泥棚茅屋”空間則傳遞出民間社會(huì)強(qiáng)烈的道德感,畢竟幾十年階級(jí)觀念的教育也一直是將貧窮與道德高尚作為一種天然的孿生關(guān)系進(jìn)行敘述的。《一潭清水》中,徐寶冊(cè)、老六哥和小林法之間的故事是在有“一潭清水”的瓜田中發(fā)生的,他們共同擁有一個(gè)讓人留戀的看瓜窩棚。但社會(huì)的發(fā)展使人的欲望不斷膨脹,對(duì)利益的貪戀讓這溫馨的窩棚最終分崩離析,因此徐寶冊(cè)對(duì)善的守望就代表了時(shí)代的精神高地。《海邊的雪》圍繞著海邊那小小的魚(yú)鋪展開(kāi),兩個(gè)貌似無(wú)用的老頭卻能夠在關(guān)鍵時(shí)刻犧牲自己去挽救年輕人的生命。魚(yú)鋪半埋在地下,簡(jiǎn)陋而不引人注意,它能夠在大雪紛飛的冬天最大限度地提供生命需要的溫度——這既是寫實(shí),更是隱喻。《外省書(shū)》中的史珂雖然居住在林中小屋里,但這似乎并不妨礙他始終懷著人“在江湖,心憂天下”的情懷。《古船》中的隋抱樸獨(dú)居在小磨屋中,為了洼貍鎮(zhèn)人的利益,他能夠摒棄前嫌為仇人的粉絲廠“扶缸”。
“泥棚茅屋”空間還能夠使讀者聯(lián)想到民間智慧的博大精深。“三顧茅廬”的故事就其本質(zhì)來(lái)說(shuō),講述的是民間智慧如何為主流社會(huì)所認(rèn)可,或者是士人如何將滿腹學(xué)問(wèn)“貨與帝王家”的人生快意。因此,“茅廬”意象是從物質(zhì)貧乏的角度來(lái)講述民間智慧的生動(dòng)文本。張煒小說(shuō)一直強(qiáng)調(diào)一種民間視角的自我認(rèn)同:“陋室”或者“泥棚茅屋”表面上強(qiáng)調(diào)的是物質(zhì)的貧乏,除了借此襯托人物的道德高度之外,更要借此說(shuō)明智慧的不同凡響。張煒曾在談及美國(guó)作家梭羅的隨筆《梭羅木屋》中指出:“人的一切最美好的創(chuàng)造,無(wú)不來(lái)自簡(jiǎn)單和純樸。”[3]28《古船》這一經(jīng)典小說(shuō)中,隋抱樸并不是傳統(tǒng)文化中諸葛亮形象的再現(xiàn)。他在小磨屋中苦苦思索歷史與現(xiàn)實(shí),弄不明白自己是不是應(yīng)該行動(dòng)以及如何行動(dòng),通過(guò)在小屋中研讀經(jīng)典著作,他豁然開(kāi)朗——必須在行動(dòng)中拯救洼貍鎮(zhèn)。一個(gè)思想的隋抱樸和行動(dòng)的隋抱樸都是典型的20世紀(jì)80年代的產(chǎn)物。也許只有在80年代的政治文化語(yǔ)境中,在對(duì)既往歷史尤其是“文革”的反思中,才可能出現(xiàn)內(nèi)心糾結(jié)的思想者形象——他既能夠回顧歷史,又能夠宏觀地、抽象地思考未來(lái)。《古船》這一小說(shuō)代表了張煒小說(shuō)中極為不同的思想傾向,即一種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一種從“思想的上帝”向“行動(dòng)的上帝”轉(zhuǎn)型的時(shí)代風(fēng)尚——盡管仍然是從民間視角所展開(kāi)的思考。
“泥棚茅屋”空間在另一個(gè)層面可以理解為深刻的苦難意識(shí)。對(duì)苦難的書(shū)寫聯(lián)系著作家持續(xù)的歷史反思與現(xiàn)實(shí)批判。文學(xué)作為現(xiàn)實(shí)矛盾的想象性解決,必須提供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困境的出路。因此,苦難就是在沒(méi)有道路之處出現(xiàn)的一條想象性的道路。通過(guò)對(duì)苦難的贊頌和對(duì)苦難的道德化展示,人們才能獲得對(duì)苦難的某種想象性超越。在這樣的意義上,那些在“泥棚茅屋”中生活著的飽經(jīng)生命憂患的老年男性,他們歷經(jīng)生活的磨難卻精神飽滿、聰明睿智,既可以看作是民間智慧的結(jié)晶,更應(yīng)該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明白其作為社會(huì)歷史鏡像的意義所在。張煒這一類型的小說(shuō)最初是從頌揚(yáng)民眾(民間)“奉獻(xiàn)”精神開(kāi)始的,它來(lái)源于革命時(shí)代流行的積極分子文化或者好人好事的寫作模式,最終逐步演繹出民間與主流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關(guān)系的反思主題。這一主題與張煒個(gè)人的“創(chuàng)傷情結(jié)”不無(wú)關(guān)系①,也迎合了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政治文化反思的文學(xué)思潮。我們不能簡(jiǎn)單地將這類空間看作作家與主流文化對(duì)抗或者疏離的理想化姿態(tài),而應(yīng)該注意到它具有的歷史反思與診斷時(shí)代的價(jià)值。正因?yàn)檫@樣,在精神分析的層面上,這些飽經(jīng)憂患的老年男性就成了張煒對(duì)父親形象的重建,以此補(bǔ)償他幼年以來(lái)一直無(wú)法紓解的精神缺憾,那些泥棚茅屋也就超越自然主義意義上的居所性質(zhì)而具有了某種安全庇護(hù)的意義。《紫色眉豆花》《海邊的雪》《冬景》等小說(shuō)中的老年男性形象所揭示出的精神創(chuàng)傷是顯而易見(jiàn)的。在《紫色眉豆花》中,兒子春林的受傷,在傳統(tǒng)的意義上襯托了老亮頭自己作為家屬的“奉獻(xiàn)”精神,這一寫作模式直接指向長(zhǎng)期流行的“人民熱愛(ài)國(guó)家”的主題。但小說(shuō)以老亮頭作為敘事視角,有意無(wú)意之中,呈現(xiàn)了他作為“犧牲者”與“奉獻(xiàn)者”的悲哀。因此,他的堅(jiān)韌、豁達(dá)表現(xiàn)出與無(wú)奈的犧牲相關(guān)的文化癥候。《冬景》幾乎是重復(fù)了《紫色眉豆花》的故事,其中的老人自足而安穩(wěn)地居住在四合院中的小屋里,他的生活狀態(tài)幾乎與土地合而為一了,他收集過(guò)冬的燃料,準(zhǔn)備過(guò)冬的食物,一切都向慷慨的大地索取。老人的小屋仿佛帶有原始意味的伊甸園,但溫暖與富足的生活背后是不忍回憶的殘酷——他的三個(gè)兒子先后死亡。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的智慧與堅(jiān)韌,只能說(shuō)是無(wú)奈與忍受的另一種表述。
從現(xiàn)代性的角度來(lái)理解“泥棚茅屋”空間,它可以激發(fā)一種與當(dāng)代社會(huì)發(fā)展這一宏觀命題相關(guān)的危機(jī)意識(shí)。換一個(gè)角度看,“泥棚茅屋”空間話語(yǔ)類似于西方的伊甸園被毀的神話原型。盡管抽象地看,這些微型空間面臨的威脅,實(shí)質(zhì)上都暗示著生存的危機(jī),但張煒不僅是一個(gè)糾結(jié)于歷史的思想者,還是當(dāng)代生活的關(guān)注者與批判者。在《外省書(shū)》這部以類似紀(jì)傳的方式寫就的小說(shuō)中,(史珂的)“屋子建在河灣一帶的防風(fēng)林中,原屬祖產(chǎn),早已破損不堪”,但在這里他感到充實(shí),“覺(jué)得嶄新的時(shí)間正從腳下滋生”。因此他一次次拒絕侄兒讓他搬遷或者修建新房的建議。與他有共同選擇的是那個(gè)叫鱸魚(yú)的油庫(kù)看守,一個(gè)“刑滿釋放分子”。他們比鄰而居,互為對(duì)方的精神慰藉。“外省書(shū)”中的“外省”意味著史珂對(duì)自居邊緣位置的確認(rèn),是與時(shí)代保持距離之后的某種批判性審視。小說(shuō)試圖從不同角度進(jìn)入不同人所代表的世界,從而在眾聲喧嘩的時(shí)代中凸顯不同價(jià)值的沖突。史珂和鱸魚(yú)就這樣被置于生活的網(wǎng)絡(luò)之中,被置于開(kāi)發(fā)商、移民者、背叛歷史者等人所形成“世界”中,他們的性格與思想因此成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文化癥候。主人公史珂周圍的故事包括:侄兒史東賓的發(fā)家史、史東賓的不道德生活以及與妻子的婚姻沖突、哥哥在美國(guó)的異國(guó)生活、元吉良作為歷史負(fù)載者的生活等。在這個(gè)近于寫實(shí)的生活片段中,作家將當(dāng)代生活做了高度濃縮,尤其對(duì)當(dāng)代社會(huì)發(fā)展過(guò)程中所遭遇的過(guò)度開(kāi)發(fā)、環(huán)境污染以及流行的拜金、道德墮落等精神困境進(jìn)行了深刻的現(xiàn)代性反思。“泥棚茅屋”空間因此具有了獨(dú)特的精神價(jià)值。在《刺猬歌》中,廖麥遭受開(kāi)發(fā)威脅的田園泥屋與史珂的屋子無(wú)疑具有同樣的象征意蘊(yùn),面對(duì)日漸逼近的開(kāi)發(fā)浪潮,他所棲息的小屋只能等待毀滅的命運(yùn)。值得注意的是,無(wú)論是史珂,還是廖麥,他們都是作為現(xiàn)代性的反思者而存在的,因而與《古船》中的隋抱樸有所不同。這從他們與所居住的小木棚或者小磨屋的關(guān)系就可以看得出來(lái):前者作為人生歸宿的存在,而后者則是作為一個(gè)出發(fā)地而存在的——廖麥在多年的流浪之后最終把大海邊上的農(nóng)場(chǎng)與農(nóng)場(chǎng)中的小屋確定為自己最后的歸宿;隋抱樸則是走出小磨屋的時(shí)代新人,他的理想更宏大,他對(duì)當(dāng)代現(xiàn)實(shí)有更強(qiáng)烈的認(rèn)同感。自然,這也并不是什么本質(zhì)的矛盾,因?yàn)樽骷业乃枷肟偸且S著時(shí)代變化的。
“泥棚茅屋”空間也是作家親近自然的一種方式,再一次驗(yàn)證了張煒一以貫之的人文理想。在《梭羅木屋》中,張煒闡述了他的空間文化觀念:(美國(guó)作家梭羅的)“這屋子太小了,屋里的設(shè)備也過(guò)于簡(jiǎn)單了。這是因?yàn)橐磺卸挤牧酥魅嘶貧w自然、一切從簡(jiǎn)的理念。”他反復(fù)闡述到:“一個(gè)人的生活其實(shí)所需甚少,而按照所需來(lái)向這個(gè)世界索取,不僅對(duì)我們置身的大自然有好處,而且對(duì)我們的心靈大有好處。一切的癥結(jié)都出在人類自身的愚蠢和貪婪上。”[3]28因此,如果脫離具體的小說(shuō)敘事,我們也許應(yīng)該明白,作家筆下那些人物共同棲身的“泥棚木屋”,其實(shí)代表了作家簡(jiǎn)單自然的人生態(tài)度。這一人生態(tài)度看似雷同于梭羅的自然主義理念,其實(shí)有作家自己深刻的歷史、現(xiàn)實(shí)人生根源。
三、“泥棚茅屋”空間的價(jià)值與意義
對(duì)于文學(xué)敘事來(lái)說(shuō),空間不僅僅是人物活動(dòng)的地點(diǎn)或故事發(fā)生的場(chǎng)域,它還是小說(shuō)意義生產(chǎn)中的關(guān)鍵要素。列斐伏爾認(rèn)為,空間是具有生產(chǎn)性的文化要素[4]47。我們亦可以說(shuō),空間是文化價(jià)值的函數(shù),空間的調(diào)整隨著文化意義的變化而變化。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能夠理解空間的生產(chǎn)性,進(jìn)而理解張煒小說(shuō)空間話語(yǔ)的價(jià)值。
現(xiàn)代以來(lái)對(duì)鄉(xiāng)土中國(guó)的書(shū)寫,逐漸形成了以魯迅和沈從文為代表的兩個(gè)傳統(tǒng),由此也相應(yīng)地生產(chǎn)出兩種主要的空間類型,前者的典型是空間昏暗逼仄的故鄉(xiāng)紹興,后者則是神秘詩(shī)意的湘西世界。從這樣的文學(xué)空間生產(chǎn)的歷史來(lái)觀察,張煒的小說(shuō)敘事既有對(duì)文學(xué)傳統(tǒng)的繼承(更偏向沈從文一脈),也有拓展與超越的一面(比沈從文更豐富駁雜)。其最大的貢獻(xiàn)在于他對(duì)民間文化空間的建構(gòu)與書(shū)寫。上文對(duì)張煒小說(shuō)中“泥棚茅屋”空間意蘊(yùn)的歸納可讓我們管窺張煒小說(shuō)中“民間”一詞的內(nèi)涵:民間首先有一種道德化的姿態(tài),其話語(yǔ)的真正指向是曾經(jīng)的“極左”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這可以看作是張煒民間話語(yǔ)的起源。在他那里,無(wú)論是對(duì)民間智慧的書(shū)寫還是對(duì)苦難的展示,字里行間都縈繞著揮之不去的創(chuàng)傷記憶。隨后,“泥棚茅屋”化身為一種現(xiàn)代性的危機(jī)意識(shí),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縮影,以對(duì)抗現(xiàn)代性發(fā)展中所遭遇的林林總總的問(wèn)題,建構(gòu)符合時(shí)代發(fā)展的新道德,因而日益具有了與時(shí)俱進(jìn)的內(nèi)容。這無(wú)疑表明了張煒?biāo)枷氲某砷L(zhǎng)性。
注釋:
① 在散文和小說(shuō)中,張煒多次提及他的父親在“文革”時(shí)期曾蒙受不白之冤,這對(duì)張煒的影響很大。參見(jiàn)張煒《游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出版)。
參考文獻(xiàn):
[1] 張煒.我跋涉的莽野:我的創(chuàng)作與故地的關(guān)系[G]//孔范今,施戰(zhàn)軍.張煒研究資料:乙種.濟(jì)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2] 巴赫金全集:3卷[M].錢中文,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3] 張煒.梭羅木屋[M].長(zhǎng)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
[4] [法]列斐伏爾.空間:社會(huì)產(chǎn)物與使用價(jià)值[G]//包亞明.現(xiàn)代性與空間的生產(chǎn).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責(zé)任編輯 楊寧〕
作者簡(jiǎn)介:焦紅濤(1973-),男,河南宜陽(yáng)人,副教授,博士。
基金項(xiàng)目:河南省社科規(guī)劃項(xiàng)目(2014BWX039)
收稿日期:2015-05-04
中圖分類號(hào):I206.7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6?5261(2016)01?01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