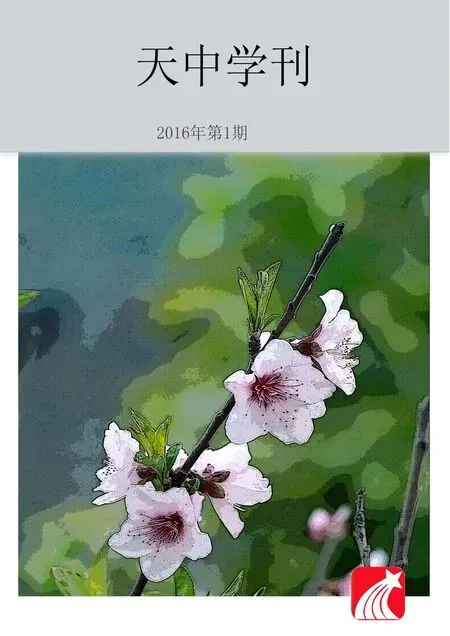論同光體詩歌創作的求新自變
侯運華(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
論同光體詩歌創作的求新自變
侯運華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摘 要:中國近代詩歌的變革,既有“詩界革命”的外在促動,也有傳統詩歌內部的求新、自變。就同光體而言,無論是抒情主體獨立意識的凸顯,還是詩歌內蘊的變化、詩歌語言的俗化等,均成為催發文學變革的新特質。其獨立意識一方面表現為自主意識、開放意識、批判意識和民間意識,一方面表現為詩人對現實問題理解的獨特性。詩歌內蘊方面,無論是吟詠新學、新知、新事物,還是描述剛剛發生的歷史事件,抑或是記錄與外國人的交往等,均具有較為鮮明的時代色彩。正是傳統文學內部的求新、自變,與呼嘯而至的“詩界革命”形成呼應,才推動中國詩歌實現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型。
關鍵詞:同光體;獨立意識;詩歌內蘊;詩歌轉型
從總體格局看,中國近代詩壇的構成主要有兩大陣營:倡導“詩界革命”的新派詩和推崇古人的崇古派,后者包括同光體、漢魏六朝詩派、中晚唐詩派、常州詞派等。兩者并非同步產生,“詩界革命”的倡導是基于對崇古派創作的不滿,梁啟超說:“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為詩之境界,被千余年來鸚鵡名士(余嘗戲名詞章家為‘鸚鵡名士’,自覺過于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然后可。”[1]1826亦即以崇古派為其批判目標,自覺與之反動,別辟另一詩界。于是,“詩界革命”倡導新派詩,促使傳統詩派發生變異,成為其發生變化的外因。那么,中國傳統詩歌是否也在隨時代變遷而醞釀內部變革呢?學界對此關注較少。本文以最具代表性的同光體為主,從抒情主體的獨立意識和詩歌內蘊的變化等視角論述其催發文學變革的新特質。
一
同光體是承續宋詩運動而至同治、光緒年間形成的近代詩歌流派。“同光體者,蘇堪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2],其代表詩人有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范當世等,理論家是陳衍,《石遺室詩話》可視為該派詩論代表作。以往學界多聚焦同光體與時代不協調之處,認為“就總的傾向而言,‘同光體’派詩人在近代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中思想較保守,作品的時代氣息較單薄”[3]474。然而,文學的發展絕非平面的直線運動,而是非常復雜的過程。即便是同光體這樣典型的傳統文學,依然蘊含諸多新因子。如從抒情主體觀察之,雖然同光體詩人思想上仍是孤臣孽子之心,但其詩歌中所抒發的顯然是只有經歷了近代社會變遷才會有的郁憤。僅此即可看出他們與傳統詩歌表達神契自然或忠君愛國的集體抒情的差異,沉郁憤懣的情緒背后是獨立的抒情主體。而獨立抒情主體的產生,恰恰是新文學萌生的前提。
具體講,同光體抒情主體的獨立意識表現為自主意識、開放意識、批判意識和民間意識。自主意識是指詩人們一方面確實知道新派詩倡導者對古詩無用的評判,在創作中自我調整;更重要的是他們對自己鐘愛的事業(這些詩人大多無需謀生,多把創作詩歌作為人生的寄托,可以“事業”視之)亦有清醒的認識。陳三立《過天津戲贈癭公》曰:“酸儒不值一文錢”,顯然意識到在動蕩不安的社會背景下,擬古詩歌作的再好,傳統學問積累再多,其價值也值得懷疑。因此,他積極參與維新活動,曾“往游滬上,一探泰西軍械之秘”(1885年)[4]152;支持父親陳寶箴在湖南的改良變法,主持湖南礦務,創辦時務學堂,捐資《時務報》,籌辦女學,做不纏足會理事(1897年)[4]402;并嘔心瀝血,總理江西鐵路建設等。而他對黃遵憲詩歌的贊許:“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才思橫溢,風格渾轉,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謂天下健者。”[4]313則表現出對“詩界革命”及其倡導的新派詩肯定;他對張恨水、平江不肖生小說的喜歡,亦凸顯出其文學觀顯然超越了傳統的雅俗之分①。對自身價值的否定已經透出他們并非糊涂的老朽,對社會政策的研究與建議更凸顯出其自主意識。鄭孝胥《紀對南皮尚書語》《題龍州小學堂》等詩,陳衍《太息一首送河瀨如侗歸日本》等均有創作主體對政策的架構。《紀對南皮尚書語》針對日本占領朝鮮的現狀,指出“韓釁初未發,蓄謀非一時”;為何如此?“中朝實久弛,文武茍以嬉。寇至紛募兵,械器窳弗治。”如何應對?詩人提出建議:“頗聞列國法,其制有三師。號為常備者,終歲聽指撝。晝警若赴敵,宵巖若交綏。其次曰預備,軍行乃登陴。又次為后備,不足則征之。朝令夕已發,有類脫兔馳。”面對封疆大吏張之洞的征詢,鄭孝胥提出了加強軍備的具體主張。這些主張,絕非傳統意義上的紙上談兵,而是詩人參考所掌握的西方軍事訓練知識而提出的,因而帶有鮮明的自我色彩。《題龍州小學堂》則對如何守邊提出自己的主張:“守邊有上策,興學以平亂。三嘆登斯學,彌天待童冠。”將歷代軍人的職責與興學結合起來,將國家的未來寄托在兒童身上,凸顯出鄭孝胥思想中政治家的素養。陳衍的《太息一首送河瀨如侗歸日本》先是感慨“我生實不辰,坐見陸沉日”;然后提出救國策略“自強在尚武,原富在戒逸”;于此策略下,詩人提出自己的貨幣、財政政策:“竊思挽時局,財政宜秩秩。硬貨定本位,紙幣相輔弼。中央集散法,制限屈伸律。股劵若泉流,國事理如櫛。求言下徵車,謂可陳造膝。”以硬通貨為本,以紙幣為輔,制定彈性利率,發行股票、債券,以使國家財政增收,國家富強方可挽救危機。其意識的超前和思維的獨特均為傳統詩人所未有,體現出強烈的自主意識。
同光體詩人的政治傾向大多保守,但其文化態度與政治傾向并不完全一致。陳三立早年力主改革、參與變法的行為眾所周知,遺憾的是此期詩歌留下極少,給人留下“作神州袖手人”的印象。然而從《散原精舍詩文集》中仍可以看出陳三立不甘落伍、開放進步的內蘊。試舉其一面論之,《祝女嬰入塾戲為二絕句》云:“安得神州興女學,文明世紀汝先聲”;《題寄南昌二女士》曰:“家庭教育談何善,頓喜萌芽到女權。”從“興女學”——實施對女性的教育(認為這是開創文明的先聲),到“家庭教育”中倡導“女權”,爭取實現家庭中的男女平等,皆凸顯出其與時俱進的女性觀。同光體的另外兩位詩人沈曾植、鄭孝胥,不僅詩歌中表現有開放意識,而且現實生活中與外國人有較為密切的交往。如1913年,沈曾植年譜中記載的84天中,與外國人交往14人次,諸如:德國人衛禮賢、漢納根、金楷理,法國人伯希和、波多博,美國人福開森、李佳白,俄國人凱沙林、喀西尼,日本人鈴木虎雄、富岡謙藏、井手三郎、長井江衍、岡千仞等。這些交往不是泛泛的禮儀來往,而是外國人將沈曾植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向其請教孔教、詩詞、書法等學問。雖然可以肯定,這種交往不是對等的,因為不懂外語,沈曾植接受對方的影響不及他所介紹的多;但是,若考慮到他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俄國股章京(1889年),曾上書借英款修鐵路并開強學會(1895年),1909年命日本教習去黃山采取植物標本,命舉人謝石欽趙日本考察稅制等開放行為,其接受外來影響是可能的。在夷夏之辨尚存的環境中,他們能夠廣泛接見不同國家的學者,與其進行文化交流,即表現出開放意識。鄭孝胥的特殊經歷使其與外國人交往更多,后期與日本人的交往性質已變,不屬于文化交流的范疇,此不贅論;通過鄭孝胥早期與外國人的交往,仍然能夠看出其特點。如1901年元旦,其日記云:
為西歷一千九百一年元旦,乃入第二十紀世運之期,西人以百年為一紀。 發片賀年:地亞孟德、客拉威、朱蘇、埃乃白,法領事瑪璽理,法翻譯陸文德,比領事薛福德,稅務司何文德[5]779。
不但以西歷紀事,而且按照西方文化習俗給8位外國人寄賀年片,可見他與西方人打交道的熟練與得心應手。如果說這是元旦節,尚屬于禮節往來,那么1902年2月里,非年非節,鄭孝胥依然6天內接待5人6次。應該注意到這是庚子事變剛剛過去之時,國人還大多對外國人抱著敵視態度,而鄭孝胥已經與外國人頻繁接觸了。選擇同光體的三位代表性詩人作為剖析對象,筆者認為以往論者憑其“同光體”的文化身份、保守的政治態度等認定其為保守的結論是過于草率了,起碼是以政治標準、文化立場來評判文學創作,難免會出現錯位現象。應該說,就其總體而言,上述觀點似可成立;但從文學視角評判之,則發現在時代大潮沖擊下,在“詩界革命”的激蕩下,傳統詩人的主體意識已經漸趨開放了。
值得注意的是,同光體詩人在利用近代傳媒發表詩作、集聚同志方面也凸顯出開放性。以《庸言》《東方雜志》等刊物為主,同光體詩人大展身手,充分利用了近代期刊傳播迅速、覆蓋面廣的特性,為該流派的形成、交流找到了極佳的平臺。據學者統計,《庸言》存在的1912-1914年,其“詩錄”欄共發表詩歌600首左右,宋詩派詩人的作品即有200首,占1/3。“其中僅陳三立、鄭孝胥、陳衍、沈曾植、陳寶琛等幾個宋詩派的重要詩人就發表117首,約占總數的1/5。”同時,陳衍的《石遺室詩話》第一至第十二卷也連載于此。“同光體”命名也是在《庸言》上完成的[6]。《東方雜志》1915-1920年的“海內詩錄”“詩文苑”欄目,有99位詩人發表詩歌1709首,“宋詩派發表詩歌約占《東方雜志》5年發表詩歌總數的70%以上。”其中,陳三立215首,陳衍129首,夏敬觀93首,沈瑜慶73首,鄭孝胥68首,沈曾植66首等;陳三立一人即占總數的12%[7]。因此,即便從現代傳播學的視角考察,同光體詩人的開放意識也是比較鮮明的②。
抒情主體的獨立意識還表現為他們對現實問題的理解與眾不同。以鄭孝胥為主,我們討論其觀點的獨特與深刻。中國近代社會面臨著列強分割、民族存亡等諸多問題,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帶來的危機是每個有責任的讀書人必須思考的問題。針對列強入侵,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建立近代化的軍隊,鄭孝胥《紀對南皮尚書語》所提出的建立常備軍、預備軍、后備軍的對策即如此。為什么要學習西方的軍事體制?是因為詩人對中國軍隊現狀的徹底失望。《煙臺舟中》寫道:“月照成山船似箭,舷間一卒話軍前。捕生虜諜渾如鬼,斬級健兒只為錢。”通過軍卒的口道出軍隊內情,讓人明白中國軍隊面對列強時緣何失敗,也透出詩人獨特的觀察視角。他寫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0月24日的日記也對此有記錄:“夜,嚴壽民來見,自言前數日愷軍營哨官在妓寮宴客,護軍營往捕,因互毆,傷數人,已亦與焉,求為緩頰。”[5]772而在民族矛盾尖銳、滿漢區別凸顯的時候,能夠大膽提出自我的民族觀則更為可貴,盡管其中也包含對革命者民族觀的誤解乃至敵意。《書日報后》云:“戊庚逮今茲,躁進互擊掊。謬興種族論,國事迫解鈕。惟予倡群學,蕩蕩辟天牖。”認為革命者倡導的種族論是“躁進”,是導致國事解鈕的謬論,因而倡導“群學”,認定只有這樣,才能為國人開辟“天牖”,帶來光明。《海藏樓雜詩》曰:“合群時未來,眾勢苦易散。相安三百年,可慮在滿漢。外族方侵凌,萬鈞系一線。幸君毋絕之,失手且糜爛。漢存滿自安,其意豈好叛?誰令走胡越,迫之乃驚竄。惜哉無大臣,獨立濟時難。”這段詩內蘊復雜,但其基本意蘊還是明白的:在“外族方侵凌,萬鈞系一線”的民族危機面前,詩人為國人不能“合群”“眾勢苦易散”而擔憂;反思清朝近三百年的歷史,最大的憂慮在于滿漢之分。強調過分區別滿漢,只能導致民族分裂,惋惜沒有力挽狂瀾的大臣治理這些問題。如果拋棄成見,就詩歌內蘊而論,這里的民族觀是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相關聯的,也是有價值的。后來,鄭孝胥作《江陰趙煥文茂才殉節紀書后》,則演變成謾罵式的詛咒:“賊臣倡犯上,舉世乃好亂。排滿實邪說,不義豈尊漢?”對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排滿革命,他顯然不能認同,乃發出自己的謬論。但是,由此可見其對民族問題是一直嘗試著尋找自己的答案的。
在詩歌創作方面,同光體也并非一味尊古擬古,而是將傳統詩歌從來不寫的素材引入詩歌,呈現出趨俗去雅的傾向。這種傾向與“詩界革命”的倡導者暗合,乃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使然,客觀上也構成對“詩界革命”的呼應,透出其民間意識。鄭孝胥《食菜尾羹綠豆澆飯》云:“雞子調黃嫩如橙,芥根縷切不妨生。會心正在酸咸外,一啜閩中菜尾羹。憎濃喜淡理誰參,舌本葷腥漸不堪。綠豆冷淘澆白飯,何如萊菔苦中甘?”日常生活中遍食葷腥,已經麻木的味覺被故鄉的食物——“閩中菜尾羹”喚起,引發詩人幾多感慨。以平易的語言描繪平常的食物,使歷來高雅離群的詩歌開始吟詠民間俗物,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陳衍的《食燒餅》也是選取平常食物作為歌吟對象:“不食肉糜食餺飥,形如魚須徑寸博。夾以羊肉爛以膜,惜哉士安不可作。”除了首句以燒餅的古稱“餺飥”入詩尚有“以學問入詩”的特點外,其余詩句可以看出詩人努力描述燒餅形狀的意向,只是限于才識,遠不及鄭孝胥詩歌傳神寄情,能夠建構起渾然一體的意境。然而,這類詩歌已凸顯出詩人主體意識的嬗變,即傳統的高雅追求雖然依舊占據主流位置,但是受時代沖擊,詩人開始從傳統詩歌題材之外尋覓描述對象,表達某種雖說不雅卻更易喚醒讀者應和的情思。而所用形式依然是傳統的七言絕句體,恰恰是舊形式與新意境的結合,與新派詩的特征具有相似性。
二
同光體留給人們忠君、保守的印象,似乎只能吟唱出歌頌皇室圣境、朝廷清明的歌聲,或者在政權更迭之際感嘆荊棘銅駝、面對夕陽抒發懷舊思古的情懷,在同光體詩歌創作中確有這些內蘊,但并不只有這些內蘊。無論是陳三立、鄭孝胥,還是沈曾植、陳衍,他們都曾經參與時代變革進程,都不同程度地融進改革潮流之中。因此,當他們創作詩歌時,不同于傳統詩歌的內蘊便凸顯出來。
陳三立被推為近代宋詩派的領袖,其詩歌創作確有以散文入詩、以理入詩等宋詩特征,包括為求新異而不用熟典等,由此造成其詩的晦澀難解。但是,與中國詩歌史上的詩詞大家一樣,其風格絕非單面,他對此頗自信。《園居慢興》云:“老夫所殉與終古,當世猶稱善屬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詩歌中還有許多順暢平易之作,也有對現實問題的諸多吟詠。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認為其詩歌,“可以泣鬼神訴真宰者,未嘗不在文從字順中”。梁啟超評價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濃深俊微,吾謂于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8]10皆指其詩歌創作關注現實、語言順暢的特征。
作為在湖南從事變法實踐的同志,陳三立對梁啟超的活動是一直關注的,他們之間的詩詞應和與欣賞是這種關注的實證。《任公講學白下及北還索句贈別》云:“辟地貪逢隔世人,照星酒坐滿酸辛。舊游莫問長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開物精魂余強聒,著書歲月托孤呻。六家要指藏禪窟,待臥西山訪隱淪。”雖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畢竟寄寓著難以忘懷的意蘊;何況透出歸隱學禪的意圖,也是對知音才言的內情。因此,他對梁啟超倡導的“詩界革命”也不可能不關注,其詩歌創作中許多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與新派詩吻合的。首先是對新詞語的運用以及由此承載的新思潮。他的《祝女嬰入塾戲為二絕句》和《題寄南昌二女士》對女性教育和女權意識的關注,已如前述。《次韻答王義門內翰枉贈一首》云:“君不見鄒魯大師冠峨峨,希臘竺乾應和多……天窮地變必有待,請聽慘惻啼湘娥,世界健者知誰何。”其中既有對世界變化的認知,也有對外國國名的引入,還有對中國成為“世界健者”的隱隱期待。《日本嘉納治五郎以考察中國學務來江南既宴集陸師學堂感而有贈》是詩人參與接待日本人活動后的情感抒發,更為集中地表現出詩人向外觀的思考成果:“國家喪敗余,頗復議新政。仍遵今皇謨,囁嚅誦甲令。四海學校昌,教育在釐正……禮樂壞不修,侈口囈孔孟。譬彼涉汪洋,航筏失導迎。盲童附駒犢,曠莽欲何騁……東瀛唇齒邦,泱泱大風盛。亦欲煦濡我,挾以御物競。群士忽奔湊,有若細流迸。觥觥嘉納君,人倫煥斗柄。創設師范章,捷速日還倂……起死海外方,撫汝支那病。”詩中有對“新政”的呼喚,有對教育興國的期待,也有希望借鑒日本強國之路以救國的思想。其中“新政”“學校”“教育”“物競”“師范”等新語匯的運用非常恰切,讓讀者體悟到陳三立雖然遠離政治中心,卻依然關心國家命運的熾熱情懷。
陳三立《蒿盦類稿序》曰:“蒿盦先生……跼天蹐地之孤抱無可與語,輒間托詩歌以抒其伊郁煩毒無聊之思,宛然屈子澤畔、管生遼東之比也。”[9]895強調詩歌的抒情作用,寄寓以詩關注現實之思。《除夕被酒奮筆書所感》即為新舊交替之際對“國家大事”的考量:“西南寇盜累數載,出沒蹂躪驕負嵎。東盡黃海北嶺徼,蛟鯨搏噬豺虎驅。”面對這樣的處境,詩人對“朝三暮四”的政策變化、“限權立憲”的荒唐行為等進行諷刺;同時,對剛剛興起的“地方自治”表示支持:“士民覆幕出至痛,地方自治營前模。事急即無萬一效,終揭此義開群愚。”認為實行“地方自治”起碼對開啟民智有益,肯定其啟蒙價值。《廬旁被雹災聊記之》則描寫“天災人禍不虛應”的情景:“城東飛雹如酒椀,城西雹大如鵝卵。擊碎夏屋千玻瓈,毀瓦破垣更無算。其時雞犬皆夜驚,滿城官吏走且喘。況當焚殺牧師后,豪酋隊艦爭射眼。魂翻夢悸夫何誰,各指彈石恣蹂踐。”如果說前一首詩里“立憲”“地方自治”等新詞匯的運用只是表現詩人對政治現象的認識與態度,那么,后面這首詩里“牧師”“隊艦”的出現則成為導致災難的關鍵性因素,是“天災”之后的“人禍”,是加重災難后果的外來因素。兩方面融匯起來,即凸顯出詩人視野的宏闊與對新事物的敏感。其他如《短歌寄楊叔玫時楊為江西巡撫令入紅十字會觀日俄戰局》中諷刺“紅十字會”:“吁嗟手執觀戰旗,紅十字會乃虱汝。”《雪夜憶內客上海》描寫帶兒女游“新世界”的場景,將娛樂場所寫入詩歌,也算最獨特的避熟求新吧!《端午集公園》則描摹“傾城仕女擁橋看”的情景,將公共空間內新異的景象展示出來;《汽車發漢口抵駐馬店口號》則捕捉住汽車飛馳的細節,描述所見之景:“萬轉金輪羯鼓撾,橫穿郡國突長蛇。”顯然,與傳統的乘轎出行或騎馬跑過不同,汽車疾馳的隆隆聲響與橫穿而過的速度感給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詩歌表現之,構成與傳統詩歌在意象、意境等方面迥異的特色。
陳三立的詩歌,還聚焦于沉重的現實,以凝重的筆調抒發對時局的理解和對積弊的憤激。《上元夜次申招坐小艇泛秦淮觀游》曰:“爾我羈旅共節物,向人但能結舌瘖。百憂千哀在家國,激蕩騷雅思荒淫。”佳節之際,詩人卻有“百憂千哀”郁積胸中,而且無法向人訴說。詩歌非常形象地把現實苦悶表達了出來,甚至采用了他很少寫于詩行的憤激語言。《次韻和義門感近聞一首》吟道:“誰云荼苦食梅酸,誰覺唇亡覺齒寒。累卵之危今至此,兩言而決恐皆難。”針對累卵危局,詩人有無盡的感慨,故欲說還休。《次韻答賓南并示義門》則反映出在理想與現實沖突中自我的迷失,如麻思緒難理清,只好寄情于詩書:“日日吟成危苦辭,更看花鳥亂余悲。閑來歲月吾喪我,圣處功夫書與詩。如此江山相向老,休論文字起衰誰。江南風景須公等,看取園亭啜茗詩。”這種源于內心深處的迷惘往往帶給詩人深深的焦慮,若是遇到現實生活中的大事件刺激,則易激起強烈的情感反應。作于同時的《得熊季廉海上寄書言俄約警報用前韻》即抒發感慨曰:“滿紙如聞嗚咽辭,看看無語坐銜悲。黃云大海初來夢,白月高天自寫詩。已向蒿萊成后死,拚供刀俎尚逃誰。癡兒只有傷春淚,日灑瀛寰十二時。”眼看祖國陸沉的錐心之痛,無法言說的悲哀之情,整日伴隨著詩人,成為難以忘懷的悲情。當這樣的情緒積淀到一定程度時,詩人常常反思生死問題。或如《與純常相見之明日遂偕尋莫愁湖至則樓館蕩沒巨浸中僅存敗屋數椽而已悵然有作》云:“崎嶇九死復相見,驚看各捫頭顱在。旋出涕淚說家國,倔強世間欲何待。”或以詩歌留住殘酷的現實畫面:“狼嚎豕突哭千門,濺血車茵處處村。”或如《題夏伏雛燕北紀難圖冊》驚異“古來未有拳民亂”的現狀,悲憫“四百兆人原禍始,淚看成海夢成絲”。或如《小除后二日聞俄日海戰已成作》直指日俄戰爭中清政府所謂保持中立的危害:“萬怪浮鯨鱷,千門共虎狼。早成鼾臥榻,彌恐禍蕭墻。舉國死灰色,流言縮地方。終教持鷸蚌,淚海一回望。”
這些詩歌并非陳三立描寫現實題材的全部作品,僅此即可看出詩人對現實重大問題的關注。舉凡關涉國家命運的大事件,在其詩歌中均有直接、間接的反映,實現了以舊形式反映新問題的目標。當然,從同光體自身看,也可視為是陳三立避熟求新的獨特方式。
鄭孝胥是有著強烈功名心的詩人,早年作《書檉弟扇》即曰:“我生實不辰,降志而辱身。如今好相戒,莫作采薇人。”因此,他時時留心有助于實現自我志向的學問,對于新事物、新知識能夠及時吸收并融匯到詩歌創作中,使其詩歌擁有新詞匯、新意象。如《冬日雜詩》記載他到日本后的見聞,既感慨“日人行新法,中國始遣使”,亦介紹其圖書業的發達:“又觀圖書館,典籍亦略備。盡蒐為目錄,頗足資考異。”同時,對日本重視商業的風氣詳細介紹:“誰能安士農?唯聞逐工商。賈胡合千萬,其國旋富強。”肯定商人對國家的貢獻,凸顯出詩人已經超越傳統重農輕商的意識。《送檉弟之日本》告誡弟弟:“為學貴平等,要自勤學始。”《書日報后》感嘆:“惟予倡群學,蕩蕩辟天牖。”《朝鮮權在衡招飲觀梅》則肯定“德法二主信時杰”,表達對弱國現狀的不滿;感慨“誰知異人華盛頓”,對國人的閉塞蒙昧表示焦慮等。無論是“平等”“群學”“華盛頓”“圖書館”等新詞匯的融入,還是對法、德、日等強國的肯定與贊許,抑或是對商業行為的認同和對啟蒙問題的關注,均凸顯出鄭孝胥詩歌中具有領先同儕的新內蘊。
由于鄭孝胥的經歷復雜,游歷之處也多,因此其詩歌視野開闊,對問題的思考也呈現多維視角。如《櫻花花下作》吟詠日本國花櫻花曰:“嫣然欲笑媚東墻,綽約終疑勝海棠。顏色不辭脂粉污,風神偏帶綺羅香。”雖不如黃遵憲《櫻花歌》舒卷自如,多姿多彩,畢竟也是對東瀛名花的描繪,超出傳統士人的視野。《題吳干臣觀察邊城籌筆圖》則透出詩人對邊防問題的思考:“會見侵邊警,寧論距海憂。南藩隳緬越,左股折蠻甌。群醉誰先覺?孤忠入九幽。圖窮心不滅,詩就涕應流。”詩中既有對邊防、海防的通盤考慮,也有對侵略者占領緬越后對中國大局安危的擔憂;同時,表達先覺者的孤獨無群以及不甘失敗的心理。顯然,這不是一般的書生之憂,而是具有大局意識和開闊視野者才可能有的思量。其他如《海藏樓雜詩》第31首詩對遼東的關注,揭露日本的陰謀:“東鄰假兵力,移民亟盤踞。意圖數年間,逼我以生聚。”指出列強的趁火打劫:“列國知其謀,染指競借箸。”告誡國人:“吾民如寄生,覆巢在旦暮。國亡定何狀,覩此應可悟。”進而發出呼吁:“及今猶可救,投藥勿再誤。遼民休酣寢,人事委天數。”《十一月十八日出山海關》感嘆:“危邦空嘆吾為虜,浩劫終愁谷作陵。盡有邊才誰用得,翻飛遙想郅都鷹。”《紀對南皮尚書語》中借鑒“列國法”,提出建立常備軍、預備軍、后備軍的建議等。這些詩歌或透視日本及列強的陰謀,或針對當局保守自閉而自負能夠守邊立功,或參考列強經驗提出建設性方案,均顯示出不再局限于傳統文化視野思考表現對象,從而與新派詩的表現傾向一致。
陳衍仕途坎坷,長期處于統治集團的邊緣位置,卻有入世情懷,因此,其詩歌反映出的自我形象是相當尷尬的。據筆者統計,《陳石遺集》共收錄966首詩,其中應酬之作達743首,占77%。翻開其詩集,多為《題×××》《壽×××》《挽(哭)×××》《送×××》《×××報飲》《×××奉和》等題目,這類應和、應酬之作大多形式精巧,內涵單薄,沒有多少價值。陳衍真正具有價值的詩歌是其關注現實和反映新潮的作品,筆者以此為主要論述對象闡釋陳衍詩歌的特點。前者如《用蘇戡韻送子培時子培有弟余有兄有子在北方亂中》云:“別淚從來不浪彈,此回端覺徹心酸。倉皇烽火傳三月,辛苦麻鞵累一官。避地依人行已老,自厓送子反良難。再將骨肉投豺虎,可免磨牙吮血殘。”題目中的“北方亂”指的是庚子事變,以此為背景,詩人抒發了戰火隔離、音訊不通、擔憂親人的焦急情感,有感而發,頗為真切。其擔憂并非多余,不久即傳來其子被聯軍槍殺的消息。痛苦之余,詩人寫下《哀漸兒》:“冥鴻兩兩將五雛,年年翻飛渡江湖。四雛南來一雛北,哀哉中鏃亡其軀。爾雛不為稻粱謀,胡獨去北天一隅……爾非道安弓劍徒,寧能為人護孀孤?謬思談笑卻羌胡,哀哉性命戕須臾……我今行將終菰蘆,環顧諸雛彌哀呼。危邦亂邦動可死,王涯宅有玉川廬。”詩前有序曰:“兒在天津學堂,亂作,住同學袁宅。袁有新婦,洋兵將據焉,兒為說退之。兵旋復來,開槍戕兒。”小序概括敘述了兒子被槍殺的過程,也告訴我們作詩的原因。盡管其中蘊含著因愛子而生的自私感情——責怪兒子不該管閑事,導致自己喪命,也凸顯出詩人依然在用傳統意象傳達情感;但是,能夠以時代動蕩為背景,描繪出“危邦亂邦動可死”的現實,亦反映出詩人對時局的關注。唯其如此,他才思考如何改造日趨腐敗的現實,預設自己的解決方案。前引《太息一首送河瀨如侗歸日本》即提出其救國策略:“自強在尚武,原富在戒逸。”詩人明白國富才能抵抗列強入侵,也才能挽救像漸兒這樣的無辜青年,因此,在詩歌中他有意為傳播新理念而引入新詞匯、新意象。此詩中的“財政”“硬貨”“本位”“股券”等財經詞匯,顯然承載著詩人治國的經濟理想。而《殘臘偕子培過江宿蘇戡鐵路局樓上約暇時相督為律詩新正臥病連日讀荊公詩仿其體寄蘇戡》中“與君隔水上高層,斜角相望認電燈”的詩句,則反映出1899年的詩人已經注意到新器物的應用帶來景觀的變化;《九日集酒樓時余以病養戒酒》記述詩人因病不能飲酒,但朋友聚會無酒不歡,于是“佳節總須求酩酊,強攜啤酒注深杯”。此細節,一方面說明在詩人眼中,度數較低、口味平淡的啤酒不算酒,病中亦可飲;一方面則凸顯出作為舶來品的“啤酒”,此時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品,將其寫入詩中,既見其對新事物的不排拒,亦顯現出去雅趨俗的特點。清末民初,陳衍與梁啟超交往不斷,既為后者改詩,也應邀在梁啟超主辦的《庸言》上發表詩歌、連載《石遺室詩話》,還多次參與雅集、詩詞唱和,說明其對“詩界革命”的態度并非頑固排斥[10]。
沈曾植學問淵博,視野宏達,且有意以學問入詩,其詩的確奧澀難解。即便有錢仲聯先生為其花費心血校注③,依然令一般讀者望而卻步。但是,沈曾植詩歌創作中也并非總是沉浸于佛老學說或經史典籍,其詩歌創作也有對現實的反映、對時事的關注和對新思潮的描述。1898年,戊戌變法“六君子”被殺,詩人于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寫出《野哭》,寄托對六君子的哀思:
野哭荒荒月,靈歸黯黯魂。薰蕕寧共器,玉石慘同焚。世界歸依報,衣冠及禍門。嵇琴與夏色,消息斷知聞。(其一)
烈士寧忘死,難甘此日名。信猶遲蜀道,命豈墮長平?精爽虹應貫,虛無獄會明。信知全物理,亂世直難爭。(其二)
草草投東市,冥冥望北辰。并無書牘語,虛望解環人。天地微生苦,山河末劫真。一哀終斷絕,千古為酸辛。(其四)
據錢仲聯先生注,其一既用《孔子家語》云:“薰蕕不同器而藏。”言劉光第雖然與譚嗣同、林銳等人的年輕氣盛不同,卻依然遭逢被殺戮的命運;也用《魏氏春秋》關于嵇康臨刑“援琴而鼓”的典故和《夏侯玄傳》記載其“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的神態,對六君子慷慨就義的行為表示贊揚。其二則引用長平之戰后,幾十萬降卒被坑殺的冤屈,一句“命豈墮長平”,與“虛無獄會明”暗用岳飛被“莫須有”罪名冤殺典故一起象征六君子的冤情;而“精爽虹應貫”則暗用荊軻典故,表達詩人對六君子身雖死、魂不滅的認知。其四用晁錯被殺東市的典故,繼續抒發六君子被殺之冤;同時,對烈士犧牲后“山河末劫”到來的命運有敏感的描述。作于1913年的《南風》則直接描寫是年7月2日至15日討袁軍攻打上海制造局的事件,詩曰:“南風骷髏生齒牙,川原白骨亂如麻。大猛火聚一燔焫,涂毒鼓聞空痛嗟。天狗有聲雷墮地,鬼目相看血是花。如何日月眼長閉,忍蟇皤服長爬沙。”詩歌以猙獰怪異的意象將戰爭的血腥恐怖展現出來,表現出詩人對戰亂的徹底否定。其中,只關注戰爭結果,而不關涉價值立場的超然態度,乃典型的遺老作為。但是,在閉目不見民國事的時候,依然關心戰爭對百姓生命的摧殘,也凸顯出即便是遺老,生在那樣的時代,也不可能做到心如枯井了!何況,就在辛亥革命發生那年,詩人作《江上》詩曰:“江上晴云雜雨霞,江東兵氣屬吳娃。排成海外魚龍隊,秀絕閨中姊妹花。”此詩被錢仲聯先生注曰:“辛亥革命時,有女子從軍者,詩蓋詠此。”[11]442能夠將剛出現的新事物寫入詩中,亦可看出沈曾植保守傳統的內蘊之外,自有順時應勢的一面。
本文以同光體為主,論述在時代大潮沖擊下傳統詩歌的求新與自變。這是尚未擺脫傳統文化氛圍的內部改良,并非革命性質變。即便如此,也有獨特價值:“中國詩特別是晚期的詩,在主題或個人用語上,往往不是獨創性的,但是這樣的詩并不是毫無價值的……使用脫胎的觀念和用語的詩,如果把這些觀念和用語結合在一起,還是能成為有獨創性的詩。換句話說,一首脫胎的詩如果能成功地把借用的觀念和用語融合成一種新的式樣,那么它就能成為一首好詩。中國詩人經常使用傳統的短語、意象和象征,就像拜占庭的藝術家使用一些彩色玻璃和彩色石子做成鑲嵌工藝品一樣:它們的獨創性不在于所用的材料上,而在于最終達到的效果上。”[12]184當然,并非只有同光體如此,魏晉六朝詩派的王闿運、中晚唐詩派的樊增祥、常州詞派中“晚清四大詞人”的創作等,不管其政治立場怎樣保守,其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里依然有對合乎時代發展趨勢的“詩界革命”主張的客觀呼應。王闿運的《圓明園詞》以圓明園的百年興衰為吟詠對象,勸諷統治者戒奢興利,對入侵者焚毀千古名園的行為進行譴責。樊增祥的《彩云曲》《后彩云曲》為晚清名妓賽金花(原名傅彩云)作傳,通過描述傅彩云一生事跡,詩人得出“彩云易散玻璃脆”的結論,可視為詩人對名妓命運的概括與同情。如果說這些詩歌只是朦朧地透出詩人相對平等地看待女性的話,那么《中秋夜無月》等詩歌則凸顯出樊增祥對清末民初社會紛亂的局勢的觀察:“亙古清光徹九洲,只今煙霧鎖浮樓。莫愁遮斷山河影,照出山河影更愁。”將時局動蕩、山河不堪入目的情景展現在讀者面前,其中對局勢的透視、對前途的失望等時代情緒皆具有代表性。鑒于此,我們認為也是對“詩界革命”主張的間接呼應。正是來自傳統文學內部的求新、自變,與呼嘯而至的“詩界革命”形成呼應,才推動中國詩歌實現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型。
注釋:
① 陳小從說:“祖父晚年喜看小說消遣,在廬山和北平,都曾向書店租小說看,我印象較深的是張恨水的章回小說,其次是平江不肖生寫的武俠小說。”見《圖說義寧陳氏》(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頁)。
② 本段用語涉及“同光體”“宋詩派”。楊萌芽以“宋詩派”名之,乃學界總稱清代宗宋的詩歌流派;筆者所論“同光體”,乃“宋詩派”延續到近代的名稱。就名詞所指而言,楊萌芽所論依然是“同光體”詩人。
③ 其成果為《沈曾植集校注》(中華書局2001年出版)。
參考文獻:
[1] 吳松,等.飲冰室文集點校:3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陳衍.沈乙庵詩敘[J].庸言,1914(1-2).
[3] 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 李開軍.陳三立年譜長編:5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4.
[5] 鄭孝胥日記[M].勞祖德,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3.
[6] 楊萌芽.《庸言》雜志與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J].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008(8).
[7] 楊萌芽.《東方雜志》雜志與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
[8]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9]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下卷[M].李開軍,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 周建國.梁啟超與陳衍的詩誼往事[N].福州晚報,2013-04-01.
[11] 錢仲聯.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1.
[12] [美]劉若愚.中國詩學[M].韓鐵椿,蔣小雯,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1.
〔責任編輯 劉小兵〕
作者簡介:侯運華(1965-),男,河南上蔡人,教授,博士。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11&ZD110)
收稿日期:2015-08-03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5261(2016)01?008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