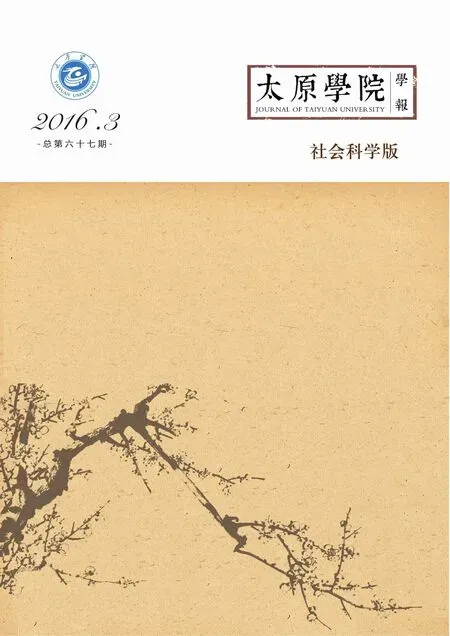從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義解讀《土生子》
管 莎 莎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從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義解讀《土生子》
管 莎 莎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將理查德·賴特小說《土生子》置于斯皮瓦克的屬下理論視野下對黑人女性的屬下性進行剖析,發現在白人中心話語與黑人父權制思想的雙重壓迫之下,黑人女性處于無話語權的社會邊緣狀態,成為了不能發聲的“屬下婦女”。托馬斯夫人、弗拉和蓓西三人被視為別格悲劇的幫兇,其實質卻是她們不被理解的親情和不被尊重的愛情,這強調了傾聽黑人女性話語的必要性以及激發黑人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重要性。
關鍵詞:《土生子》;斯皮瓦克;屬下;黑人女性
20世紀40年代,美國非裔作家理查德·賴特的代表作《土生子》(Native Son)問世,這部被譽為“黑人文學中的里程碑”[1]333的作品猶如一股颶風引起了整個西方評論界的注視,“真正迫使美國社會對黑人文學刮目相看”[2]159。評論界傾向于從存在主義、種族主義、心理學等層面多角度探析主人公別格的人物意義,卻往往忽略了對小說中黑人女性形象的屬下性進行剖析與探究。賴特從男權社會價值觀出發,塑造了麻木無知的黑人女性形象:托馬斯夫人、弗拉和蓓西。作者盡管客觀地描述了黑人女性的苦難生活,但刻畫過于簡單化,并沒有看到她們內心的復雜性,也從未立足她們的視角去思考問題。筆者試圖將文本置于斯皮瓦克的屬下理論視野下,針對小說中黑人女性的屬下性進行剖析,旨在揭露黑人女性在白人中心話語與父權制思想雙重壓迫之下的“失語”狀態,突出傾聽黑人女性的話語的必要性以及黑人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的重要意義。
一、斯皮瓦克后殖民主義理論
身為后殖民批評家兼女性主義者,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將關注點聚集在第三世界女性身上。恰是她第三世界的生活經歷,使其更能透徹地洞悉“屬下”。“屬下”一詞最早來源于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一書, 文中原意是指農村勞動力和無產階級。斯皮瓦克在《屬下能說話嗎?》 中對“屬下”概念進行了闡釋和引申,按照她的觀點,“屬下”是用來指那些沒有自己話語權或不能表達自己意愿的邊緣群體。
斯皮瓦克在此篇文章中還透過對寡婦殉身這一古老的印度習俗的探究,毫無保留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話語和男權話語二者對殖民地女性的話語扭曲。在印度本土話語中,婦女只有在丈夫逝世時進行自焚,她的肉體才會得到解脫,這一習俗透露出了本土的男權主義思想。此外,英國早期殖民者將“寡婦”一詞的傳統寫法sati改為 suttee。sati的原意是“好妻子”,而 suttee則有“忠誠”地自焚殉夫的儀式之意[3]140。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改寫造成了一種只有為夫殉身才是忠誠的話語暗示。英國早期殖民者對殖民地話語的隨意篡改,不僅破壞了當地原有的話語秩序,扭曲了原有的話語內涵,還給第三世界女性帶來了深重的話語壓抑氛圍。
因為深受帝國主義話語和男權話語的雙重壓迫,殖民地女性往往被推到社會最邊緣地帶。斯皮瓦克指出黑人女性正是“最底層的無產階級”,值得注意的是,她們數百年來都處于理論話語的空白區域。究其原因,白人女性有西方女性主義者的關注,第三世界的男性有后殖民主義理論家注目,然而以黑人女性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婦女的境況往往被忽視。她們是沒有話語權的沉默者,即使發出了聲音,也會由于沒有傾聽者而產生不了任何意義,不免成為空洞的能指。
二、《土生子》的后殖民解讀
伊萊恩·肖瓦爾特在《代表奧菲利亞:女性,瘋狂,及女性批評的責任》中曾說到:“女性在父權語言中是‘空白的’(absence),‘否定的’(negative)。在父權制文化中,女性被剝奪了思想和語言,被任意演繹和書寫”[4]35。在賴特這部充滿父權觀念的小說中,三個黑人女性(托馬斯夫人、弗拉以及蓓西)是生活的逃避者,是“瞎子”(blind),是別格悲劇的間接制造者。作者筆下的她們將白人的吩咐視為唯一的生存選擇,無視別格的反抗與掙扎,也不去探尋自己所受痛苦背后的深層社會根源,而只是按部就班地活在社會的邊緣。賴特真實地反映了帝國主義中心話語對黑人女性的侵染,使其墨守白人世界的生存法則,始終被遺忘在無聲的角落,沉默無語。
(一)悲劇的幫兇們
托馬斯夫人身體健碩、整日操勞,是美國文學作品中典型的黑人母親形象。在這個缺失父親的家庭里,盡管托馬斯夫人總是忙于工作,生活卻依然拮據,需靠救濟勉強度日。面對這樣的生活,她從未想過深層次的原因,偏執地認為只要兒子接受救濟的工作,全家就可以迎來生活的希望。對宗教的信仰是托馬斯夫人接納白人中心話語影響的一個重要體現。由于生活的苦難,托馬斯夫人等黑人女性將現實無法排解的痛楚與無奈轉化為精神上對宗教上帝的篤信。所以,就意識形態而言,黑人女性往往在潛意識中已經被主流文化觀念同化,甚至依賴于此種文化,她們的“聲音”已完全淹沒于白人中心話語的大潮中。
斯皮瓦克認為,黑人女性根本沒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經過宗教的浸潤后,話語的性質已然改變。如在小說的結尾《命運》一章中,別格因殺害了白人女孩而被警察逮捕,手足無措的托馬斯夫人首先能想到的不是尋求法律援助,而是希望得到上帝的庇佑,“要下決心,好好祈禱,孩子”[5]320。托馬斯夫人雖然心急如焚,但篤信宗教的她自己卻未意識到這對別格無絲毫實際幫助。
視野再轉向別格的妹妹弗拉,一個乖巧聽話、循規蹈矩的女孩子。她不問世事,只寄心于縫紉課,縫紉是她將來能否在白人世界存活下來的保障。弗拉雖然不信仰宗教,但受母親的影響她自覺地接納了以白人為中心的文化觀念,認同并遵守白人主流文化思想。小說中她贊同母親,認為別格去道爾頓先生家工作才是“正途”。她和哥哥為數不多的交流都在勸別格不要再游手好閑,每一次交流都以話不投機、面紅耳赤為結局。作者認為別格的“不務正業”,正是他對白人中心話語的強勁反擊。若從這個角度審視,弗拉在讀者面前已成為一個沒有抱負且愛嘮叨的庸俗女人,她客觀地加速了別格對這個家庭的疏離。
至于別格的女朋友蓓西,在賴特的筆下,她更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女人,麻木無知、酗酒成癮。她并不是真的愛別格,雖然時常唆使別格為她偷竊、花別格給的錢,但是當別格陷入了麻煩卻不能與他一同分擔。當別格的反抗意識爆發之時,蓓西并沒有充當一個積極的角色,反而成了別格逃跑時的負累。作者認為,是蓓西的好奇心讓她自己陷入了絕境,是她自己激發了別格的滅口之欲,一切都是她自找的。
在整部小說的描寫中,作者一直是站在男性的立場,以白人中心話語與父權制的口吻進行敘述,賴特筆下的黑人女性除了愚不可及、麻木無知之外,還充當了帝國主義的幫兇,體現了作者潛意識中的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傾向。那么拋開上述的偏見,真相確實如此嗎?
(二)不被理解的親情
黑人女性的境遇曾這樣被描述:“那白人把包袱扔下,叫黑人男性撿了,因為他不得不這樣做。但是他并不背著它走,他遞給他家里的女人。就我的理解來看,那黑女人就是世界的驢子。”[6]14這段話深刻地描繪出黑人女性所受到的壓迫,不禁讓人想起了托馬斯夫人的形象。在作者筆下,托馬斯夫人似乎除了批評別格游手好閑之外,就是在他不爭氣時哭訴自己的苦痛,“別格,有時候我心里想,我干嘛要生下你來”[5]12。身為母親的她雖然愛著別格,卻無法理解別格反抗帝國主義的夢想,對他的關心只停留在生活上而沒有到達思想上,未能給予在抗爭道路上的別格一份關愛,客觀上使其孤立無援。從作者的視角看去,托馬斯夫人無疑應對別格的失敗承擔一定的責任,她的母愛沒有到位,反而成為沉重的負擔。但是我們跳出作者預設的思路,重新審視這個人物時,不禁會有另一番思考。當別格面臨絕境時,托馬斯夫人為其下跪求情,“求求您,太太!別讓他們殺死我的孩子!他從來不曾有過機會”[5]343,這是一位母親發自肺腑的呼喊,她并非對孩子的追求毫不知情,然而別格卻不理解母親的苦心,覺得母親的這次下跪是他反抗之路上的莫大恥辱。
反之,別格對于親人是如何的呢?小說中刻畫別格的心理獨白:“真想一揮手,把她們抹掉。”[5]95他想要擺脫她們來獲取自由卻又不能,因為他還需要母親和妹妹勞動所得來生存。全家在母親的支撐下勉強度日,他卻還要想著自己享受,向母親要錢買雜志看電影。就像托馬斯夫人所說,別格“只知道自己開心”[5]12。他從來沒有關心過這三個黑人女性的苦難,反而像白人一樣瞧不起她們,在剝削她們勞動的同時,又將自己的苦難歸結于她們。別格體現了作為黑人男性自私自利以及對黑人女性壓榨的一面。
(三)不被尊重的愛情
“如果我不感到饑餓,我就是病了。如果我沒有生病,我就是在倒霉。”[5]269蓓西每天都要忙碌于白人的廚房,廚房里的那小片天地就是她的整個世界。盡管如此,她依然經濟拮據、生活窘迫。黑人女性不僅在經濟上是廉價勞動力,在法律上更是被忽略的群體,她們的生命是無法和一個白人女孩相提并論的。[7]在白人的法律中蓓西被謀殺這一事件并不值得關注,她的死只是調查白人女孩死亡原因的一個證據。正如同別格用來殺人的斧頭刀子等一樣,蓓西的尸體已經被觀念上物化成為了法官任意挪用的物證。不論是活著還是死去,蓓西自始自終都從未有過作為人應有的尊嚴。身為黑人男性的別格也被帝國主義思想同化,將蓓西的生命視為草芥且毫無畏懼地將其殺害,事后竟無所憂心,與誤殺白人女性的心態截然相反。
蓓西和別格同為受到白人中心話語壓迫與剝削的弱勢群體,應相互理解并聯合起來共同反抗才對。而事實則令人嘆惋,蓓西不但一直受到白人的剝削,同時也要忍受著黑人男性的傷害。不是對立面的白人殺死了蓓西,恰是她同一陣營的戀人別格讓其喪命,“別格在殺死她之前還沒忘記再一次利用她的軀體來滿足自己的性欲”[8]。由此可見,別格和蓓西雖然是戀人關系,卻未曾有過平等的真愛。對于別格而言,蓓西只是一個黑人女性,是釋放欲望的工具,是隨時可棄的負累。令人憂心的是,黑人女性不僅受到白人世界規則和中心話語的制約,還要承受著同屬一個種族的黑人男性的父權制壓榨,雙重壓迫下的黑人女性毫無話語可言。
三、結語
賴特在小說中多次暗示其主題,正是黑人女性不明事理地催促男性按照白人世界的法則生存,恰好不自覺地與白人主流秩序吻合,使得黑人男性的抗爭之路異常艱辛。然而,筆者竊以為這一主題的背后存在著對黑人女性的誤讀。斯皮瓦克后殖民主義理論闡明,屬下自己不能發聲,只有通過非屬下的中介其聲音才可能被聽到。在這部小說中,不管是抗爭還是夢想都是黑人男性所訴說與把控的,從未涉及黑人女性。黑人女性處于無聲且無地位的社會邊緣地帶,其屬下性特征突出,不僅被白人剝奪了話語權,更被淹沒在黑人男性的聲音里。主人翁別格只看到了母親的醉心宗教,但并未意識到這正是白人意識形態同化的結果。別格只看到了妹妹弗拉的循規蹈矩、女友蓓西的酗酒成癮,卻不知壓抑在這表象之下、無處噴薄的女性自我意識。黑人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是整個黑人民族解放的重要前提,而黑人男性卻并未意識到這一點,反而歧視自己陣營內的女性,這一做法無疑削弱了黑人民族抗爭凝聚力。
參考文獻:
[1]董衡巽.美國文學簡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2]秦小孟.當代美國文學:概述及作品選讀(中冊)[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3]羅剛,劉象愚.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4]柏棣.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7.
[5]理查德·賴特.土生子[M].施咸榮,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6]Hurston, Zora Neale.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M].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90.
[7]段淑丹.雙重壓迫下的失聲者——從后殖民女性主義看《土生子》中的黑人女性形象[J].名作欣賞,2013(1):36-37.
[8]劉戈.被犧牲掉的黑人女性——試論理查德·賴特《土生子》中的黑人婦女形象[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1(4):88-90.
[責任編輯:姚曉黎]
Interpretation of Native Son from Perspective of Spivak’s Post Colonialism
GUAN Sha-sh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Putting Richard Wright’s novel native son in the theory of Spivak’s study, analyzing the image of black women of the novel, we can find that, under the double oppression of the White centered speaking and patriarchy ideology, black women are in the marginalized status without voice, and they become the “subordinate women” without speaking. Mrs Thomas, Flad and Bessie are regarded as the complicity of tragedy, but the essence is the family affection not to be understood and the love not be respected. All this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to listen to the female speaking and the importance for the black female self-consciously awakening.
Key words:Native Son; Spivak; subaltern; black women
收稿日期:2015-11-09
作者簡介:管莎莎(1991-),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2014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論。
文章編號:2096-1901(2016)03-0052-03
中圖分類號:I712.074
文獻標識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