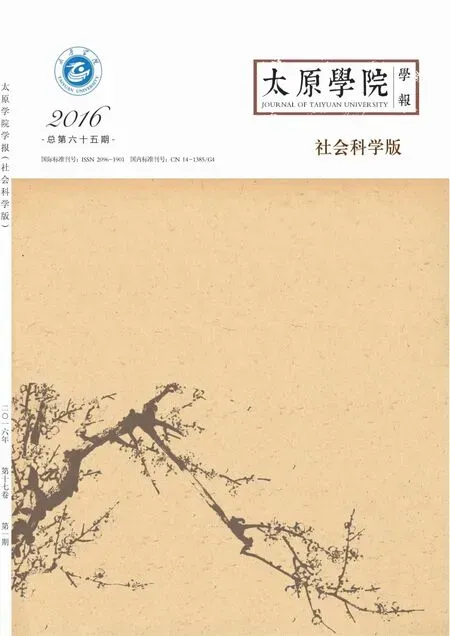黑暗中的舞蹈——論電視劇《推拿》的敘事特色
張 冉
(宿遷學院 教育系,江蘇 宿遷 223800)
?
黑暗中的舞蹈
——論電視劇《推拿》的敘事特色
張冉
(宿遷學院 教育系,江蘇 宿遷 223800)
摘要:電視劇《推拿》以盲人群體為聚焦對象,并創造性地運用舞蹈展現盲人的內心世界,是一次獨特而成功的敘事實踐。舞蹈成為整部電視劇的敘事單元之一,承擔著多重敘事功能。在情節構建方面,舞蹈推動了劇情的進展;在敘事視角方面,實現了多視角轉換;在敘事主題方面,展現了疼痛母題;在審美接受方面,統一了移情與間離的敘事效果。舞蹈通過多重敘事功能成功抽取出盲人流動、跳躍的心理變化,組成獨立、重復的段落,使電視劇以表現沙宗琪推拿中心盲人群體各異的心理見長,形成整部劇作的意境美和詩化風格。
關鍵詞:電視劇《推拿》;舞蹈;敘事特色
在電視劇創作中,《推拿》首次將鏡頭推向盲人群體,觸摸盲人日常生活與心理流動的每一個細節。該劇改編自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畢飛宇的長篇小說《推拿》,以沙宗琪推拿中心為焦點,聚焦盲人群體,延續了小說對社會的塵世關愛和文藝擔當,獲得了第十三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曾塑造了一些盲人個體形象,如,古希臘神話中的盲人預言者忒瑞西阿斯、塞繆爾·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瞎子波佐、中國上古神話中舜的父親瞽叟、史鐵生《命若琴弦》中四處流浪賣唱的盲人師徒等。但是,大規模塑造盲人群像,還原盲人原生態生活的文學作品較為少見。而在電視劇創作中,導演康洪雷稱此題材為“無人區”[1]。
那么,電視劇《推拿》如何用鏡頭觸摸黑暗世界的每一個細節呢?文學創作可以依賴文字進行大段的心理描寫和全知評價,展現盲人心中的黑暗與光明。比如畢飛宇的小說《推拿》中,為了展現后天盲人小馬的滄桑沉默,作者大段評論道:“后天的盲人沒有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在涅槃之后,他直接抵達了滄桑……小馬的沉默里有雕塑一般的肅穆。那不是本色,也不是本能,那是一種爐火純青的技能。”[2]而電視劇《推拿》鏡頭中的舞蹈取代了一部分文字的心理描寫和全知評價的功能,成為此劇突出的敘事特色。金嫣、曲芒來的愛情共舞、沙復明與張宗琪的對抗共舞、都紅的獨舞等有力推進了劇情發展、實現多視角轉換、展現疼痛母題、統一移情與間離效果,在滿足受眾的審美期待和情感預約的基礎上,引發受眾的深層思索,潛移默化地透視并轉變著這個時代的社會心理,形成整部劇作的意境美和詩化風格。
一、推動劇情進展
舞蹈貫穿整部《推拿》電視劇,仿若一顆顆閃耀的珍珠,串聯成了一條星光熠熠的珍珠項鏈。舞蹈是劇情進展的重要組成環節,具有重復性和隱喻性。依賴于反復出現的舞蹈,盲人日常生活的瑣事獲得了不同的意義。可以說,舞蹈是電視劇《推拿》的元敘事信號。“元敘事信號是對文本中各部分及潛存于其下的符碼的注解。”[3]舞蹈元敘事信號多集中在金嫣與芒來;沙復明與張宗琪;王泉與孔佳玉;王泉、沙復明與牛三勇四重人物關系的呈現中,有力推動了劇情的發展。
金嫣因曲芒來的杜鵑啼血而來,事實上他們的愛情亦如杜鵑啼血般撕心裂肺。一次又一次的共舞,由卑微到哀傷,些許欣喜之后,陷入更為卑微的泥濘,可謂“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4]。《推拿》電視劇的第十至十四集,相對集中展現了兩人舞蹈肢體上的沖突、對抗,將金嫣的艱辛愛情點點滴滴地推進、絲絲入扣地剝離。金嫣是一個愿意用一生來追逐愛情的女子,渴望追逐自己所愛而勝過被愛。她不遠千里從大連來到南京,懷著一顆謙卑的心,用無微不至的生活關懷、溫暖并感化著失戀的芒來,可等來的卻是一句“我配不上你”和一個更加謙卑的人。于是,一場舞蹈在金嫣的意識流中上演,金嫣主動伸出雙手、敞開懷抱,芒來卻躲躲閃閃,進退維艱,近在身邊,卻又若即若離,仿佛遙不可及。舞蹈的盛宴是金嫣內心痛苦與希望、愛與被愛反復斗爭的過程。最終,金嫣決定將愛繼續下去,用更加卑微的姿態迎來一顆低到塵埃中的心靈,帶來了下一段較為融洽的共舞,推動后續情節的演進。舞蹈中的金嫣著色彩艷麗的戲裝,拋出水袖,如一朵嬌羞欲放的花朵,卻舒展著一片肆意延伸的花瓣。好景不長,芒來骨子里的卑微怯懦、優柔寡斷終究還是在舊愛(鄧曉梅)歸來后全面顯露。金嫣表面故作堅強,內心卻千瘡百孔。無以言表的痛苦化為金嫣身負芒來,艱難行走的舞臺表演,預示著以后的愛情道路,將如背負千斤重擔一般,越來越艱難。舞蹈背負著兩人愛情發展變化的重荷,直觀視覺呈現著一段愛情的杜鵑啼血。
沙復明與張宗琪亦友亦敵,舞蹈不斷闡釋著兩人合作的過程即為博弈的過程。沙復明有超乎一般盲人的細膩、忍耐、堅強,又志存高遠。他不僅要開自己的推拿店,打響自己的品牌,而且日以繼日地閱讀盲文書籍。在知識的海洋中,他翩然起舞,邁著太極般的舞步,在心中勾勒著城市的面貌。而張宗琪從視覺到內心,都可以稱為是半盲,視覺上,他有一只眼睛能看見,但另一只卻沒有視力;內心中,他能夠主動關心兄弟,聆聽沙復明的情感經歷,但又精于算計,看重實利,禁不住金錢的誘惑。于是,他明知妻子韓秋霞利用推拿中心廚師職務之便克扣盲人推拿師們的伙食費,卻裝聾作啞,不聞不問,直至爆發“羊肉事件”。此時的沙復明一個人坐在公園的長椅上,黯然地在腦海中上演著黑白舞劇:張宗琪夫婦穿著奢侈昂貴的衣服,邁著怪異、夸張的舞蹈步伐。舞蹈表明沙復明開始懷疑張宗琪,并繼而引發“股票事件”。張宗琪私吞了合伙炒股贏利的兩百萬,以股市有漲有跌為由欺騙沙復明。黑白舞劇再次上演,加劇了沙復明對張宗琪的猜疑、失望,直至沙復明在博弈中勝出,終于使“沙宗琪推拿中心”變更為“沙復明推拿養生會館”。
王泉與孔佳玉相濡以沫的愛情一直被重壓在健全人過分的苛求中,終于在舞蹈里得以升華。王泉的存在對于弟弟王海而言,只是索取錢物的對象。孔佳玉的存在對于王海而言,只是索取錢物的妨礙者。王海可以直接對孔佳玉冷言冷語,根本無視哥嫂的感情。而孔佳玉的父母堅持認為盲女的丈夫必須是健全人,否則日子就只能摸著過了,這叫“摸日子”,而不叫“過日子”。為了贏得孔佳玉父母的認同,身為盲人的王泉竟然學做飯。百般努力之后,王泉主動拜訪孔佳玉的父母,可是依然沒能如愿。他一個人在車站踽踽獨行,仿若看看到整個城市的男男女女輕輕地揮著手,跳起了送別舞。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告別著一顆低落失望、手足無措的心。舞蹈宣泄了痛入心扉的悲傷,催生了滑落不止的眼淚,同時也為后面劇情的轉折蓄勢。
相比于前三組關系的現代舞蹈,王泉、沙復明與牛三勇的對抗則以古典戲曲舞蹈形式推進。中國古典戲曲通過舞蹈來展現曲折的情節和古典韻味的情境。戲曲藝術家王萍曾說:“在傳統戲曲唱、念、做、打的‘四功’中,不論哪一功都由內而外,通過形體來表現情節、表達人物思想感情的外部動作——從最簡單的比擬手勢到復雜的武打技巧,都蘊含著極豐富的舞蹈動作。”[5]王泉、沙復明、牛三勇三個人之間關系頗具戲劇性的轉變正是通過戲曲舞蹈來實現。王泉腰間綁著按摩賺來的辛苦錢,回家替弟弟王海還賭債。在回家的路上,他內心慌亂,踏著戲曲的鼓點聲,邁著慌張急促的腳步,一方面害怕弟弟受索債人的虐待,另一方面又不想視若生命的辛苦錢打水漂,可是,到了家門口,卻隔門聽見弟弟與索債人的友好閑聊。當他打開家門,腦海中呈現著一幕古典戲曲:粉白臉的牛三勇與扮小生的王海互相勾結,欺詐扮丑角的王泉。這種欺詐關系在下一段戲曲中得以扭轉。沙復明知曉了此事之后,用言語玄機和推拿治病兩重手段制服了牛三勇。于是,戲曲舞蹈上演了。沙復明扮武生,背插靠旗,手握月牙鏟與牛三勇(扮武丑,手拿雙錘)登臺打斗。幾個回合之后,牛三勇倒地,丟掉兵器,握拳臣服。兩段戲曲舞蹈實現了三人關系戲劇性的轉變,著力彰顯了劇情的進展。
二、實現多視角轉換
舞蹈不僅推動了劇情的發展,而且實現了電視劇多重視角的轉換。畢飛宇的原著《推拿》有意識地融合了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敘事視角,獨創性地使用“第二”人稱敘事。畢飛宇曾說:“這個‘第二’人稱卻不是‘第二人稱’。簡單地說,是‘第一’與‘第三’的平均值,換言之,是‘我’與‘他’的平均值。”[6]因此,一方面,盲人用自己的聽覺、觸覺去感知世界,另一方面,一個站在人文立場的評論者、觀望者始終存在,用語言直接說出盲人的尊嚴訴求。而電視劇《推拿》也追求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的自由轉換,既沒有以“零聚焦”的方式審視人物,全知全能地展示故事,也沒有鎖定“核心聚焦人物”沙復明,以沙復明的視角講述故事,而采用設置多重視角,并在此之間自由轉換的敘事策略。但是轉換的途徑變化為舞蹈,可以稱為電視劇美學上的超常規實踐。
首先,電視劇《推拿》通過舞蹈展現盲人群體特殊視角,從而完成了多重視角的設置。從整體來看,《推拿》在客觀視角中挖掘著推拿中心的盲人群體生活原生態。沙復明辛苦維持著沙宗琪推拿中心,一次又一次廢寢忘食地給客人推拿,并受到健全人吳和平的百般刁難,最終積勞成疾,因胃出血住進醫院。王泉因為天生眼盲,內心充滿著對父母的愧疚,所以年少離家便拼命地學習和賺錢,不斷給家里寄錢。孔佳玉、都紅兩個女孩從小到大都生活在父母愈加無微不至的關懷中,渴望自食其力。尤其是都紅,她執著地憑借自己的努力,學會了彈鋼琴,后來發現盲女彈鋼琴無非是健全人流淚感動的素材而已,又執著地學會了推拿,決意不虧欠任何人,不論是普通的社會健全人,還是推拿中心的同事,甚至父母。馬躍小時候因車禍而失明,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母親,由此迷戀上了孔佳玉身上的母性。客觀鏡頭對盲人的生活經歷津津樂道,勾勒出了一幅盲人群體的生活畫卷,既不矯揉造作,也不粉飾生活。從局部來看,每一個盲人都在感受著身邊的人和事,都有著各異的主觀視角。“視角”一詞偏重于“視”字,從某一角度看社會、看生活。盲人如何“視”?舞蹈中的盲人仿若獲得了更為宏大的視覺,不再停留于聽覺與觸覺兩方面。而且舞蹈展現了多位盲人各不相同的視角,將視角由“核心聚焦人物”(沙復明)擴展到“次核心聚焦人物”(王泉、金嫣、曲芒來、都紅等),達到了散點透視的效果。例如:沙復明靜坐在南京市圖書館盲人區閱讀,卻在意識流中翩翩起舞:他邁著舞步自由地游走在城市的街道上,穿行于路邊的石柱之間;在廣場的中央打著太極,胸中自有丘壑,將整個城市,乃至世界的景象盡收于眼、了然于心。這是沙復明心中的社會,是他對社會的評斷:遼遠、壯美、空間闊綽,也是他對人生的態度:積極、進取、志存高遠。同樣對待社會和人生,金嫣、曲芒來視角展現的評斷與沙復明完全不同。金嫣與曲芒來多次的共舞都圍繞著一個主題——愛情。在舞蹈中,金嫣占據主導,曲芒來的舞蹈動作卻一直畏畏縮縮,瞻前顧后。金嫣認為盲人的人生最需要的是愛情,要用一生來談一次戀愛。而曲芒來則認為盲人的人生是健全人悲憫情感的寄托物,以健全人的需求來決定存在。面對社會和人生,他選擇逃避,常常坐在推拿室的角落里,乃至躲在心靈的黑暗中。舞蹈展現了盲人各異的人生觀,各異的內心世界,使整部電視劇以展示不同的內心世界見長,繼而成功建構了本部電視劇的多重視角。
其次,舞蹈帶來了多重視角之間的自由轉換和有意識的視角越軌。第一,多重視角指在“我”“他”“她”之間自由轉換。例如,“逼債事件”,電視劇先以戲曲舞蹈從王泉的限制視角展現對弟弟的焦慮、擔憂,再轉向全知視角,牛三勇與王海正在友好閑聊,前后形成鮮明對比,接著轉向王海的限制視角,笑嘻嘻地迎上哥哥,認為弟債兄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懂哥哥賺錢的辛苦和對弟弟的擔憂。再如,金嫣在超市第一次表達感情受挫,舞蹈一直延續,場景得以順暢地從超市轉向推拿中心,也從金嫣的限制視角轉向高唯對愛情的看法,繼而轉向沙復明對愛情的期待與無奈,深情吟誦著《詩經·蒹葭》。第二,有意識的視角越軌指“讓原本不在場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理直氣壯地以目擊證人的身份去展示那種并未親眼目睹的事件,讓第一人稱的‘我’適時地搖身一變為無所不知的‘他/她’。”[7]無論在不在場,每一個人物都如在場一般,全部知曉某個場景的某段情節,并對此情境發表自己的觀點,超越了主觀視角的局限性。這是一種明顯的違規敘事,但卻使情節發展加速,意義傳達加深。例如,當沙復明與牛三勇戲曲舞蹈過招時,兩人與王泉處于不同的空間中,一方在推拿室,一方在老板辦公室。牛三勇在不知道王泉位置的情況下,直接在戲曲中告知缺席的王泉:“王泉兄弟,你弟弟那筆帳,我不管了,我肯定不管了。”這出戲僅僅存在于沙復明與牛三勇的意識流中。可是不在場的王泉卻知曉來龍去脈,跨越了戲曲和現實,傷感獨白道:“牛三勇這個事情,并沒有從我的心里頭抹掉。他是敗了,可他不是我打敗的。”三重視角的有意識越軌省略了三人之間面對面的溝通交流,簡潔有力地揭示了王泉復雜的心理,表面上如釋重負,內心里卻終有不甘。
三、展現疼痛母題
舞蹈通過融合多重視角,默默地顯露著盲人群體細膩、復雜的內心世界,共同匯聚成疼痛的母題。書寫疼痛母題是小說作者畢飛宇重要的創作特點。他曾說:“現在為止,我只寫了一個關于‘疼痛’的故事,只不過這個故事有不同的名字罷了……疼痛首先是氣質,然后才是身心。我是一個疼痛的人。”[8]在三玉系列小說中,文革遺留的日常暴力依然在左右著生活;在《哺乳期的女人》《家事》中,空村與空鎮帶來留守兒童的精神缺失;在《相愛的日子》里,一段低溫的愛情發生在陌生的城市,最后不得不輸給物質……《推拿》也是一個關于“疼痛”的故事。盲人無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人際一直處于社會的邊緣,包括文藝創作的邊緣。電視劇《推拿》經過編劇的改寫,雖然加入了不少溫情,但撲面而來的首先還是疼痛,在主旋律下,加深了電視劇的人性深度。舞蹈無疑是疼痛的聚焦點,展現出盲人的人際之痛和尊嚴之痛。
盲人與盲人之間、盲人與半盲之間、盲人與健全人之間難以突破隔閡,甚至欺騙,而這些人際之痛正是舞蹈展示的核心意蘊。金嫣與曲芒來演繹盲人與盲人之間的愛情。兩人之間隔閡重重:曲芒來的自卑、曲芒來與鄧曉梅的舊情、金嫣的強勢、鄧曉梅的重歸。金嫣的疼痛淋漓盡致地體現在兩次哭泣中的舞蹈。第一次,芒來不肯接受愛情,金嫣狂風驟雨般的舞蹈伴隨著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哭喊聲一直從舞蹈延伸到現實,戲里戲外都在嘶吼、痛哭。第二次依舊痛哭。鄧曉梅的突然歸來讓芒來再次陷入搖擺之境。如果說第一次是金嫣與鄧曉梅的舊影斗爭,那么第二次則是和真實的鄧曉梅奪夫。絕望的舞蹈、低沉的音樂與哭聲一起延續著,延長了金嫣痛苦的時長,也延長了觀眾痛苦的時長。金嫣希望通過愛情來獲得盲人存在的價值,可是這條路終究如她在劇中所說:“真像走鋼絲一樣,每一步都那么驚險。”對于盲人與半盲人之間,往往有些視力的人便獲得了明顯的優勢。張宗琪在諸多事情上欺騙沙復明,自認為瞎子什么也不知道。而沙復明得知后,在意識中上演的舞蹈可謂鮮血淋淋。舞蹈中的沙復明只能躺在推拿床上,眼睜睜地看著張宗琪與妻子韓秋霞拿著刀、叉,面目猙獰地享用著自己,滿嘴鮮血。這一場景帶有鮮明的隱喻性。半盲在無情地吞噬著盲人,活生生的吞噬。沙復明的身心疼痛移情到觀眾的身心,帶來疼痛的窒息感。對于盲人和健全人之間,一些健全人對盲人存在歧視。孔佳玉的父母明顯歧視王泉,認為盲人無法做飯、交電費、接送孩子等等。王泉只能淚眼朦朧地看著車站的送別舞。盡管他勤勤懇懇地工作,為了完成正常人能做的事情,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但依舊游走在整個社會的邊緣,被主流社會的人排斥在外。
生活在健全人為主體的社會中,盲人的尊嚴之痛無法回避。尊嚴是人對尊重的需求,是“建立在穩固堅定基礎之上的對于自我的高度評價,包括自尊以及受到他人的尊敬”[9]。對于盲人,社會民眾往往投以同情、悲憫的眼光。但是悲憫不等于尊重,帶著居高臨下的視角,創傷了盲人敏感的心靈。例如都紅,眼盲遮掩不住她的天生麗質,埋沒不了她的鋼琴天賦。但是,她的優秀卻輸給了健全人的悲憫,一次登臺演奏的巴赫鋼琴曲卻被評價為報答全社會。在健全人的眼淚中,她無法忍受悲憫,決然放棄音樂。在推拿中心,她遭遇不測,大拇指(推拿中使用最多的手指)被門夾斷,無法再做推拿。都紅躺在病床上,做了一個美麗又驚恐的夢,夢境中,陶醉地彈著鋼琴,手舞足蹈地當起了指揮,可突然發現當自己靜止不動時,音樂仍在繼續,夢境外,疼痛從手指一直蔓延到心里。舞蹈中的突轉表明都紅認識到了推拿困境與鋼琴困境的相似性,自己再次成為了別人悲憫的對象。于是,她選擇離開,踏上了重新尋找生存尊嚴之路。畢飛宇指出:“悲憫是好的,悲憫是人類最美好的感情之一,但是,這里頭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尊嚴。我們這個民族有我們的民族心態,在悲憫上,我們是博大的,在面對尊嚴的時候,我們有些薄弱。”[10]社會中泛濫的同情給盲人帶來的更多是傷害。盲人和健全人一樣是“人”,一樣有人的尊嚴。只有真正地尊重每一個盲人,乃至每一個殘疾人,盲人才能切實融入主流社會,社會民眾才能有健全的人性,社會才能實現公平正義。
誠然,電視劇《推拿》結尾一一化解了上述舞蹈展現的種種疼痛,給了觀眾一個傳統的大團圓結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說的深度。但是,電視劇作為一種大眾文化消費形式,承載著中華民族沉淀下的大眾審美心態——大團圓的審美情節。這種審美情節將事件發展的客觀理性輕易擊潰。在電視劇的發展過程中,觀眾通過演員的舞蹈感同身受,與盲人一起歷經種種疼痛。在電視劇的結尾,觀眾的疼痛感得以一一消除,重新回歸到完滿、平衡、和諧的精神狀態。可謂“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11]。
四、統一移情與間離
舞蹈讓觀眾體會到盲人身心的疼痛,這既是日常敘事移情的作用,也是間離日常敘事的效果,達到了移情和間離的對立統一。一方面,舞蹈場景使觀眾看到了盲人的意識流動。盲人的主觀視角使觀眾獲得了審美上的親切感。觀眾在第一人稱主觀視角中更容易受到劇情、人物和場景的感染,形成移情效果。觀看舞蹈之前的情節是一個情緒積壓的過程。積壓的情緒在舞蹈鏡頭中得以宣泄。以金嫣為例,觀眾隨著劇情的進展,與金嫣一起積累著焦慮、急躁、憤怒的情緒。當金嫣在舞臺上旋轉、跳躍,觀眾也直接進入人物的內心,情感也隨著主觀視角一起宣泄。在第一人稱主觀視角中,觀眾的情趣和劇中人物的情趣往復回流,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這也是評論界常說的“造夢工廠”帶來的“現實幻覺”。
另一方面,若凸現文本主體敘事意圖的話語所指、強化特定信息的話語能指,則需擴大心理距離,形成間離效果。舞蹈場景使空間突變,由生活場景突變為舞臺場景,或由彩色生活場景突變為黑白夸張的生活場景,打斷了正常的敘事流,使觀眾在情感的變化中拉開了心理距離,調動起了觀影的想象力。以王泉車站送別舞為例。在日常的生活中,車站是個迎來送往的地方,雖然人滿為患,但是再多的人也不會突然奏起音樂,跳起舞蹈。車站突然變成了舞臺,大眾突然變成了演員。此時的觀眾盡管對王泉內心的戀愛傷痛感同身受,但仍然會清醒地認識到日常生活流的突然停頓,并開始深入思考導演的創作意圖,形成中國古典繪畫中所說的“留白”效果。電視劇《推拿》中其他的舞蹈場景也是如此,切斷了日常生活和常規敘事的進展。金嫣與曲芒來的舞蹈發生地往往由超市、推拿中心的小院突轉到舞臺。沙復明與牛三勇的戲曲發生地也由推拿室突轉到舞臺。通過間離敘事,觀眾看到了電視機前的電子屏幕,仿若戲曲舞臺的“第四堵墻”,能夠以獨立而冷靜的思維進行劇作意義的再建構。
舞蹈形成的移情與間離相統一的效果帶來更積極的藝術審美。“根據心理學的優勢原則,大腦皮層中經常有一個最優勢的興奮中心,其時由于負誘導作用,周圍區域的活動都受到抑制。當人‘入戲’很深,完全感性地被劇情本身抓住時,往往無暇顧及舞臺形象的象外之旨,更難以去作理性的思考。”[12]而舞蹈帶來的心理距離,則可以一定程度地抑制感性的激動,使觀眾獲得理性思考的空間。從而,通過感性與理性的統一,被動接受與主動想象的統一,觀眾得以享有完整的電視劇審美心理過程,得以因感動而審視自己的內心,進而改變對盲人群體的態度,從悲憫或歧視到尊重。
五、結語
從上文所論述的推動劇情進展、實現多視角轉換、展現疼痛母題、統一移情與間離效果四個方面看,舞蹈已經參與了敘事,成為了獨立的敘事單元,帶來特有的敘事功能。舞蹈將盲人心理的復雜性、流動性、跳躍性抽離出來,使之具體化、形象化,使現實時空與虛擬時空分離開來,又互相映襯,產生了超越電視劇劇情本身的抒情化色彩和意境美。進而,從接受美學上來看,舞蹈使整部電視劇在滿足了親和、圓滿之美的大眾審美需求基礎上,深層蘊含著殷切的人文關懷和厚重的哲學理念。
參考文獻:
[1]于連.《推拿》改編研討會在京舉行[J].當代電視,2012(2).
[2]畢飛宇.推拿[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45-46.
[3]杰拉德·普林斯.敘事學——敘事的形式與功能[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24.
[4]宋濤.唐詩宋詞[M].沈陽:遼海出版社,2009:97.
[5]王萍.身段雜談——身段·身法·韻律[J].舞蹈,1978(5).
[6]畢飛宇.《玉米》后記[M].上海: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8:239.
[7]張育華.電視劇敘事話語[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43.
[8]吳虹飛.畢飛宇 我是一個疼痛的人[J].南方人物周刊,2009(5).
[9]馬斯洛.馬斯洛人本哲學[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8.
[10]張莉,畢飛宇.理解力比想象力更重要——對話《推拿》[J].當代作家評論,2009(2).
[11]周錫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10.
[12]孫惠柱.第四堵墻——戲劇的結構與解構[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87.
[責任編輯:王麗平]
Dancing in Darkness——On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V play “Massage”
ZHANG Ran
(Education Department, Suqian College, Suqian 223800, China)
Abstract:TV play “Massage”, taking the blind group as the focus, creatively uses dancing to show the inner world of the blind people, which is a successful narrative practice. Dancing becomes one of the narrative units of the whole TV play and bears multiple narrative functions. In plot construction, dancing puts the plot forward: in narration perspective, it has realized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in narrative theme, it shows the motif of ache: in aesthetic reception, it unifies the narrative effect of faithlessness and alienation. Dancing, by multiple narrative functions, successfully shows the fluting and leaping moral changes of the blind and forms independent or repeated paragraphs, so as to make the play show out the different inner worlds of the blind group in Sha Zongqi Massage Center and forms the artistic beauty and poeticized style of the whole play.
Key words:TV play “Massage”; dancing;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中圖分類號:J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1901(2016)01-0084-05
作者簡介:張冉(1984-),女,江蘇宿遷人,宿遷學院教育系講師,研究方向:江蘇文學的影視改編。
基金項目: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媒體空間視閾下江蘇文學的影像訴求”(15ZWC007)
收稿日期:2015-11-19